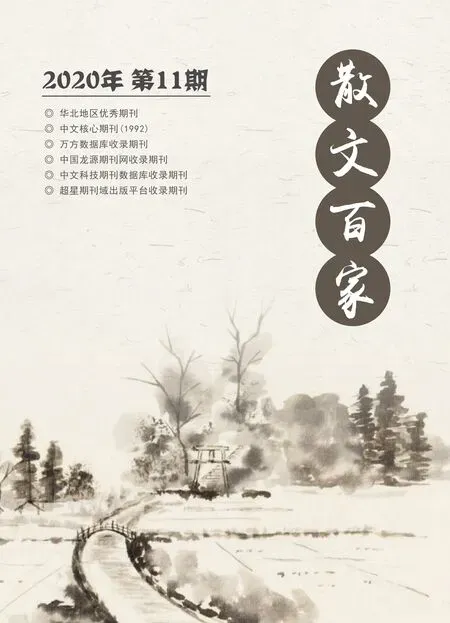关注才是最好的改变
程 艳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
那个小萝卜头,个头矮矮地,每天都是乐呵呵地,他是我们班的开心果,有他在的地方就充满了欢笑。每天中午他总是第一个吃完饭,然后忙碌地收拾那些摆放凌乱的饭盒,他一盒盒地移动着,一层层地摆放着,油渍沾满了手指手背,他头也没抬,专注地蹲在那里一层层地叠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是那么弱不禁风,每次站起身来擦擦额头的汗,咧开嘴笑了。日日如此,整整一年半,我们似乎都习惯了这个小萝卜头为大家默默地付出。已经习以为常地享受着漠视着他所做的这一切。
有好几天,他的作业没写;好多天,他上课随意说笑。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地当着他的爷爷大发脾气:“作业缺了多少次,叫他订正也没有反应,回家什么也不写,课堂上又插嘴嬉笑……”我如泼妇一样数落着这个孩子的劣根性,我面目可憎地在一位老人和孩子面前谈他的种种不是。情绪失控到全然忘记他的好,他的善良,他的真诚。尽管我知道他多么渴望得到老师的关注,我想以冷落,孤立来唤醒他顽皮的恶习,当我一直怀着救赎一个灵魂的高尚借口时,孩子转学了。他毫无征兆地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的视线,逃脱了我自认严厉而且高尚的藩篱中。我知道他的离去自然有他特殊的原因,可是他爷爷曾把我当成孩子的救命稻草,曾殷殷嘱托我,他是个特殊的孩子,需要我更多的关注。一切如烟云散去了。遗憾和自责深深地在我的心底挥之不去,也许,不是当年的年轻气盛,也许一切都会改变。
他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他如一个摄像机记录着我成长的足迹。
在时间的流里,我知道哪怕多一点点地关注,对于一个特殊家境的孩子是多么重要。工作的第5个年头,一个特殊的男生走进了我的视线:他皮肤黝黑,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很少与人搭讪,在班级里他似乎成了一个独来独往的侠客。脸上写满了本不该是这个年龄该有的沧桑和忧郁,他就像一座孤独的山。
有一次,同学都走了,班里只有他一个人。
“怎么不回家呢?”
“家里没人。”
“那你吃什么?”
“带了吃的。”
“是什么?”
他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早餐剩下的煎饼。我默然了。“老师,打架了,张仁泰打人了。”当我赶到教室时,大声责问:“怎么回事?”大家一阵沉默,班长递给我一张揉成团的纸条:仁泰是杂种。
我看到仁泰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深深地埋着头,颓废而沮丧,那一头干枯的没有修剪的杂草特别显眼。
带着种种的疑问,我决定要去家访。起初他很是吃惊,甚而惊慌,最后无奈答应。他带着我走过繁华街道,穿过栋栋高楼,来到了城中村。脏乱的小路,嘈杂的小摊,乌烟瘴气,人群喧哗。我紧跟其后,生怕迷路。我们挤出人群,穿过小巷,爬上破旧的楼层,挤进了一间小屋。我惊讶万分,那是一间多么破旧而凌乱的屋子啊!一张上下床,被子蜷缩杂乱,敞开了盖的辣椒瓶,饭粒污渍还停留在桌上,几件脏衣服散乱地扔在地上。这是深圳小学生的家吗?他尴尬地看着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安慰他。仁泰第一次抹起了眼泪,简单地叙说了自己的家境:父母离婚了,母亲嫁到东莞。父亲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朋友,以前他的日子还好,爸爸做生意,每个月有足够的钱花费。可是前不久爸爸坐牢了,什么原因他不清楚,但是父亲交给了女朋友一笔钱,要她好好照顾自己的儿子。起初这个阿姨还做饭给他吃,后来就给他钱自己去吃外卖,再后来就很少给他钱。再后来仁泰就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仁泰默默地擦拭眼泪。我听着这个好像从书上读来的故事,竟如此真切地在身旁演绎。我郑重地握着他的手说:“没饭吃,你就去老师那吃。没有什么困难抗不过去的。”
在那半年的时光里,我试图尽一切可能地去帮助他,时常邀请他来吃饭。半年里给了他姐姐般的照料,他剪掉杂草了,精神多了,憨厚的笑容,和同学们有说有笑,全然没有了苦涩,内心无比的开心。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也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是啊,也许我的能量有限,我的帮助杯水车薪,但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孤苦无依的孩子,我知道一次鼓励,一句暖言,一点善意的帮助意味着什么。
后来我收到他的短信,“老师,谢谢您,是您带给我从未有过的力量,再大的挫折我也能面对。是您让我感觉到世界上还有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您。” 初三的时候他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学校的开放日,期待之情溢于言表。我甚是惊喜,后来得知他的父亲已出狱,他的母亲也常来看他,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时光荏苒,我一直在努力弥补我曾经的遗憾。我尽其可能地成全帮助那一个个特殊的生命个体找到自我,找到自信。“你试试,再来一次。”“我相信你!”“你做得真好!”这些话是我常常说给孩子们听的。它一次次地在师生对抗中发挥着神奇的魔力,如无声的泉眼,汩汩地涌出清流,滋润万物。
一路走来,有遗憾,有波澜,有感动,丝丝缕缕缠绕心头。好在常常三省吾身:为人师可阅读乎?育人亦有长进乎?学生成长日有进步乎?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风起云涌的教育变革中我愿如一脉清泉,滋润学生,迂回婉转,因物成形,随圆亦方。
真正关注孩子,才是教育最大的幸事。
——根据课文《小萝卜头的故事》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