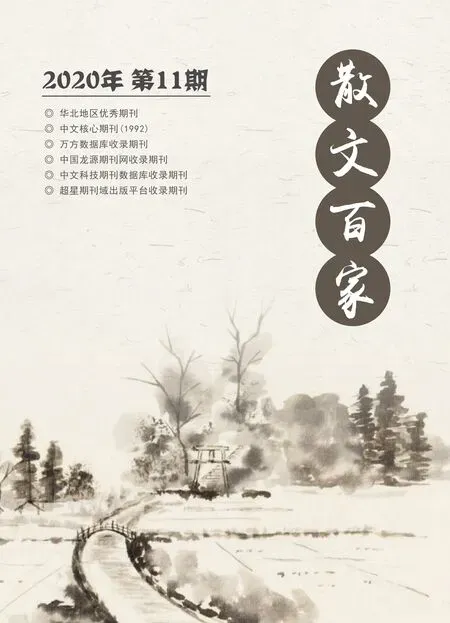这里有我一份故事
杨璐瑶
四川省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6级15班
这片土地,原本就多产故事。
潺潺的孔雀河畔,头戴毡帽的楼兰姑娘似乎在淘洗着什么。
葡萄美酒夜光杯,仙乐飘飘轻绸回,该是无数人幻想中的大唐西域。
……
几十年后,前金阿姨第一次回到这里,捡拾起昭苏草原上、回荡着儿时笑语的梦。
李玲老师看到天山流泪了,她说不知给多少学生讲起这座迷人的雪峰,而自己从未来过。
……
那,这里有我的故事吗?我是否只是一个过客?
《远方的家》里那个在雪山木屋前弹吉他的老爷爷、《冬牧场》里那只闪烁着天空之色的戒指……再到每一篇令我缱绻的文字。不,我与这里已经相识很多年了,我对她很亲近,她对我,和别人不一样。
她在以怎样的方式与我见面?
是对面那个来自石河子的男孩吗?一场穿越在平原与荒漠的火车之旅?
是偶然看向窗外、祁连山赠我的一片星海吗?
是乌鲁木齐白色的高楼身后那泠色闪耀的雪峰?还是清晨的凉风吹动着杨树叶子沙沙响?
都是,这些都是我最心满意足的见面方式。
我痴迷地望着路上穿行的陌生而美丽的面孔,他们精致的鼻梁、明亮的眼睛、特有的强烈阳光下健康的皮肤……不时走来一曳长裙的优雅女子,又一位紧身短衣的摩登女郎,她们都抹上亮丽的口红、戴着闪耀的宝石,铃铃笑语与乌黑长发间尽洋溢着一股平原女性没有的活力,就算是稳妥妥抱着小孩子、推着婴儿车的妈妈们,照样精致漂亮。人群中一位老太太很特别,她虽然背有些驼、走路需要人扶着,但依然佩着珍珠项链、戴着微光闪闪的纱巾,画了眉毛、抹着口红,是的,她依然很美。她们确是唐朝那只能歌善舞的民族的后裔。
砰地电梯门一闪,我不合时宜地闯入了一个世界。斑斓的灯光和玻璃屏风……我还来不及看,欢快的乐曲里走出一位高高的、妆容精致的维吾尔姑娘。我目不转睛地看向她,她是那么骄傲自信、魅力四射,而自己颇像一只稚气的小羊,呆呆地立在角落里,局促不安被人一览无余。
“藏族人向往天堂,维吾尔流连人间。”我很自得于自己的想法。
我总是不自主地搜寻着一切新奇的事物,她对我来说真的好像一片“异域”,彻彻底底地有着和我不一样的生活,踏在这片土地上,似乎每一次呼吸都有来自雪山的空气,每一次抬头都看见粉色的微光,每一个脚步都有踩下去的重量。
她的天黑得很早,她的阳光不温不燥,时来轻柔的风,总让我想闭上眼。
导游每次叫我“小姑娘”,我都会报以她一个微笑、一声谢谢。尽管她和大家之间有一些不愉快,但我总能原谅,并认为这是新疆人依然天真的特点。
有人说四川人叫“川耗子”,精明得很。
而新疆人不善言谈,甚至计算能力不太好,他们似乎有些木讷。
也许这片土地和内陆隔了些大山大河,他们没那么重地受到内陆习气的污染,也因为历史吧、因为祖辈们千辛万苦开创这片土地,他们愿意保留些朴实的品质。
我相信千篇一律的冷水鱼餐馆不是他们的本色,我不愿意多看一眼大巴扎里目光有些冷淡的商贩,我不能说服自己像同行的人那样接受一些失落。
因为这片土地的雪山长河、空气阳光这么纯粹。
因为我心里还珍藏着那段亲切的对话。前金阿姨和一位祖籍东北的胖叔叔,两个异乡人一个回到这里、一个安居在这里,一个回顾自己的童年、一个谈到自己曾经带过一队泸州的老兵,在乔尔玛陵园哭了。我记得那时是中午,空气很静,我们躲进凉亭里,享受着这温馨的休憩。
但当我走进路边的水果店,向卖水果的小姑娘要了一只塑料袋,我似乎一下子从幻梦坠入了现实。其实乌鲁木齐和中国的城市有什么分别呢,人们的生活都一样,柴米油盐一样、喜怒哀乐也一样。可是,正因为人们的记忆,因为有情感的人们,用文字、图像,传达出蕴涵丰富的乌鲁木齐、引人心生迷恋,我依然愿意,以文字、以图像、以音乐来记忆她。
我路过她,好像是一阵风,轻轻一瞥。
但我自信这里有我的一份故事。我怀着那么一种热烈的感情来到这里,受到她美好的迎接,我也给她留下了一些东西,比如给卖哈密瓜的维吾尔老爷爷一个微笑的回应,真诚地对街边手舞足蹈的小男孩笑了笑……
最后飞机起飞,我捧起一本写她的书来。身边一位叔叔可能往返于成都与乌鲁木齐已经很平常了,电话里他告诉对方可能几天后又会回来。而在我,这是一次郑重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