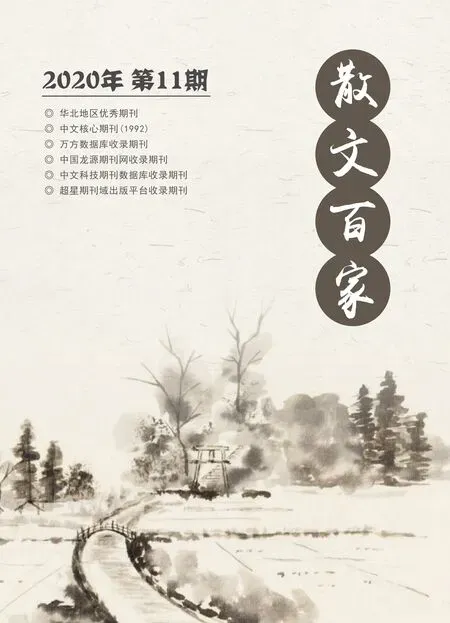《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中怡芬姑母的病态心理解析
王 琼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西西的成名作,也是其早期短篇小说之一。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在咖啡厅等待男友到男友捧着鲜花到来这段时间里的内心活动。全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整篇文章将“我”的心理独白完全展现在读者眼前,真实地描绘了80年代香港底层生活的艰辛。文章中一共出现了三类人物:第一类是“我”和怡芬姑母,特殊的职业性质使我们成为最接近死亡的人;第二类是远离死亡的人,这些人因为对死亡的原始恐惧疏远我和姑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即将接受考验的夏;第三类是已经死去的人,即我的工作对象。本文将针对第一类人物中怡芬姑母的病态心理进行解析。
一、从“我”的内心独白解析怡芬姑母的病态心理
首先说一说“我”,“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为什么她不适宜和任何人恋爱?她和夏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整个文本的语言来分析作者似乎一直在絮絮叨叨,文章表达以长段、长句为主,全文语调缓慢低沉。从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我”的职业是一名仪容化妆师,我和怡芬姑母从事的是同一种职业,是姑母把我带入这个行业的。显然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或许这种职业收入不菲,但由于其特殊的职业性质和人类的原始心理恐惧,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并不容易为普通人群所接受。但是“我”对自己的事业执着又充满傲骨,同时也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与尊重。面对自己的婚姻与恋爱“我”始终持悲观态度。
既然“我”渴望和普通人一样拥有再简单不过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不选择改行呢?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有着和其他女孩儿一样的憧憬:向往美好生活、向往爱情、向往有人呵护。怡芬姑母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才会把“我”带入这个行业?其实,怡芬姑母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继承和延续。如果把怡芬姑母看做不为世俗偏见而畏惧转身的人,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未免把姑母的形象过分拔高了。姑母也是人,是一个及其普通的人,她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向往阳光下的美好生活。爱人在知道她所从事的职业后失魂落魄的逃离了,怡芬经历了失恋的打击从此变得沉默寡言。爱人在死亡面前的胆怯表现出了普通人的庸俗与不堪,是不值得谴责的,可怡芬姑母却对此耿耿于怀。她为什么不选择改行并且还要将可以预知的痛苦带给自己唯一的亲侄女儿呢?姑母自以为勇敢、自以为执着,却固执地将自己的孤独带给他人,错误的把“我”当做母亲的再现,忽略了“我”对恐惧的感受,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心理的具体表现。怡芬姑母是可怜、可恨又可悲的。
二、从人物性格分析解析怡芬姑母的病态心理
怡芬姑母因为自身的工作性质被男友抛弃,她因此变得沉默寡言并且对身边所有的人都有了戒备心理。她从此自我封闭、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把躺在自己面前的工作对象当作朋友,当作自己的倾诉对象。试想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遭遇各种挫折,难道因为一次恋爱失败就永远不再接触异性了吗?甚至把这种拒绝由异性之间的爱延伸到朋友之间的友情,把人世间的一切美好都拒之于千里之外,这是缺乏健康人格的一种表现。
仔细分析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文章从始至终所描述的害怕接触这个“特殊职业”的人都是“我”和怡芬姑母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远离我们的也是这些亲人和朋友,就连“我”也是“被勇敢”的。怡芬姑母带我入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喜爱化妆、喜欢这个职业,更不是因为自身具有奉献精神,而是狭隘的利用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来测试朋友的真诚度和勇敢度,这种测试建立在对他人缺乏信任的基础之上。怡芬姑母把心目中的爱人和朋友置于一种理想化境界,怡芬姑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爱人和朋友,而是一种具有决绝和贞烈品质的载体,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因此在怡芬姑母性格的主要成份是沉溺与固执,表现在生活中就是一种病态行为。
三、从择业观念解析怡芬姑母的病态心理
“我”是怡芬姑母带大的,因此怡芬姑母“理所当然”地对“我”未来的命运做出了安排。关于怡芬姑母做出这种安排的出发点文中是这样叙述的:“从今以后,你将不愁衣食了”,“你不必像别的女子那般,要靠别的人来养活你了”;而“我”的想法则是:“怡芬姑母这样说,我其实是不明白她的意思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跟着她不必靠别人来养活。难道世界上就没有别的职业可以令我也不愁衣食、不靠别人来养活么”?这说明我从内心深处并不太乐意接受这个职业。但是因为我和怡芬姑母相依为命,二人的性格呈现重叠状态。我逐渐被姑母同化,具体表现就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理想化择人标准。
从以上两段独白我们不难看出,怡芬姑母的择业观美其名曰是一种进步观念——即女性能够自食其力固然是好事,但未必只能受限于这狭小的空间。即使文化程度低,也未必只能从事这一种职业,还可以有更多其他的选择。只要是靠劳动吃饭,工作是不分贵贱的。作为一个女人,最自然的想法应该是从事一些常人能够接受的职业。试想怡芬姑母和主人公若是母女关系,她还会让“我”去从事这样不被世人理解的职业吗?明知会有职业尴尬存在,明明能够预测未来命运,却偏偏还要把侄女推向这个不易被常人所接受的行列并剥夺了她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这种做法让常人难以理解。这难道不是病态心理的第三种表现吗?
四、从设置开放式结局的角度解析怡芬姑母的病态心理
中国人历来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因此无论电影、电视剧还是文学文本多数结局都是皆大欢喜。但西西的这篇作品并没有明确写出结局,而是留给读者多元化的想象空间,这说明女主人公对夏还有一丝期待,且“夏”这个名字也是有独特寓意的,他是女主人公灰色人生中一抹独特的阳光。女主人公根据怡芬姑母的爱情悲剧对自己的恋爱做出悲剧判定,但是她的内心还有另一种声音在呼唤,那就是假设了一个类似自己父母爱情故事的喜剧结局。这说明“我”并不能接受怡芬姑母强加给我的勇敢、脱俗,“我”对爱有自己的渴望、期待和表达,我”对结局的美好设想是合情合理的。
这样的结局设置允许读者作出多元化解读,从另一个侧面则影射出怡芬姑母的病态心理,她以偏概全,用自己的遭遇覆盖他人的命运。夏是“我”心目中的阳光地带,作者表达的主体倾向是期待夏能够接受“我”和“我”的职业。姑母病态心理驱使下强加给“我”的孤独无法阻挡“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文中的“我”代表的并不只是我自己,而是这个社会上所有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群体的代表;“我”的呼声是整个社会中女性弱势群体的呼声。
命运给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如果你对命运妥协,那么命运将会如死水一样平静。怡芬姑母的选择看似是在和命运抗争,但最终还是可以将其归为妥协,并且将这种妥协殃及他人。因此这是她病态心理表现的第四个层面。
五、结语
文本中的怡芬姑母是一种介质,她把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连接在一起。对过去的“我”的回忆实质描述的是现在的“我”的处境。我的本质是一个朴素、本真的女子,但是怡芬姑母试图用她的病态性格对我进行同化。过去的我是怡芬姑母的化身,择业观、性格等各方面都深受姑母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能抑制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毕竟怡芬姑母的心理是病态的。对这种病态心理的掌握,有助于读者正确把握文本的丰富性、复杂性,文本本身也因为这种“表里不一”的矛盾而显得更有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