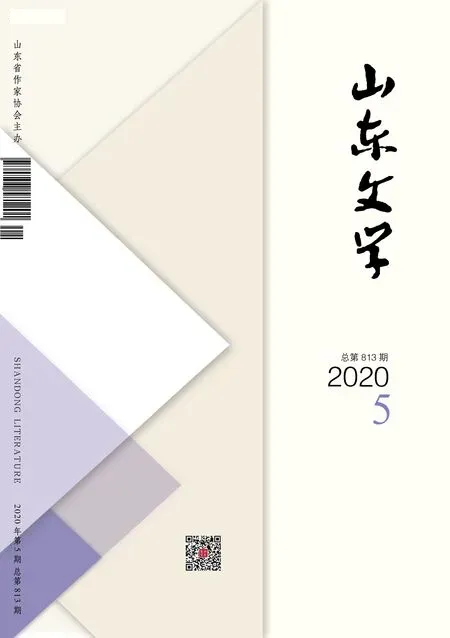大坝随感
陶 纯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鲁西北乡下艰难求学的时候,从大喇叭里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里面有两句“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我隐隐约约知道,中国的万里长江上,有个三峡,那是个很美很美的地方,宛若仙境,如果再垒上大坝,把长江截断,把水拦住,那么,将是千秋万代的功业。
我的故乡在黄河岸边,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事情,不是陶醉于黄河的美景,而是几乎每年冬天生产队都要抽调壮劳力,到黄河及其附近支流清淤,疏通河道。隔三岔五,夏天赶上大洪水,不仅壮劳力上堤巡防,连妇女都要上堤。老人们说,黄河的河床比我们村最高的房屋都要高,只要黄河开口子,就像大水灌老鼠窝一样,谁也跑不了。常常是天还未亮,睡梦中的我就听见有人在胡同里敲着破锣喊人上堤。等我睁眼醒来,正做早饭的母亲说,父亲上堤了。
长大以后才知道,自从黄河中游的三门峡修了大坝,黄河水患已经基本解除。这几十年黄河不是患水大,而是患水少,干渴的日子里,老家附近的黄河河段经常出现即将断流的情况,不由让人怀念当年过大水上河堤巡防的旧时光。
有了走南闯北的经历之后,才知道,黄河的水和长江的水,那不是一个等级概念,黄河比之长江,真是小巫见大巫。尤其是九八年的抗洪,经历过那个夏天的人,谁能忘得了?当时三峡大坝尚未修好使用,否则历史上可能也就没有九八抗洪这一说了。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有幸参加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组织的三峡笔会,那是我第一次与三峡亲密接触。我们乘船从奉节白帝城沿江而下,壮美雄阔的三峡风光让人叹为观止、目不暇接。我们从宜昌下船,参观了高高耸立的葛洲坝大坝和葛洲坝发电厂,然后又来到正在建设中的三斗坪大坝工地,记得当时正在开挖坝基,现场机声隆隆,响彻河谷,飘向天际。偌大的施工场面令人倍感振奋。我记得很清楚——讲解员一再讲到三峡大坝建成之后的种种好处,我本人还专门在未来三峡水库蓄水最高位,175米的平台上照了一张相。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三峡大坝早已经建成,巍然屹立在宽阔的江面上,成为万里长江最大最坚固的一道屏障。二十年里,我没再有机会亲近三峡。然而,三峡工程偶尔出现在我的视野,却很少听到赞美声,更多的是非议。比如说,当初为了筹钱建三峡工程,国家把每度电费抬高了一点钱,三峡投资两千个亿,说是建好之后,电费会大大降低,可是早就建好了,为什么电费迟迟没降下来?全国人民跟着买单二十多年,上头说话不算数嘛。比如说,大坝建好后,长江航运大受影响,通行能力大大下降,过船闸要排半天的队。比如说,三峡水位抬高一百多米,三峡自然风光改变了,不那么壮美了。比如说,库区淤积得很厉害,不出多少年,就得炸掉大坝,恢复长江河道原有的风貌。比如说,为了建三峡工程,毁掉了多少多少文物。比如说,三峡大坝永远是一个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爆发战争,大坝会成为首要攻击目标,那么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国土就会沦为泽国,损失难以估量。更有甚者,竟然把汶川地震也算到它头上,说是它改变地质结构从而引发的地震。不久前,网络上又有传言,说是三峡大坝裂缝了,十分危险。总而言之,说来说去,建三峡工程弊大于利。
我仔细想了想,二十年来,不知为什么,似乎很少听到有关三峡工程的好话。坏话听多了,连我这个自认为头脑还算清醒的人,也开始似信非信,人云亦云。坦白地讲,我也跟着说过一些三峡的坏话。个人吐槽最多的,不是引发地震、大坝裂缝之类的胡说八道,因为这个不值一驳。
我似信非信、半信半疑的,是另外的那几个说法,或者说传言。社会上、网络上争议比较大的,也不外乎这几点。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不是有一个机会帮我擦亮眼,我恐怕还会继续说人家三峡的坏话。
初冬时节,我跟随一个作家代表团走进三峡集团。我是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参加这个活动的。在北京玉渊潭公园附近的三峡集团总部先搞了个见面会,然后全体人员乘大巴去首都机场。去机场的路上,比较拥堵,陪同我们的集团副总经济师杨骏先生驾轻就熟地给我们介绍情况,他只讲了半个小时,便把我所有的疑惑都给解释清楚了。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曾经的浅薄,网上的传言,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呢?
四天的活动:在宜昌看三峡大坝、船闸、发电厂;考察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心;参观移民安置示范村许家冲、秭归新城、屈原祠;到兴发集团附近的江岸考察长江生态修复工程情况,等等;然后转至岳阳,调研三峡集团投资建设的城区雨污分流工程等多个长江生态环保项目,等等。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三峡工程的认识。
现在我可以回答身边人的疑问了:你说三峡工程建成后电费没降,这不能怪人家三峡集团,三峡水电的成本只有两毛多钱,现在每度电费五毛多,是国家统筹的结果。三峡集团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大坝建成十多年来,集团给国家上缴的利税,已不止国家当初投进去的两千个亿(这笔钱还包括百万大移民的花费,以及输变电工程的投资),也就是说,这项投资早就收回了。你说长江航运受到很大影响,事实上航运能力大大提高,过去川江无夜航,因为浅滩有危险,现在水位提升,大吨位的船可以全天候通行。过船闸排队时间较长,那是因为现在的运力增加了数倍,船多了,自然会慢下来。你说三峡自然风光受影响,那是想当然的结果,库区水位抬高,不会改变三峡的自然风光,水面宽阔了,或许它更显得旖旎多姿。你说库区淤积得很厉害,将来得炸掉大坝,那更是一派胡言,唯恐天下不乱,可能是从三门峡那儿得到的启示吧?因为缺乏经验,当年三门峡筑大坝后确实出现泥沙不断淤积,下游河床日益抬高的大问题,后续工程改造颇费力气,争议不断。但是三峡不是三门峡,长江不是黄河,长江上游由于生态环境相对好,加之近年来保护得力,泥沙顺江而下的情况并不严重,三峡库区的泥沙淤积比当初设想的还要乐观,因此全国人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说毁掉了多少文物,事实上因为三峡工程,库区两岸的文物保护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国家投资很大,江岸各种历史文化景观不论是迁移重建的也好,还是原地保护的也好,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可以说,没有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肯定没有现在好。上一次来三峡,我参观过未迁移之前的旧屈原祠,这一次又走进迁移重建的新屈原祠,感觉到新的比旧的,规模变大了,敞亮气派多了,旧的太憋屈了。假设屈原在天有知,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的。如果你非要说文物旧的比新的好,那么过多少年之后,新的也会变成旧的,只要保护得好,建设得当,人民心中有先贤,把先贤的精神薪火相传下去,当代人就算上对得起祖宗先人,下对得起子孙后代。
顺便说一句,三峡移民们为国家工程做出了重大奉献。好在很多人也因之过上了远超以前的好日子,比如整体搬迁的屈原故里:秭归新城,如果不建大坝,就不会有现在的它。参观期间,我问过三个当地人,是新城好,还是旧城好?他们无一例外地说,当然是新城好,至少先进了十年。
当然,建三峡也不是没有代价,主要是生态上的,比如有一种鱼,是长江中最大的鱼类,有长江鱼王之称,它还有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好名字:中华鲟。每当夏秋两季,生活在长江口外浅海域的中华鲟,要回游到长江,历经三千多公里的溯流搏击,来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待幼鱼长大一点,又携带它们游向大海。由于更早的葛洲坝的阻隔,中华鲟已不能到达金沙江繁衍。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你想,那么大的工程,总要有一点代价,不可能事事如愿。好在国家有关部门从一开始就注重对中华鲟的研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成立了中华鲟研究所,人工繁衍中华鲟已是家常便饭。
在宜昌期间,有一天在电梯里,我遇到一位来此参加水电会议的领导干部模样的人,他对跟随他的两位部下说,当初国家缺电,才决定搞三峡工程,如果搁到现在,可能就不会批准这个项目了,现在风电核电用不完。我忍不住马上纠正道,三峡工程的第一大任务是防洪,然后才是发电,九八抗洪都知道吧?二十年过去,为什么长江荆江河段没再出现大险情?如果不是有大坝,中国人也许会多次经历那样的场面。那位领导同志愣了愣,他立即接受了我的观点,冲我点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
小时候故乡人在黄河岸边的忧患历历在目,九八抗洪更是全国人民难忘的悲壮记忆。黄河、长江这两条母亲河哺育了中华民族,但也给中华民族留下数不尽的历史创痛。治水如治国,大江何日安然?关于黄河,毛泽东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三门峡大坝建成,黄河水患成为过去。三峡是一个梦,关于长江,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兴建三峡工程,但那个时代根本办不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心中构架了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葛洲坝工程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但是远远不够,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高,为三峡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这个梦终于得以实现。对于这么一个伟大的成就,有大量的非议和贬损,始作蛹者要么是别有用心之人,要么是一些无知的人。当然,在坚固的大坝面前,一点流言不过是几朵浑浊的浪花,丝毫不能撼动什么。
如今,三峡集团已投巨资在沿江几个城市搞污水管网改造试点,新建改建大型污水处理厂,很快即可见效。但愿不远的将来,沿江各城市不再或者少往江中排污,那时的长江才是最美的长江。
——三峡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