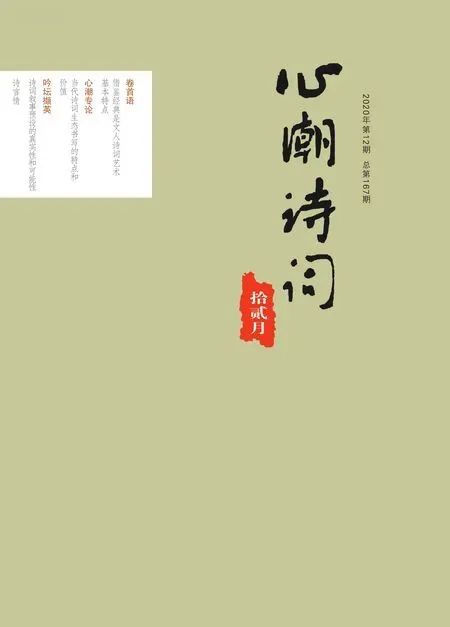诗词的现代性
(按姓名音序排列)
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教授委员会主席):“现代性”是一个西方舶来品。“现代”(modern)一词发端于欧洲中世纪开始之时,当时人们进入基督教时期,用以区分异教与罗马的过去,现在,我们常常用以区别由旧到新的时代转变。现代性是反对传统的,意味着告别那些历经年岁的经典,转而依靠某种唯独适用于当下的本真性。关于“现代性”的大讨论与艺术实践在西方世界从未停止,仿佛只要活在当代,就必须被纳入讨论范围;亦好像如果不符合“现代性”,就成了当代圆桌上的不合时宜之物,就应当被时代的浪潮踢除出去。
然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亦被纳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整体进程之内,包括诗词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学也遭遇了现代性这把尺规的考量。在五四“爱国、进步、民主、自由”轰轰烈烈的思潮下,现代性在中国各行各业各个学科展开,自此以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受到西方科学化、系统化影响,成了专业学科,至今历经多次重新书写。然而在今天,诗词却又处于一个被当代文学、文学史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当我们带着是否具有“现代性”这一问题考量现当代古体诗词时,如果以西方现代性概念直接套用中国诗词的现状,其实就会陷入某种以西释中的中国文论的失语状态。故讨论诗词的现代性时,我更倾向于从诗词是否还适应现当代中国文化环境的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诗词作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新诗共同丰富着文学的内涵。古体诗词与白话新诗双峰并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现代性是去中心化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行为去选取创作与阐释的对象。
第二,当代诗词以古体写今事,在新与旧的碰撞下别出心裁,亦可用于表现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颖的时间意识。中国古代的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的时间观念被打破,当代诗词就是在这种全新的语境下进行书写。
第三,诗词对于当代古代文论的创新与话语重建之意义。诗词的当代写作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蓬勃发展的典型范例,在这些诗词作品中,中西文论得以共同阐释、对话与共生。
李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现代,顾名思义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现代性,从字面上来说是“在当前时代存在的东西”所具有的“属性”。我们要认真地思考“存在于现代”这个概念,这里面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现代“产生”的事物,这属于“新瓶装新酒”;一个是现代继承下来的,仍然有生命力并不断创新发展的事物,虽是“旧瓶”但装的也是“新酒”。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定义“现代性”是能够反映时代特征、富含时代信息的客观属性。
在现代背景下产生的诗词是否具有现代性,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诗词是不是蕴含有对当前社会各种现象的描写、思考与探索。例如,“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是汉代时的爱情宣言;“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是20世纪70年代的爱情宣言。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所以现代性,取决于诗歌的主题,所反映的精神是否具有时代性,不在于写作形式。我们今年抗疫时就有诗家写出“妙手斩魔颜不改,仁心医病爱无声”的佳句,与新体诗“你们刚毅的脸上,被严捂的口罩,勒出一道道沟痕,横的、竖的深深嵌入你的容颜”相比,对英雄的赞扬、对时代的讴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产生于这个时代的,无论是新体诗还是旧体诗,只要踩上这个时代的节拍,就具有现代性。
对诗词的现代性,目前的争论还主要是在表现形式上,是源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束缚,将批判精神用到极端化,完全与旧世界割裂。但实际上,只要这份文化存在,就不可能将传统全部格式化,用一个全新的系统来取代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文化模式。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实现百花齐放。
对于诗词来说,新体诗不要将旧体诗边缘化,旧体诗也不要排斥新体诗。旧体诗有一种倾向,固执于旧时的格律,还有在用词用字上只求“古意”,在题材上不愿意拓展,这一类诗的时代性就较差。生于斯世,就要爱这个时代,用手里的笔反映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的主题歌谱写乐章。
李仲凡(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事实上,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它关系着现当代旧体诗词的价值评估,能否入史,甚至旧体诗词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未来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前些年陈友康、王泽龙等学者对现当代旧体诗词“现代性”的发掘与讨论,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起源和界定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到卡林内斯库,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阐释过他们的理解。但是无论怎样讲,“现代性”的所指还是有一些公认的内涵与边界的,比如以“理性”“自由”为其核心的价值理念等。法国诗人和批评家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①[美]马泰·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如果我们从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出发,就会发现,现当代旧体诗词虽然披着古典的外衣,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在鲁迅、郁达夫、田汉、聂绀弩等现代旧体诗人的作品里,有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精妙刻画。在这方面,现代旧体诗词的价值和其他新文学样式一样,并无高下之分。另外,现代人旧体诗词中的新词、新律、新格调等古典诗词中不具备的新元素的出现,代表了传统诗词文体最新的审美倾向,这一点也和现代性概念的早期内涵是相通的。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能够具有现代性,根源有二:一是新文学占主导的大环境的影响,二是现代“人”的观念在现当代旧体诗词中的渗透。
我们在借用现代性视角审视现当代旧体诗词时,最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因为其在诸多方面和古典诗歌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古典性或非现代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对于现当代旧体诗词来说,这二者经常夹缠扭结在一起,无法截然分开。在现当代旧体诗词现代性的问题上,学术界需要有更审慎全面的视角。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确有许多现代性的成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当代旧体诗词也表现出了诸多无法被归结为现代性的特征。
马大勇(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现代性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哲学社会学概念,每个人对它的理解似乎都只能盲人摸象,取其一端。如王巨川所云:“对于现代旧体诗词是否具有现代性问题的分歧……是因其个人(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不同,故而影响到研究者对文学本体的认知及其历史演变的误读。”故而,“现代性”争论中往往出现“鸡同鸭讲”、郢书燕说的情况。简而言之,我以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有人要求“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精神特征的现代性,而且是包括了文学语言、文体样式、文学思维等文学本体形式的现代性特征的”,这种面面俱到的概括当然没有问题,但我很怕一旦分析到具体作品的时候,便会有力不从心的情况出现。我的意思是,当一篇文学作品不能全面具备以上质素的时候,其中哪些因素更重要,决定了它更贴近现代性呢?我个人绝对倾向于“思想内容”与“精神特征”这些内在的基核,而不是文学语言、文体样式这些外在的元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现代性与古典语言、古典文体形式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不应以排斥这些因素为前提才能得以确立。
第二,李仲凡《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一文最为通达平允,似可作为这一公案的“总结陈词”:“在谈论现代旧体诗词时,其现代性不应该被忽视或否定,同时,它的非现代性也应被注意到……承认现代旧体诗词传统或非现代的一面,并不会降低对现代旧体诗词价值的认定。我们也不应因为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而否认它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应当看到,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本身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既是现代旧体诗词与其他新文学体裁相比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也恰恰是它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之所在,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跳出‘现代性’的框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旧体诗词更为丰富的一面,而不再仅仅为它的现代性做意气之争。我们不能为了争取现代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而把它的所有方面都说成现代性的……现代旧体诗词应否或能否入史取决于它自身的艺术价值。现代性问题不应该成为它是否入史的主要评判依据。”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旧体诗词因其精巧的形式,千百年来备受文人墨客和文学爱好者的喜爱。晚清以降,中国文学开始自身的现代转型,其中以前备受歧视的小说从边缘到中心,而之前身居文学殿堂高位的诗词却遭遇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语言的变化。
旧体诗词的语言结构基本以单音节和双音节为主,单音节占的比重很大。像日、月、星、辰、风、霜、雷、电、梅、菊、兰、竹等表示自然景物或现象的单音节名词往往穿梭于旧体诗词的字里行间;像表示人类情绪的喜、怒、哀、乐、愁等单音节名词紧跟其后;甚至于像表示抽象观念的道、仁、礼、德、忠、孝、节、义等单音节词也可以自由出没。因此,旧体诗词在传统语境中,描绘自然、表达情绪和深化思想,在用词上不存在任何障碍。而晚清以来随着翻译的兴起,新名词带着现代性的内涵进入汉语语境,丰富汉语表达的同时也挑战汉语表达,尤其是严重挑战着中国旧体诗词的语言结构。新名词以双音节居多,三音节和四音节也不少,还有一些是五音节及以上的。晚清的中国人用旧体诗词去表达新事物、新名词时,往往要借助旧体诗词加上注释的方式才能比较完整,何如璋的《使东杂咏》、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就有充分表现。而当新名词进入汉语后再要进入旧体诗词语句中时,就构成了对旧体诗词的挑战。蒋观云的《卢骚》一诗被认为是在运用新名词上非常成功的例子,全诗如下:“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昌新义,君威扫毒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卢骚”“法国”“民约”“平等”“自由”“革命”等双音节词很自然地嵌入其中。谭嗣同的诗句“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令盛于巴力门”中运用“喀私德”“巴力门”两个译名就有点勉强。梁启超的“变名怜玛志,亡邸想藤寅”“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中的新名词就被“削”得不成样子。“玛志”即“玛志尼”,“藤寅”即“吉田松阴”,“华拿”中的“华”即“华盛顿”,“拿”即“拿破仑”,“卢孟”中的“卢”即“卢梭”,“孟”即“孟德斯鸠”。旧体诗词中也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之句,“李杜”也是姓氏的合并。不同的是,“李杜”是两个完整的姓氏的合并,而“华拿”“卢孟”都不是。因此,新名词的涌入,对旧体诗词的挑战在于:一方面,新名词如果要进入旧体诗词,往往面临被“削”的命运,旧体诗词的语句必须得自带注释,才能将现代性内涵表达完整;另一方面,新名词如果直接进入旧体诗词的语句,就会顶破旧体诗词的语言结构,从而拆散旧体诗词的整个形式。这就是旧体诗词的现代性困境。
毋庸否认,中国的旧体诗词仍拥有许多“粉丝”,在表现一时一地的个人情绪方面仍有其优势和生命力。新文学作家如郁达夫、郭沫若、胡风、聂绀弩,还有学者如马一浮、陈寅恪等人,都创作了较为丰富的旧体诗。但是也要看到,旧体诗词在表现现代人生活的广度、深度以及复杂性方面,显然不如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