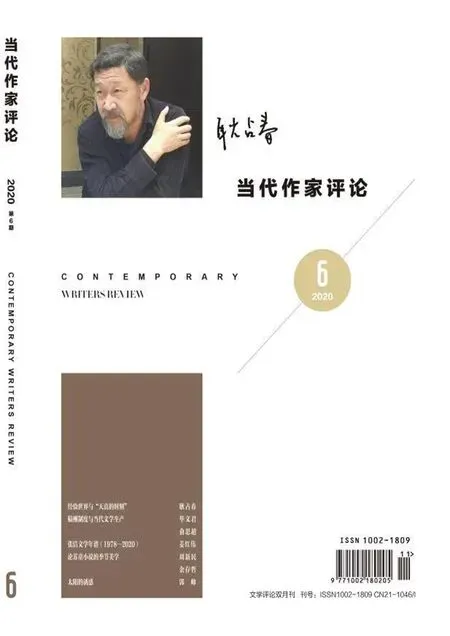太阳的诱惑
——理解顾城的精神世界
郭 帅
一、隐藏“太阳”的朦胧诗人
1981年,顾城写下了著名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诗中,“我”幻想自己领到一支神奇蜡笔,可以任性地涂抹:天空、淡绿的苹果、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地平线、没有见过阴云的爱人、玻璃糖纸、北方童话的插图、东方民族的愿望、满是窗子的大地……。诗歌中拥挤着几十种顾城所渴望图画的意象。然而,如果我们真的用画纸将顾城的“风景”呈现出来,将会感到画面十分阴郁,因为它缺少一个意象——太阳。
这可能是解读《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的密匙,所谓“任性”,应该就是不画太阳。(1)顾城会作画,在他的所有画作中,几乎找不到太阳的形象。此一时期(朦胧诗潮初期),在顾城的其他诗歌中,我们也很难直接找到太阳的踪影:天空常是空空荡荡,只有月亮、星群和乌云、鸽子,黎明的地平线上也总是干干净净。
当我们把顾城放置于朦胧诗潮流中,可以发现,顾城是有意将“太阳”意象隐藏了起来。在乍暖还寒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朦胧诗人尤其是《今天》群体激烈地出场,以象征主义手法恢复诗歌的隐喻功能,“太阳”成为最理想不过的对象。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朦胧诗也的确经由对这类宏大意象的解构成功地形成了“仪式的抵抗”。可以这样说,除了顾城,几乎所有朦胧诗人都曾对“太阳”意象宣泄过愤怒,这些诗句也由于强烈的对抗性而脍炙人口。(2)“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北岛《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它(向日葵)把头转了过去/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这高高抖瑟的风筝/它的细长的系绳/是不是仍然拴在/太阳铁青的手脖子上?”(根子《白洋淀》);“不错,我们是混账的儿女/面对着没有太阳升起的东方/我们做起了早操”(多多《蜜周》);“太阳从那里沉落/留下重重黑暗/当它再度升起/却没有带来新的一天”(田晓青《虚构》);“我的女儿就要被处决/枪口向我走来,一只黑色的太阳”(江河《没有写完的诗》);“啊!在那地黄天也黄的日子里/我曾想:有一个/奇异的绿色的太阳”(梅绍静《绿》)。以上节选自洪子诚、程光炜主编:《朦胧诗新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同被认作朦胧诗人的顾城,却将“太阳”隐藏起来。更为吊诡的是,顾城在此阶段之前,一直在使用“太阳”意象。也就是说,顾城并非天然地隐藏“太阳”,恰恰是在其他朦胧诗人大量使用“太阳”意象的同时,他却戛然停止了对“太阳”意象的使用。
顾城对“太阳”意象的理解,起源于一次美学训练。最早出现在顾城诗歌中的“太阳”,与政治无关,显得是那样地清新自然,如“穿过长满冰霜的玻璃/晨光已铺满大地/万盏灯火结束了工作/明亮的太阳正在升起”(1967);(3)顾城:《早晨》,《顾城诗全集》(上),第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太阳落山了/世界像是一幅巨大的剪影”(1969);(4)顾城:《黄昏》,《顾城诗全集》(上),第1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艳红的太阳/用晨雾的手帕/擦去满脸的水滴”(1970);(5)顾城:《海湾》,《顾城诗全集》(上),第50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你金色的眼睛/看着太阳/太阳走远了/红衣服忘在草滩上”(1970)。(6)顾城:《割草归来》,《顾城诗全集》(上),第5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这时的“太阳”,在顾城眼中并不宏大,也许,十几岁的顾城还无法领悟“太阳”的奥义。
但是,关于“太阳”的一切,父亲顾工很快就对顾城进行了深刻的启蒙。1970年开始,诗人顾工带着顾城下放到山东半岛潍河流域的火道村。顾城最早的一批诗歌精品就诞生在此时此地,包括屡屡被人提及的少年成名作《生命幻想曲》(1971)。多年之后,顾工仍记得顾城写作此诗时的情景:“我和十四岁的顾城在河滩上晒着黝黑的肢体。他用手指在砂砾中写了一首歪歪扭扭的《生命幻想曲》。”(7)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诗刊》1980年第10期。这首即兴创作的诗中,顾城将自己幻化为一艘帆船,表达了航行世界的宏愿,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几句:
太阳是我的纤夫,
它拉着我,
用强光的绳索,
一步步,
走完十二小时的路途。
我被风推着,
向东向西,
太阳消失在暮色里。(8)顾城:《生命幻想曲》,《顾城诗全集》(上),第67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稍一体味,我们便能感受到很强的画面感。父亲顾工感到“多么好,我真惊奇他那细小、柔弱的手指怎会画出这样宏丽、壮美的句子”。然而,父亲同时也在诗句中感到了巨大的危险,“我赶快帮助顾城用沙子把诗句掩埋起来”。(9)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诗刊》1980年第10期。
父亲不仅掩埋了这些美丽而又危险的诗句,还以共产主义诗人的自觉,规训顾城关于诗歌的秘密,尤其是某些意象的使用规则。在此之后,顾工更有机会带着顾城前往一些革命圣地,“让他多知道些革命、征战、老一辈走过的艰辛的路、滴血滴泪的脚印”,“让他心灵中永远充满瀑布般的阳光”。(10)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诗刊》1980年第10期。
父亲的启蒙和修正是成功的。当父亲将这种“强大的能量”展示给14岁的顾城时,顾城明显地感到了“革命”的“最美好的那一刻”。宏大情感开始进驻顾城的诗:“巨石在嶙峋的岩坡上翻滚/在撞击中抛出无数裂片/有一天这裂片把我刺痛/告诉我怎样写斗争的诗篇”(1972)。(11)顾城:《巨石》,《顾城诗全集》(上),第9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在火道村,顾城开始学习做一名劳动者,种田、喂鸡、养猪、木工……沉浸于对极致纯粹的无产者生活方式的寻求中,他说自己“甚至是一个共产主义者”。(12)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从这个阶段开始,我们在顾城的诗歌中再也找不到那一轮清新自然的“太阳”,再也见不到可以随意拟人化的“太阳”,即使出现,也有着清晰而又安全的所指,显然,那是父辈的“太阳”。1973年,顾城用一首小诗《醒》表达了他的这种省悟:“太阳烤热了血/我像又有了生命/我又有了视觉和听力/一片大自然的幻影幻声。”(13)顾城:《醒》,《顾城诗全集》(上),第10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是的,在父亲的指引下,顾城的血被“太阳”烤热了,在政治和人生的意义上获得了某种新生,他从此也获得另一种观照世界的视角。彼时代特有的抒情方式也找到了顾城。从这一年开始,顾城写作了大量“工农兵诗歌”,并接受古典诗歌、民歌和毛泽东诗词的影响,写作了大量的旧体诗和童谣。在1971—1979年间,顾城所写作的旧体诗、战歌、童谣的数量比白话诗多,在这个领域,顾城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仅仅描写被“太阳”烤热了血的诗篇就有很多。(14)如《白云梦(其四)》中“沙岸高奏凯旋曲,热血扬波荡乾坤”(1972),《双赠·自赠》中“满怀革命志,一腔战斗情。扬笔书时代,我为人类生!”(1974),《火炬,燃烧的旗》中“我们感到了父辈的体温/心中奔涌着血的潮汐”(1974),以上均见顾城:《顾城诗全集》(上),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上涌动着一股质疑革命领袖的暗潮,此时顾城写作了《历史小议》:“沧桑亿万载,功罪与谁评。黄河出清海,红楼没绿林。人民架长车,斗争驱巨轮。天地自翻覆,不待蓬雀鸣。”(15)顾城:《历史小议》,《顾城诗全集》(上),第201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这首诗化用了毛泽东《念奴娇·昆仑》一诗的“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表露出顾城宏大的历史意识,和维护“太阳”光辉的决心。
若读一读1971—1979年顾城的所有创作,我们可能会预测少年顾城最终将成长为他父亲那样的忠诚的革命诗人。1979年,《一代人》发表于《诗刊》,“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16)顾城:《一代人》,《顾城诗全集》(上),第283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这首短短的小诗被视为朦胧诗的代表作。然而,最先为这首诗叫好的,是一批反对朦胧诗的革命老诗人:方冰认为这首诗是“不朦胧的好诗”,“含意蕴藉而深沉”;(17)方冰:《我对于“朦胧诗”的看法》,《光明日报》1981年1月28日。周良沛赞赏《一代人》是历史给新诗的“使命”;(18)周良沛:《说“朦胧”》,《文艺报》1981年第2期。艾青也对“一代人”表示了充分理解。(19)艾青:《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与此对照的是,当时为朦胧诗辩护者,几乎无人举《一代人》作为例子。因为此时的新老诗人和批评家都知道,“光明”意味着什么。
在“太阳”和“光明”这类意象面前,朦胧诗人和老一辈诗人形成了思想和艺术上的断裂性认识:“终于,我们站起来对艾青说:你们的太阳已经过去,我们的太阳正在升起!”(20)黄翔:《致中国诗坛泰斗——艾青》,李建立编:《朦胧诗研究资料》,第82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一代人》是顾城对“太阳”的一次捍卫,也是最后一次捍卫,在《一代人》发表前后,顾城已在朦胧诗潮流中,悄然将“太阳”隐藏了起来。
二、怀念“太阳”
父辈的启蒙或许只是一个引子,顾城更多的是出于自律而对“太阳”生成了强烈认同。马悦然认为,顾城的诗“根于‘文化大革命’”,“那种荒凉,那种寂寞和那种诱惑,都是同时的”。(21)⑩ 顾城:《顾城哲思录》,第222、193、11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是的,顾城的诗歌常常带着“那种荒凉、那种寂寞和那种诱惑”,这也是革命年代颁发给顾城的礼物。与北岛等人不同,顾城对“文革”没有恶感,反而喜欢革命年代的漫长和安全,喜欢跟随父亲在下放的北方农村体验自然和简单,喜欢北京古城的慢节奏和历史感。最关键的是,顾城从内心深处认同并欣赏革命领袖所独具的魅力,在形而上的意义层面,他认同着革命领袖。(22)到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到了国外,即使某些海外媒体有所“诱导”,顾城依然没有发表过关于革命领袖的任何“黑话”。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知:
首先,顾城欣赏并怀念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顾城有他自己的艺术哲学,迷信精神的强力。他认为诗歌的核心在于表达“精神的自然”,“精神一旦到来要做什么事,人力就不是那么可以左右的了,尤其是在精神强大的时候。强大的精神是可以从个人范围漫溢出来,而到达另一个人的;我们说的艺术打动人,就是这样的现象”。⑩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顾城毫不避讳地表达着他对领袖的欣赏:“我为什么愿意讲毛泽东呢?不是因为他做了领袖惊天动地,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偌大的国家,而是因为他具有的特殊性情,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原质。毛泽东晚年的意识不仅超越了人的生存法则,而且超越了人的精神法则,在于现实极其危险和可怕的同时,作为他个人又是非常纯粹的。”在其他朦胧诗人乃至于其他当代作家那里,我们很少能见到对晚年毛泽东有这种评价。相对于北岛等人,顾城不是在现实的层面而是在一个纯粹精神的层面去认识和肯定晚年毛泽东。毛泽东的去世,顾城当时未置一词。我相信,顾城是出于不可描述的内在纠结难以名状。很多年后,当他终于可以消化这种痛苦时,他说:“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即失去了那样一个强力精神,包括不在乎死的信心和精神,又失去了本来的宁静。”(23)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88、189、191、191、226、19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在革命年代,顾城被笼罩在革命领袖的精神强力之下,他感到的是宁静。从领袖那里,他也认同了“不在乎生死”的精神强力。在顾城的青少年时期,这种认同非常关键,它直接参与了顾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建构。顾城沉浸于无比强大的精神强力所制造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并非犬儒主义的忍从,而是可以超越生死的主体力量。在某种意义上,顾城分享了这种精神强力。
其次,从文化观来看,顾城认为革命领袖是当代“道家”哲学的体现。顾城迷恋自然,“自然”就是他的哲学观。他认为中国文化分为显性/隐性两面,“隐性的一面在自然中间,它不断给显性文化提供着营养,提供着一种安宁的哲学观照,使人能够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而从容不迫”。(24)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88、189、191、191、226、19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关于“自然”,顾城推崇庄子的《齐物论》和《逍遥游》。“齐物”和“逍遥”与顾城以“自然”为诗的追求相契合,单在艺术逻辑方面,可以说顾城就是一个道家。然而,在“无为无不为”的辩证法中,顾城又喜欢“无不为”。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极致的自由。所以,顾城也很喜欢孙悟空这类人物,“他是一切秩序的破坏者,也是生命意志的实现者。他作恶也行善、杀人也救人,不是因为道德——他不属人世,而纯粹由于兴趣使然。孙悟空这个象征是中国哲学无不为意识的体现”。(25)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88、189、191、191、226、19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正是在“无为无不为”的道家人物序列中,顾城极大地肯定了毛泽东,“如果说孙悟空是个精灵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精灵附体的人。他喜爱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喜爱孙悟空的大闹天宫,‘金猴奋起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顾城由此这样评价自己所经历的“革命年代”:“他制造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就是庄子反文化意识的现实体现,恰如人世间的大闹天宫。”(26)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88、189、191、191、226、19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顾城从他所沉迷的道家精神说开去,在哲学层面定义了革命领袖及其革命:“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线索,就是从庄子的齐物,到孙悟空的‘齐天大圣’,再到毛泽东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文化大革命’。”庄子—孙悟空—毛泽东,形成了顾城意识中的道家人物序列。并且,顾城称这个序列是“无为无不为思想入侵中国文化而至入侵中国现实的大过程”。(27)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88、189、191、191、226、19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顾城当然也认为他自己也属于这个道家人物序列,在“齐物论”哲学层面,他与庄子、孙悟空、革命领袖是同一种精神存在。
再次,顾城将革命领袖视为一个极致的虚无主义者。在顾城看来,世界本是清净无为的所在,万物相通一理,齐生齐死。“没有目的是寂静的,是超乎个性的;但没有目的的‘我’则是自由的,有着可能难以想象的鲜明个性。”顾城本人以及他的诗歌,不重视对意义的寻求,不进行价值的预设。在真实的世界面前,顾城坚持超越,然而,他并不向往彼岸。(28)“目的和概念已经不再束缚他,包括生死概念,人类的生存准则和与之相应的道德意识与他无关;他自性的灵动,使他处在永远的创造之中,不仅生可为游戏,死也不例外。”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9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顾城最为珍视的正是这种“自性”——极致的自由丰富以至于虚无,极致的自我以至于无我,永远的自我超克。在这个意义上,顾城略过现实,欣赏革命领袖那些天人之际的话语:“令人惊讶的不是他(毛泽东——引者按)的行为,而是他的态度;他用一种嘲笑的态度看待自己发动的革命,就像如来看在自己手上翻跟头的猴子一样。他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也会说:‘一万年后,我们都很可笑。’”(29)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88、189、191、191、226、19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顾城是在绝对精神的高度理解了这种话语。
可以说,顾城对革命领袖的形而上认识,不仅形成了他对革命年代的认同,更使他获得了精神和哲学层面的升华。在很大程度上,他不是革命领袖光芒照射下的共和国之子,而是革命领袖的精神对话者。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包括其他朦胧诗人)认为是“春天的故事”,而对顾城而言,这可能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悼念的开端。顾城在这个时期,曾悄悄地写了一首叫作《夏末》的小诗,表达了这种痛苦:
太阳的
温存和暴烈
早已被阴云偷去
细细的向日葵
举不起奉献的花
垂手呆立(30)顾城:《夏末》,《顾城诗全集》(上),第46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在朦胧诗中,“向日葵”和“太阳”常是成对出现的意象,“向日葵”常隐喻着无辜的受骗者和愤怒的觉醒者。(31)最著名的就是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它把头转了过去/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它脚下的那片泥土/你每抓起一把/都一定会攥出血来”。转引自洪子诚、程光炜主编:《朦胧诗新编》,第70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然而,在顾城这里,“太阳”的光芒被阴云“偷去”,“向日葵”由于无法向“太阳”敬献花朵而“垂手呆立”。顾城用“向日葵”这个意象,举行了一次不为人知的秘密悼念,也向芒克等人的“向日葵”实施了一次秘密反讽。
与此同时,面对热热闹闹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顾城也曾写下《街景》一诗:
黄白色
变质的太阳
在热尘中浮动
在天窗中滚荡
沸沸扬扬(32)顾城:《街景》,《顾城诗全集》(上),第44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顾城刻画了一轮黄白色“太阳”。在顾城看来,此时的“太阳”不过是黄白之物,漂行在“爱的海流/欲的汪洋”中,不是红太阳,而是“变质的太阳”。顾城在朦胧诗、“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潮流中固执地、隐秘地建构着自我的精神世界。
历史地看,朦胧诗阶段,顾城受到了过分经典化的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潮流的裹挟,他对“太阳”的隐蔽应该是临时性的技术策略。从1977年开始,顾城明显地感受到社会上越来越强大的反思潮流。他对当时社会上,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思想艺术需求有所了解,他当然也知道怎样的诗歌是被时代所需要的,(33)顾城多次表示当他最初看到《今天》的时候,很受感动。顾城:《顾城哲思录》,第8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他对其他朦胧诗人所表达的某些激烈情绪也不无激赏,他也积极但有其限度地参与到了这种诗歌合唱中。然而,这个阶段是顾城诗歌生涯的危机时段,他在革命年代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受到冲击,在内心深处,顾城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升起于其他朦胧诗歌中的那轮反义隐喻的“太阳”,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像北岛他们那样去说“我不相信”。顾城惶惑了,迟疑了。虽然他不期然地与北岛等人被视为朦胧诗人式的诗歌英雄,但他的困惑深深地植根于内心。他固然不认同北岛等人激烈的情绪,却又不能不合时宜地表现出来。若是固执于那轮“太阳”,他知道他很快会被甩出时代的飞轮。与舒婷、北岛等人的诗歌相比,顾城在这一阶段的诗不仅朦胧,而且十分晦涩,这也映照着他内心的纠结。
三、“我要成为太阳”
顾城毕竟与北岛、芒克等人有着太大的不同。北岛等人的诗歌世界是用广场、纪念碑、花环、受难者等历史遗像搭建起来的,而顾城的诗歌世界是由自然本物构成。北岛等人当然可以通过黑化“太阳”来扩张抒情的深广度,但顾城不能。当北岛等人在投入地消耗政治—历史激情的时候,顾城悄悄地离开了朦胧诗。他要抚平内心的纠结,思考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放置那轮“太阳”。正是在这个期间,顾城写下了著名的《安慰》:
青青的野葡萄
淡黄的小月亮
妈妈发愁了
怎么做果酱
我说:
别加糖
在早晨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
红太阳(34)顾城:《安慰》,《顾城诗全集》(上),第55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安慰》,就是顾城的自我安慰。时隔多年,“红太阳”这个久违的意象,复现于顾城的诗歌中,复现于中国当代诗歌中——这是顾城的诗歌生涯,也应该是当代诗歌史的一个重要时刻。他终于找到了宏大情感的安放方式,并迫不及待,乃至炫耀似地呈现了出来。小诗中,顾城自比为玩耍的孩童,将“红太阳”喻为篱笆上甜甜的“红果子”。这当然不是冒犯,也不是对“红太阳”的祛魅:顾城在另一首《红果》中写道“我拿起一个红果/红的像最忠诚的星星”。“红果”是被太阳晒红的,星星点点的红果像“忠诚的”满天星星,这种画面想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应该不难想象。这是隐蔽的自我技术,顾城在诗歌幻想术中回溯到革命年代的童年,再次品尝了“红太阳”所带来的甘甜。在自然本物的世界中,顾城迎回了“太阳”,真正意义上的童话诗歌创作时期由此开始。
对于顾城,“童话”是一种绝妙的装置:一方面,“童话”能够使顾城重新得到“时间”,即他童年的“革命年代”;一方面,“童话”使顾城重新得到“空间”,即北方农村的自然。对此顾城曾写道:“一个没有油漆的村子/在深绿的水底观看太阳/我们喜欢太阳的村庄”。(35)顾城:《就在那个小村里》,《顾城诗全集》(上),第8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与此对照,20世纪80年代,顾城在改革开放(时间)后的城市(空间),感到了压抑。显然,“后毛泽东时代”不是他自如的世界,“这是我难以承受的,满街都是茫然的人,一阵风就能吹起所有尘土”。(36)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8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童话”使顾城回溯到使他感到安全、朴素、神秘的青少年时期。他从1980年代的“自我”出发,将童年、少年(20世纪70年代)和成年(朦胧诗时期)所受到的压抑整合起来,在童话诗中实现了消解。为了纯化精神世界,顾城在诗中放逐了“父亲”这个告诫他“太阳”危险的信使,诗歌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父亲”这个意象。他顺势丢弃了“工农兵”式的抒情方式,也冲破了北岛们所经营的历史反思新传统,不再尴尬地分享他们的愤怒和身份,他将批评家们对朦胧诗寄予的意识形态厚望甩在一边,将什么黑夜、乌鸦、纪念碑、枪口、鲜血等清除出自己的诗歌世界。可以说,面对诗歌,顾城通过童话诗再造了自我。与此同时,顾城把“太阳”迎回诗歌中,如《雪下大了》(1981):
还是让门铃歌唱吧
把太阳带回家
我们是夏天的爱人
冬天只是一个童话(37)顾城:《雪下大了》,《顾城诗全集》(上),第66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顾城是不喜欢雪的,他也不喜欢冬天和阴天。他喜欢夏天,喜欢烈日骄阳的晴天。在朦胧诗人们纷纷放逐“太阳”的20世纪80年代,顾城“把太阳带回家”,自有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秘密快感。
在童话诗歌中,顾城实在太自由了,现实的和艺术的某些“禁忌”对他已全然失效了,毕竟,谁能责难一个“孩童”呢?顾城越写越大胆,“太阳/太阳在重新微笑/在一动不动,注视着/渐渐围拢的翅膀/风暴中/浓密翻滚的愿望”(1982);(38)顾城:《海中日蚀》,《顾城诗全集》(上),第85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冷冷落落的雨/弄湿了洼陷的屋顶/我在想北方/我的太阳和灰尘”(1983)。(39)顾城:《异地》,《顾城诗全集》(下),第1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太阳”和“光明”“理想”“生命”“生长”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使顾城感到满足。(40)当时文艺界进行着所谓的“朦胧诗论争”,诸多批评家认为朦胧诗代表着“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们列举了很多朦胧诗人的诗,当然也包括顾城的诗,然而,他们避开了顾城所有写到“太阳”意象的诗歌,包括《一代人》和《安慰》。此时顾城已届而立之年,在朦胧诗潮流中,他获得了巨大的象征资本,曾经那个“红太阳”下的孩童顾城,作为精神主体成长起来了。他开始在诗歌中试图以“太阳”的位置去照耀别人,比如《我要成为太阳》(1981):
我要成为太阳
我的血
能在她那更冷的心里发烫
我将是太阳(41)顾城:《我要成为太阳》,《顾城诗全集》(上),第70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这显然是一种渴望。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现代化,使长居北京的顾城内心不再宁静,他觉察“中国文化是去了它寂静的核心、它的根。人也离开了它的传统生活和自然情味,开始妄想妄动,就像离开水的鱼那样妄然”。(42)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8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这不能不对顾城的诗歌构思形成强烈的冲击。他的童年体验越来越遥远,那轮“太阳”带给他的精神强力也越来越暗弱。“我要成为太阳”,成为顾城主体精神结构的一种需要。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顾城在1983年的转变。这一年的顾城,得到了另一种极其重要的生命体验:他拥有了一位登记结婚的妻子谢烨。谢烨对顾城几乎百依百顺,顾城的“任性”“自由”在现实中得到了彰显。顾城重新感到了安全和平静,他的精神强力也将以另一种形式存在。1984年,顾城写下了著名的《我是你的太阳》:
我知道红砂土的火将被鱼群吞食
在近处游着我的中指
我知道婚约投下的影子
……
在你的目光里活着
永远被大地的光束所焚烧
为此我成为太阳,并且照耀(43)顾城:《我是你的太阳》,《顾城诗全集》(下),第111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在他和谢烨组成的现实世界以及精神世界中,顾城逐渐使他的主体性落位于“太阳”。面对谢烨,顾城扮演的正是“太阳”的角色,在谢烨的崇拜的目光里活着,照耀着谢烨,孜孜不倦地“塑造着她的整个精神世界”。(44)文昕:《最后的顾城》,《诗探索》1994年第1期。(对于后来者英儿,顾城也认为他们是在精神而非现实的意义上相爱。)我们很难再见到有人如此热切又如此自信地改造别人的精神世界。
到了激流岛时期,顾城的自我象征能力趋于圆满,他正式地幻想自己为独一无二的“太阳”。如果我们从空间诗学的角度去观察顾城此时的诗歌,可以发现这些诗歌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和自足感。如果再看一看此时顾城的画作《激流岛画本》,可以发现画中所有的意象仿佛都在被一轮并不存在的“太阳”俯视。在顾城的潜意识中,激流岛—革命中国、顾城—革命领袖是同构的存在。这是顾城一生中最为恣意的阶段,他戴着那顶象征着王冠的圆帽,开始特别注意建构诗歌的空间。在诗歌之外,顾城以海水四围的孤岛为自己的王国,修补他那又大又破的房子为“城堡”,养鸡种菜,满足于无道德无法律的极简生活。当英儿来岛之后,顾城又过上一夫二妻的生活。顾城有首诗这样写道:
我在城里住过
爱一个女孩
她在水边
看灰云彩
她的样子像朵莲花
后来
她爱上我
在厨房做菜
她自己告诉我
有个女孩像她(45)顾城:《娥皇》,《顾城诗全集》(下),第84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理解这首诗的关键就在于题目《娥皇》。娥皇、女英和舜帝,就是顾城意识中岛上王国人物的关系。顾城在岛上过的虽是极其朴素的生活,但他的自我认同中,他是一个王者(《英儿》中,谢烨、英儿称他为“可汗”)。他的“基本国策”,就是闭关锁“国”,自力更生。顾城在某些时刻承认他“内心燃着一种不可理喻的独占疯狂”,但从这一时期顾城的诗歌来看,他似乎已经沉浸于这种封闭性所带给他的内在安稳与漫长绵密的狂欢,他毫无征兆地使诗歌构思放弃了逻辑,放任语言和意象——顾城认为这是他写诗最得意的阶段,在自我意识中,他终于建构起了完全的主体性。1992年,顾城在德国交流时写下《我做了一个梦》:
这就是你的爱
你说树也在等
花也在等
它们是你的侍从
等待太阳返回家门(46)顾城:《我做了一个梦》,《顾城诗全集》(下),第811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为了维护“太阳”,顾城努力地将任何具有超越性的事物推出他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诗中,我们找不到如下意象:人群、其他男人(甚至自己的儿子)、其他诗人、雄性和大型动物、父母、西方文学及语言、现代化物品。对激流岛之外的空间,顾城也一概舍弃,只有两个例外,即他还是会吉光片羽地写到童年时代的北方农村,并连篇累牍地写到首都北京(组诗《城》即北京,共52首),“我几乎每天做梦都回北京,但是那是我童年有城墙、碟垛、城门的北京”,“在梦里,我常回北京,可与现代无关,那是我天经地义要去的地方”。(47)顾城:《顾城哲思录》,第16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北京,何以在身在海外的顾城的意识中是“天经地义”要去的地方,令人殊堪玩味。
然而,英儿的离岛及谢烨的婚变,彻底冲破了顾城王国的封闭性。我们很难估计这两件事情对顾城精神世界的冲击到底有多么剧烈,顾城的内心不仅仅错愕,更可能充斥着被背叛的愤怒。他的诗歌中,也第一次出现奸恶者意象,即著名的《鬼进城》:
鬼
无信无义
无爱无恨
鬼眼一睁
鬼
没爹没妈
没子没孙
鬼
不死不活不疯不傻(48)顾城:《鬼进城》,《顾城诗全集》(下),第82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诗境黑暗阴森,这种基调在激流岛时期的诗歌中绝无仅有。这也象征着此时顾城精神世界的面貌。他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国般的世界,他就是太阳,他自述“最使顾城醉心的还是英儿和雷(谢烨——引者按)一起生活的和美场景,看到他们一起行走,就好像看见了童年的梦幻”。(49)顾城:《英儿及其他》,第108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然而,在《英儿》的“尾声”部分,顾城写道:“真正令人费解的不是顾城和英儿的异样恋情,倒是最正常的谢烨,是她和英儿之间的始终友爱的微妙关系。到底是什么使她用正常的情感来对待这一异常生活的?我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一起神气快活地在这个岛上走来走去共度朝夕的。”(50)这段文字,由顾城口述,谢烨笔录,有一句题记“鬼/又一次演电影”。顾城:《英儿及其他》,第410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顾城曾无比醉心的画面,当他曾自以为“太阳”般照耀过和改造过灵魂的谢烨真实地裸露在他面前时,顾城感到的应该是被背叛的耻辱和愤怒。顾城的举斧杀妻,更像是对背叛者的惩罚,而他的自杀,也更像是亡国者的自我了断。
顾城人生最后一首诗写给儿子杉,也是他唯一一首给儿子的诗:
我看见你的眼泪
你手里握着的白色的花
……
我要回家
你带我回家
……
我会回来
看你
把你一点一点举起来
杉,你在阳光里
我也在阳光里(51)顾城:《回家》,《顾城诗全集》(下),第86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这也是顾城激流岛时期唯一一首具有清晰情感的诗,也是最后一次写到“太阳”。看着儿子,顾城不能不想起他的童年,想起曾经照耀过他的“太阳”。之前顾城曾对儿子说“我不太相信,照过我的太阳,又会照着你”。(52)顾城:《英儿及其他》,第254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然而,顾城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众叛亲离的绝望和浓郁的死意中,他选择了相信。顾城对他的王国的一切感到绝望,只有不在他的王国里的儿子,才使此时的顾城感到一点点安慰,“门开着/门上挂着一把锁/太阳是凉的/只有心里有点热”。于是他把最后的阳光许给了自己和儿子,“你在阳光里”“我也在阳光里”。
四、当代抒情主体的极致与极限
自缢的顾城,脱下了那顶王冠似的帽子,象征着激流岛上对“革命中国”的戏仿实验的失败。在顾城的诗歌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作为“太阳”的宰制欲望。在青少年顾城的意识中,革命年代确曾产生过极致的诱惑。顾城在那个时代讴歌“太阳”,在朦胧诗时代也秘密地捍卫着“太阳”的光辉,但是,这都不足以表现顾城作为一个精神主体对革命年代和“太阳”的感受。当他的精神主体足够成熟的时候,他便用激流岛上的王国实验来加以外化。
很大程度上来说,顾城的精神动力来自于“革命年代”。唐晓渡曾说革命年代给顾城“暗中受其诱惑的力量”,“每一个经历过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情境的人,即使再善良,也不难理解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53)唐晓渡:《顾城之死》,《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顾城是一个高度依赖精神存在的人。领袖的精神强力、道家风采、虚无主义和超越生死的生命哲学,对顾城有一种深刻的吸引。顾城在激流岛上同化了革命领袖的精神人格,同构了一个极致的抒情主体。
这种极致的抒情主体,也达到了20世纪中国抒情传统的某种极致。五四时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启蒙诗人,曾经建构过极致的精神主体: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单是这条吞噬“日”的“天狗”,就能象征彼时代所诞生的个人主义极致主体。然而,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激荡巨变,启蒙诗人的精神主体性建构被更为实际的宏大焦虑(革命救亡)合理地压抑,合情地让位于“向太阳”的革命精神建构。
艾青等革命诗人建构起了“向太阳”的集体主义抒情主体。这一抒情主体也是充满革命伦理的自洽。如果说五四时代的“天狗”是解构性主体,那么,《向太阳》等诗篇则主要呈现为建构性主体。“天狗”作为相对抽象的抒情主体的功能,主要指向启蒙者的“私人遭遇”和“伟大意愿”。而“向太阳”的群体则将“抒情”作为“人民真正具体的命运来加以感受”,从而“塑造能直接地同时又典型地表达出时代生活问题的这样一些个人命运”。如此一来,在某种时代和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抽象,往往因此而具备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力量”属性。《向太阳》实际是在超越抒情的维度上揭示了“历史的重要人物之所以重要,正在于他们把散布在生活本身中间的、以纯粹个人的形式、纯粹私人命运的形态出现的问题,提高到想象的高度,加以一般化”。(54)〔匈牙利〕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第129页,张佩芬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故而,艾青一代抒情主体只不过是将“历史的重要人物”的主体性,以诗学问题的形态“提到想象的高度,加以一般化”,于是“太阳”被选择成为这一“想象的高度”和“加以一般化”的人格化象征。
“向太阳”这种诗学形态具有严格而又封闭的秩序和规则,位于顶端的精神主体被认同为“太阳”。在无限的“被需要的重复”中,“向太阳”逐渐从最初的集体有意识衍化为集体无意识。这当然是由某种历史共识所决定的。出于革命伦理的自觉,郭沫若在1949年之后反复说他的诗歌应该被焚毁,因为那只“把日(太阳)来吞了”的“天狗”极其可疑,他的泛神论从“向太阳”的那天起就破产了。当郭小川展现出“望星空”的姿态时,集体无意识几乎自动地模拟出郭小川的隐语结构:“望星空”是对“向太阳”传统的悖逆。
可以这么说,革命年代的抒情主体不必要占有其绝对精神主体,这在“继续革命”的诺言中固化为一种诗歌常识。所以,当今天看来一点也不朦胧的朦胧诗出现时,艾青一代诗人才会“气闷”。
我们当然能体会谢冕等人搬出五四时代的郭沫若来为朦胧诗正名的意图,在北岛和谢冕等人看来,文学作为政治“共识地带”的历史即将终结。然而悲哀的是,他们却并没有像五四时代那样成功地建构起强大的个人主义主体性,而是在人道主义诉求中“必须从翻译文学中寻求各自的风帆和船舵”,(55)张定浩:《批评的准备》,第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从而再次聚合并再次分散于新的集体主义。即使“崛起论”者再如何褒扬那句“我不相信”,它也只具有虚无主义的激情表象:讽刺崇高却放过日常;表达情绪并流于感性;表现人道时却混于人性;专注审美但略于经验;歌颂爱情却无视身体;充斥着梦与理想的同时却回避着欲望;努力地在宏大叙事终结的废墟上建构着“自我”,然而很快却发现“本我”的分裂迫在眉睫。“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渐渐只能以“漂泊和孤悬(海外——引者按)”模拟朦胧诗最初的语境,借以维持着渐近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照结构。(56)“如果没有后来的漂泊及孤悬状态,我个人的写作只会倒退或停止。”见唐晓渡、北岛:《“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诗探索》2003年第11期。那对历史的“反思”,那曾赋予朦胧诗人的巨量象征资本,却在“现代化”中国成为巨大的精神负担。多年以后,旅居海外的北岛这样回味:“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57)转引自陈超:《北岛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果然,北岛在多年的幻觉代偿之后,在厌倦了没有“太阳”的深夜饮酒和午门夜游之后,回到了语言,写起了纯诗。(58)张桃洲:《去国诗人的中国经验与政治书写——以北岛、多多为例》,《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如果北岛是诚实的,那么,20世纪80年代初“崛起”的到底是什么?(59)见何同彬:《晦涩:如何成为“障眼法”?——从“朦胧诗论争”谈起》,《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我想,与其说崛起了“美学原则”,倒不如说崛起了解构主义的激情更为合适,特别是当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打出“PASS北岛”的旗帜时,“崛起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过早地从而过分地发动了朦胧诗的经典化,一两年前还可以作为“美学原则”的朦胧诗很快“圭臬已死”。(60)徐敬亚:《朦胧诗后——圭臬已死》,《文艺争鸣》1988年第6期。
“第三代”诗人将“现代化”(政治学)为旨趣的朦胧诗推向了语言学的世界,被评论界称为“后朦胧诗人”。作为精神主体,“后朦胧诗人”和“朦胧诗人”同样是虚弱的,乃至于是分裂的。在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他们都是“弑父”的一代,然而当时却并没有勇气也没有意愿亲自成长为“父亲”。“弑父”的冲动消解于另一轮“弑父”的冲动中,“朦胧诗人”的集体主义激情消解于“后朦胧诗人”的语言迷津中。是否可以这样说,大约从这个节点起,抒情成为一件难事,刚健主体的建设也成为一件难事。
实事求是地看,顾城是一个例外。他不仅是最早离开朦胧诗的人,也是朦胧诗人中最先停泊于语言之岸的人,他的精神主体因此而得到了超拔。的确,海外生活使顾城隔绝了“现代化中国”,他也没有北岛等人“反思”历史的欲望和负担,如果说海外经验是北岛“反思”历史的解构力量,那么顾城的海外经验则是一种主动的结构性力量。“语言”(存在之家)与“激流岛”(“王国”)有机结合为他的主体性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顾城极度自律地建立起了他作为“太阳”(国王)的极致主体。
然而,顾城并没有成功。在“语言”和“海外”,顾城并没有和“革命年代”的那个“自我”分离。张清华认为顾城的悲剧“在于他至死都没有走出‘精神的童年’”。(61)张清华:《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我想,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顾城在精神上没有成年,而是他没有脱离童年的“精神”。在潜意识中,顾城是不愿意走出这个“精神的童年”,顾城的自喻“太阳”也不过是一种微妙的幻觉代偿技术,使他童年时代能够写政治诗,成年后却能够写童话诗。在纯粹精神层面,顾城实现了极度的自由。
在某种程度上,顾城标志着他那个时代抒情主体所能达到的一个极致。我们也悲哀地发现,他也没有真正完成自我的主体性建构,甚至由于极致而无法圆满以至于异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人之死”已成为重要话题。与顾城相似,海子也曾很多次自诩为“太阳之子”,“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他们对成为“太阳”充满冲动,并借以象征着抒情主体的强度。但是,他们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太阳”而不是别的意象来标榜自我主体的极致呢?以赛亚·伯林说浪漫主义是一场“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62)〔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3页,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那么我想,原因只能在于顾城、海子对“太阳”的不约而同的渴望和想象。由此可说,他们的失败,不能不暗示着当代诗歌抒情主体建构的困境,不能不意味着当代中国抒情传统的内在限度,不能不使我们感到,虽然顾城们已经到达了某种极致,但还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类摩罗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