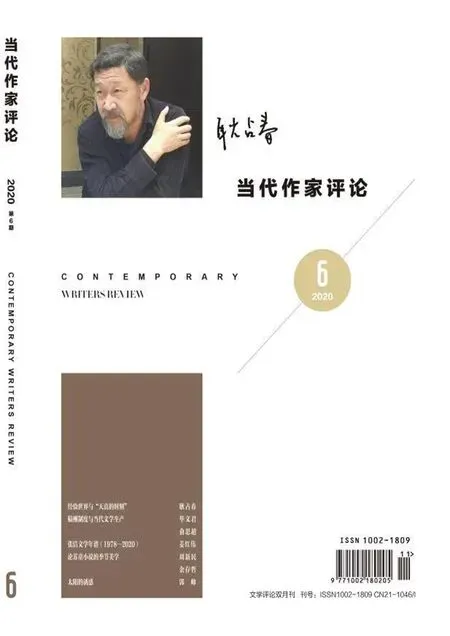论满族作家叶广芩小说创作的京剧意蕴
曹转莹
叶广芩,是晚清隆裕太后的亲侄女,慈禧太后的侄孙女,是当代典型的京味儿满族作家,是“在自己的姓名上就浓浓地渗透其作品之魂灵”(1)阿城:《流年惊风雨 今个叶广芩》,《时代文学》2004年第1期。的作家。自1994年创作家族系列小说以来,叶广芩发表了《本是同根生》《采桑子》《全家福》等作品。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状元媒》,包含11篇以同名京剧曲目命名的系列中篇小说,即《状元媒》《大登殿》《三岔口》《逍遥津》《三击掌》《拾玉镯》《豆汁记》《小放牛》《盗御马》《玉堂春》《凤还巢》,小说以京剧入味,架构起整个“金氏”家族成员的命运兴衰。有论者指出,“所谓京剧系列小说,是指叶广芩以京剧名做小说名,同时小说中也巧妙运用该同名京剧的典故和内涵。这些小说都是对清末以来社会历史及皇族后裔人生境遇的书写,其笔墨老道辛辣,文字耐读,且见境界,京腔京韵圆熟悦耳,是老北京的一幅‘浮世绘’,描摹人性在历史巨变中的千姿百态。”(2)王虹艳:《享受想象力的盛筵(代序)——2009年度中篇小说观察》,北京文学月刊社编:《2009中国文学中篇小说排行榜》,第1、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叶广芩此系列小说以京剧为突破口,提炼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题目设置上直接致敬京剧情怀,行文叙述中带着京剧唱腔儒雅、精致的韵味,故事情节推进与戏剧情节相呼应,将对京剧的痴恋转化为晕染着传统文化内蕴的文字,并杂糅着她对满族遗民文化中“贵族精神”的新阐释。本文从叶广芩满清皇族后裔身份与京剧之间的纯正关联、京剧对其创作的潜隐文化滋养等方面,挖掘其小说中京剧意蕴的深层创作表征,探求其对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衰退的感伤和对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
一、语言:古朴典雅的念白遗风
洪堡特说:“一旦人在心灵中真正感觉到,语言不仅仅是实现相互理解的交流渠道,而且也是一个实在的世界,即一个精神必须通过内部创造活动在自身和事物之间建立起来的世界,他便走上了一条恰当的道路,能够不断地从语言中汲取到新的东西,不断地把新的东西赋予语言。”(3)〔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209页,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语言风格是作家艺术个性在精神输出上的表现。1986年,叶广芩、叶广宏兄妹合著出版长篇小说《乾清门内》,初步奠定了典雅、缜密、舒缓的叙事格调,如话家常式地书写了清朝末年紫禁城中慈禧、光绪、惇王奕誴、隆裕太后等皇族人物的故事。而后,叶广芩的家族小说中出现了以京剧为主,大量使用包含评剧、秦腔、昆曲、京韵大鼓等种类多样的戏曲曲目,她对老北京风情的熟稔已融入主人公灵魂,她笔下的满清皇族后裔的生活习惯投射出纯正的京韵,而对满族辉煌民族历史的向往使其勾勒现实生活时略显单薄。
京剧唱词的特点一定程度影响了京剧爱好者文学创作的语言格调。不同于秦腔的粗犷、昆曲音调情节的细软,京剧独有的古雅与大众化的苍凉感、深厚的古典文学积淀已转化为叶广芩雅致的语言风格。京味儿作家邓友梅指出叶广芩的小说具有“墨香”。(4)邓友梅:《沉思往事立残阳——读叶广芩京味小说》,叶广芩:《采桑子》,第3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叶广芩精心设计作品名字,长篇小说《采桑子》以满族才子、叶赫那拉家族的文学家纳兰性德的《采桑子》这首词的词牌、词句作为书名、章节名和整部家族系列小说的标题,其中包含八个中篇《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醉也无聊》《醒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曲罢一声长叹》。小说有优雅的行文气质、考究的遣词造句,佐以古典文学的段落互文,以规则礼制为范本,甚至加入戏剧名篇中的对白。这种叙述格调如同《梦也何曾到谢桥》中六儿戏剧性地成为大服装设计师后不屑地帮老父亲给“我”送旗袍一般,“精致的水绿滚边缎旗袍柔软的质地在灯光的映射下泛出幽幽的暗彩,闪烁而流动,溢出无限轻柔,让人想起轻云薄遮、碎如残雪的月光来。旗袍是那种四十年代末、北平流行的低领连袖圆摆旗袍,古朴典雅,清丽流畅,与现今时兴的,与服务小姐们身上为多见的上袖大开衩旗袍有着天壤之别”。(5)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采桑子》,第324-32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旗袍是旗装的现代转型,以此对满族旗装的精致叙述,表现出与京剧相同的严格精致的精神内涵,使对古典文明的崇敬与浅薄的现代模仿形成鲜明对照。作者叙述语言的“高傲”姿态既有对语言的严格自省,也有对粗俗语言滥觞的自觉抵制。
京剧是集唱、念、做、打、舞于一体的艺术表演方式,它重视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以程式化的表演手段叙述故事,刻画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京剧口诀对唱腔唱词要求严格“一字走了调,全盘皆是输”,对“翻跟头”则要求“上去一个蛋,下来一条线”。叶广芩小说文字运用得精致源于对叙述“信达雅”的要求,即追求古朴、精炼,寻求与自我性情相吻合的语言书写。叶广芩认为做人和作文是一样的,追求一种冲淡之趣,求的是一种心态的平静,让人慢慢去体会余味,人生的平淡,文章的平淡,那才是将人做到了极致,将文作到了极致。(6)叶广芩:《颐和园的寂寞》,第6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10。叶广芩否认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叙事”,其小说中关于古董、饮食、绘画、书法等方面的知识作为带有昔日满族遗风的生活积累,以碎片化方式呈现为家族回忆。这些包含满族遗民文化的书写,于不同学识层次的读者而言不存在阅读障碍。因为小说以说书人般的叙述节奏娓娓道来普通社会大众的人情冷暖。
长篇小说《状元媒》由几个中篇小说组成,多以同题戏剧唱词为题记,或由一段京剧念白引出,点出典故来源。类似于京剧演员在梨园登台亮亮嗓子,开腔后又止于简短的独唱,从经典曲目拉回到现实生活。小说《大登殿》题记:“宝钏封在朝阳院,代战西宫掌兵权。参王驾来问王安,讲什么正来论什么偏。——京剧《大登殿》唱词。”(7)叶广芩:《状元媒》,第51、141、18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小说《逍遥津》题记:“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我恨奸贼把孤的牙根咬碎……欺寡人好一似猫鼠相随。——京剧《逍遥津》汉献帝唱段。”(8)叶广芩:《状元媒》,第51、141、18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小说《三击掌》题记:“上脱日月龙凤袄,下脱山河地理裙,两件宝衣来脱定,交与嫌贫爱富人。休怪儿与父三击掌,一朝肠断两离分。——京剧《三击掌》王宝钏唱段。”(9)叶广芩:《状元媒》,第51、141、18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念白独立于开篇,同《诗经》中每个独立篇章的大序有着同样的结构设置。同为满族作家,老舍出身贫民阶层,与叶广芩的少年生活境遇完全两样。老舍的行文叙述更平和,是更接近口语的京味儿叙述。而满族“格格”身份决定了叶广芩不同于老舍等京味儿小说作家的语言叙述模式。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的叶广芩,以别致清新的叙述步调结构全篇,与精炼、雅致的语言趣味相互映衬、交相呼应。叶广芩营造与主干故事不能割舍的背景氛围,穿插其中的枝桠情节之间也相互独立。她用词不造作、不拿捏,饱含京味儿文化的语言总带着书卷翰墨的气息,有着京剧表演的舞台美感。她用典雅的京腔京韵讲述满族大宅门内旗主儿的生活,渗透着老北京皇族生活的独特京味儿风韵。
二、情节:人生如戏的命运互文
中国戏曲在艺术上自成体系,在文本、音乐、表演与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有一整套创作规范与要求,并且形成了程式性、虚拟性、写意性为特点的戏曲美学。(10)丁盛:《论当代昆剧创作观念的嬗变》,《艺术广角》2019年第5期。当代文学作品中采用小说与戏曲故事相互借鉴的文学表现手段的现象并不罕见,张爱玲、李碧华等人的小说都将京剧作为叙事工具。京剧是清朝徽班进京后吸收昆剧、梆子、汉剧等多种声腔剧种而形成的,许多传统京剧曲目也出自这些剧种,或是通过增加、删改而创作出新曲目。作为清朝统治者的满族促成与推动了京剧的繁荣,“从一定意义上说,清代满族上上下下对俗文学的喜好,正好为京戏在清代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条件,京戏能否产生,并且发展成为国戏就很难说了”。(11)赵志忠:《民族文学论稿》,第110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宫廷贵族与平民欣赏京剧的同时,对这种传统文化形式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戏迷“票友”陶醉其中,不断地将身边的人和事,以京剧故事的价值观念进行现实通感。叶广芩小说中对京剧情节的直接借鉴与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手法相同,对京剧情节的植入多是部分节点的契合。
京剧是老北京人重要的娱乐活动,成为连接老北京和满族的重要文化纽带。纯正的满族“格格”身份使叶广芩对京剧体会深切。京剧与文学文本的互文对照,不仅成为叶广芩文学创作的特色,同时传达出传统京剧的精神内蕴与价值观念,散发出独特的审美意蕴。1999年,叶广芩凭借散文集《没有日记的罗敷河》获得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她在作品中回忆童年在颐和园的生活细节:“父亲不仅戏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一家人经常在晚饭后一起演戏,父亲和三大爷坐在金鱼缸前、海棠树下,拉琴自娱。而几位兄长也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一家人演《打渔杀家》《空城计》《甘露寺》《盗御马》等,戏一折连着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12)叶广芩:《琢玉记》,第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童年与京剧的关联持续终生,此种夏夜全家唱戏、听戏的场景在小说《豆汁记》《谁翻乐府凄凉曲》《唱晚亭》中都有再现。这种满清皇族的生活经验成为其家族系列小说的现实参照。小说以京剧作为引子,将满族后裔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家国情思,置于新的文化语境进行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煅烧。后来到西安生活的40多年中,叶广芩师从全巧民学习京剧,这种文化记忆的延展、生长及其小说创作中显性或隐性的文化符号标记,使其满族身份融入文学创作的灵魂深处。长期的京剧审美经验为叶广芩的思维方式、行为作风染上一层京剧文化风格,使其将小说创作与传统京剧融会贯通,形成思想和形式的完美结合。
戏曲的通俗性、大众性使其成为中国人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与表达人生思考的艺术形式,其中传统历史戏蕴含着古人遗留的精神财富。看戏、听戏、唱戏是叶广芩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叶广芩小说多取材个人生活体验讲述家族轶事,穿梭其中的京剧情节总与现实人物命运紧密相连。京剧与小说像在唱双簧,故事情节如一场即将散场的戏曲,低吟人生过往的沧桑与无奈。京剧对作者思想内层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创作思路、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等影响深远,为小说营造了整体氤氲的京剧气韵氛围。作品多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观察事态变化,吟唱京剧字正腔圆的旋律,诉说戏剧化的故事,讲述如大格格、二哥、三姐以及家里的厨师、门卫等家族成员的沧桑人生经历。经历过身份认同危机的叶广芩在以京剧为文化娱乐生活的环境中长大,戏曲已构成她认知生命的启蒙图景,这是现实与历史的呼应。叶广芩对昔日的生活充满怀念,习惯从京剧中汲取创作素材,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安排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在与京剧的逐渐融合过程中挖掘出深邃的人生哲理。她以传统经典京剧曲目命名的小说中,戏剧是一味不可缺少的作料,戏剧的故事内容被切碎后分布于小说的各个部位,其中人物命运的发展、转折与京剧的剧情安排保持高度一致,作品穿越历史长河复活了满清皇族后裔的现实生活。
传统的京剧与文学离得较远,相比较而言,昆曲更讲究文本,京剧则重在表演,是以演员为中心的剧场。(13)郑晓强、林侃、余潇:《将京剧与文学拉得更近些》,《福建日报》2009年12月2日。京剧评论家认为京剧的突出特色在于演员个人的角色表演,而与剧本的文学性之间关联不大。叶广芩选取的曲目往往与其所讲述的故事密切关联,但又并非它的本来面目。在小说中,京剧作为互文性文本存在,作者设置人物在小说中看戏、说戏、演戏,以一篇曲目一个家族成员为主的人物中心方式进行。小说叙述中保持着清晰的叙事逻辑,故事套故事,对人物身世甚至相关其他故事也如数家珍。京剧中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规则,在规定范围内的服装是符合人物的身份、职业和性格的,是经过多少年的积累才沿袭下来的。不能为了华丽、漂亮而穿不合规定的服装。(14)张永和、钮骠、周传家、秦华生:《打开京剧之门》,第2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戏台规矩如叶广芩的家族老规矩,更确切地说是宫廷生活经历所形成的不可摒弃的生活态度。
京剧《拾玉镯》中,傅朋对孙玉娇一见钟情,借故将玉镯丢在孙玉娇家门口,最终孙玉娇三拾玉镯接受傅朋,玉镯成为二人的定情之物。叶广芩在同名小说《拾玉镯》中对京剧进行重述,赫鸿轩与同名人物孙玉娇偶然相遇。与京剧相似,玉镯最终也是赫鸿轩与孙玉娇结为夫妻的定情之物。但京剧中的孙玉娇与小说中的孙玉娇性格完全不同,京剧中的孙玉娇娇俏可爱,而小说中婚后的孙玉娇性格泼辣,行为彪悍。小说与京剧之间文本互文,但人物的价值观与京剧的关联则是作者对京剧所传达的价值体系的再创造。
叶氏家族中流传关于叶广芩母亲的戏剧化故事与京剧《大登殿》相似,即母亲是薛平贵后娶的代战公主,张芸芳是先娶的王宝钏。尽管代战公主年轻漂亮有本事但只能进西宫,先娶的王宝钏又老又丑却因寒窑苦等薛平贵18年而封在昭阳院当正宫。新的京剧剧情是代战公主先给王宝钏行礼请安,王宝钏则端坐不动,待代战行礼过后,王宝钏才过来搀扶并与之寒暄。西院的代战公主最终仍败给了晚到18年的王宝钏。小说中母亲嫁给大自己18岁的老公本有着上当受骗之感,可经状元媒人刘春霖劝解,竟在妻妾的身份差异里找到了平衡。名分如京剧里的穿衣打扮一样有着严格的程式化标准,张芸芳妾的身份打消了母亲的顾虑。张芸芳责令老七替自己给“太太”磕头行礼的瞬间,宣告了这套不可逾越的宗法制度在老宅子中的地位。两个人在没落的皇族家庭里,虽然夫妻关系受《婚姻法》保护,但依旧没有“站错位置、穿错衣服”。尽管张芸芳比母亲进门早,年纪比母亲大,家庭背景比母亲好……但叶赫那拉本家姑奶奶的懿旨确立了张芸芳为奴为婢的身份,为这出家族戏剧提前定下不可逾越的家族“规矩”。
《小放牛》本是情节相对轻松的京剧,但在叶广芩同名小说中却是牵连着五姐、张安达、敬懿皇贵太妃等人的一出意味深长的戏。开篇点出作品的戏剧出处,戏中杏花村的酒香蔓延到我的目的地——杏花深处的养老院。五姐曾经和张安达上演过《小放牛》,其中牧童的角色从五姐的第二任丈夫转移到真正的出色演员张安达这里。原本这是为敬懿皇贵太妃带来欢乐的轻松剧目,却意外地成就了张安达的梦想,同时又衔接起五姐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故事。张安达一直未能走出太监的身份局限,轻松而凝重地走向严格的尊卑观念。小说“圆形人物”的塑造原则,超越了京剧截然分明的人物道德评价标准,丰富了故事的同时发现了人性的复杂难测。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京剧情节经艺术处理已融为一体,小说与京剧题目相同、结构吻合、人物命运安排相对应。《三岔口》中父亲和孙团长讨论开黑店的刘利华是否应该被禀杨延昭之命暗中保护焦赞的任堂惠杀死,再到考虑到小连和大连的人生不同选择的结局,最后到监狱国庆联欢会上小连上演此戏时剧本已按照父亲所期待的艺术规律,将戏中的刘利华改为杨家将战线的人,双方握手言和。一方面这是京剧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小连、大连的命运也满足了读者阅读的心理期待。
三、背景:星罗棋布的京剧典故
在《颐和园的寂寞》里,叶广芩写到“我”在颐和园,在曾经杨小楼、梅兰芳等京剧大师唱戏的大戏台上唱《打渔杀家》。戏剧成为“我”童年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后来,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大戏台倒塌标志着“我”童年生活提前结束,“我”过早地承担起家庭重担。而戏剧陪伴自己走过孤独的时光成为生命中珍藏的纯真、温馨的记忆,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我爱戏,爱得如醉如痴”。(15)叶广芩:《颐和园的寂寞》,第33、38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10。
叶广芩的小说时间跨度很大,多从老一辈所处的满清时代讲起,某种自豪感在回忆中升腾。叶广芩中年跨入文坛,将浓重的怀旧气息浸泡在老北京胡同中,滴落在保留着满族遗风的民间。远方的生活场景散发出独特的味道,而小说中最有魅力的正是那遥远的故事。在由远及近的叙述过程中,近处的风景总会黯然失色。她对家族当下生活的叙述略显单薄,不及对过往的追溯苍劲厚实。叶广芩骨子里的京剧因子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活力,她“喜欢唱京戏,还像儿童一样喜欢自己一个人耍木偶,给木偶编台词”。(16)杨鸥:《“格格”作家——记叶广芩》,《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0月31日。叶广芩从父亲生动再现《梦华琐簿》中清末北京梨园行的轶事开始迷上京剧,而真正爱看戏的成熟原因则是“体会到中国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体会到昔日无数个甜酸苦涩的梦”。(17)叶广芩:《颐和园的寂寞》,第33、38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10。虽然她最初学习戏曲的愿望因母亲反对而有始无终,而后师从秦腔表演艺术家全巧民学唱也无果,甚至断定“此生与戏无缘”,但这份痴情在叶广芩的生活里依然烙印深刻。
组成长篇小说《采桑子》的多个中篇几乎都集聚了京剧意味,如《谁翻乐府凄凉曲》中叶广芩多次使用点戏、饮场等戏剧专业词汇。对花旦、老旦、青衣、小生等出场与唱功的描绘充分体现出她对戏剧专业领域的精深认识。其中,戏痴“大格格”对《宇宙锋》中的青衣唱段无论程派抑或梅派都游刃有余,“大格格圆润的嗓音,那些裹腔包腔的巧妙运用,一丝不苟的做派,华美的扮相,无不令人感心动耳,加之那唱腔忽而如浮云柳絮,迂回飘荡,忽而如冲天白鹤,天高阔远;有时低如絮语,柔肠百转,近于无声,有时奔喉一放,一泻千里,石破天惊;真真地让下头的观众心旷神怡,如醉如痴,销魂夺魄了”。(18)叶广芩:《采桑子》,第38-39、2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对“大格格”唱功的赞美是对京剧唱腔的精细体验,也是对其他家族成员京剧素养的另类呈现。京剧角色行当的固定评价体系在叶广芩小说中同样奏效,“大格格”所偏爱的青衣唱段正是其人生轨迹“人生如戏”的表现。“专攻程派青衣的她这回却破天荒唱起了梅派看家戏《宇宙锋》里‘金殿装疯’一折。《宇宙锋》是说秦二世胡亥荒淫无道,见宠臣赵高女赵艳容貌美,欲纳为妃,女矢志不从,装疯哭闹,胡亥纳妃之意乃罢……大格格在今天这种场合选择了这出戏,在金家不少人的心里投下了不详的阴影。”(19)叶广芩:《采桑子》,第38-39、2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满清皇族在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改姓“金”,这与叶广芩家族系列小说选择的金氏家族相契合,“大格格”选择悲凉的戏剧《宇宙锋》则是对其人生前路的一种心灵感知与预设。叶广芩的父亲生于光绪十四年,曾毕业于官办的机械学堂,后来专事陶瓷美术工作。伯父是早期的留日学生,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院顾问,1963年病故。(20)叶广芩、叶广宏:《乾清门内》序言,《乾清门内》,第1页,西安,未来出版社,1986。文化渊源深厚的家庭赋予叶广芩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于收藏鉴别、古诗词句,甚至是中医等方面的知识她都信手拈来。叶广芩的小说创作营造出满清皇室贵族遗少的生活氛围,将我们带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奇境地。在叶广芩看来“那原以为只有自己才能体味的对于家、对于人生的复杂情感,一种广大而深邃的文化氛围,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情变易史,一种时代风云与家事感情相扭结的极为复杂的情绪,情不自禁地包蕴而出……”(21)叶广芩:《颐和园的寂寞》,第338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10。
京剧是历史悠久的国粹,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是京味儿的一剂重要材料,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实质或变异形式成为叶广芩小说创作的重点,在她的小说中,京剧像一剂京味儿的药引子一样不可或缺。叶广芩小说用京剧做背景,使人有种在戏园子听戏的感觉,各色风俗人情、人文景观踊跃攒动。小说《豆汁记》中,父亲和母亲饭后看戏的细碎生活缩影反映了北京市民生活的常态,说明京剧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如调料般潜移默化地调制着其精神生活。给小说插上京剧的翅膀,一方面增添了小说的文化内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经典的传统京剧故事多出自古代名人轶事或是以民间故事为原型,而叶广芩的新鲜独特之处在于她为我们呈现的多是与其格格身份相符的相关人物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或道具与京剧偶然契合,看似写家庭成员的故事,但真实的时空感有着历史的诱惑力。在其小说中,京剧是一种回归逝去时代的精神寄托。
四、意蕴:传统美德的文化期许
清军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在加强政治统治的同时,不断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使其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逐渐被同化,而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坚守却得到统治者的深切认同。叶广芩小说的流行与文化消费时代大众对满清文化的热衷有关,特殊的格格身份无形之中保证了叶广芩所描绘的满清皇族生活的真实性,为其“现身说法”的文学作品的传播增加了成功的砝码。她的特殊身份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境遇。全家人曾因满清皇族身份而受牵连,昔日的尊贵消失殆尽,养尊处优的成长环境消磨了家庭成员的生存技能,所以在受尽白眼和排挤后,他们学会了沉默。中年叶广芩偶然接触到小说,同时新时期宽松的文化环境允许她开始回味往日生活,对满族身份的认同感觉醒。叶广芩对满族文化中的传统道德体系,眷恋中有批判,批判中又有着深深的无奈与不舍。新时期以来,叶广芩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着浓厚的荣誉感,她每次登台领奖,都以现代旗装表达她对民族身份的强调。她对京剧剧情谙熟于心,借用京剧形式表达生活中的点滴体验,表达她对戏剧性命运的感慨。京剧典故的精神内核能够点明主旨,寄托着叶广芩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怀念,她不断呼唤着仁、义、礼、智、信这些久远而不失时代意义的价值取向的回归。京剧本身是程式化的,不同的角色和脸谱有着固定内涵,擅长青衣的“大格格”、演丑角的“老五”、爱扮老生的“老大”,家族系列小说中每个家族成员所选择的京剧行当都与自身性格特征与价值观念紧密相关。满族重“礼”,尤其是满清皇族后裔的皇家之“礼”遵循着更严格的标准,小说中“我”的问安要顾及王府中所有的活物、“我”在接受长辈舅太太训话时要纹丝不动、“我”必须要在大年夜前拔除银安殿前的所有荒草等严苛的礼仪要求固然死板,却在后代人的坚守中保留着最原始的礼仪文化的精髓。
在京剧传统剧目《三击掌》(又名《红鬃烈马》)中,唐朝丞相王允,因反对女儿的婚事剥去三女儿王宝钏的衣衫,将其赶出家门,两人三击掌后发誓永不相见的情节被叶广芩作为引子写入同名小说《三击掌》的序幕。父亲曾在南屋呵斥七哥脱光衣服以惩戒他迷恋大嫂柳四咪的“荒腔走板”。同样,王阿玛与参加革命的儿子王利民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发生争执,最终也勒令儿子脱掉衣衫并将其赶出家门。但与京剧情节中王宝钏当上皇后与父亲再次相见不同,王利民与父亲此别竟成了永别。京剧为“我”父亲敲响教育子女的警钟,甚至波及“我”哥哥们也不敢轻易让孩子脱光衣服,更是不会将其赶出家门。
叶广芩笔下的文学世界在历史回望之间恍如隔世。关于写《大登殿》的动机,她说是对“以往生活细节逝去的无奈和文化失落的不安”,“借《大登殿》来回顾一段姻缘,回顾母亲的性情,姻缘在其次,目的是将老辈的信念传达给今人,大家从片段细节中追溯历史、品味人情、琢磨生活、感念今天”。(22)叶广芩:《创作谈:历史的旋回碎片——写在〈大登殿〉发表的时刻》,《民族文学》2009年第1期。这其中的表达信念是什么呢?——是对当下“小三儿”“包养”等行为的批判。这就是“我”在得知博美送给“我”的披肩来自其“包养人”后便打消了初见时的欣喜和爱惜的原因。显然博美在叶广芩眼中是“穿错了衣裳,走了腔的”。《豆汁记》中,莫姜以德报怨地包容在自己脸上砍下刀疤的落魄丈夫刘成贵及他的儿子。经莫姜感化,刘成贵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借在东直门外国营粉坊工作之便常为叶四爷一家送去豆汁以度过难关。莫姜坚韧的人性光辉在改造刘成贵的同时,也支撑她坚强而有尊严地活着,而养子却造了叶四爷的反,这种泯灭天良的不义之举让刚烈的她选择“自杀”,以断绝此种屈辱的生活方式,这与京剧中所倡导的忠义不谋而合。
“投射在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是判定民族文学的深层的稳定的标记”,同时,“作家的内心世界具有不同的文化因素,这常导致他的一个艺术整体,甚至一个意象,都可能极为内在地融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23)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第43-44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面对现代社会的时代变迁和家族的兴衰,怀旧成为一些当代满族作家创作的情感需求,他们通过对家族命运历史的回忆,观照现实生活境遇,深刻反思传统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满族作家的身份,使叶广芩的小说对老北京满族严守礼仪、仗义助人、自由和谐等传统道德理念在人物本性的呈现方面尤显贴切,她对满族人的精神气韵有着精准的把握,对中国儒家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有重新繁荣的期待。“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像一把无形的尺度,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之中,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都是一种状态,唯不能堕落。”(24)叶广芩:《采桑子》,第43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出身曾带给叶广芩不被理解的酸楚,而她所否认的叙事“贵族化”反而是其家族真传的厚重文化艺术韵味,是其不可磨灭的身份养分。“国粹”京剧已内化为叶广芩文学生命中的文化品质与灵魂特性,她怀着文化焦灼感寻觅传统与当下的连接,借助笔下饱含京剧韵味的人和事,融合京剧与文学,书写出时代、自我、社会转型的苍凉感,企图唤醒沉睡的传统,接续美好精神品质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