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小诗,气魄不输郭沫若
咸立强
“世纪老人”冰心如同一座永远闪亮的灯塔,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成长的航标。在中国现代作家谱系中,冰心用清新而简练的话语、浓厚又隽永的温情感染了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读者。她的爱如涓涓的细流,虽不能掀起惊天动地的豪情,却总有水滴石穿的永恒力量;她的爱如宽广的山脉,虽没有悬崖陡峭的惊险,却包容着延绵不断世的永世情怀。2020年10月5日是冰心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感怀的时刻,让我们重温她的作品,感悟在她真诚美丽的语言中所展现出伟大母爱的慈祥与叮咛。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张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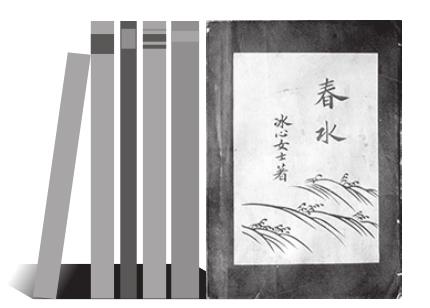
冰心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在现代文学的发生期、有些寂寞的“五四”文苑里,冰心的散文、小说与诗歌都是深蓝的太空里闪烁着的晨星。作为诗人的冰心,以“小诗”闻名于世。被誉为“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叙及冰心时说:
直到冰心的《春水》出版后,新诗界才发现了一颗明星,无论怎样写去,都觉着美妙自然,曾博得千万读者的赞叹……造成了所谓“小诗的流行的时代”。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小诗”这个名词与冰心紧密相连。谈到“小诗”,就会让人想起冰心,自然不能不提及她的《春水》与《繁星》。冰心以一人之力造成了一个“小诗的流行的时代”,凡稍微了解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人都不会否认冰心小诗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何为“小诗”?周作人在《论小诗》中说:“所谓小诗,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认为小诗最适宜表现人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情之深切热烈者适合创作长篇巨制,感情真实却又不那么迫切的就适合创作“小诗”。短小的诗篇对应的是细微的感觉。冰心的《繁星》与《春水》,表现的自然都是刹那的“感觉之心”,篇幅大都比较短小。刹那而不是持续时间较长的感觉,自然可以视为不那么深切热烈,故而可以称之为“小”。与模糊难辨的感觉上的大小相比,从篇幅的短小界定“小诗”似乎问题更多。就《繁星》与《春水》而言,所收诗篇并不都是周作人说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繁星》所收诗篇共164首,其中4行以内的诗篇共108首,大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的诗篇至少都有5个诗行,第92首长达15行。在诗集《春水》中,诗行最多的第五首共有18个诗行。十几行的诗还能算是“小诗”吗?从行数来界定“小诗”,其实有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周作人限定“一行至四行”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最多是“四行”,“四行”与“五行”的篇幅有本质上的差异吗?如果说这种认知来自约定俗成,那么奠定这种认知的基点都有哪些?第二,按照周作人的“小诗”观,《繁星》与《春水》中数量不菲的五行以上的诗篇是不是“小诗”?第三,诗行的多少与篇幅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共七个诗行用字过百(还有18个标点符号),冰心的《繁星·134》全诗也是七个诗行,却只用了35个字7个标点符号。同样都是七个诗行,冰心的诗就给人“小”的感觉,这“小”就具体表现为短小的诗行、简单的节奏。总而言之,“小诗”的提出及概念界定,自有其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理论与实践、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周作人围绕着“小”来谈“小诗”,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里“古已有之”的传统,强调了“小”的价值和意义。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他讲冰心的诗歌创作时却偏偏强调其“小诗”之“大”,而且将冰心和郭沫若两个人的新诗创作进行了对比:
奇怪,在《冰心诗集》里的诗像比《沫若诗集》里的诗都更厉害一点。郭沫若氏《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诗里极力说“啊啊!力哟!力哟!”他只不过如诗人自己所说是力的诗歌,力的舞蹈,所以“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冰心女士一些豪放的诗作却更是夸大。
废名觉得无限的太平洋把地球推倒,无非就是让地球上又来了一个“洪水时代”,但是冰心《春水·101》说到“地球粉碎的那一日”,给人的感觉却是“不知成何景象”。废名揭示了冰心“小诗”创作里蕴涵着的大气魄,而且这“大”的结论是与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的比较中得出来的,这种比较意义上的“大”确证的不是相对的“大”,而是一种绝对的“大”,废名想要告诉人们的便是现代中国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中含有一种真正的大气魄。
废名认为冰心和郭沫若两位诗人的“新诗恰是表现着第二期新诗特别之处”,讲述两位诗人的新诗创作时总忍不住反复进行对比:讲冰心的诗时,先讲的却是郭沫若的新诗创作,讲到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时,又用了大量的篇幅谈冰心的诗。废名讲述两位诗人的方式,也为后来的学者们所接受。陆耀东在《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中叙及冰心,也是开篇就将冰心与郭沫若对照着进行叙述:
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时代革命精神似“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泻千里,汹涌澎湃,在中国诗史上,曾是半夜荒鸡,起了开一代诗风的作用;那么,冰心的诗,就像是涓涓细流,是时代洪波激起的涟漪。
与废名突出“小诗”之“大”不同,陆耀东强调的是“小诗”之“小”,认为小诗“很难充分表现时代的滚滚洪流,思想的浩瀚海洋。在中国的小诗中,至少还找不到表现宏伟气势的典型特征”。郭沫若的“大”诗与冰心的“小”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陆耀东也是在比较中叙述了冰心和郭沫若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但是对“大”与“小”的具体剖析和所得出的结论,与废名大相径庭。
如何理解冰心和郭沫若两位诗人诗歌创作的“大”与“小”,废名和陆耀东可以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角度,但是在本质上两个人的理解又有相通之处。在陆耀东看来,郭沫若诗表现的是“时代洪波”,而“时代洪波”才是“五四”的“时代革命精神”的真正代表,这自然是“大”;冰心诗表现的则是“时代洪波激起的涟漪”,“就像是涓涓细流”,“涟漪”与“细流”与“时代洪波”相比自然就是“小”。通过这种区分,陆耀东凸显了郭沫若新诗创作的时代精神,吻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女神》文学史书写经典化的内在要求。废名并不否认郭沫若的“大”與冰心的“小”,但是却别出心裁地对两位诗人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大”与“小”做了辩证分析。在废名看来,在冰心的“小”中,蕴涵着“大”气魄。虽然废名将郭沫若和冰心两个人的诗歌创作都视为了“五四”精神的代表,但是废名并没有将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视为“五四”精神的不同表现。在废名看来,郭沫若的“大”与冰心的“小”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本质上都表现出一种大气魄,而这种大气魄才是真正的“五四”时代精神,这也是废名阐释冰心“小诗”创作中“大”的根源所在。就“五四”时代精神之“大”的肯定与阐释而言,陆耀东与废名并无根本性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