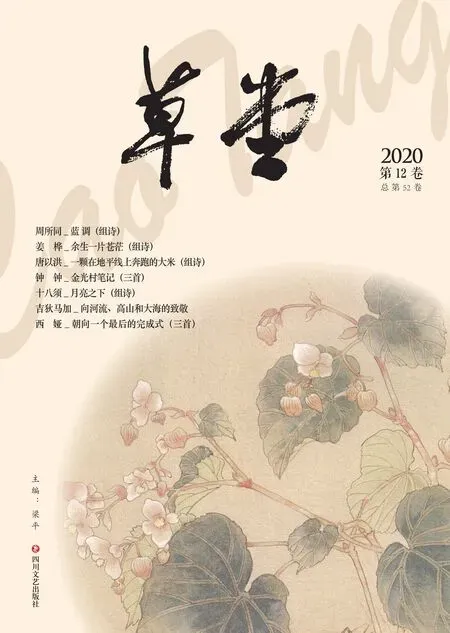约翰·阿什贝利晚期诗选
◎[美]约翰·阿什贝利 /诗 [中国] 少况/译
[松松散散]
亲爱的鬼魂,在正午人群中
什么样的居所?我要写
一个小时,然后阅读
别人已经写好的。
你没有豪宅让这个在里面发生。
但你的历险如同藏身处,
你知道在何处停下另一种
秩序的历险,像把握住天气。
我们也被卷入发生的这一幕,
当我们一起说同样的短语:
“我们曾有过那些中的一个”
它像瞎蒙一样重要。
我们中的一个留在后面。
我们中的一个在桥上向前
像踩在地毯上。生活——它精彩——
紧跟着,然后落后了。
[还有遗忘]
我上次看见你,匆匆忙忙回来取东西时,
我们穿着卷尺,孩子们可以去看电影。
我浮现在那个背景里。老头不可思议地看着大海。
总是脚来敲门,
不是那个时,便是某个东西或别的
忧郁。总是会有人觉得你恶心。
我喜欢用醉人的美味让你
脱离大部分兴趣,我们
相互交谈。以前起作用,这次
也会起作用。
在七号寻找那个奇怪的号码。你知道
我需要一个理由再乘船
下海。一个人如何做到这个?老头
看海回来,他的回答轻率。
不管是不是橡皮蛇,我最珍贵的倒挂金钟
在鱼缸里狂吐唾沫,所有的肩膀同时
开始支撑我。我们在一个客栈里旅行。
你要把一个苹果设计成什么样?
然后酒店的人们如此喜欢我们,
有可能是在一场暴风雨之前,我向后靠,
等风来吹我,它来了,一件我们
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湖畔栏杆
旁边吃饭。某种东西不是赢得就是将
失去藏在这个箱子里的证据。
到处是鸻鸟——把那个变成“恋人们”,毕竟
他们获得了法科和医科的学位,没人会坚持
在外景地追逐它们,那铺着沙子的路
我曾经在这里穿过。
这些日子,老头经常和我不谋而合;他说话
有点俏皮,妙趣横生,虽然它们不能
自圆其说。而我,我也有事情瞒着他:
一些没人应该知道的事情。
我肯定他们会以为我们现在准备好了。
我们没有,你知道。一个冰箱曾经在这里生长。
把唠叨给我,我会在盘子里装满曲奇,
因为它们可以,它们必须,传递。
[另一个例子]
我们的例子中,地球,
我们知道星形的宇宙:
区分,
某处,
七月街道的。
你是坐在一个桶里面还是上面?
他们如何带我们过了栅栏。
那唯一的马遭到羞辱。
但它是不健康的,你说。
我们必须另有一个例子,
只要一个。
缺少的是窗户里的面孔,
很久以前消失的尖叫。
什么说要召回它们?
像纸蚂蚁那样被救活,
然后忍受永恒前漫长的真空,
仍然被允许在月台上
买些东西?
火车在掉头离开——
没有熟悉的引文。
来,把一些放在一个盘子里,他说。就是这样。
[一个人的诗]
约翰夜里进了城,
钟声敲响。
该死的船漏水。那么,我……
这很不寻常。
别介意,把那个碍眼的递给我。
他来见一个裁缝。
更多的我在运河上
并在知晓。
双胞胎拖拽着葡萄干和李子,
我的狗节奏,因为只要我们能忘记,
靠午夜破碎的鼓,
聚到一起,有了意义。
还要四处走走,聊聊。
然后都钻进了一辆小汽车,开走了。
它的尾巴是银红色的。
班卓琴在车里直立着。
一阵阵大一和大二的悲伤
不知何故从我身旁溜走。
我们现在老掉牙了,
完全搞不懂我们的生活。
它是在他说给我听的方式中,
在田地的中心,泥泞的
或在岩石上,让我们羞愧。
不仅仅是精神刺激,
在小空心下面,鸟儿爬行,
被请求给予宽恕。一些担心
它们会飞走。
到早晨,全被射入地狱。
[虚假礼貌的花园]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是我唯一爱的事情,
而它总是避开我,像叶子中的丁香花,
太忙碌于仅仅一个回答,一个反驳。
上次我看见你是我们在一起的开始,随着白天的光线
保持不变,即使它们越来越短,
套上冬天的玩具。
在望着油漆晾干和青草生长之间,
我没有太悲惨的事情跟随着。
我有这个融化的灵丹妙药给你,大家
都去的音乐会第一排的票。
我应该
磨炼我的风格,擦亮我的皮肤,获得那种
至关重要的光芒,以便一些人
可以听见我在说什么,而其他人消失
在含糊不清的录音通知的一片混乱中。
那天发生了许多事情,
另外,不是纳税人,
他们是重要的,过来找我,
而是酒店的其他客人,
有人可以描述为陈旧,
中了风。少得可怜是一个不错的词用来描述
潮水在涌来和退下之间的流动,
如同谁在什么狭窄水道以后将
永远记住那些时候热切的观看,
犒赏和快乐。
马上是滑向大海,
极其自然地,作为该去的地方。
他们从未在意,再没来拜访。
但在大损失的帐篷里,
它也没关系。另外,我们不是
认真的,我应该补充道。
[眠村]
呃,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染了------
我想要无限期地留在这里吗?
我们有树木要修剪,密码要破译,
整个就是盲目地跑进夜——
她无法说出“鱼”这个字。痴呆的潜水艇
所残留的也取消不了他的基因。是的,阁下,
尼莫船长,阁下,我们已经看见了路前方的
垃圾。什么!我为自己消遣创造的那个痉挛,现在
它清楚地从裹着它的章鱼唾液中冒出来,
而我,一条地区铁路下方的支线,被怀疑持续时间的
咔嚓咔嚓声碾压,而我必须在这里立着,
一个表面的谜。外面,生活继续唠叨个欢,
像绣花的毛巾,也许会太虚弱,无法反对,
如果我们决定将野餐推迟到十一月。
我知道;路堤下方的拱门
是我所做的一部分。我也被断了挥霍无度的路,
在某个银色的年代,它目前已经迷失在信封的暴风雪里。
马具上的铃铛发出多么冷漠的声音!
我们只能做这些,去跟上傻瓜的脚踏车。
而在采石场的中立角落,
历史相同的作乐在把男人们的眼睛哄骗
进顽固的迷信。所以我们必须拿它开玩笑,
趁还有时间,收线,捞起我们捕获的,但微滴
在排水沟里爆炸。赌船带我们摆渡离开,
路过飞燕草,路过六角手风琴,再次看见了旧名字,
短暂地,在楼房布满尘土的门脸上。我
以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你。没有,
我还在这里。
你想跳出一扇害羞的窗户吗?
渐渐地,一个人听懂了狐狸的恸哭:
没事,它冷静,
它们哈哈大笑。这只是一种植物,
它仅仅在下一次作数,
而我们戴着头部护目镜,穿着亮丽的吊袜带……我体内的
派对怪兽说让我们放肆,更冷静的头脑说跳水,
像一个青蛙跳水,当著名的夜晚快到来,
像一声叹息起泡的外表。
[乳白天空]
越来越明显地,教练员不会用他的,或我们的
方式处理事情——用一切曾经多么可爱难倒了我。
我们稳稳地站成一圈,
某个惊叹号盛开凋谢。
那头奶牛走过来,为亚麻
请求我们原谅。然后每个人都进入正典,
更多的船失踪了,更多的人在海上,一车猫眼石
从安纳托利亚带来霉运。洗一下,
就没了。不必再收拾房间,
袜子。
幸运的是,有一个裁判确保
行为编了码,一切都筛进火车
从不在意的网里,天边还有乐趣。
蓝调——我们有没有提起过?
那能量来阉割火星上的一切,除了没有生命之物,
那被接纳的,抓紧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