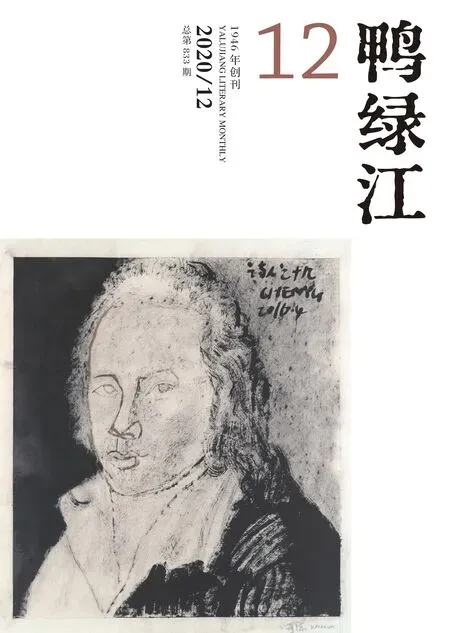向我开炮!(组诗)
李 皓
上甘岭
小时候的黑白影片,再恰切不过了
190 余万发炮弹,5000 余枚炸弹
劫掠过的山头,除了黑乎乎的血
冒着黑烟的焦土,粉碎的石头
变成炭灰的树木枯枝,熏黑的弹壳
乌青的脸,露出破洞的军装
好像除了雪地一样白的牙齿,乌黑一片
除了红色的军旗,到哪里寻找彩色
就连从黄继光后背,与机枪子弹
一起喷出来的,都是黑血
噢,王万成和朱有光他们的爆破筒
在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一刹那
确实发出了一团火红的光
但迅疾又变成一缕缕青烟
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一手抓起
一头断线,用自己的身体
接通了线路的时候,我也没看到光
电流在他的身体里走动了三分钟
副团长的命令穿过他的身体
他依然是黑白的。他把光拽进血管里
直到把两座高地拽进了史诗
一座597.9 高地,一座537.7 高地
当山头被硬生生削低两米
范弗里特的“摊牌行动”打了谁的脸
而倔强的秦基伟迫使美国人
灰头土脸地退兵。当兵那些年
每当听到空降兵十五军的名字
我都肃然起敬,郑重地把右手抬到眉间
我写这首诗恰是2020 年11 月25 日的深夜,离上甘岭战役胜利
已经过去了整整68 年。想起那
数以万计的志愿军的生命,我突然想哭
我何时能写出两米高的诗行,然后
在今夜焚烧,让那些化成泥土的英魂复活
让坑道复活,让金达莱复活
哦,上甘岭
为了正义,为了国威,为了友谊
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罗盛教
零下20 摄氏度的冰河,或者叫冰窟
根本没有吓倒志愿军第47 军141 师
侦察队文书罗盛教
或者罗盛教根本就把栎沼河
当作了联合国军的队伍
他疯狂地扑了上去,在刺骨的
河水中摸索,寻找,呼唤
用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传达指令
崔莹,你要活着
跟死神较劲,那是我的事情
拉锯,一次又一次
冰面,差一点做了死神的帮凶
在志愿军战士面前
死神只能妥协,只能乖乖地
把崔莹送回温暖的人间
而死神并没放过耗尽力气的罗盛教
当他倒下,最终成为一条永不
干涸的河流,严冬里的国际主义
让友谊拧成带血的纽带
系着石田里,系着呜咽的栎沼河
邱少云
你是个一诺千金的人
潜伏之前
你刚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宁愿自己牺牲,决不暴露目标,
为了整体,为了胜利,
为了中朝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我必须原原本本,把这段话
放进我的诗行。我必须说
至今,我还没有一行诗
可与这段誓言,媲美
你在申请书里说了
你在战场上就不想重复了
你像个哑巴一样面对熊熊的火焰
直到生命终止,你再没吐出一个字
你是不是把那些字都咬碎了
你是不是把那些字
都死死地摁进了泥土里面
不让它们发出一点声响
今天,我允许你说一声:疼——
我允许二十六岁的你
对着五十岁的我大喊大叫,甚至大骂
邱少云,给我一些疼好吗?
鸭绿江断桥
美国人不懂中国哲学
打断了骨头
筋仍然还连着呢
况且你能把滔滔鸭绿江水
炸断吗
水,是另一种桥
一衣带水是个美妙无比的词
当大鼻子美国人浑水摸鱼的时候
我们和对岸已情同手足
断桥是我们伸出的手
能拉你一把的时候
我们绝不缩回
有些人跨过断桥,就再也
没有回来。三千里江山
处处,都埋着志愿军的忠骨
两岸鸡犬相闻,鸭绿江的流水
却从来不发出一点声音
许是怕惊动或惊醒一些什么
即使偶有风吹草动
那雄赳赳的脚步声还是压过了水声
军用胶鞋与钢铁的互动堪称完美
桥短了一截,脚印还在
钢铁也许会锈蚀,但
爱有爱的源头,恨有恨的决绝
“两洲三国”胡琴
罐头盒子是美国的
当然不是美国主动给的
而是志愿军拼了性命
缴获的
马尾是中国的。这马
是给志愿军补给的马车
驾辕的马
还是一匹功勋卓著的战马?
木材显然是朝鲜的
善于就地取材的志愿军战士
从上甘岭尚未烧焦的树枝
截取了这具有音乐天赋的一段
马尾与罐头盒子的摩擦
是毛发与钢铁的较量
钢铁发出了欢快的叫声
哆——来——咪——发——唆——啦——西
坑道里那些几乎被炮弹
震聋的耳朵,此刻
长出了舞蹈的小脚,痒痒的
那是家乡小调的步伐
伤口柔软起来,那一颗颗
绷紧的心柔软起来
那唯一的苹果的芳香,甜汁,光芒
与一支跑调的琴声拥抱
像那些受伤的躯干互相搀扶
这把胡琴有着三千里江山
最硬的骨头,用一根又一根马尾
与坚船利炮针锋相对
他们哀号着退却,再不敢回头
他们丢盔弃甲,也丢下了交响曲
一般悲怆的命运。三八线皎洁的月色
总是掠过一阵阵大雁的哀鸣
大雪节气题丹东火车站毛泽东雕像
十二月的寒风
掀不动你大衣的衣角
衣领一尘不染
你的右手挥起来
就没有落下,袖口
极其动感
你不说话,所有的话
都在语录里
你指着远方,大雪
一夜间就覆盖了鸭绿江
那些不敢涌动的暗流
一年又一年
眼看着大树叶落纷纷
纸老虎蠢蠢欲动
蚍蜉总是贼心不死
却不敢妄议当年
锦江山
鸟儿都飞走了
把叩门的声音,踮得
更加空洞,悠远
一枚硕大的红叶
阻断我望向窗外的视线
我不知道
江水是不是像大海一样
涨潮
有些美留在途中
江山之美不在峰值
山间的日月
比你及腰的长发
还长
当秋叶和阳光
一齐垂到你我身上
我的江山
便愈加锦绣
战争都偃旗息鼓了
锦江山却怎么也
无法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