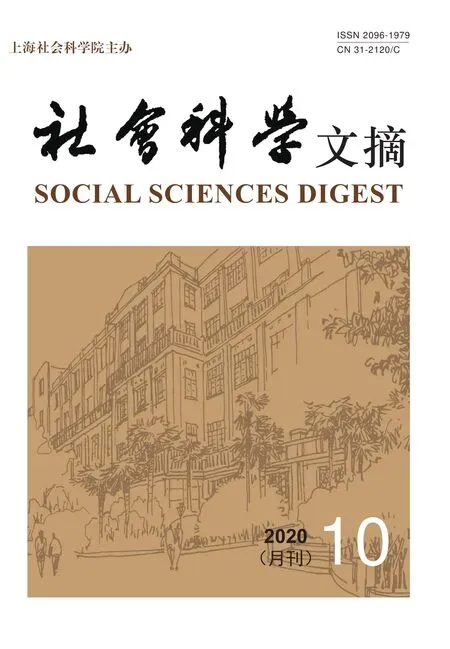理论视镜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未来走向
——与周雪光先生商榷
文/姚选民
在研读周雪光代表作《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的过程中,笔者察觉到一种可称之为“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文本作者经由对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揭示,不仅有力回应了一系列重大课题,而且蕴含着一种具有一定价值意蕴的主体逻辑结论:晚清以降180多年来国家治理转型(或现代化)的探索实践表明,中国为应对晚清以来国内外环境情势大变局,在其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摸索出了契合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文本作者在研究的逻辑“收尾处”却突兀地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未来走向(或现代化转型)要“另谋出路”,“从根本上解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另辟蹊径”。这与其主体逻辑存在悖论,笔者拟称之为“周雪光悖论”。
“周雪光悖论”:一种理论化之问题处理
一方面,经由其研究,文本作者让人对晚清以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期待。“为什么中华文明长期延续而未遭遇像其他帝国一样衰亡的命运?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辽远广阔的国土、多元文化同时又是中央集权的政体可以长时期地生存下去?为什么中国社会经历了历史上的停顿、低迷徘徊,在今天能够出现经济上的大发展?”文本作者从两大层面回应了其问题。一者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先秦特别是秦汉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机制:一统国家体制和有效国家治理之间的矛盾。中国国家治理机制的典型气质或根本表征是一统国家体制,该体制仰赖两个主要维系因素,一个是科层体制,另一个是一统观念。先秦特别是秦汉以来国家治理制度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演化出了一系列具体治理机制来应合其主要矛盾机制。另者从中微观层面,在阐述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演进之“变”与“不变”过程中,揭示出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各层级机制或制度的生成逻辑。在应对晚清以降国内外情势之大变局的过程中,除开其他具体治理机制或制度,国家正式制度所衍生之最为重要的核心治理机制或制度是执政党的卡理斯玛权威常规化。
文本作者的研究表明,在应对晚清以降180多年来国内外情势剧变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基本实现了其现代化历史转型过程,而其目前的迫切使命业已转变为了如何再进一步完善这一套国家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在研究之逻辑“收尾处”,文本作者却突兀地让人觉得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成就的取得似乎是“暂时性的”,仍需要“釜底抽薪般”大转型。文本作者没有遵从研究的主体逻辑,反而得出了让人惊讶的结论。并且格外强调,在应对一脉相承之国家治理主要矛盾机制的问题上,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体治理机制或制度生成的适变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文本作者之所以会导出该结论,主要在于他研究之主体逻辑中的次级逻辑,而该次级逻辑尤其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一统国家体制与有效国家治理这一主要矛盾机制的“不可调和”面相:其一,一统国家体制的“负荷太重”;其二,一统国家体制严重牺牲效率;其三,一统国家体制难以朝所谓当今世界“通行”甚或现代西方世界的“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方向发展。
直观来看,文本作者对支撑次级逻辑的这些理由相较于文本中支撑主体逻辑的基干理由,舍本逐末,以次级逻辑替代或消解了主体逻辑,出现了前述的“周雪光悖论”。
“周雪光悖论”出现的原因分析:韦伯“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理论视镜之价值底蕴
“周雪光悖论”的出现跟其所采用的核心理论分析工具即韦伯的“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这一理论视镜有关。这一理论分析工具似乎是价值无涉的。文本作者在运用韦伯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不自觉受该理论分析工具本身之学理逻辑及其所承载之价值逻辑的支配。韦伯提出了他关于权威的“理想类型”分类学,即传统权威、卡理斯玛权威和法理权威。如果“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这一理论视镜真是“价值无涉”的话,那么,文本作者会很自然地认为,“国家治理模式不是任意选择的,常常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过程有着深刻关系,有明显的途径依赖性”,加之晚清以降180多年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功转型事实,那么,文本作者研究中的主体逻辑结论应该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其特定时空的合法性,应是向着目前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这一基础之上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而不是朝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即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转型。
若不对韦伯这一理论视镜的价值底蕴进行有意识的反思,且接受该理论分析工具中的价值逻辑,那么,文本作者就会形成其目前的结论,自然会产生当前这种矛盾或“悖论”。一者,韦伯的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其实是蕴含着价值逻辑的,韦伯关于权威的“理想类型”分类学,并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类型分类学。在韦伯看来,传统权威和卡理斯玛权威在现代世界的存在是“暂时性的”,都要向着法理权威转型,法理权威是其他两种权威形态发展的最终归宿。韦伯的“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理论旨在突显法理权威的合法性,其他两种权威是为此意旨才被建构出来的,并且缘于现代西方世界奠基于法理秩序或“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而产生的世界性成就,其他之传统权威和卡理斯玛权威这两种权威类型在此映衬下更是在事实上“没有存在合法性”。另者,从文本作者对韦伯的征引来看,韦伯所言的“官僚制”才真正配得上人世间唯一真正具有合法性的权威类型即法理权威。似乎只有西方时空中的“官僚制”才是真正的科层制,可以成为现代“普适”民主宪制的基础,而其他类型社会中的科层制被罔顾事实地宣称为韦伯所言之“官僚制”为适应其他权威类型及其支配形式而产生的殊相。韦伯式“官僚制”结构的法理权威(或“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才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的国家治理为适应现代文明冲击这一国内外情势大变局而转型(或现代化)的未来基本走向。
基于这种带有极强价值底蕴的逻辑大前提,加之文本作者所揭示之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中所存在的种种或大或小的“问题”,目前结论便能够很自然地被导出:要想有效解决目前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一统国家体制与有效国家治理之间的主要矛盾,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以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构建为“基本走向”。然而上述分析表明,文本作者的这种逻辑推论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基本走向:以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基本走向为参照
不自觉受韦伯“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理论分析工具中价值逻辑支配,文本作者得出了其研究中似是而非之“预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未来走向”。
一方面,现代西方社会所追求的“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一种具有内在“普适性”的善治秩序状态。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表明,人类社会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多元文明间的分野,其中基督宗教世界或伊斯兰教世界里的美好秩序是上帝秩序或真主秩序,佛教世界里的美好秩序是“自然”秩序,而在中华文化圈里的美好秩序则是“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
作者文本中的法理权威或“法治”形态主要指涉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所逐渐形成之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法理秩序或“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这种法理秩序或“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主要是指欧洲中世纪基督宗教世界之上帝秩序的“古典化”或古希腊罗马化。
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宗教统治时期,作为上帝指示之化身的教义经典,《圣经》不仅是人们外在行为的规范,而且是人们内在精神思想的法则。正是现代西方社会的这种社会发展历程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秩序思维方式或思维结构。在西方中世纪,作为跟上帝“达成”的契约,《圣经》在社会运转和运行的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在文艺复兴运动甚或“上帝死了”之后,社会成员特别其中的政治精英基于自身意愿所达成的政治契约——现代之法或法律——在人们的秩序思维结构中亦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中世纪基督宗教统治对现代西方人之秩序思维结构的养成及其一脉相承,加之文艺复兴运动中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法律文化元素的汲取、借鉴或继承,造就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形态——法理秩序或“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
另一方面,不同的文明或文化有不同“法治”形态,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法治”建设有其特定内涵。
当前中国社会中主流的“法治”说法,是“依法治国”这一表达的缩写,甚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表达的缩写。“法治”概念的权威定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该权威定义直观来看中国社会的“法治”形态,显然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形态,而是“治国”秩序或“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
一者,重提“国治”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概念表达,并将“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作为中华文化语境下人类社会之善治秩序的重要表现形态,是因为中华民族自人类“轴心时代”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关于美好生活或美好秩序状态的想象。“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达成的基本条件,是国家或社会内部大部分人“身修”,以及大部分家庭“家齐”等情况的普遍实现。反观先秦以来的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特别是晚清以降180多年来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转型或现代化,“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仍是中华民族所追求之美好生活或美好秩序的硬核内容要素。“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概念在新时代亦增附了新时代条件下的意蕴内涵,其中作为其核心内容之新时代的“身修”,自然增附了如“公民道德”等意蕴内涵;作为其核心内容之新时代的“家齐”,自然添附了如“小康家庭”等意蕴内涵;等等。
另者,在历史上,在追求“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的过程中,处于同时期即先秦时期“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法家“法治”思想成为了秦汉时期中国主流政治精英实现其国家善治秩序状态目标的有效途径,并发展成为“治国”或“依法治国”法律文化历史传统。一如前述,“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作为人类社会之善治秩序状态的重要表现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中华民族所追求和向往的善治秩序状态,那么,中国实现“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的有效“治国”或“依法治国”途径,很大程度上在晚清以降180多年来中国之治国理政的问题上仍是一脉相承的。相较于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形态即法理秩序或“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中国社会在其特定时空中形成了相对独特的“法治”形态即“治国”秩序或“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
当然,“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在晚清以降180多年来的国家治理转型(或现代化)过程中增添了一些新的秩序要素,如社会主义政治秩序要素,那么,今天我们实现该种“法治”价值的有效“法治”样式,亦即“治国”秩序方式亦会增添一些新的法律文化元素,如现代西方社会的法理秩序要素,亦即中国“法治”样式会受现代西方社会“法治”形态之“法治”样式的某些影响。
故此,切不可以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就是我们想要的美好生活或美好秩序,亦切不可以为中国的“法治”形态跟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形态完全一样。一如前述,中华民族有自己追求的美好生活或美好秩序,也就是人类“轴心时代”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所形成的“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我们亦有自己追求或实现“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的“法治”样式,也就是“依法治国”的方式。缘于时代变迁,它们都内附了新增之现代性内涵,而在现时代均有新的表现形态。其中,前者作为中国“法治”形态之“法治”价值部分,在当前新时代就集中表现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善治秩序状态;后者作为中国“法治”形态之“法治”样式部分,在当前新时代则集中表现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因此,相较于现代西方社会对“法治”这一至善法理秩序状态的“法治”价值追求,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对其美好生活或美好秩序的追求,亦即旨在实现对“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的“法治”价值追求。
再议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未来走向
那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转型(或现代化)要向何处去?“当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遵循晚清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第一阶段(即晚清鸦片战争以降到改革开放中国崛起势头初现这一时段)的基本走向,另一方面要根据当下中国国内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新情况,做出相应的走向调整。”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转型(或现代化)应在如前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基本走向上继续向“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迈进。
从中华文明所追求之“国治”(内含“天下平”内容)这一至善“治国”秩序状态来看,中国国家治理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条件下转型(或现代化)所面临的任务,显然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事情,其所置于其间之“天下”亦当要纳入其追求善治秩序的思考范围。在晚清以降之近现代时期,中国国家治理在转型的过程中面对国内外变化情势,只能着力追求做好一个内含天下格局的国家。然世易时移,当今中国业已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阶段,正式进入了“强起来”之发展阶段,基于中华文明自人类“轴心时代”伊始被逐渐赋予的基因血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就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容构成“质的飞跃”之重要表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走向包括全球治理取向内容,不仅有其理论上的必然性,而且有其现实上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