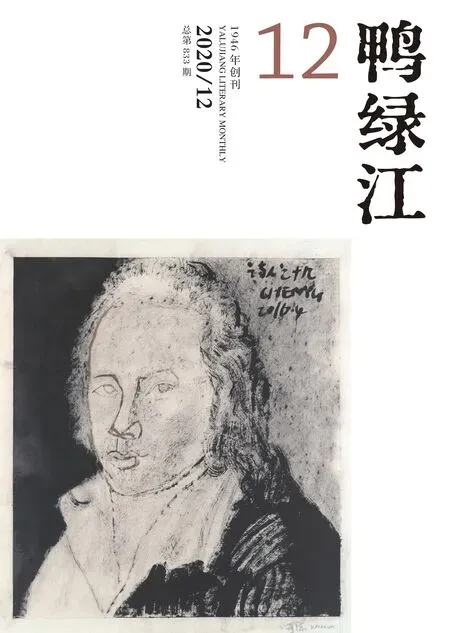青年的路和青年的雾(对谈)
——从范俊呈的《白鸟》说起
陈培浩 王威廉 范俊呈
1
陈培浩:本期我们从青年作家范俊呈的短篇小说《白鸟》说起。我如果不说读者不会知道,这是一篇有多个版本,甚至几乎难产的小说。当我看到第一个版本时,其实有点惊喜。认识俊呈有好几年的时间,俊呈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却因为写诗跟我认识。大学时代,俊呈的诗就频频在《诗刊》《诗选刊》等诗歌杂志露面。无疑,他是具有相当语言天分的。而且,俊呈似乎很早就确立了要当作家的理想。写诗之余,他也开始悄悄操练起小说。不过,在我看来,他大学写的那些小说还不具备“小说性”,很容易就发现这是一个具有良好语言感觉者进行的稚嫩小说练习。不过,看到《白鸟》的初版本,我感到俊呈的语言才华没有丢,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懂得写出好的小说语言,而不是将好的诗歌语言放在小说中,他懂得怎样去叙事,甚至,他叙事的语调还颇为从容老练。所以,在谈发表这个版本的《白鸟》时,我想请俊呈先来详细谈谈这篇小说修改的几个版本和你的想法,不同版本你分别有什么样的寄托?
范俊呈:老师说到天分,对我而言,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毫无天分的人来写作。天分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可以信任的是日复一日投身其中的劳作。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笨拙而谦卑地写,不要忘记自己是小说的学徒,小说的门户并不会为我打开,甚至并不需要我,只是我需要小说,只有长远地坚持去写,才有可能去推这扇门。关于语言,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最直观的就是语言的感受,词与词碰撞的声响,句子间节奏的律动,这种悦耳动听的乐感一直使我着迷。说回这篇小说,小说的原名是《你所处之地不曾有人抵达》,一对夫妻在结婚十几年后,妻子在丈夫的魔法下,进入了一部电影,成为电影里的人物,随着电影的结束,妻子并没有返回来,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培浩老师建议我修改时,我觉得小说里面“我”和女主角在海上的分别可以提升为小说的主题,于是想到了鸟的意象,就把之前的叙述拦腰斩断,重新发展后面的情节,将小说名改为《白鸟》。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主要是想通过不同的取径,看能不能发展出新的可能性。
陈培浩:在最初看《白鸟》时,我给你提的建议是:小说在以老练甚至是有个性的语言讲述一个故事时,小说里面所有人物,不管着墨多少,他们的性格和命运逻辑必须个体成立,整体合拍;而且在故事的背后,最后能开一扇窗,能通往生活或生命更辽阔幽深处。事实上,在你反反复复修改出多个版本的过程中,我既感动于你所说的“既然选择了小说,每一篇就都应该全力以赴”,但又觉得你有时没有分清路和雾。明明脚下有一条可以走向清晰的路,但你却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浓雾中。但我也警惕我这种感受的“侵略性”,所以你是否也反过来回看这个过程?经过这次反复修改,你对小说的艺术是否有了新的认识?这次修改,对你来说,有了哪些收获和教训?
范俊呈:到目前我写的小说,包括这篇,在写出来之前,我自己并不知道最终完成后的形态。我之前的写作习惯,有时只是脑海里出现一句话,有时是一个词语,有时是一个标题,甚至是茫茫黑夜漫游,什么都没有,就是打开空白文档,接下来就交给音乐了。我的每篇小说都是伴随着音乐写出来的。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心流状态”,说创作者忽略了时间的流动,将全部精力投注在创作上,音乐会使我进入这种状态。其实我不懂音乐,甚至从音乐演变而来的文学术语“复调”之类的,我听音乐时都不容易察觉出来,但是音乐会使我投入到思考正在写的东西上面来。说到修改,我以前的一篇小说也修改好几遍,直到我觉得完成到自己现有能力的极限了,但之前我每次修改只改一遍,放下它以后会想接下来怎么改,有时候不经意地就有了方向,然后再去修改,这样进行到四五遍。这次我是集中地一天中反复修改,反复读句子,可能读到形成记忆了,有了一种定式的思维,就难以打破原有的东西。这次修改有很大收获,中间几经动摇,在没有明晰具体脉络时就急于删改,导致重蹈覆辙,过于着急了,其实慢下来才能精细。
陈培浩:《白鸟》第三个版本中,吴沛东找到“我”,告之将不久于人世的事情,并将方子佳托付于“我”。“我”和方子佳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做起爱来。这个设置让我觉得特别费解,倒不是用道德眼光去评价人物的行为,只是这种行为无疑是违反普通人的伦理感觉的。小说当然可以写非常之人非常之事,但小说家也有义务去解释这种“非常”,当小说使“非常”获得可理解性,小说同时也就获得了内涵。但我似乎没有看到你试图去解释这种“非常”,一个朋友也看了这个版本,她的意见很特别,我说这篇小说体现了当下青年写作的某种症候性,她同意这个判断,但对体现了何种“症候”却有不同看法。她认为这篇小说试图去书写一种当代青年在性上的无所谓、无负担的状态,不是小说家没有处理好,这恰恰是小说的价值。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小说当然可以去彰显这个朋友所说的那种性的无所谓,但我想在那个版本中作者并无此意,写的反而是多年之后寻找“初恋”和“托付”。我的意思是,小说家必须有相当的自觉性,假如想往一个方向去,就要更有效地让小说内部呈现出一条道路,小说的叙事元素之间应该具有更强的有机性。
范俊呈:我写的过程中没有察觉,就是语言推动着语言往下写,崇正老师看过后跟我讲了,我重新去读才恍然大悟,确实是我疏忽了,修改那篇的话我会把它改掉。小说要大胆地想象,小心地求证,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其实也在塑造自己,应该细心和虔诚。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影响别人,可能就在于他的价值观,我后面读也有点颠覆自己的价值观,应该自省。
陈培浩:本期讨论《白鸟》,倒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理想的文本,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症候性的青年作家文本。我以为这种症候性既是艺术上也是思想上的。就内容上说,我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刚从大学毕业没几年,本应青春勃发的青年作家,范俊呈何以选择借由一个身处中年危机的中年人视角去感受世界?事实上在我看来,可能不仅范俊呈本人如此,这种“未老先衰”的青年,跟这个时代“丧”的青年亚文化不正相一致吗?在艺术上,当下青年作家往往精于自我感觉世界的呈现却拙于与现实短兵相接的及物性经验,所以写作上看似有现实,其实没有扎实的经验,所以就玩起了某种“象征装置”。这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威廉,你对《白鸟》有什么观察?
王威廉:范俊呈的短篇小说《白鸟》在我看来是一篇有意思的小说。因为俊呈这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印象不错,还算比较熟悉。所以,从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他的生活和他的小说之间的同构关系,以及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奇妙关系。当然,往大里说,还涉及作家的传记与作家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更大话题。他是学计算机出身的,目前在出版社工作,在这篇小说中,男主人公是学计算机的,他的妻子是在出版社工作,这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身上的两种经验具体化为了人物,并且还变成了一种不能分割的婚姻关系。不妨说,这也是俊呈的两个自我、两种经验在进行一种对话。俊呈还年轻,他对婚姻生活是没有经验的,但是他想象了婚姻场景中的许多细节,不但是有着某种真实性,而且还想象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瞬间和场景,令人能够品味良久。这些细节分明是他想象的产物,但是在小说文本当中,却也承载了对于艺术空间现实感的营造功能。我对这篇《白鸟》的故事结构还是比较看好的,它有悬念,有细节,有氛围,显示出了他不俗的文学才华。如果非要说不足,短板就在于对于白鸟这个意象的挖掘让人感到有些不满足。可白鸟这个意象,正是这篇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之所在。方子佳为什么要那么绝望?为什么要出走?从小说里来看,还是缺乏个体生命内在动机的探索以及对于外在时代背景的勾连,所以就会让这种动机显得比较虚无。生活中当然有特别个人化的虚无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写作的时候,写小说的时候,还是要赋予这种主题一种普遍性。那么,我想这可能正是俊呈在修改小说的过程中所强化的东西。他改了三个版本,我觉得还是有所进步的,他也在体会着用怎么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去逼近自己所想要表达的主题,让它以情节的方式获得深度。
2
陈培浩:俊呈,你的诗在《诗刊》《诗选刊》《草堂》《诗歌月刊》等刊物发表过,小说在《青年作家》《作品》《南方文学》《广州文艺》《滇池》上发表过,简单谈谈你的写作之路好吗?你小时候生活在云南,大学时来了广东,也在花城出版社实习过,也谈谈生活对你写作的影响如何?
范俊呈:如果从最早的写作说起,初中就开始了,那时的语文老师可能从作文中看出我可以写,她给了我很多书看,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在那时候就看了,四大名著也是那时看的,印象中还有麦尔维尔的《白鲸》,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活着》。上高中后,相继看了余华的很多作品,还有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等作家,几乎高中阶段就在看这些作家的作品。高中时在理科班,也在断断续续地写,但开始投稿是在上大学以后,有了可以交流写作的师友。我是大二开始到花城社实习的,后面来到广州,遇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朋友,无论写作还是处世为人上,都对我颇有教益,他们都在帮助我成长,这段经历对我影响特别大。
陈培浩:很多写诗的人无法完全从诗到小说的转换,你是怎么慢慢摸索到两种文体不同的门道的?诗和小说在你的写作体验中有何不同?
范俊呈:没有刻意去转换,就是自然而然,诗歌还是小说写作,都无规律可循,只有通过不断地写,不断挫败,不断领悟,才懂得怎么写。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但如果把诗歌语言放到小说里,往往会过于浓,浓得化不开。关于小说写作,用帕慕克的话说,小说是第二生活,包含了作者的生命体验,它是融合了虚构和真实的载体。小说和诗歌写作都要突破技艺,也有相通的地方,就像罗伯特·M·波西格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里所说:“在所有关乎技艺方面的工作背后,都有一个类似‘道’或类似于‘禅’的东西,一通百通。”
陈培浩:谈谈你写作的精神资源。在你的写作过程中,哪些作家构成了你的师承或资源?关于这个问题,王小波很坦荡地写了《我的师承》一文来交代,但也有很多作家并不愿意让读者知道他的真正师承,有点遮遮掩掩。对于90 后一代作家的写作资源,我们很有兴趣。
范俊呈:您提到的王小波就是其中一个,王小波对我的影响就是思维的乐趣,小说产生于孤独的时刻,但构思一篇小说,无中生有的过程是美妙的。海明威让我体会到怎么处理对话;契诃夫告诉我,简洁是天才的姐姐;汪曾祺让我知道,写小说就是把一件平淡的事情说得有情致。有时候写作的感召并不直接来自小说,我睡前经常会翻的书是马尔克斯的《活着为了讲述》,村上春树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略萨的《写给青年作家的信》,他们让我明白,只有献身文学如同献身宗教的人,把时间、精力、勤奋投入到文学抱负中去,他才有条件成为真正的作家。
陈培浩:在90 后作家中,你的发表量还可以,可以说是较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你有自己的“小说观”吗?
范俊呈:小说观应该是小说写到一定的量,回头来审视自己的作品才形成的观念,我现在小说的量似乎不足以谈小说观。我觉得自己还在进步,这一时间段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一些看法都会发生改变。倒是可以说说写小说的理由,这个理由和博尔赫斯的理由是一样的: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
陈培浩:最后一个问题,请谈谈你对“青年文学”或者说文学的“青年性”的看法。你认为你这一代的青年作家所表现的青年性跟以前的作家有什么不同?
范俊呈: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成长周期,有人二十几岁就写出杰作了,有人到四十岁,有人到六十岁,无论早晚,都要经过青年的写作阶段。高歌猛进也好,如履薄冰也好,归根结底都是在和自己的内心较劲。青年时对文学的激情是难得的,但当它经历过时光的打磨,我更相信的是迟缓的力量,无论在什么生存状况下,持续而平缓地写作,然后就是不要失去天真。我觉得跨时代地比较作家的青年性是难以比较的,就是在同一代人的青年作家里面,具体到个体,写作的来路和去处都是迥异的。
3
陈培浩:我们这个栏目叫作“新青年·新城市”,主要关注青年作家的城市文学写作,这一期也来集中探讨青年写作的问题。“青年文学”和“文学青年”一体两面,但又有不同的指向,“文学青年”既指热爱文学的青年,也可推而指文学中的青年。文学青年形象充满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画廊。事实上,世界文学史上同样充满了各种类型的青年形象: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少年维特、拜伦的唐·璜、司汤达的于连、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凯鲁亚克的嬉皮青年以及塞林格的霍尔顿·考尔菲德。至于“青年文学”,不仅是青年写的文学,更是关于青年的文学,是追问何为青年的文学。“青年文学”投射着不同时代、民族对于青年的审美想象,又折射着作为精神跋涉主体的作家以“代”出场,又从“代”中逃离,从“代”到“个”的个体探索。文学青年似乎天然地跟性、颓废、反叛、水晶爱以及残酷青春如影随形。可是也未必,如果你看到哈姆雷特对to be or not to be 的冥思,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对超人哲学的实践,你会发现,“青春”不仅是嬉皮士式的性乱和颓废。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青春想象。
王威廉:青年文学和文学青年,这两个提法很有意思。它们之间无疑是有关联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我更感兴趣的。“青年文学”应该指的是青年人写就的文学作品,体现了青年人对于世界的观察力、判断力、想象力等,这种观察与判断未必是成熟的,未必是有效的,未必是深刻的,但是它体现了人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状态,并且经由文学作品把这种转瞬即逝的情感状态保存了下来,成了永恒。“文学青年”,另外一个别称叫“文艺青年”,文艺青年可以写作,也可以不写作,但其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把文艺的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从而与日常生活的逻辑、状态、方式有些格格不入。在有些时代,这种格格不入是一种时尚;在有些时代,这种格格不入会被人所嘲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还好,因为大体上这还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文艺青年只是一种跟别的文化群体一样的存在,他们自有他们的可爱之处。说回文学,文学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每一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利。所以说,文艺青年未必就比非文艺青年在写作上更占优势。当然,如果作品写得多了,沉溺在自己的作品当中,那么青年文学的作者也是有很高的可能性会变成文艺青年的。
陈培浩:我其实特别想跟你探讨的是,你的写作似乎一出场就没有“青春性”这种东西。如果说青春是热血,是情热,你的作品一开始就呈现出冷凝的思辨特征;如果说青春性是经验的不及物性,你的作品在思的同时,也有着在场的现实经验。比如《非法入住》正是基于近二十年来在中国具有极大普遍性的蜗居经验。所以,一种“思的青春”是怎么形成的?
王威廉:可能我比较早就对这种“青春写作”进行了宣泄。在我高一的时候,我就喜欢读鲁迅、郁达夫的文章,喜欢雪莱、拜伦的诗,自己尝试着写了不少诗,还让朋友帮我复印成了小诗集。如果你能看到我那时候的作品,你肯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青春化的写作者。但是上大学之后,我就觉得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抒情性的宣泄,更是一种让人认识这个世界、把握这个世界从而建立个体精神基础的艺术形式,这种对于写作的理解让我不再写那种青春化的作品。而且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好是青春文学全面崛起乃至泛滥的时候,从郁秀的《花季·雨季》到韩寒、郭敬明的全面崛起,那样的文字占领了时代对于“80 后文学”的全部认识,这在客观上也加大了我对这类“青春文学”的疏离感。
陈培浩:关于青年写作,我曾经谈过这样的观点:“青年写作通过对创伤的放大跟秩序化生存形成某种对峙。青年文化往往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尚未被纳入到主流的象征秩序之中。从精神分析角度看,青年主体一直处于‘父’的压抑之下,从而产生了青春期象征性的弑父冲动以及挑战权威失败的感伤。青春作为一场主流秩序不可克服的病提供了自身的反抗潜能,因而青年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便在于它超功利地在秩序之外提出一种理想生存的可能。不管是哈姆雷特、少年维特还是觉慧,青年主体在未纳入文化象征秩序、未占据父之位置之前,它的理想性、挑战性以及由之伴生的感伤性都是其文学价值所在。不过,青年主体的反抗和创伤一旦在融入象征秩序过程中被疗愈,一旦青年主体占据了旧秩序中‘父’之位置,并心安理得地维护旧秩序的运作,它也就安全地被转化。”所以,在我看来,青年写的未必就是青年文学。今天的青年作家,是否依然还有勇气和能力去冒犯,去与凝固的秩序较量,从而推动着写作秩序产生一点点的位移,我既怀疑又期待。
王威廉:今天的青年写作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话题,因为如果在单一的文学传统里面进行写作,那么青年写作必然是有所创新、有所颠覆的。但是,我们在当代中国文学当中,每个青年作家的来路实在是太复杂了,中国文学自己的脉络只是成为其中之一,而面对整个中国以外的文学史,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也不局限于某几个国家或者是某几个时段的作家作品,一样特别复杂。有些人还喜欢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有些人继续迷恋浪漫主义作品,有些人推崇现代主义文学,还有一些人喜欢后现代主义作品,所以在评价的时候就缺乏一种标准性。当然,即便如此,文学还是有它严格的尺度和标准的。我们在强调“世界文学”的时候,并非是在中国去写别国文学的赝品或复制品,而是应该立足中国,以世界的视野来观照自身,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让自己这个故事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有一种血肉的联系。我想,这才能够称之为是一种“世界文学”。我的意思是在今天的青年写作,可能青年人的习作期或学徒期,或者说是一种受影响的阶段,要持续得更久。只有青年作家充分掌握了这些复杂丰富的文学传统以及洞见了复杂的现实之后,我们才能够期待他们在文学上有真正的创新。中国文学真正成为世界文学之重要一环,必将是由青年作家去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