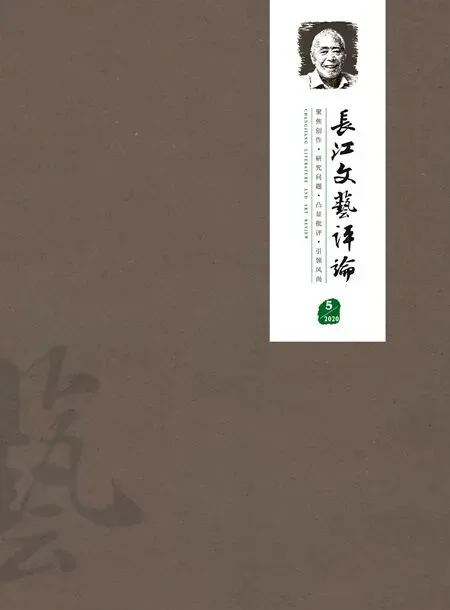《生命之证》:建构国家抗疫叙事新美学
◆青 屏
刘诗伟、蔡家园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证——武汉“封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在《中国作家》(纪实版)2020年第10期发表后,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10月17日,湖北省作协、《长江文艺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第12期“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集中研讨这部作品。湖北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李修文主持沙龙,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坤斗,湖北省评协驻会副主席、二级巡视员、《长江文艺评论》常务副主编李建华,湖北省作协理论室主任韩永明及作家刘诗伟、蔡家园出席了研讨活动。
以下为发言辑录:
李修文(湖北省作协主席):
《生命之证》在2020年度显然是湖北文学最重要、最重大的一个收获和成果,我本人也见证了这本书从萌发、采访到最后的诞生。目前《中国作家》已经发表,长江文艺出版社也即将出书。在疫情期间,当两位作家决定要深入现场进行采访时,我对他们的安全充满了担心,但他们毅然决然去履行一个作家在当时最应该履行的责任。他们做出决定准备去采访的前一天,我在电话里跟他讲:既然如此,就送你们八个字——壮士许国,不必相送。我们作家只能拿着手中的笔,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行使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我个人的感受,这部作品是本年度关于抗疫叙事最优秀、最出色的作品,是两位作家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完成的一部个人意义上的赤诚之作。放在全国范围来看,也是一部中国要建立核心抗疫叙事以来最重要的扛鼎之作。今天的研讨有两个目的:一是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告诉全国的文学界或者说公众,湖北有这么优秀的作家,诞生了如此优秀的作品;二是针对这部作品的研讨推介才刚刚开始,我也希望从大家的发言中得到启发,并把这些启发变成具体的工作内容,静水深流地陪同这部作品共同成长。
李建华(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生命之证》的发表是湖北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两位作家都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和较高的理论素养,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在意料之中。全篇共十六章,前四章主要描述疫情爆发、国家采取“封城”行动及最终战胜疫情的过程,中间九章分别叙述了不同人群在抗疫期间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包括建设者、医生、护士、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等,最后三章是叙述武汉重新回到与世界交流的正常轨道、开城等等,全书洋溢着高昂的英雄主义和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一部为历史存档、为民族铸魂、为人类问道的优秀文学作品,它为抗疫叙事与灾难文学的建构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张冰(《中国作家》编辑):
阅读过众多抗疫题材作品以后,拿到《生命之证》觉得眼前一亮。首先是它很客观。这部作品以客观的视角、细腻的笔触真实再现了武汉这座英雄城市所经历的抗疫大战,这是许多作品所缺失的。其次是全景展示。它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全景式书写武汉“封城”抗疫的长篇报告文学,从方舱医院到社区,从医生护士、志愿者到科研工作者,甚至插管小分队队员都有所涉及。第三是丰盈。聚焦草根群体使得《生命之证》具有丰盈的细节之美。通过塑造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形象,凸显了人类生命力之顽强,彰显了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方向。第四是超越性。《生命之证》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来自于灾难现场,两位作者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其苦痛、欢欣感同身受;更重要的是其采取的宏大叙事,节制情感,超越自我,对自然、生命、个人安危与公共关系、疾病与病毒的关系、国家制度与卫生防疫体系、国际援助机制与科技创新乃至文明水平都进行了思考,抵达了相当的深度。
梅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这是两位作家亲临一线采写武汉“封城”抗疫的重磅作品,多角度、双声部描述“封城”抗疫,为武汉、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抗疫的珍贵记录和在场解读。《生命之证》提供了一个视角,是这次抗疫的最大公约数:拯救生命。作家对这场疫情和抗疫的书写与解读是很成功的。作品分为16章加一个引子,从解封后回望整个“封城”的起源,居家抗疫的种种艰难,对病毒认知的过程,全面展现了国家抗疫的恢弘场景,描述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组织下,本地医护、外地医疗救援队、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志愿者、科研工作者等全民参与的“封城”抗疫全景,并不回避抗疫前期至暗时刻的一些问题,关于抗疫中政府高效部署、社区全力投入、医护舍命战斗的描述和思考都很深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十四章“武汉告诉世界”,展现本地抗疫经验和国际交流活动;第十五章“开城向天问”,非常华彩,从中感受到作家对这座城市的深情。两位作家常有匠心独运的构思,采用了许多小说化的笔法,使叙事过程很生动。《生命之证》显然是一部非常成熟的国家抗疫叙事作品,做到了引子说的“愿将伟大事实与真相献给人类”,其中关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描述和思考,也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张贞(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生命之证》兼备新闻场域和文学场域的优势,把真实性和文学性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意义和文学审美内涵。它的“空间叙事”感很强。从叙事艺术看,真实的表达需要空间维度,如果缺少空间维度,真实性就会被遮蔽。如列斐伏尔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中所言,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生命之证》的空间叙事具备三个维度的审美意义:首先是地理空间。书写了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各大医院,还有家庭、社区、街道、网络等各个空间,所以空间个性化氛围和情境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全景化情感体验和丰富而鲜活的生命状态。其次,作家在对地理空间的排列组合中创造出独特的文本空间。作品中虽然看到的是一个个碎片化的空间,但所有空间都因为同一种情绪基调汇聚在一起,勾勒出一个心理情感层面的“文本空间”——与病毒作战;所有人和事件都在这个想象文学空间中相遇、酝酿、累积、叠加,最终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后,文本空间带来了独特的审美文化空间。具体体现为:克制而充盈的情感体验;共同参与历史进程的在场感;从人类视野出发的生命关怀意识……从这个维度来看,疫情重新建构了我们每个参与者的生活状态和生命认知,这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如何理解、面对这种变化,是这部作品带给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叶李(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两位作家用无畏的行动以及坚守文学尺度的书写确证了文学的良心,奉献出带着生命体温的作品,是值得尊敬的写作。从直面生命之“症”到做出生命之“证”,如何理解“证”?第一层意思是求证、求真、求一个明白。作家依据亲历性的体验、多方面采访的记录还原武汉经历的这场生死劫的来龙去脉,以诚探真,正本清源,和满天乱飞的惊人传闻、耸人听闻的视频剪辑以及所谓内部人士消息形成了强有力的对峙,并激浊扬清,恪守文学的伦理,还事实以尊严,令人重新认识暗夜中的人性辉光,再次擦亮团结、互助、奉献、忘我、忠诚、爱这些词语,从而抚慰伤痛。作品也因此具有抗辩意义。同时,《生命之证》不满足于挖掘新鲜材料,现炒热卖,而是立意颇高,境界不凡:“把人类的真理重新叙述一遍”。重述即重新出发,乃文明的自我修复与蜕变更新。“证”的第二层意思是证明和证实——证明人在危机时刻的高贵德性。《生命之证》提出了人类的悲欢是相通的,用真诚的写作再次证明文学具有让我成为一切人,让一切人成为我的伟大品格。另外,“证”也是证词和证言。灾难是最大的荒诞,面对荒诞,文学必须给出自己的证言。证词其实就是见证自然与社会的灾难,是对宏大历史叙事和历史记录进行补充的重要形式,是返回现场的重要凭借和方式。证词保存了创伤的“当时形态”,也使得创伤不能轻易被遮蔽性话语覆盖。让伤口处于打开的状态可以昭示我们曾经怎样生活,又应该如何生活——伤口应该成为思想的本体,而不是特殊工具。《生命之证》的“证”最终落实到了生命层面——生命之证,根本上证的就是生命之可贵、生命之庄严,就是生命至上。生命之证与生命之思、生命之诗、生命之悟交相融合,抵达的正是灾难文学的丰富和宽广。
陈国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这部作品有三个特点:第一,为社会留档,见证武汉抗疫全过程。两位作家是疫情的亲历者、幸存者,亲身经历了武汉“封城”抗疫的全过程,同时他们也是目击者和见证人,《生命之证》首先是属于见证文学。第二,为民族铸魂,塑造了新的英雄群像。武汉“封城”抗疫的生死战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好人好事的宣传上,《生命之证》塑造英雄群像时力求在全景观照下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第三,为人类问道,反思灾难主题和文化。两位作者把武汉的抗疫经验推向了人类,反思人类应该怎样科学应对灾难问题,使文本具有人类性、世界性。
李雪梅(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如何穿透后真相时代的迷雾,完成抵达真相的写作?《生命之证》从三个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一是将个人生命体验作为写作的起点;二是全景式书写抗疫时空;三是对疫情进行同步反思。如何将自身鲜活的内在生命感受与整体性的国家抗疫行动对接,又如何突破被社交媒体高度结构化的外在经验和话语的统一规训,都是疫情书写面临的“危险”。两位作者以智慧与勇气、良知与理性,将见证者、亲历者、采访者和写作者的身份综合在一起,奉行生命至上原则,从真切的个人生命体验出发,以真诚的在场写作成就了一部抗疫叙事的典范之作。见证过疫病的凶险与无情,体味过武汉这座城市的疼痛与新生,作者坚信“只有奉出全景的武汉抗疫事实,才可能抵达与之匹配的写作”。作品共十六章,几乎都是第一手采访资料,力求在时间和空间上全覆盖,全景式展现宏阔悲壮的抗疫现场。作品重点梳理了很多关键事实以正视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品最大限度还原了抗疫行动中人们的真实处境,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的恐慌与愤怒、绝望与希望、努力与挣扎,都得以感同身受的展现。作品采用特写、剪接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思应是灾难文学最重要的伦理。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应该是疫情反思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最重要的落脚点。作品提醒人们注意人与病毒一直共处、并将持续共处这样一个有意无意被人们忽略的客观事实。虽然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大疫后人们的精神创伤、疫病后遗症、经济形势、环境以及生活方式都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作者在疫情期间的写作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叶琼琼(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
《生命之证》是一部用生命书写的作品,体现了勇气和担当。全文在纵横两个维度全方位展开,努力写成“历史档案”,既是对历史重大事件的还原,也是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文中有大量的数据,印证了呈现历史真相的书写态度。作家采取俯瞰的姿态,能从总体上把握整个抗疫,因而显得全面客观。作品试图从人类命运的角度,对理性、体制、理念、伦理、科学、法度、合作、预防、统筹、发展等人类社会的命题和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进行透视和审视,展现出个性和深度。两位作家对生命和文学的敬畏与真诚,让这部作品从一众抗疫作品中脱颖而出,具有文学与史料并存的双重价值。
朴婕(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品的叙事人包含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客观的记录者。所谓全景叙事,是因为它提炼了众多声音和多层次画面。第二重身份是专业工作人员。这种身份会让叙述者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去观视疫情动态,从而从基层到顶层的各个层面上形成相应的叙述。第三重身份是武汉人的身份。这重身份让视角进入到了内在层面,充分表达了在地者的体验。在三重身份的相互作用下,从中读出两种故事:如果接受主体是疫情期间在武汉的人,那么《生命之证》会激发很多他/她对于自身经历的回想;而对于疫情期间不在武汉的人,会从文本本身去阅读这个故事,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感受这个“中国”故事。这部作品的内在轴线很清楚,从突发灾难、到沉郁顿挫、到看到希望、到重获新生,有一个乐观、坚强的中国故事的内核。尽管作家在抒情上很克制,但最终还是传递出一种昂扬的情绪,这与它唤醒了关于中国的叙述有关,因此它也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史诗。而这两种故事也反映出疫病带给我们的双重思考,“病”“疫”是有区别的。对于“病”的讨论,常常是反思性的,比如关于身体的、生命的或者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或者把它作为一种隐喻、一种象征、一种寓言去反思。而“疫”则更接近一种灾难,人力无法左右。所以我们讲“疫”的故事时,就会关注怎样发动集体的力量,救出更多的生命。《生命之证》既讲出了个人叙事,也讲出了国家叙事。
彭宏(湖北警官学院副教授):
这部全景式表现武汉抗疫斗争的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与时代同步伐,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二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立言,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这是近年来报告文学中少有的对平民英雄群像的展现,堪称扛鼎之作。三是一部难得的精品。它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阐释得淋漓尽致。当下最突出的中国精神就是抗疫精神,《生命之证》就是对伟大抗疫精神的印证。四是《生命之证》体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两位作家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虽是报告文学,但通过家国叙事、在场视角、英雄群像,呈现出广阔性、纵深感,绘就了一部特殊的民族史诗,它是有灵魂的、可留存后世的创作。所以我对作品的总体评价是:魂魄雄浑,气质悲壮,本正神清。灾难文学完全可以有另外一条道路,传承儒、道的立场和情怀,如“家国同构”“天人合一”。我认为《生命之证》的立场,就体现了这样的中国立场、中国情怀。面对灾难,作家不应置身事外地去一味指摘、批评,而应以“参与”的姿态,促进改革和进步,也就是“建构”。文学对灾难的表现,一定要建立“共同体意识”。《生命之证》对此有深入表达。
雷登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生命之证》中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与个性化的文学表达融会交织,是文学观照现实、回应时代的生动写照。两位作者以“生命”超越一切的视角,以整体性和个人化兼顾的姿态,高难度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生命之证》在文体和形式方面具有独特之处。这部作品是两个作者相互配合完成的“双声部”作品。虽然我们从行文细节中可以发现两位作者的细微风格差异,但总体来说,两位作者密切协调,使作品成为一个高度融合的整体。在文体方面,副标题叫做“全景报告”,但报告中又融合了科学话语、新闻报道、采访和抒情话语,体现了一种文体融合。《生命之证》体现了一种难得的生命诗学:它建构在尊重生命、维护生命、反思生命的基础上,它充分尊重生命的逻辑,对纯粹工具化的写作方式保持着警惕,体现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不仅有反思,还有建构。这部作品“风正神清”,同时又丰富充盈。
刘萍娉(武昌理工学院教师):
这部作品采用了多重视角叙事。不仅从作者的主观视角来阐述自己身边的所见所感所闻,也有以第三人称视角来展示客观的事实真相,更有以文中人物的第一人称视角、用日记的形式来表达当事人自我的内心感受,多重视角的叙事转换都在述说着书写内容的真实性,也尽可能地给读者提供多重角度来看待整个事件。
朱旭(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生命之证》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规避了陷入虚伪、空洞的材料本位主义,非常巧妙地对庞杂的素材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展现了中国人朴素却值得敬佩的气度和精神。王国维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段话用在《生命之证》这个文本上是非常恰切的。
刘天琪(湖北省作家协会编辑、博士生):
抗疫叙事应当是一种国家叙事。从这个定位来回顾疫情期间的叙事过程,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疫情初期,因为抗疫要求,作家暂时不能在第一时间深入灾难现场,那么,这一阶段的抗疫叙事大部分由新闻媒体来完成和建构,以短视频、新闻报道的方式传达出来。这一阶段的抗疫叙事的目的和功能是非常明确的,主要是科普防疫知识,提振民众的抗疫信心,唤起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感。这一阶段的抗疫叙事比较偏重于引导性的话语模式,它的社会性也会比审美性更多一些。经过对疫情的有效防控,抗疫叙事会进入第二阶段,更多的文学和文艺作品参与进来,叙事的形式和门类会更加的丰富和多样化,比如会出现电影、电视剧、音乐这样一些艺术形式,甚至会形成主题创作的井喷。第二阶段的抗疫叙事相比于第一阶段来说更加深入,更具理性色彩。比如《生命之证》是以“为社会留档、为历史存真、为民族铸魂、为人类问道”的定位和目的来采写的,显然就比第一阶段要深入得多,它是以一种文学方式对这场疫情进行表达和思考,不是一般的感性或情绪主导的状态。
裴亮(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整个疫情期间我都在海外,武汉抗疫经验是完全缺失的,这部作品给了我一次“全息”的投影,一次“整体”的回望。第一,非常值得肯定是这部作品对作为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文学表现和历史叙述的标志性意义。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提出,文学作品是结构与事件、事实与行动的统一体,它与外在的社会历史既对立又交织;而作为事件的文学作品以特定的形式策略在世界中出场。《生命之证》具有双重意义。第一个层面在于这个作品能在高规格的《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中国作协将本书列入“中国抗疫全景叙事写作计划项目”等等,这一系列过程都共同构成了这部以书写“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为旨归的抗疫报告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事件登场的标志性意义。第二个层面体现在文本内部对疫情这一突发事件本身的“个体化”文学记录与“公共性”历史表述的完美融合。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对武汉抗疫的历史回顾与总结,需要找到一种介乎于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叙事方式。因此,它一方面必须符合历史叙事的“求实、求真、求证”的根本规则;另一方面它又要符合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创作的内在要求,比如“在场性”的细节记录与“私人性”的情感体验等。因为作者有意识地在个体的文学表达与整体的历史叙事之间寻求较好的结合,所以从阅读感受上来说,作品中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个人的“文学叙事”两者之间不仅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作者的“愣怔”,两处都叫人鼻子一酸。第二,这部作品具有作为“同时代”新冠肺炎记忆与疫情书写的“全球”连锁的意义。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室信一曾在《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一书中提出了“思想连锁”的概念。这个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回望抗疫的这段过程时,跳脱出武汉视野的局限。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轮廓变得清晰可见,在疫情全球性同步蔓延之时,往往会使我们产生共生感和共属性意识。不仅仅使我们在生命体验上、也使我们在思想上认识到了人的移动、病毒的移动所带来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病毒的传播促发的文学对环境危机的书写、对创伤记忆的记录,也会成为今后我们思考全球连带性与整体性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所以,我认为这部作品将成为同时代思想跟文学记忆的连锁文学表达。
杨晓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这一年在海外,不能以“亲历者”身份参与讨论。阅读《生命之证》就是接近一次“回顾式研究”,不仅是感情的波动与释放,也会更自觉考虑“写作”作为一种生活实践的意义及可能。“抗疫文学”的讨论容易只重视“抗疫”主题而忽视其文学价值;针对报告文学的特殊性,更容易只肯定其纪实功能,而不去讨论它之于当下创作的启示。但我觉得《生命之证》在三个方面迫使我们回到“什么是文学”的基本命题上来。首先是怎样重新定义作家,作家是不是先天拥有“写作”的权力?两位作者都提到自己曾是写日记的一员,但深感日记只记录了武汉的千分之二,所以才萌生出要到抗疫一线先做调查研究的念头。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见证者和写作者,但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手机“朋友圈”里,又恰恰暴露出以“证真偏见”为出发点的思想的懒惰。因此,“逆行”采写的价值首先不是其不惧疫病的勇气,而是作家投身“知”与“行”的反省与验证。所谓生命之“证”,首先是对自己生命感觉、思考能力的重新锻造。第二,今天的文学语言如何自我更新,如何应对与诸种日常语言搏斗的难度。在《生命之证》中,我们读到新闻报道的语言、以数据思维为根基的科学计算的语言、媒体宣传中“感动中国”式抒情的语言、从政策文件到具体治理过程中难免格式化的语言等等。这些语言当然不是理想中的文学语言,可如何从这些形质分离、刻板语言中争夺出那些本来与具体生命感受息息相关、有活力的语言呢?《生命之证》至少提供了两点启发:一是特别能呈现地方性性格的方言的运用;二是两位作者因不同代际经验与历史感觉,用写作者的自我形象为一般语言系统充填了具体的令人信服的个性。第三,是不是多视角、多文体杂糅就必然构成叙述的复杂性,所谓全景叙述仅仅是指“体量”上的全面吗?虽然《生命之证》也确实涉及到从国家到基层各种群体在抗疫中的贡献,但我觉得《生命之证》中最有文学性的部分恰恰是它结构化把握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能力,是尝试辩证地从冲突中为个体或群像塑形。《生命之证》里有不少“重复”的生活事实——这些未被“剪裁”的重复,恰恰是所谓全景式书写应当努力的方向。
文坤斗(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我记得2月下旬国家卫健委跟湖北省作协沟通,商议能否请作家深入采访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当时中央指导组也提出了这个要求,中国作协也派了小分队,那是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而刘诗伟、蔡家园深入一线实地采写,可以说是不辱使命。从作品在《中国作家》发表后的反响和刚才各位的发言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部优秀作品,是目前中国文学界全景式反映这场疫情斗争的作品中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也是前面专家说的“扛鼎之作”。两位作家表现出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为湖北文学界增光添彩,体现了湖北作家真正的使命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