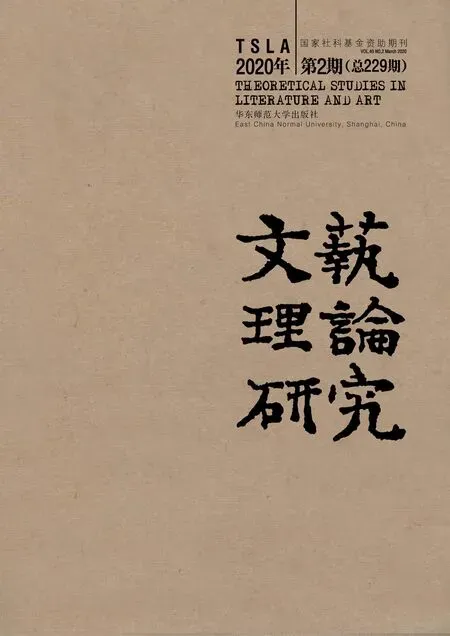经典的游戏性接受: 以宋人对杜甫诗歌的戏仿为中心
姚 华
戏仿概指对文本带有戏谑意图的模仿和改写。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权威”“颠覆已知”的理论自觉,以及消费社会的娱乐狂欢,各类“大话”“恶搞”式创作频繁出现在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中,以至戏仿往往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的一种症候。存在于古典文学中的游戏精神则较少受到学界关注。事实上,戏仿作为一种古老的创作技巧,其存在遍及古今中外。然而相较西方文艺传统对“戏仿”(Parody)理论的丰富论述与建构,①中国传统文论对游戏性写作相对较为轻视。本文旨在为考察戏仿现象提供一种古代视角。对于文章领域中戏仿史传、公文而成的拟体俳谐文写作,学界已有一定的关注。②然而诗学领域却缺少相关研究。戏仿式写作虽于古代笔记、诗话中频频可见,但零散不成系统,且因其为游戏文字而多受忽视。至于这类文本究竟拥有怎样的表现与功能、产生过哪些作品、具有怎样的写作传统与幽默机制,皆缺少正面的讨论。故此,本文试以宋代士大夫对杜甫诗歌的游戏性改拟与续写为例,尝试揭示存在于古典诗歌写作中的戏仿现象,进而讨论其在经典接受过程中的意义。
一、 戏仿杜诗: 经典性与游戏性
戏仿式创作通常以经典文本为仿拟对象——“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模仿,在古典时期,都隐含着对模仿对象的致敬与崇高地位的认可。因为只有神圣的或者经典的文艺作品,人们才会去模仿”(龚芳敏37)。宋代是一个对前代诗歌传统进行全面整理、选择并塑造“典范”的时代。杜甫的经典化便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人推尊杜诗,在实际创作中也多有拟杜、效杜的行为。在此背景下,戏仿杜诗的现象亦随之增多,构成经典接受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
宋代笔记、诗话类著作数量繁多,保留了不少宋人日常生活中游戏嘲谑的资料。从这类记载中可以看到,宋人间玩笑戏谑的一种形式是对经典诗歌文本进行改拟。原作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再生长的文本结构,改拟之作则在与原作的对比中制造反差与张力。在以下这段记载中,杜诗便作为一种可供改造的文本资源而被游戏性地使用,参与这场游戏者皆为北宋前期的知名士人: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欧阳文忠公、刁景纯同知礼院。景纯喜交游,多所过从,到局或不下马而去。一日退朝,与子京相遇,子京谓之曰:“久不辱至寺,但闻走马过门。”李邯郸献臣立谈间,戏改杜子美《赠郑广文》诗嘲之曰:“景纯过官舍,走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长骂。多罗四十年,偶未识磨氈。赖有王宣庆,时时乞与钱。”叶道卿、王原叔各为一体诗,写于一幅纸上,子京于其后题六字曰:“效子美谇景纯。”献臣复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题篇,献臣小书”。欧阳文忠公又以子美诗书于一绫扇上。高文庄在坐,曰:“今日我独无功。”乃取四公所书纸为一小帖,悬于景纯直舍而去。时西羌首领唃厮罗新归附,磨氈乃其子也。王宣庆大阉求景纯为墓志,送钱三百千,故有磨氈、王宣庆之诮。今诗帖在景纯之孙概处,扇诗在杨次公家,皆一时名流雅谑,余皆曾借观,笔迹可爱。(沈括319—20)③
刁约,字景纯。据此记载,刁约知礼院时常与人来往应酬,以至累日不入太常寺,引起宋祁的谴责。李淑遂改拟杜甫名作《戏简郑广文虔兼呈苏司业源明》一诗对之进行嘲戏,王洙、叶清臣、欧阳修、高若讷等人亦参与其中,可见彼时士人的雅谑风气。杜诗原句为:“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仇兆鳌249)诗中寒士郑虔郁郁不得志的行迹被替换为刁景纯过官舍而不入、不识西戎唃摩氈、为王宣庆作墓志铭等有趣轶事。李淑的拟作延续了杜诗的表达结构,但全然改换了诗歌内容,变杜诗的悲凉慨叹为滑稽嘲谑。然而只有熟稔原作之人才能更好地玩味“便遭官长骂”的巧切、以“纸钱”替换“酒钱”的可笑等埋藏在诗句中的幽默。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轶事所涉之人,不少在杜诗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宋祁曾手书杜诗,且为《新唐书·杜甫传》之作者;王洙则编有《杜工部集》二十卷,后由王琪刊刻,流传甚广,成为后世杜集的祖本。据学者考证,改诗一事发生于康定元年(1040年),可证“早在康定年间(1040年—1041年),北宋京城的馆阁文人圈已经熟读并喜爱杜诗”(曹雪聪 孙宗英58)。杜诗作为彼时馆阁文人所分享的公共性知识,是幽默得以从文字间浮现的潜在背景,并以此强化了特定群体的认同与亲密感,具有促进文人交际的意义。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康定年间,宋人对杜甫的普遍推尊尚未形成。然而戏拟并不仅仅存在于杜甫经典地位未形成之时,④相反,只有伴随杜诗在士人群体间传播的普遍化,对之进行改拟才能更为广泛而成功地起到幽默效果。阮阅《诗话总龟》曾引《王直方诗话》云:“秦少章不见十年,忽一日见访,书一篇为惠云:‘不到王家近十年,子猷风韵亦依然。旧时朋友今何在,别后新诗谁与传?’余戏曰: 莫太犯老杜,所谓‘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211—12)秦觏(字少章)、王直方为苏轼、黄庭坚之后学,与苏、黄交游密切。彼时杜诗历经庆历诗人之推崇,再由苏、黄等元祐诗人之尊赏,已成为学诗者普遍效仿的对象。《王直方诗话》中多处论老杜诗,如谓“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23)、“老杜‘风吹客衣日杲杲,树搅离思花冥冥’,此最著意深远”(100)、“山谷云: 作诗须要开广,如老杜‘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之类”(52)。正因对杜诗极为熟悉,王直方才能轻松识破秦觏所赠之诗与杜甫原作《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之间的微妙联系。同书中尚有“潘邠老诗多犯老杜,为之不已”(22)、“徐师川《紫宸早朝诗》一联云:‘黄气远临天北极,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予观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犹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一联也”(98)等记载,可见改拟的背景正是彼时极为兴盛的学杜风气。
此外,杜甫诗中具有开创性与个人性的表达方式,也容易成为宋人的戏仿对象。因为只有原作能被轻易识别出来,改拟才具有幽默的效果。而改拟之作其实也在不断确认原作最具标识性的特征、强化对其风格的识别,进而推助原作的传播,并反过来促成原作的经典化。
例如陆游《家世旧闻》曾记载了这样一条文人拟杜诗嘲戏的例子:“作乂与马巨济善。巨济在太学有声,及赴省试,作乂拟杜子美《杜鹃》诗体,作诗戏之云:‘太学有马涓,南省无马涓。秋榜有马涓,春榜无马涓。’”(188)杜甫《杜鹃》诗的开篇方式非常特殊:“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仇兆鳌1249)叙述语言如口语般通俗易懂,复沓的表达方式则类似谣谚。以如此朴拙之句作为诗歌开篇是杜甫的大胆创造,其特殊性也引起了宋代论诗者的关注。关于其为题注还是正文、是杜甫自创还是有所渊源、是否有讽喻蜀乱的政治内涵等,宋人诗话中多有讨论,如《王直方诗话》称“识者谓前四句非诗也,乃题下自注,而后人写之误耳。余以为不然,此正与古谣语无以异,岂复以音韵为限也”(王直方86);王观国《学林》谓“子美《绝句》诗曰:‘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诗正与《杜鹃》诗相类,乃自是一格也”(242);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乐府有江南古辞[……]子美正用此格”(288—89)。由是可知,杜鹃诗是宋代诗坛较受关注的诗学话题,并以其体式的特殊性为士人所注意。陆游记载中李作乂嘲戏马巨济的诗句,便套用了杜诗这一极具个性化的表述结构,用“太学”和“南省”、“秋榜”和“春榜”的对比暗示马巨济省试不第的窘况,叙述看似冷静克制,未下一句议论,但讽刺意图却已在这一直接的对比中体现得非常鲜明。
另一个例子则为宋人对《饮中八仙歌》的戏拟。杜甫原作一诗连叙八人的写作方式别具一格,后人多有“古无其体”“老杜创体”“特其变体耳”等创体之誉(陈伯海主编1408)。此体为唐朝仅见,宋人却多有拟作。这类诗大多以集会为背景,一一描述参与集会的众人形象,勾连出一幅集体的人物群像。⑤而诸如唐庚《会饮尉厅效八仙体》诗,则已明白在诗题中称“八仙体”,可见对杜诗体式特殊性的自觉。而在杜甫“八仙诗”的接受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带有游戏性质的仿拟之作。赵鼎臣的“病中九客歌”,便在套用杜甫名篇表达结构的基础上,将内容替换为一组更具滑稽色彩的人物群像:
将军胆气凌秋天,百札曾将一箭穿。倒床忽作儿女眼,悲啼出泪如涌泉。会稽令尹形悍坚,新买蛾眉费万钱。未容纤腰小回旋,径烦药饵亲调煎。山阴大夫祖文渊,弯弓射贼口垂涎。壮士亦苦头风偏,河润九里风化传。坐令丞簿相牵联,请医买药争后先。剡中有宰正鸣弦,携琴忽泛子猷船。入城巵酒不下咽,但饮柴胡如吸川。沃洲公子黠可怜,斩关夜遁呼不前。道中挥断九铁鞭,抱病谁复能轻便。铸钱短簿非凛然,捧心欲效西子妍。青衫从事世所捐,亦遭病鬼相傍缘。戏成嘲语如怪颠,一读坐使沉疴痊。(北大古文献研究所编14883)
此诗在形式上套用杜诗,所押之韵亦与杜诗相同,但却将盛唐时期风流潇洒的“酒中仙”一一置换为病态各异的“病中人”。“悲啼出泪如涌泉”“请医买药争后先”“但饮柴胡如吸川”“捧心欲效西子妍”等句,以戏剧性的夸张笔墨描述各人之病态,将杜甫原诗“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等绘人笔调中本就带有的调谐、漫画色彩进一步放大,故赵鼎臣诗中自称“戏成嘲语如怪颠”。杜甫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在诗歌表达方式与题材内容上的开创性及实验性密不可分。而宋人的戏仿之作,则在改拟的过程中蕴含着辨认、学习杜诗艺术的意求,同时也在试探着杜诗体式所可能具有的包容性。
可以看到,杜诗作为经典所具有的知名性及公共性、作品的风格化与个性化,都为宋人以杜诗为对象的游戏提供了可能。而宋人的戏仿行为,则又反过来印证了杜诗所具有的上述经典特征。
二、 苏轼《续丽人行》: 故意的“误读”与经典的“重构”
上文所举戏仿杜诗之作大多只限于玩笑。这类玩笑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应该远比我们所知的更多,只是若没有笔记、诗话等文本记录,它们在笑声之后很快就会被遗忘。但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对前代经典的戏仿之作最终获得了独立的艺术价值,并因其创造性而为经典的内涵补充了新的内容。苏轼《续丽人行》便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
此诗从诗题即可看出是对杜甫名作《丽人行》的续写之作。续诗一般指接续他人或自己的残句,为之补足成篇。此外另有一种续诗,如白居易《续古诗十首》、刘攽《续董子温咏陶潜诗八首》、范成大《续长恨歌七首》等,所续者为原作的风格、主旨,是一种严肃的模仿。续杜诗是宋人学习杜甫的一种表现,如吴则礼《续百忧集行》、洪咨夔《续洗兵马上李制置》等作,皆为对杜甫原作诗意的延续与补充。苏轼《续丽人行》虽在形式上相类,却在写作姿态上与上述诗作大异其趣。所谓的续作在这里意味着重新“拼贴”原作的某些基本元素,故意对之进行脱离历史背景与原诗语境的“误读”,从而创作出与原作意趣全然不同的作品。这类续作由游戏意识所引导,蕴含着对原作的调侃与“重构”。就对经典诗歌的戏仿式续写而言,苏轼应当是具有开创性,甚至可称“前卫”的。
《续丽人行》的主题与杜甫原作大为不同。此诗实际为一首题画诗,其写作情境如苏轼在题序中所称:“李仲谋家有周昉画背面欠伸内人,极精,戏作此诗。”元丰元年,苏轼在友人家偶见唐人周昉所绘“背面欠身内人”图一幅。画中美人背身微侧的姿态让诗人联想起杜甫《丽人行》中所描述的画面,遂以《续丽人行》为题,写下了这首充满戏谑意味的题画之作:
深宫无人春日长,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莺啼空断肠。画工欲画无穷意,背立东风初破睡。若教回首却嫣然,阳城下蔡俱风靡。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心醉归来茅屋底,方信人间有西子。君不见孟光举案与眉齐,何曾背面伤春啼。(811)
周昉以擅绘宫中仕女著称,苏轼很自然地将画中场景想象为唐朝宫闱深处。睡起独自梳妆的美人显得极为孤寂、无聊,莺飞燕舞、生机无限的春日景象反衬出美人被虚掷了的美好青春,遂有“空断肠”之叹。紧接着的四句则紧扣美人的“背面”做文章,称画工描绘这一姿态是出于“欲画无穷意”的有意之为,留给观者想象画中人美丽程度的空间。行笔至此,苏轼犹未脱离题画诗的一般写法: 描述画面内容、议论画家笔法。然而从诗的后半段起,苏轼突然引入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观画视角: 他略显突兀地将画面的观看者转化为诗人杜甫,由画中场景联想到杜甫《丽人行》中描述的一次著名观看。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仇兆鳌156),杜甫《丽人行》一诗记述了虢国夫人、杨国忠等杨氏兄妹曲江春游之场景。诗中对丽人盛大的出行场面及奢华的衣着、饮食、器物等作了极细致的观察与描画。尤其是对丽人的形貌装扮,杜甫毫不吝惜笔墨之铺陈:“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仇兆鳌156)激发苏轼灵感的正是“背后何所见”一语——苏轼借此注意到了美人身后的注视者,诗歌画面之外那位“蹇驴破帽”的“杜陵饥客”。苏轼将这一形象移至其《续丽人行》一诗中:“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杜甫《丽人行》结尾有“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仇兆鳌160)之语,苏轼借之作为诗人只能从背后观看、无法上前接近丽人的理由。而杜甫并未提及观看丽人出行后的感受,续诗则为其补足——苏轼想象杜陵饥客对美人一见倾心、久难忘怀,遂在自己的茅屋中辗转思念。这一续接原作的想象全然反转了杜甫原诗的书写意图,将冷眼旁观、深沉思索的诗人形象描画成落魄多情的寒士,消解其道德严肃性。最后,在全诗末尾,苏轼宕开笔墨议论称,倒是市井中的平民女子不会有宫中人的悲寂。她们虽不及丽人美貌,却反而可以享受举案齐眉、和谐相伴的日常爱情。
以往研究者大多注意到苏轼于这首诗中所呈现的题画思维、论画观念或自出己意的立论方式。⑥然而将之置于杜甫《丽人行》一诗的延长线上进行解读,从经典接受的角度予以考察,则能发现诗中包含了苏轼对杜甫诗歌的一种特殊阅读方式——故意的“误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原诗意义的“重构”。
《丽人行》一诗是安史之乱前旅居京城的杜甫书写当时社会景象的著名诗篇。此诗在写作手法上颇有值得注意之处。从表面上看杜甫只是在铺陈物象,描述杨氏衣妆之丽、厨膳之奢,诗中并无直接的议论和批评,但在后世论诗者眼中,杜甫看似客观的“观看”与“陈述”中实则隐含了鲜明的批评立场:“此诗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仇兆鳌157),“通篇俱描画豪贵浓艳之景,而讽刺自在言外”(陈伯海主编1414),“风刺意较显”(沈德潜145)。皇室贵族极度奢华的生活与隐约可见的私情皆是对腐朽政治不争的暗示,如浦起龙所言:“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228)苏轼的《续丽人行》却在自许“戏作”的游戏姿态下,只关注字句最为表面的意义。无论杜甫的书写伴随着怎样不屑的嘲笑,这样细致的观察都无可避免地在形式上呈现出对“美”本身的关注,便也自然地伴随着诉说欲望的可能。苏轼敏锐捕捉并故意放大了杜甫对丽人的注目,将诗人隐含其后的批评态度全然隐去,只注意观看者沉醉其中的表面姿态,进而想象杜甫“心醉归来茅屋底,方信人间有西子”的多情与痴迷。“当一个表达方式原系用之于转义,而我们硬要把它当作本义来理解时,就得到滑稽效果。”(柏格森77)这样一种脱离原作语境、仅对词语作表面阅读的解读方式,正是一种“故意的误读”。
更深一层而言,苏轼的“误读”其实是与传统阐释学原则之间的游戏。杜诗以铺陈为讽喻的书写方式本身即蕴含着歧义可能,如《唐诗归》对《丽人行》的评语:“本是讽刺,而诗中直叙富丽,若深羡不容口者。”(陈伯海主编931)杜诗“直叙富丽”,可作“艳羡”或“冷嘲”等方向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原作的意义在“劝”与“讽”之间微妙地游移。决定杜诗内涵在历代解诗者眼中是“讽”而非“劝”的,并非来自文本内部的证据,而是有赖诠释者依靠“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原则,结合写作背景及杜甫其他作品得出的结论。⑦苏轼则有意“断章取义”,违背传统诗学的诠释习惯,进而推导出让人惊异的结论。
《续丽人行》因苏轼的诗名、“画工欲画无穷意”的论画美学以及全诗末句的精警议论成为宋代诗歌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作品。苏轼之后出现了大量同题写作,南宋韩驹、姜特立、杨万里等人皆有《续丽人行》诗,高斯得作有《三丽人行》,元人胡天游亦有《续丽人行》,直至明代仍有人作《重续丽人行》。而苏轼对杜诗的“误读”,亦借苏诗的影响力而在诗歌史上有了位置。杜甫遂在传统的忧世济民等严肃形象外多了更为柔情的一面。诚然这一面貌只是苏轼诗歌中的虚构,并无历史真实性;但它却凭借苏轼的诗名,作为诗歌典故而流传,在艺术领域里拥有了一定的生命力。陈师道《戏寇君二首》云“老杜秋来眼更寒,蹇驴无复逐金鞍。南邻却有新歌舞,借与诗人一面看”(335);胡诠《戏题陈晦叔经略秀斋》有句称“杜陵破帽随金鞍,心醉归来空掩关。不须更问许玉斧,二十四山如髻鬟”(北大古文献研究所编21581);范成大诗中云“高唐赋里人如画,玉色頩颜元不嫁。后来饥客眼长寒,浪传乐府吹复弹”(116)……在游戏性写作的谱系里,“眼长寒”的“杜陵饥客”开始与对美色的窥探产生了意外的联系。
三、 戏仿传统: 娱乐导向下的经典传播
杜甫在宋代诗坛获得了经典性的地位。由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到,宋人对杜甫的接受,既有严肃思想领域内的尊敬与推崇,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游戏与娱乐,二者可以并行而共存。虽然相较于严肃的接受,戏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主流,然其仍有自身的写作传统及对于经典传播的特殊功能。
宋人对杜诗的戏仿,常发生在与人玩笑戏谑的语境中,多为对他人某种可笑处境的描绘。此与流行于民间娱乐及士人日常生活中的“嘲谑”(或称“嘲诮”)传统有着密切关联。中国古代的嘲谑传统源远流长,早期典籍中即有不少对民间谐辞及嘲谑文的记载。隋唐之时,文人之间相互嘲诮之风已极为盛行,且嘲诮多以诗的形式展开,故《全唐诗》有专门的“谐谑”四卷,录载其辞。“嘲诮诗”多以夸张之语描写对象,充分利用谐音、隐语、离合、双关等文字游戏渲染被嘲对象性格或形象上的某种缺陷,娱乐意味非常明显。⑧因其多出现在酒宴等场合之中,亦被视为唐代酒令“行令方式与著辞方式的一个重要来源”,“嘲和酒令的界限,常常难以分辨”(王昆吾96—97)。宋人对杜诗等经典文本的改编、戏拟,可以视为嘲谑文化的延续,是嘲诮诗的一种特殊形式。伴随出版文化的发达与宋代诗人知识结构的扩展,引用、改拟前代诗文也成为宋代士人日常娱乐的一种形式。如宋人有以“集句”形式写作嘲谑诗的现象,⑨其中的趣味即建立在对前代文本的游戏性使用上。又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曾记:“贡父晚苦风疾,鬓眉皆落,鼻梁且断。一日,与苏子瞻数人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子瞻戏贡父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贡父恨怅不已。”(125)苏轼改拟刘邦《大风歌》中的名句嘲戏刘攽的塌鼻,此条记载称诸人“各引古人语相戏”,可见改拟经典之句是宋代士人间常为的一种游戏方式。此类嘲谑在历代上绵延不绝,明清笔记、笑话中也常见这类记载。⑩由是可知,中国古代改诗、拟诗的戏仿写作多属“嘲谑”现象;也正因此,这类作品呈现出一些西方“戏仿”理论未曾注意的特征——西方戏仿理论从自身的文学传统出发,多关注仿作者对原文本的态度:“戏仿者关于被引用文本的态度历来主要有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戏仿者模仿所选文本的目的在于嘲笑,戏仿的动机是轻蔑。第二种理论认为戏仿者模仿原文是为了以原文的风格写作,动机在于对原作的同情。”(罗斯44)这些皆是文本接受角度上的考察。然而中国古人的戏仿,主导戏谑的动机往往不在于与目标文本的互动,而在于与目标读者的互动——所谓的“戏”常常并不直接指向诗,而是指向人。对经典的戏仿并非纯粹文学领域内的现象,而有其自身所属的文化背景与娱乐传统,这是考察中国古代戏仿需特别注意之处。
此外,在宋人对杜诗的戏仿写作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即以苏轼《续丽人行》为代表的“故意的误读”——通过对文本进行明显背离其原意的曲解形成幽默感。这一文本“误读”在民间娱乐中也有着悠久的传统,或可称为一种“讹语影带”式的文本阐释方式。“讹语影带”是流行于六朝至唐代的一种表演伎艺:“主要是通过对言语的讹化、曲解来制造戏谑效果,以达到娱乐观众之目的。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剧录》一书中曾用‘以经文入讹语,影带成趣’对它作了概括,我们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潘建国19)如优人李可及表演“三教论衡”,称如来、老子与孔子皆为“妇人”:“《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有娠’乎?”“《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高彦休1350—51)李可及的立论看似极荒谬,却又有儒释道三家经典的具体文本为立论依据,通过谐“敷座”“而坐”为“夫坐”“儿坐”,“有身”为“有娠”,“待贾”为“待嫁”,以此“证明”三教之圣人皆为妇人。此即“讹语”为戏——“利用中国文字一音多字、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的特点,故作曲解,以制造新奇、诙谐效果”(潘建国19)。唐宋时期,“讹语影带”式的“误读”延及诗歌,成为一种常见的论诗游戏。如唐人称白居易的《长恨歌》为《目连经》,因“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一语似在描述“目连救母”的景象。宋人谓“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句为“患肝肾风”,谓“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句“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论诗者将他人诗句抽离出具体语境,仅就字面意思附会其含义,对之作出迥异于作者原意的曲解,此与戏仿写作有着一致的幽默机制。中国古代虽以尊经好古为正统,“讹语影带”式的“曲解”经典却在民间娱乐中源远流长、自成传统,是古典幽默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改拟、续写等戏仿行为中,正确地理解或欣赏原作已非接受者的目的,如何使文本生发出带有幽默色彩的新内涵,才是真正的意图。有别于严肃的传承,戏仿可以说是由娱乐需求所推动的一种经典接受形式。也正因此,在戏曲、小说、笑话等通俗文学及民间娱乐中,戏仿经典的现象更为频繁,也更显夸张、荒诞。娱乐导向虽弱化了经典的严肃内涵,却也转化了文本的功能,使之在民间文化与士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娱乐的形式并非不能承载严肃的意义,当“嘲谑”的对象指向不公的社会现象与政治事件时,游戏性的写作便具有了反讽与批评的功能。如南宋“江湖诗案”的起因之一,即为诗人改刘子翚《汴京记事》中的诗句讽刺权相史弥远:“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为极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初,刘诗云:‘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今所改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遂皆指为谤讪,押归听读[……]于是江湖以诗为讳者两年。”(周密316)再如太学生曾戏改苏轼词嘲讽蔡京:“蔡京为左仆射日,官守司空,坐彗星竟天去位。太学诸生用坡公《满庭芳》词嘲之。今记其数语云:‘光芒长万丈,司空见惯,应谓寻常。’末句云:‘仍传儋崖父老,只候蔡元长。’蔡命字正取元者善之长也。长音丁丈反,而其解《易》以为长短之长,故因以为戏。”(洪迈1351)张岱《陶庵梦忆》也曾记录明人改林升《题临安邸》诗以讽刺太守:“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时杭州刘太守梦谦,汴梁人,乡里抽丰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词馈送。有轻薄子改古诗诮之曰:‘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可作西湖实录。”(83)通过改拟经典文本表达对现实的批评态度,这类戏仿符合儒家思想对戏谑功能的认可,即《文心雕龙·谐隐》所谓“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会义适时,颇益讽诫”,而不至于“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刘勰270)。“戏仿”的写作形式对批评功能的表达具有特殊作用。一方面,文本前后在雅俗、正谐上的强烈反差强化了反讽的力度;另一方面,经典文本为世人所共知,则又增强了改拟文本的传播效力。娱乐元素帮助促成了经典的传播,使之成为社会舆论的一种表达形式。
宋人对杜诗的戏仿为考察古典诗歌的游戏性写作传统提供了值得关注的个案。诚然,戏仿只是经典接受史上的潜流,然而只有关注到所有潜流的存在,才能看清历史长河的整体面貌,并更好地理解其曾有过的博大与包容。在改拟、续写等游戏性的接受过程中,文本的意义得到了开放性的呈现与演绎。经典在文学传承的谱系之外,拥有了民间文化、日常生活、社会舆论等更广泛领域内的生命力。
注释[Notes]
① 参见玛格丽特·A·罗斯: 《戏仿: 古代、现代与后现代》,王海萌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② 徐可超《汉魏六朝诙谐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提出了“拟公文体俳谐文”的概念。刘成国《以史为戏: 论中国古代假传》(《江海学刊》4(2012): 191—97)则对戏仿史传的假传文学传统进行了梳理。
③ 刘攽《中山诗话》亦记载了此事,但内容较为简略,且细节处与沈括所记有所出入。据曹雪聪 孙宗英:“‘景纯过官舍’: 北宋戏改杜诗一事考略”(《杜甫研究学刊》4(2017): 55—59)一文考证,沈氏《补笔谈》所记应更为可靠。
④ 曹雪聪 孙宗英《“景纯过官舍”: 北宋戏改杜诗一事考略》一文认为,戏改杜诗的现象反映出彼时“杜诗并未被深入地经典化,杜甫其人也没有被高置庙堂”,“是杜诗影响力由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中间状态”。笔者以为此观点有待商榷。
⑤ 相关论述详参熊海英:“集会诗中的人与我”,《武汉大学学报》3(2008): 310—13。
⑥ 相关论文参见张高评:“同题竞作与宋诗之遗妍开发——以《阳关图》,《续丽人行》为例”,《文与哲》9(2006): 225—62;谢寅睿:“杜甫《丽人行》与苏轼《续丽人行》之比较”,《语文知识》2(2013): 89—91。
⑦ 衣若芬《美感与讽喻——杜甫〈丽人行〉诗的图像演绎》一文,从诗画对比的角度也提及这一问题:“绘画的视觉美感是否能达到杜诗的讽喻作用。杜甫《丽人行》极尽形容的华奢排场,隐含着对滥权者的不耻与批判,此乃‘意在言外’的诗学传统,对于画家或观画者,也存有同样的共识吗?”见《游目骋怀——文学与美术的互文与再生》(台北: 里仁书局,2011年),第177—78页。
⑧ 如《朝野佥载》曾记:“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见张鷟: 《朝野佥载》卷四(北京: 中华书局,2008年),第86页。对唐人嘲谑的详细论述,参见李鹏飞:“唐人的‘嘲谑’”,《文史知识》(1)2013: 20—24。
⑨ 如《西清诗话》曾记:“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石曼卿官册府时,五鼓趋朝,见二举子系逻舍,望曼卿号呼请救。因驻马,召问卒长,曰:‘昨夕里闬间有纳妇者,二子穴隙以窥,夜分乃被执。’曼卿力为挥解,卒长勉从之。二子叩头拜于马前。曼卿为按辔口占一绝云:‘司空怜汝汝须知,月下敲门更有谁。叵耐一双穷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见蔡絛: 《西清诗话》卷下,《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张伯伟编(江苏: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4、223页。
⑩ 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诙谐”类记:“有失貂皮暖耳者,时严冬忍冻恚甚。同榜一友,改崔颢《黄鹤楼》诗嘲之云:‘贼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余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油油。寒眸历历悲燕市,短鬓凄凄类楚囚。九十春光何日至,胸包权戴使人愁。’”(北京: 中华书局,1997年)第671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亨利·柏格森: 《笑》,徐继曾译。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
[Bergson, Henri.Laughter. Trans. Xu Jizeng.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5.]
曹雪聪 孙宗英:“‘景纯过官舍’: 北宋戏改杜诗一事考略”,《杜甫研究学刊》4(2017): 55—59。
[Cao, Xuecong and Sun Zongying. “‘Jingchun Passes the Official House’: An Examination of Rewriting Du Fu’s Poem in the Song Dynasty.”JournalofDuFuStudies4(2017): 55-59.]
陈伯海主编: 《唐诗汇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Chen, Bohai, ed.CollectedCommentsontheTangPoem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5.]
陈师道 任渊 冒广生: 《后山诗注补笺》。北京: 中华书局,1995年。
[Chen, Shidao Ren Yuan and Mao Guangsheng.Houshan’sPoemswithSupplementedAnnotati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范成大: 《范石湖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Fan, Chengda.TheCollectionofFanShihu.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1.]
高彦休: 《唐阙史》。《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Gao, Yanxiu.AnUntoldHistoryoftheTang.ATreasuryofMiscellaneousSketchesandStoriesoftheTangandFiveDynasties. Vol.2.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0.]
龚芳敏:“西方文艺批评中戏仿的功能演变”,《文艺评论》1(2015): 36—40。
[Gong, Fangmin.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Parody in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tureandArtCriticism1(2015): 36-40.]
洪迈: 《夷坚志》。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
[Hong, Mai.TheRecordsofYij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编: 《全宋诗》。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Institute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 Archives, Peking University, ed.CollectedPoemsintheSongDynas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陆游: 《家世旧闻》。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
[Lu, You.AnecdotesHeardfromMyFamil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潘建国:“唐表演伎艺‘讹语影带’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3(1996): 19—23。
[Pan, Jianguo. “A Textual Research on Tang Performing Arts ‘Insinuated Mockery (Eyu-Yingdai)’.”JournalofShanghaiNormalUniversity3(1996): 19-23.]
浦起龙: 《读杜心解》卷二。北京: 中华书局,1978年。
[Pu, Qilong.AnInterpretationofDuFu. Vol.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8.]
仇兆鳌: 《杜诗详注》。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
[Qiu, Zhaoao.DuFu’sPoemswithDetailedAnnotati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刘勰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Liu, Xie and Fan Wenlan.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ofDragonswithAnnotation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玛格丽特·A·罗斯: 《戏仿: 古代、现代与后现代》,王海萌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Rose, Margaret A.Parody:Ancient,ModernandPost-Modern. Trans. Wang Haime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阮阅: 《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九。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Ruan, Yue.GeneralCompendiumofPoetryCommentaries. Vol.19.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7.]
苏轼: 《苏轼诗集》卷十六。北京: 中华书局,1982年。
[Su, Shi.CollectedPoetryofSuShi. Vol.16.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沈德潜: 《唐诗别裁集》,长沙: 岳麓书社,1998年。
[Shen, Deqian.AnAlternativeCollectionofTangPoetry. Changsha: Yuelu Press, 1998.]
沈括 胡道静: 《新校正梦溪笔谈》第三卷。北京: 中华书局,1957年。
[Shen, Kuo and Hu Daojing.ANewCriticalEditionofMengxiEssays. Vol.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7.]
王观国: 《学林》。长沙: 岳麓书社,2010年。
[Wang, Guanguo.ForestofKnowledge.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0.]
王昆吾: 《唐代酒令艺术》。北京: 知识出版社,1995年。
[Wang, Kunwu.TheArtofDrinkingGamesintheTangDynasty. Beijing: 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 1995.]
王辟之: 《渑水燕谈录》卷十。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
[Wang Pizhi.CollectionofCasualRemarksatShengRiver. Vol.10.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王直方: 《王直方诗话》。郭绍虞辑: 《宋诗话辑佚》。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
[Wang, Zhifang.PoetryCommentariesofWangZhifang. Guo, Shaoyu, ed.CollectionofSong-DynastyPoetryCommenta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吴曾: 《能改斋漫录》。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Wu, Zeng.CasualRecordsfromNenggaiStudio.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79.]
萧涤非主编: 《杜甫全集校注》第一册。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Xiao, Difei, ed.DuFu’sCompleteWorksCollatedandAnnotated. Vol.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张岱: 《陶庵梦忆》卷七。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
[Zhang, Dai.DreamyRemembrancesfromTao’an. Vol.7.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周密 朱菊如: 《齐东野语校注》卷十六。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Zhou, Mi and Zhu Juru.WildWordsfromEastofQi,CollatedandAnnotated. Vol.16.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7.]
——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
——以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辑录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