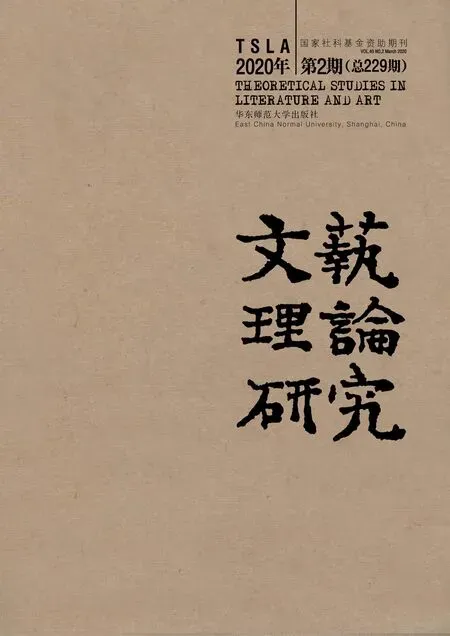迈向“行吟诗”
——评萨拉扎克的现当代戏剧诗学
赵英晖
引 言
法国现当代具影响力的戏剧理论家,较早如萨特、巴特、多尔(Bernard Dort),他们的研究注重戏剧的内容和形式中所体现出的历史、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在他们对剧作、演出、剧场等的批评中,戏剧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形态,不仅是对历史问题、时代问题和人的普遍境遇的反映、影射和反省,而且“能够并应当干预历史”(Barthes135),为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提供济世之方。他们指出法国当时流行的“市民戏剧”(thétre bourgeois,这种戏剧形式由狄德罗、博马舍提出,发展至萨特、巴特的时代已不同当初)的缺陷以及使之得以产生并流行的“市民阶层”(la bourgeoisie)在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方式和认知结果中存在的种种顽症(Sartre106,120-21)。较近的如于贝斯菲尔德(Anne Ubersfel)、帕维(Patrice Pavis)、兰格埃尔(Jean-Pierre Ryngaert),他们的戏剧批评中明显不再有萨特等人的“介入性”和社会历史担当,戏剧也不再是反映市民阶层和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问题的镜子,他们较大地受到法国符号学、叙事学发展的影响,将讨论集中在文本和演出本身,分析戏剧文本的内在结构、戏剧流派的发展理路演变、某位剧作家的创作主题、文体等方面的特色、戏剧舞台的符号意指形成机制等问题。
与他们相比,萨拉扎克(Jean-Pierre Sarrazac)有一种整体性、发展性的戏剧观,他并不断章取义地看待纷繁芜杂、奇观异象迭出的现当代戏剧,而是把它置于戏剧发展史中,为其追溯过往、描摹现状、绘制明天。他紧紧把握现当代戏剧有悖于传统戏剧(drame)①的“无序性”(le règne du désordre)(Poétique13)、“杂糅性”(hybride)(L’Avenir19),力图在混乱中发现有序,为多元的异质因素找到共同特征和共同起源,他的现当代戏剧诗学“目标与启蒙时代的莱辛一样: 在作家的群体中找到每个作家特殊的做法,找到这些做法共同的关键所在,在两者——做法和关键点——之间实现永恒的有成效的往来[……]”(Thétresdumoi11-12)于是,他找到了“行吟诗”(rhapsodie)这个富含差异又不乏统一的概念。他借用这个脱胎于荷马史诗、饱含中世纪诗歌创作特征、带有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音乐色彩、至今仍在日常法语中发挥功效的词,并突出其包含的综合、自由、异质同一的意义,他认为这个概念能够涵括现当代戏剧相较于传统戏剧(drame)最突出的特色,也代表着“戏剧的未来”(L’Avenir193-94)。
萨拉扎克的戏剧思想及其统摄概念“行吟诗”在西方戏剧理论界影响巨大,他本人于2010年获得“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Critic,简称IATC)授予的“塔利娅奖”(Thalia Prize),②他1996年创建的“现当代戏剧诗学研究团队(Groupe de Recherche sur la poétique du dram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汇集了今日法国戏剧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和来自欧洲大陆及北美的学者。③本文将对“行吟诗”概念的理论源起进行评介,对其含义进行解析,特别是解析这个概念中包含的对戏剧“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再认识,最后,指出这个概念中存在的一处尚未被学界谈及的或可商榷处,即在反对斯丛狄(Peter Szondi)“叙事剧”理论的核心理念即“叙事性”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依赖它。
一、 “行吟诗”的理论源起
“行吟诗”概念颇具独到处,但并非无本之木,而是与多个思想史和戏剧史的脉络盘根错节,萨拉扎克在与黑格尔、卢卡奇、阿多诺、利科、德勒兹等思想家,尤其是布莱希特、斯丛狄、雷曼(Hans-Thies Lehmann)等戏剧理论家的对话中延续他们的思索、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进而思虑其所未虑。
首先,“行吟诗”概念建立在对现代性经验审视的基础上。黑格尔《美学》中体现出艺术的各种特殊类型由特殊历史时代的人对现实认识的特殊性决定(第一卷94—95)的思想。萨拉扎克也是在人类生存状态的变迁中寻找戏剧演变的始因。他借助法国当代哲学南希(Jean-Luc Nancy)、德·赛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著述,当然尤其借助使得这些著述得以形成的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等西方重要思想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着重指出现代人的“分离”状态是“行吟诗”产生的精神土壤,他所谓“分离”即人与上帝或超于世界之上的绝对者的分离、与他者的隔阂和与自我的分裂(Lexique8-9),以异质因素的“无序”“杂糅”为特征的现当代戏剧正是从这样的人类生存基调中演绎出来的艺术形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然”(L’Avenir67)。如果说传统戏剧(drame)对应着古代人和近代人对世界的认识,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意义关联整体,一个可理解的、确定的、秩序井然的完整存在;现当代戏剧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反映的则是这样一种世界观的瓦解和以消解整一性和绝对性为特征的现代文明的确立。萨拉扎克由此把对戏剧形式变革问题的探讨与对人类命运、现代文明困境的思索联系了起来。
第二,萨拉扎克一改文艺批评领域将戏剧的源头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习惯,他越过这个两千年来由亚里士多德《诗学》奠基并初步架构、经法国古典戏剧理论添砖加瓦、在黑格尔《美学》中得到巩固的戏剧传统,出人意料地将“无序”和“杂糅”的“行吟诗”与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联系起来,他认为柏拉图融合理性与非理性、打通logos和mythos界限的思想是今日戏剧的精神源头。如同尼采在对艺术本质的探讨中区分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一样,萨拉扎克把从中世纪戏剧到莎士比亚,从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布莱希特到克洛岱尔(Paul Claudel),从贝克特到科尔代斯(Bernard-Marie Koltès)的“不规则”戏剧,与主张秩序、整饬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式理性主义戏剧区别开来,后者在戏剧史上长期作为准绳和范例,而前者一直为后者所不屑,即使是惊世骇俗的离经叛道者,也一直被视为附属、边缘或异类的存在,但这一脉源流始终不曾间断,直至今日壮大为一片恣肆汪洋。
第三,“行吟诗”概念是对卢卡奇、阿多诺、斯丛狄、雷曼等人的“戏剧危机”论的回应。这些戏剧理论家十分重视传统戏剧(drame)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的形变,斯丛狄称之为“戏剧的危机”(Krise des Dramas),卢卡奇称之为“戏剧的颓废”(Dekadenz des Dramas),阿多诺和雷曼甚至称之为“戏剧的死亡”(Tod des Dramas)。他们认为在这场转折中,传统戏剧(drame)在情节、人物、对白等方面均遭受到了瓦解性的冲击。萨拉扎克赞成“危机”一说,承认今日的戏剧已不复旧观,但他自始至终反对现当代戏剧研究界普遍接受的传统戏剧(drame)已死的说法,他提醒道:“必须警惕那种宣称传统戏剧(drame)已死的现代主义主张,也要警惕当下的时髦说法,称它已消亡于舞台创作。”(L’Avenir189)他认为“应当考虑传统戏剧(drame)的扩展”(Poétique16),把戏剧的现状看作百年前这场“危机”的延续和出路探寻,不存在“现代戏剧”和“当代戏剧”之分(Poétique18-19),无论是昔日的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还是今天的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科尔代斯、萨拉·凯恩、约恩·福瑟(Jon Fosse),他们都是传统戏剧向“行吟诗”转变途中的同路人。传统戏剧一直在摸索新的可能性,在一种不断的自我质疑中成为“形式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戏剧,也即更加行吟诗式的戏剧”(Poétique17-18)。
最后,“行吟诗”概念的提出尤其出于对斯丛狄“叙事剧”理论的反思。斯丛狄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论述“戏剧的”的对立概念如何在戏剧中萌生、确立并将戏剧带往“远离戏剧”(5)的方向。斯丛狄的主要观点是: 产生于文艺复兴的近代戏剧再现的是人际互动关系,剧中人物以对白方式存在,人物关系是主体间际关系,无主客之分。但19世纪末的戏剧中出现了“叙事形式的主体”(6),也即出现了一个“知道所有人的情况”(68)的超级人物,人物关系变成了这个超级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即“单个的自我与对象化的世界之间的对立”(43)关系。这样一来,“人自身的社会存在对人来说成为对象性的东西”(111),戏剧中发生了主客分离,“叙事剧”由此诞生,并引领着19世纪末以后的戏剧发展方向。萨拉扎克的“行吟诗”与斯丛狄的“叙事剧”思想渊源颇深。萨拉扎克称自己的研究与斯丛狄思想的关系是“批判的忠实”(Lexique8)。一方面,他认为在所有对现代戏剧的讨论中,唯有斯丛狄揭示出了现代戏剧之所以是其所是的内源性因素(Lexique7),而他的工作也同斯丛狄一样,通过戏剧形式研究(而不是主题研究)(L’Avenir18),在戏剧自身发现其实现自身边界迁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萨拉扎克对这样的“叙事性”是否存在持保留态度(详述见本文第三节),即便存在也是对现代戏剧特性的片面把握(详述见本文第四节)。“行吟诗”及其相关概念“行吟诗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代替斯丛狄所谓的“叙事剧”和“叙事的主体”而提出的,以期更加精准地涵括现当代戏剧的特性。
因此,以“行吟诗”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由若干概念组成的解释现当代繁多戏剧现象的思想体系。其中有萨拉扎克对戏剧史上已有概念的沿用;有他新创的概念,如“生活的戏剧”(drame-de-la-vie)、“寓言”(parabole)、“迂回”(détour)、“亚戏剧的”(infradramatique)等;也有他对已有概念的新阐释,如“歌队”“元戏剧”“复调”等。所有的承继和创造,无一不由“行吟诗”概念统摄,由之生发,最终又促成其发育。“行吟诗”在《戏剧的未来》(L’Avenirdudrame, 1985年)中问世后,便在萨拉扎克后来陆续刊行的著作中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有时作为被全面剖析的主要阐释对象(Poétiquedudramemoderneetcontemporain, 2012年),有时作为所探讨问题的最终指向(Thétresdumoi,thétresdumonde, 1995年),有时作为论述基调潜藏在他对戏剧问题的看法中(Thétresintimes, 1989;LaParaboleoul’enfanceduthétre, 2002;Strindberg,L’Impersonnel, 2018年)。
那么,萨拉扎克“行吟诗”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涵括了现当代戏剧的什么共有特质呢?
二、 “行吟诗”即“缝合”
“行吟诗”一词起源悠久,最早指吟游诗人演绎的史诗,尤指他们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演绎,他们通常从中截取片段,在演绎过程中盛装出场,既讲又演、且歌且乐(Universalis2017)。但萨拉扎克在用“行吟诗”一词命名现当代戏剧的时候,并未将我们的注意力过多引向词源学考察,而是更重视这个词今天的日常、字面含义,或者说,在他看来,这个词今天的日常、字面含义已道出了它从古希腊至今在文学、音乐、日常生活领域一直被沿用的原因,当然也是他自己青睐于它的原因。他根据两部常用法语词典《利氏》(Littré)和《小罗伯特》(PetitRobert)给出rhapsodie及与之同词根的数个单词的含义:“名词rhapsodage指缝补的动作;动词rhapsoder指缝补、整理;形容词rhapsodique指由碎片、片段组成的;名词rhapsodie指行吟诗人讲述的一系列史诗片段或非常自由的乐曲创作。”(L’Avenir21)萨拉扎克先给出rhapsodie的动词、动名词、形容词,旨在突破人们在看到rhapsodie一词时难免会陷入的由古希腊“行吟诗”和18世纪诞生的音乐体裁“狂想曲”所营造的意指空间,而是要让人们从先于这个意指空间处开始认识这个词,利用同根单词间的意义关联突出它们共同的本意:“缝合”,或曰“一系列”“片段”“自由”的“缝合”,这其实也是人们最初以之命名“行吟诗”“行吟诗人”和“狂想曲”的原因。在现当代戏剧,也即萨拉扎克所谓的“行吟诗”中,被“缝合”起来的是什么成分呢?最初,萨拉扎克认为是“戏剧(dramatique)片段和叙事(épique)片段”(L’Avenir36),后来,“行吟诗”的“缝合”内容有了进一步扩展: 除原有的dramatique和épique外,又加入了抒情(lyrique),“行吟诗”是“叙事、抒情和戏剧这三种主要文学表达形式的不断混合”(Thétresdumoi17)。
诚然,在对现当代文艺作品的描述中,“混合”“拼贴”“碎片化”“片段”等词绝无新意,已属常谈,现当代戏剧情节破碎、人物模糊、对白脱节、因果关联瓦解……与传统戏剧(drame)对照鲜明,这是理论家的共识。萨拉扎克承认现当代戏剧的异质化表现,但并不停留于共识,我们认为,他之所谓“缝合”的特殊处在于:
1. “缝合”说是继亚里士多德、布瓦洛、狄德罗、黑格尔、卢卡奇、托多罗夫等之后对文学体裁关系的再探讨。在萨拉扎克之前,黑格尔虽将戏剧体诗置于抒情诗和史诗之上,认为戏剧体诗是史诗与抒情诗的综合,兼有抒情因素和与之相对立的史诗因素(《美学》第三卷下99),但他并不认为三者的界限应当打破,他如亚里士多德一样强调戏剧与史诗在摹仿方式、摹仿内容和由此引发的接受效果上的差异。而萨拉扎克的“行吟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首先意味着体裁间界限的消弭,“传统戏剧在今日如凤凰重生,但不是自旧体裁的灰烬中,而是彻底摆脱了体裁概念”(L’Avenir19)。2.在尊重“创作的多样性、复调性”的基础上,找到多样表现的“共同关键点”(L’Avenir16)。他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将研究止步于“多样性”等外在、笼统,并不触及每一部现当代戏剧本质特征的描述,而是努力寻找只属于现当代(而不属于其他时代)戏剧且为现当代戏剧共有的特质。他从研究戏剧文本和演出的基本美学范畴(情节、人物、时空、话语、动作等)出发,最终目的是在“多样与共同之间实现永恒的、有成效的交流”,非其如此,无法认识“自我重生中的戏剧创作”(Thétresdumoi11-12)。而且,正是由于抓住了这个“共同关键点”,“行吟诗”概念的提出,对解决戏剧研究界在命名今天的戏剧时陷入的语汇困境而言,无疑是一个有效的尝试。常见的命名方式,如“当代戏剧创作”(Ryngaert的著作题目Ecrituresdramatiquescontemporaines)、“当代戏剧”(Pavis的著作题目LeThétrecontemporain)等,更多的是借助“当代”一词给这批戏剧一个时间定位,并不求彰显其共同的本质特征。雷曼的“后戏剧剧场”(postdramatisches Theater)是一个突破,将当代戏剧的某些特征——比如文本主导型戏剧被剧场主导型的“后戏剧”取代——彰显在对它的命名中,在“后”学昌盛的时代,这个词很快被广泛接受,而使人忽略了它力所不及之处,即那些并不曾在文本与舞台的竞赛中败阵的文本主导型戏剧: 例如,在法国,虽然凯恩特(Tadeusz Kantor)和威尔森(Bob Wilson)的戏剧在20世纪70年代引发了对剧场性的追求,但仍有大批戏剧创作者始终不渝地以文本立足,例如科尔代斯、维纳维尔(Michel Vinaver)、施米特(Eric-Emmanuel Schmitt)、曼亚纳(Philippe Minyana)等。
同时,萨拉扎克还强调,由多种体裁“缝合”而成的“行吟诗”是一个异质统一的事物,也因其异质统一,而成为了一个“不断发展”(Poétique394)的事物。萨拉扎克一方面指出“行吟诗”是“戏剧、叙事、抒情的万花筒”,是“充满活力的马赛克拼贴画”(Lexique189)以突出其异质包容、斑斓错杂的特色;另一方面他着重指出多文学体裁在“行吟诗”中的“缝合”是重新形成一个整体,他用希腊神话中的牛头怪米诺陶洛斯(L’Avenir19)、马驴所生的“骡子”、卡夫卡笔下半猫半羊的怪物(L’Avenir40)来比喻“行吟诗”,意在指出这头“怪兽”与亚里士多德在描述戏剧情节时用以做比的那只体态优雅、结构单纯、比例恰当、动作协调的“美丽的动物”(亚里士多德74)形成鲜明对照。并且,“通过交叉与杂交”(Poétique393)而成的这个具有内在差异的统一体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动的过程,是无中心、无边界、总在伸展变化中的“逃逸线”(Poétique393),或者如卡夫卡的怪物般具有无限形变的能力(L’Avenir40)。
那么叙事与抒情是怎样与传统戏剧(drame)“缝合”在“行吟诗”中,形成这样一个独特整体的呢?
三、 “小说化”: 传统戏剧与叙事的“缝合”
萨拉扎克所谓传统戏剧(drame)与叙事的“缝合”,是指传统戏剧(drame)通过叙事“流溢”(“débordement”,“forme extravasée”;Poétique302,393)出自身之外。
萨拉扎克“行吟诗”中的“叙事”,并不是经斯丛狄阐释的“叙事”(斯丛狄所谓的“叙事性”详见本文第一节),而是更接近巴赫金的“小说化”概念。斯丛狄对“叙事”的理解主导着戏剧叙事性研究,但萨拉扎克对之并不认同,他认为: 斯丛狄阐发这种主客体关系的出发点是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创作,而布莱希特本人在戏剧理论和实践中并未能解决主客体关系问题,他“因意识形态而忽视了某些东西: 主要是戏剧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主体性”(Lexique17),斯丛狄—布莱希特式的主客分离,即“叙事主体以一种帕尔纳斯式的冷静描述客体”(Szondi113)的现象在戏剧中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萨拉扎克对戏剧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的思考,其实是沿着萨特的路走的: 萨特在《叙事性戏剧与戏剧性戏剧》中认为,当观众发现一件艺术作品表象的内容与自己相关时(萨特称这个时候观众“参与”(participation)了艺术作品),这件艺术作品就不再是观众的“客体”(objet),而是因观众的“参与”而成为了观众的“映像”(image),如同观众在镜中照见了自己(Sartre118)。也就是说,一旦观众对艺术作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不必是完全的)理解,“客体”就成了“映像”。我们与我们的“映像”的关系是我们理解或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它;我们与我们的“客体”的关系是我们完全不理解它,而需要有人来给我们解释。叙事性与戏剧性的区别就在于“戏剧性是让我们理解,叙事性是有人给我们解释我们不理解的东西”(149)。布莱希特的“陌生化”就是要“呈现、解释、让观众评判,而不是让观众参与”(105),即让被呈现之物对于观众而言完全客体化,达到观众完全的不理解,从而实现引导观众理解的目的。但是萨特认为布莱希特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目的,因为“参与是戏剧深刻的本质”(144),一方面,因为理解必然随着解释而发生,一旦理解发生,则完全的“客体”便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布莱希特赋予自己的戏剧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使命,即:“既要展现个体行动也要展现构成这个个体行动的条件的社会行动,他要展现一切行为中的矛盾,同时也要展现产生这些矛盾的社会制度,所有这一切包含在一部戏剧中……”(105)既然是社会共同的条件,那么必定既是戏中人物的生存条件,也是观众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共情的发生、“参与”的发生、“映像”的发生便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即便是布莱希特也无法做到不引起观众的任何共情、让观众完全置身于被看事物之外、使得被看事物完全“客体”化。因而,萨特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总结说:“叙事性中有一个明显的不足: 即布莱希特从没有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解决主体与客体的问题,因而,他从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戏剧中给主体它应有的位置。”(149)斯丛狄所谓的“叙事剧”在萨拉扎克看来,同样也忽略了萨特所说的戏剧中不可避免的“参与”的必然性,即观看者对被观看事物产生共情的必然性,“世界”不可能被完全“对象”化,斯丛狄—布莱希特意义上的“叙事性”根本不成立。
萨拉扎克倾向于借助法国戏剧实例和巴赫金的“小说化”(romanisation)概念来解释,强调叙事成分的加入给传统戏剧(drame)带来的“开放”性(L’Avenir27,49)。他认为法国戏剧中早就具备不属于传统戏剧(drame),而属于“叙事”的成分(L’Avenir36),且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 博马舍称自己的“费加罗三部曲”(LaTrilogiedeFigaro)为“阿尔玛维亚家族小说”(roman de la famille Almavia);本就以小说创作与理论著称于世的左拉,在写戏时更是把对小说的主张付诸戏剧实践;维泰兹(Antoine Vitez)呼应阿拉贡(Louis Aragon)的“戏剧—小说”(Thétre-roman)《巴尔的钟声》(LesClochesdeBle, 1934年)创作“戏剧—叙事”(thétre-récit)《卡特琳娜》(Cathrine, 1975年);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叙与戏结合的《夏雨》(LaPluied’été, 1990年)被视为“可读之戏”(un thétre de lecture)……巴赫金认为小说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而言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复调性和“流动发展”(511),在于它没有固定的程式和规范(513),在小说成为主导文学体裁的时代,其他文学体裁都发生了“小说化”现象(508),也即题材具有了现实性,展现人物的空间和时间不再受限(509)。萨拉扎克反复使用“小说化”一词,尤其强调“行吟诗”是传统戏剧“流溢”出原来有限的时空维度,或者说,他尤其强调,“叙事”就是导致传统戏剧“流溢”出它原有时空维度的因素:“由于叙事剧,我们进入了空间和时间的另一个维度,遥远的维度。”(L’Avenir25-26)萨拉扎克称“传统戏剧封闭,叙事剧开放”(L’Avenir27),这种“开放”性可归纳为如下两方面: 1.戏剧时空被无限扩大,传统戏剧包含的“舞台内空间(微宇宙)和包围它的舞台外空间(大宇宙)的二元对立”遭到了质疑,萨拉扎克意义上的叙事剧的空间“是自足的,外与内相互联系起来”(L’Avenir26),如布莱希特、克洛岱尔的戏剧都“志在扩展至整个宇宙”(L’Avenir26),人物可以自由地穿行于时空中的任何地方;2.“使遥远者相逢”或曰“把相异事实并置”,叙事剧因而成为了“无止境的片段集合”(L’Avenir25-26),瓦解了传统戏剧中对于情节跨度、连贯性、完整性、集中性的要求,例如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贝克特的《最后一盘录音带》、拉噶尔斯(Jean-Luc Lagarce)的《我们是英雄》(Nous,leshéros, 2002年)等。
但是,可以看出萨拉扎克对戏剧“小说化”原因的认识与巴赫金颇有不同: 巴赫金的“小说化”思想具有小说本位的倾向,这样一场变动,对小说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而言是弱势在强势裹挟下的随波逐流,它们“被”小说化了。萨拉扎克的分析更强调戏剧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其自身的坚守和内源性发展动力,萨拉扎克认为法国历史上出现的戏剧“小说化”现象,可以从戏剧的源头找到依据,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已被理解为戏剧的原动力和发展脉络的情节,本身就是叙事性的而不是戏剧性的,因而,戏剧从诞生之日起,自身便包含了异己的力量。这样,“缝合”“戏剧”与“叙事”的“行吟诗”,不是“对一个知名范例(布莱希特)亦步亦趋的仿效”(L’Avenir38),也不是在小说强大影响力的左右下不自觉的屈从,而是诞生自本身具备自我解构以及在解构之后重生的能力的戏剧本身。
四、 “内心戏剧”: 传统戏剧与抒情的“缝合”
如果说通过“流溢”而实现的传统戏剧(drame)与“叙事”的缝合是传统戏剧(drame)的向外扩展,那么,传统戏剧(drame)与抒情的缝合则是它的内化。“行吟诗”是传统戏剧(drame)同时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改变自己。
在对“行吟诗”抒情性的研究中,萨拉扎克仍在试图解决斯丛狄的疏漏,他认为: 斯丛狄戏剧思想诞生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如日中天之时,因而,斯丛狄“热衷”(Lexique10)于把戏剧中发生的各种变化都贴上“叙事性”的标签(Poétique296)。“唯叙事论的倾向”(Lexique8)将叙事剧作为形式变革的唯一结果,但实际上,这并不能概括现当代戏剧全貌,而是对戏剧现实的“目的论歪曲”(11),“违反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戏剧的现实”(8)。萨拉扎克此处所谓“违反”在很大程度上指斯丛狄理论对现代戏剧抒情性的忽视(Poétique305),例如,萨拉扎克指出,斯丛狄特别关注《鬼魂奏鸣曲》中的人物亨梅尔在第一、二幕中的表现,亨梅尔在这两幕中对其他人物和事件进行解说,因而斯丛狄称他是“叙事的主体”,但斯丛狄却将这部戏的第三幕视作“败笔”,因为亨梅尔已死,戏剧恢复为少女和学生间的传统对白。可是在萨拉扎克看来,第三幕正是这部戏的“独特性”和“现代性”所在,这段穿插着沉默、独白、祈祷的对白是戏剧抒情性的体现(Lexique12-14)。
抒情“是特殊主体的表达,用优美动听、富有节奏感、以音乐为模范的语言,使主体情感生活经验的内容变形甚至升华”(Maulpoix),它的源泉是“主体的内心生活”(黑格尔,第三卷下199),因而“精神活动的主体”(187)在抒情中起主导作用。“行吟诗”的“抒情性”主要指各种形式的内心表达,因为萨拉扎克也使用“主体内戏剧”(thétre infrasubjectif)(Thétresintimes19)或“内心戏剧”(127)来指称“行吟诗”。与之相反,他用“主体间戏剧”(thétre intersubjectif)(Thétres du moi81)来指称传统戏剧(drame),传统戏剧(drame)以人际互动关系为创作基础和展现内容,这就意味着将所有与人际互动无关的内心表达边缘化。
萨拉扎克所谓“行吟诗”的“抒情性”含义有二。
1. 人物抒情的变化。萨拉扎克指出,在“行吟诗”中,“人际(interpersonnel)或主体间际(intersubjectif)关系常常让位于主体内心(intrasubjectif)或者我与世界的关系”(Poétique66-67),改变人物命运的事件不是如在传统戏剧(drame)中那样在人际互动中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的层递被呈现,而是在大幕拉开前就已发生,戏剧要展现的不是人与人的冲突本身,而是冲突之后人的状态,即“行吟诗”“描绘的不是事件,而是事件对主体的影响”(Poétique304),“行吟诗”的“抒情性”是指“对被世界和自身冲动所影响的主体自身的再现,这个主体力图从内心进行自我表达和思考自我”。(Lexique99)。易卜生、斯特林堡、奥尼尔、皮蓝德娄、贝克特、杜拉斯等人的作品中都有这样的“主观化”(Thétresdumoi10)现象,“把整部戏剧集中在人物心里”(Lexique13)。
传统戏剧(drame)并非不呈现“事件对主体的影响”,例如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甚至将对内心世界的展示提升到与对外部世界即行动的展示同样重要的地位:“诗人充分地达成艺术的多样化目标,给观众打开双重视野,同时照亮人类的外部和内心;通过他们的话语和行动来照亮外部,通过旁白和独白来照亮内心;总的来说,就是把生活的戏剧和内心的戏剧交织在同一幅画面中。”(Hugo,“PréfacedeCromwell”)《克伦威尔》(Cromwell, 1827年)和《欧那尼》(Hernani, 1830年)中,几个重要人物均有大段独白吐露内心的真情实感。浪漫主义剧作家已认识到人际冲突无法展现主体的全部思虑。
但是,传统戏剧(drame)中的抒情段落是与行动紧密相关的,例如罗德里戈(LeCid, 1636年)面临家族荣誉和儿女私情冲突时的内心矛盾、费加罗(LeMariagedeFigaro, 1784年)对自己漂泊生涯的回顾和对自我身份的焦虑与求索……谢拉尔(Jacques Sherer)对此有精辟总结: 很多时候,作者安排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白,其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抒情,还为了让人物在抒情的同时,在思考中作出决断,从而推动剧情发展(245—48)。也即是说,在传统戏剧(drame)中,抒情的出现必须能在“主体间戏剧”情节发展中找到原因,它的结束也必须能够推动“主体间戏剧”情节发展,它并非自足、独立,它需要一个来自外部的原因发动,并指向一个自身之外的目的,所以罗德里戈的大段抒情之所以被允许镶嵌在“主体间戏剧”中,是因为两下权衡的情感挣扎最终导向了一个决断,这个决断引发的行动推动了情节进展。
而在“行吟诗”中,存在大量不具备决断功能的内心表达,人际关系不是抒情产生的原因,也不是抒情要推动的对象,有的戏剧中甚至没有人际关系,例如在梅特林克的《闯入者》《盲人》《室内》中,人物在惶惶不安中等待一个已发生的灾难被揭示出来,人对事件的感受,或者说事件对人内心的冲击是戏剧要展现的全部内容。萨拉扎克指出马拉美、叶芝、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巴列—因克兰(Ramon Maria del Valle-Inclan)以及《地狱》(Inferno, 1898年)之后的斯特林堡的作品都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作“戏剧诗”(Poétique304)。
2. “行吟诗”也是作者个体体验的抒发。摹仿论美学观念统治下的传统戏剧(drame)强调隔绝虚幻与真实的“第四堵墙”,作者这个属于现实世界的存在不应当出现在虚构作品中,而是必须隐身(黑格尔,第三卷下266—67),在整部戏剧中保持不可见和沉默,不能作为抒情主体进行直接的情感表达。而且,这也是由戏剧的“群体性”决定的,戏剧本就诞生于祭祀祝祷的宗教集体仪式,“戏剧的宗旨是群体效应”(卢卡奇2),“群体绝不会对完全个体性的事件,或是对只从个体角度对事件进行观察而得出的结果产生自发或强烈的感受”(卢卡奇3),“只有实现观众的统一才有戏剧”(Sartre 20)。斯坦纳指出浪漫主义时期出现了违反这一原则的剧作家(Steiner 136),而后来的斯特林堡更是将戏剧这个“公共形式前所未有地私有化了”(294)。
萨拉扎克认为“行吟诗”的重要特征就是戏剧创作者如同诗歌创作者一样将自我展现在作品中。他称斯特林堡是开“第一人称戏剧”(Thétresintimes28)或称“自传式戏剧”(31)之先河者,因为斯特林堡“总在人物中强加他自己的在场,人物是他的投射和影子”(Strindberg,L’Impersonnel17)。继斯特林堡之后,阿达莫夫(Arthur Adamov)、杜拉斯、拉噶尔斯(Jean-Luc Lagarce)等剧作家都在探索在戏剧中进行主观表达的可能性: 他们会塑造与自己身心经历高度吻合的人物,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直接展现在舞台上,戏剧的台词、情境、布景、情节、人物形象都成了作者内心的直抒胸臆,而斯特林堡晚年在斯得哥尔摩创建“内心剧院”(Intima Teatern)④的目的也在于此,即向观众呈现“一个存在或一个事物的最内心、最本质的东西”(Thétresintimes67)。
但是,萨拉扎克反复强调: 注重内心表达的“行吟诗”并非“戏剧的私有化”(Thétresdumoi130),“行吟诗”虽然不再在主体间关系的基础上展开,却并没有完全回缩进私人生活,而是表现出我与世界间的张力:“所谓‘内心的’(intime),不是‘私密的’(intimiste),‘私密的’(intimiste)意思是戏剧行动紧缩、封闭、隔绝在私人生活或主观想象范围内,而‘内心的’(intime)蕴含着由内心和内部空间生发的对外部世界(社会、宇宙……)的向往。”(Thétresintimes68)“行吟诗”是超个人的,不是唯我论式的自我无限膨胀,而是在我与世界的关系这个维度中展开。从萨拉扎克的解说中,可以区分出我与世界的两种联系方式: 一是人物在世上做真实或梦幻的旅行,站在自身的角度看世界,例如《一出梦的戏剧》(LeSonge, 1901年)、《缎子鞋》(LeSoulierdesatin, 1929年)、《罗贝托·祖科》(RobertoZucco, 1988年);另一种是站在世界的角度看待自身,人物活动的物理空间闭塞,但他的当下存在通过他的内心与他的过去未来、与世界的时局动荡、与天地间不为人认知和掌控的神秘力量紧密联系,例如,斯特林堡戏剧中的人物带着焦虑的心情不断倾听他周围环境中的声响,梅特林克戏剧中人物的内心在宇宙神秘力量的压迫下展现出来,这个力量是基督教上帝、古代的命运观念与神秘自然的交融。
五、 一处矛盾:“行吟诗人”
无论是“小说化”“内心戏剧”的说法,还是对“无序”和“杂糅”的强调,萨拉扎克的“行吟诗”理论志在实现对斯丛狄戏剧理论的修正和拓展。然而,萨拉扎克虽对斯丛狄戏剧思想的关键概念“叙事性”和“主客分离”持反对态度,提出以“小说化”取代之并以“抒情性”补充之,但他在提出“行吟诗”的关联概念“行吟诗人”时,却不自觉地接受了斯丛狄在叙事剧中发现的主客分离现象,也即主体对客体的反思维度。
如本文第一节所述,斯丛狄在阐释叙事剧中主客体分离现象时指出,“叙事性”即出现一个对其他人物行动进行叙述和评价的超级人物,人物关系由主客不分变为主客分离。也就是说,叙事性戏剧和非叙事性戏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虚构世界发生了叙述分层,分化为普菲斯特(Manfred Pfister)所说的“内交际系统(人物与人物之间)”和“中间交际系统(虚构的叙述者和虚构的接受者之间)”(4—6),⑤“叙事的自我”和被它“对象化的世界”分属不同“交际系统”,也即不同叙述层次,一个叙述层次对另一个叙述层次的观察、评说构成了戏剧中的反思维度,而在非叙事性戏剧中则不存在这样的叙述分层。对叙事性戏剧中这个反思维度的发现,并不止斯丛狄、普菲斯特二人: 萨特对“客体化”的解释中也突出了叙事剧中这样一种反思维度,并希望市民戏剧的风貌、市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能够在这样的一种反思中发生改观;阿贝尔(Lionel Abel)等学者将那些具有自我意识、检视自身的剧作称为“元戏剧”,“元戏剧”其实就是发生了叙述分层的戏剧。“叙事的自我”“中间交际系统”“元戏剧”是斯丛狄、普菲斯特和阿贝尔对同一现象从不同角度的阐述和命名。
萨拉扎克称斯丛狄的“叙事的主体”概念“值得关注但尚有不足”,不足在于斯丛狄没有认识到“这个叙事的主体同时也是戏剧的主体和抒情的主体”(Poétique312),也即是说,萨拉扎克认为现当代戏剧中并不存在斯丛狄所谓的纯粹的“叙事形式的主体”,如果有,那么也是一个融戏剧、叙事、抒情功能于一身的异质杂糅的主体,它既是人物和事件的观察者,也是主观感受的表达者,并且依然保有传统戏剧人物作为行动载体的功能。所以,他主张用“行吟诗人”(rhapsode)代替“叙事的主体”。
他在解释“行吟诗人”时与解释“行吟诗”时一样,也强调“缝合”之意,称“行吟诗人”是“一个半隐半显的操作者或称意识”(Lexique82),“把被撕裂的东西连接起来并把被他连接起来的东西撕裂”(L’Avenir25)。即是说,“行吟诗人”一方面把戏剧极大地不规则化(叙事化、抒情化),造成了各种传统戏剧要素(人物、对白、情节、场次衔接)的稀释、瓦解,例如斯特林堡、皮蓝德娄、科茨(Kroetz)、热内(Jean Genet)等作家;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将这些碎片并置而使其互相冲撞出意义,他们的工作是“将‘材料’布置、安装,使之成为‘主题’”(Lexique82)[这里所谓“材料”,指一切可用来构成戏剧的东西,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属于剧场的动作、声音、声响(Lexique110);“主题”指“经构建、编排而彰显出的事件和动作”(Lexique81)]。“行吟诗人”是“无序”“杂糅”的“行吟诗”实现异质统一的关键角色。与之类似,亚里士多德也称戏剧诗人是“工匠”(陈中梅,《诗学》“注释”228),他要制作的是“情节”,所谓“情节”(fable)既指材料也指对材料的加工: 指戏剧选取的神话或帝王将相的故事,也指戏剧动作的连接,这个连接工作必须把这些事件组织成单一、完整(有“结”有“解”)、统一(各个部分比例恰当、联系紧密、运作协调,构成有机体系,拥有统一的秩序、统一的目的)、自足(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依赖于外部原因)的整体。与情节的“工匠”相比,“行吟诗人”的“材料”广泛得多,对“材料”的组织方式不拘一格。与斯丛狄的“叙事形式的主体”概念相比,萨拉扎克的“行吟诗人”确实将现当代戏剧更多的共有特征囊括了进来。
然而,问题在于: 1. 如本文第三节所述,萨拉扎克在对“叙事性”的解释中,坚持认为“叙事性”只是同一层面的空间距离变化及其导致的异质融汇,否定斯丛狄指出的主客分离现象,也即反对叙述分层的观点。但萨拉扎克列举“行吟诗人”的具体存在方式时(Pétique315—28)却明显表现出叙述分层思想,他说行吟诗人可以是整部戏剧不现身的策划者(相当于小说中的叙述者),也可以若干形式现身于戏剧中(如歌队、通报者、舞台指示、既属于剧情又对剧情进行评价的人物等),也即存在两个交际系统,一个属于人物,另一个属于行吟诗人。并且,在对“行吟诗人”的描述中,萨拉扎克用了如下说法:“作者—行吟诗人”(Poétique330)、“它处于戏剧与现实的边界”(L’Avenir45)、“作者的参与或显或隐”(L’Avenir52)……这些说法明显混淆了两个叙述层次——“外交际系统”与“中间交际系统”。当然,鉴于萨拉扎克的“行吟诗人”是抒情主体,而作者与抒情主体一致正是抒情作品的特征,萨拉扎克在解释“行吟诗”的抒情性时,举出了斯特林堡等剧作家以戏剧直抒胸臆的做法(参见本文第四节),所以“外”与“中间”交际系统的混合在对“行吟诗”的解释中无可厚非。但应当注意的是: 无论“行吟诗人”属于“外”还是“中间”交际系统,他都已不在“内交际系统”中了,与剧中人物处于两个叙述层次,对剧中人物和事件起支配作用,也即是说,萨拉扎克在提出“行吟诗人”概念时与斯丛狄等人一样注意到了叙述分层问题,但却在对“行吟诗”叙事性的解释中否定这一现象的存在,萨拉扎克的“行吟诗”理论在对待“叙事性”所包含的这个叙述分层、反思维度的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矛盾。
2. 萨拉扎克的“行吟诗人”概念体现出一种作者意图决定论思想。萨拉扎克说“行吟诗人”是“在行吟诗冲动的激发下”“在行吟诗计划驱策下”行动的(Poétique338),他甚至使用了“démon”这个源于苏格拉底,后被文艺理论家解释为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并加以阐发的词汇,以及“作者意愿”(Poétique331)这样更直白的表述来解释行吟诗及其意义的形成,也即将新戏剧形式的出现归因于一个由“行吟诗人—作者”设定的、主观的规划、企图。“行吟诗”理论背后隐藏着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批评的那种主体美学——把艺术作品的本源归结为艺术家(1),在艺术家内心为艺术作品寻找根据。并且,萨拉扎克忽略了观众接受的作用,也即阐释学告诉我们的,作品的意义决定于接受者的预期视阈或经验视阈,而非作者意愿。
结 论
萨拉扎克认为,19世纪末至今发生的戏剧变革原因有二: 一是人“把握现实的典范方式发生了危机”,二是“主体间际关系及其艺术表现发生了危机”(Lexique139)。“行吟诗”就是这个双重危机下的产物: 一方面,它或依然摹仿现实,但从对客观现实的摹仿更多地转入对主观现实的摹仿,或否认摹仿再现,不以相似性、符合论为依托,戏剧中的一切都完全可与现实比肩,而不是屈居其次的复制品;⑥另一方面,戏剧由展现间际氛围内的人转入表现与绝对、与他者和与自我“分离”的人。在“行吟诗”中,体裁的界限不再构成任何障碍,具有与传统戏剧(drame)不同的表现内容、比它更善于呈现个体生命体验的叙事和抒情,与它发生了多重的交织与碰撞,使它发现并卓有成效地尝试了迁移自身边界的可能性。“行吟诗”是戏剧在元规则、普遍性的合法地位遭到质疑的现代文明中,在面对异质性因素,并反思自己的传统规定性时表现出的新姿态,新的戏剧形式在对现代性经验的审视和对统一可能性的探求中发生了。
注释[Notes]
① drame(英语为drama)是一种特殊的戏剧形态,在西方戏剧中长期占据至高的规范位置,它通过扮演而不是叙事来摹仿,由一系列事件构成情节,这些事件由情境、人物性格和目的引发,不同人物因性格和目的不同而必然形成冲突,事件之间因果相继,冲突不断升级,但最终必须化解,秩序重新建立。详解可参阅拙文“也论‘戏剧性’——与董健先生、谭霈生先生商榷”,《戏剧艺术》4(2019): 12—25。本文为行文方便,称drame为“传统戏剧”,而以“戏剧”作为drame、叙事剧、“行吟诗”等所有戏剧形式的统称。
② 该奖项为双年,2006年创始,奖励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有杰出贡献者。至今共7人获奖,获奖者除萨拉扎克外,还有今日在戏剧创作和批评界享有盛名的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巴尔巴(Eugenio Barba)、雷曼(Hans-Thies Lehmann)等。参见IATC会刊CriticalStage官网
③ 参见法国戏剧研究院(Institut de Recherche en Études Thétrales简称IRET)的网页
④ 国内学者常将之译作“亲密”,我们认为译作“内心”更符合斯特林堡之意。
⑤ 还有一个“外交际系统”指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不属于虚构世界。
⑥ 否定摹仿再现的剧作,以阿尔托的戏剧或者雷曼在《后戏剧剧场》中提到的德国当代剧作为代表,萨拉扎克对之涉及不多。盖因雷曼已有著述,认为传统戏剧(drame)已死,现当代戏剧以全面的剧场性为特征;而萨拉扎克认为传统戏剧(drame)未死,剧场性并非现当代戏剧的全貌,他的著述重在解释传统戏剧(drame)的开放和与其他体裁的融合。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亚里士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年。
[Aristotle.Poetics. Trans. Chen Zhong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米哈伊尔·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Bakhtin, Mikhail.TheCompleteWorksofBakhtin. Trans. Bai Chunren and Xiao He. Vol.3.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Barthes, Roland.Ecritssurlethétre. Paris: Seuil, 2002.
黑格尔: 《美学》,朱光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年。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Aesthetics. Trans. Zhu Guangq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Heidegger, Martin.Holzwege. Trans. Sun Zhoux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Hugo, Victor. “Préface deCromwell.” 15 February 2019
汉斯-蒂斯·雷曼: 《后戏剧剧场》,李亦男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Lehmann, Hans-Thies.PostdramaticTheatre. Trans. Li Yin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格奥尔格·卢卡奇: 《卢卡奇论戏剧》,罗璇译。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Lukács, György.KritischeSchriftenUberDramaUndTheater. Trans. Luo Xuan.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6.]
Maulpoix, Jean-Michel. “Le lyrisme, histoire, formes et thématique. ...” 10 January 2019
Pavis, Patrice.LeThétrecontemporain:Analysedestextes,deSarrauteVinaver. Paris: Armand Collin, 2004.
曼弗雷德·普菲斯特: 《戏剧理论与戏剧分析》,周靖波、李安定译。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
[Pfister, Manfred.TheTheoryandAnalysisofDrama. Trans. Zhou Jingbo and Li Anding. Beijing: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Press, 2004.]
Ryngaert, Jean-Pierre.Ecrituresdramatiquescontemporaines.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Sarrazac, Jean-Pierre.Thétresdumoi,thétresdumonde. Rouen: Médianes, 1995.
- - -.L’Avenirdudrame.Ecrituresdramatiquescontemporaines. Vevey: Éditions de l’Aire, 1981.
- - -.Thétresintimes. Arles: Actes Sud, 1989.
- - -.Poétiquedudramemoderne,DeHenrikIbsenBernard-MarieKotlès. Paris: Seuil, 2012.
- - -.Strindberg,L’Impersonnel. Paris: L’Arche, 2018.
- - -. (dir.),Lexiquedudramemoderneetcontemporain. Belval: CIRCE, 2010.
Sartre, Jean-Paul.Unthétredesituations. Paris: Galliamrd, 1973.
Sherer, Jacques.LaDramaturgieclassiqueenFrance. Paris: Nizet, 2001.
Steiner, George.Mortdelatragédie. Paris: Gallimard, 1993.
Szondi, Peter.PoésiesetPoétiquesdelamodernité.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1982.
彼得·斯丛狄: 《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王建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Szondi, Peter.Theoriedesmodernendramas(1880-1950). Trans. Wang Ji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Universalis2017. Pari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