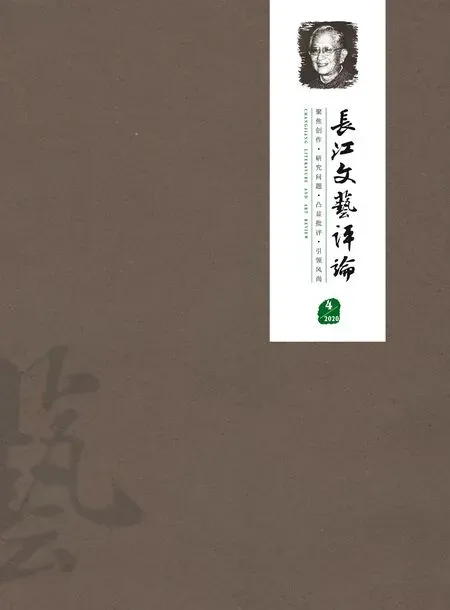新力量导演的“电影节生存”与艺术电影的多元样貌
——中国新力量导演系列研究之一
◆李 卉 陈旭光
近年来,中国新力量电影导演的涌现,以其开放性、多元性终结了沿袭多年的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作为一个开放而松散的群体,新力量导演既有群体层面的诸多共性,亦存在个体层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偏重商业诉求、以获取票房为目标的商业电影导演,如徐峥、大鹏、郭敬明等;游走于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在保留个性化表达的同时兼顾市场的“体制内作者”导演,如宁浩、刁亦男、曹保平等;侧重个人表达与艺术创作的艺术电影导演,如杨超、毕赣、万玛才旦等。其中,后两类导演的涌现,离不开电影节体系的孵化与推动。赵宁宇在《导演的产业化生存》中提出了导演的“产业化生存”[1],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力量导演的“三种生存”,即“技术化生存”“产业化生存”“网络化生存”[2]。笔者认为,对于新力量导演群体中偏重中小成本艺术电影创作的那一部分青年导演而言,“电影节生存”则是他们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
与第五代导演“出口转内销”的海外获奖、国内卖座的双赢路线,及第六代导演成名之初的独立制片、海外获奖、全球巡展而国内被禁的电影节路线不同,新力量导演置身于中国加入WTO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及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并不断升级的新阶段,依托于日趋丰富多元的国内外电影节平台,在获得官方命名、享受政策扶持的同时,亦找到了通往国内外电影节展与院线市场的道路。“体制”与“市场”作为曾经制约第六代导演创作并使其转向海外电影节生存的两大要素,对新力量导演来说并非桎梏,甚至得以借力,以“体制内作者”的身份自觉,借助电影节平台初试啼声,进而走向市场,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新活力。
一、“创造”新导演:新力量导演的“电影节生存”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容,以及电影格局由大片时代向多元类型的演化,电影行业急需一批新鲜力量来提供优质内容,填补市场空缺。与之相应,各种“扶持计划”层出不穷,既有政府发起的资助项目,如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起并主办的“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扶持计划”(简称青葱计划)等;也有影视公司主导的扶持项目,如民营企业光线传媒发起的致力于把演员打造成导演的“新导演培养计划”、互联网影视公司阿里影业的“A计划”等;还有依托于名人的各类扶持项目,如贾樟柯的“添翼计划”、宁浩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等。
在这一潮流之下,国内各大电影节增设了创投板块与青年导演训练营,包括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等在内,这些电影节在评奖体系之外,亦不断发展和完善新导演的扶持与培养系统。“创造”新导演,而非仅仅“发现”他们,是电影节发展至今形成的新模式,所谓“嫡系导演”见诸世界各大电影节,中国亦不例外。新力量导演的电影节生存,首先是一种借助电影节平台实现融资、完成拍摄的电影创作方式。相比第六代导演初出茅庐之时因缺乏融资渠道而在国营制片厂体制之外独立拍片的窘境,当下的新力量导演拥有更为多元的筹资渠道、更为可靠的体制内成长方式,电影节生存只是新导演出道的其中一种方式,坚持这一路线的新导演往往有着坚定的艺术追求和明确的作者意识,以拍摄“艺术电影”而非追求商业利益为初衷,而新时代的国内电影节平台在发挥传统的艺术评价功能的同时,视电影为一种流通交易的商品,为新导演的艺术电影作品走向观众、走上市场配备了一整套支持体系。董越导演的长片电影处女作《暴雪将至》即受益于FIRST影展创投项目,通过在创投会上结识新锐制片人肖乾操,项目由几千字的大纲一步步发展成由段奕宏、江一燕等实力演员加盟的中等投资电影,并在制片人的运作下入围“戛纳制片人工作坊”,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关注度。最后,《暴雪将至》在院线上映的同时,亦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等多个奖项,成为新导演借助电影节获得投资、完成创作、走向市场、收获奖项的典型案例。越来越多的新导演被国内电影节发掘与培养,继而走上市场、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电影新力量的重要源流之一。
新力量导演的电影节生存,还是一种借由电影节的影响力与评价机制而建立作者身份、获取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的方式。学者玛莉·德·法尔克将电影节称为“成长站点”,认为其悬置了电影世界的商业市场法则,放大了电影作品的审美成就和文化特性,“发挥着通往文化合法化的作用”[3]。在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的分类标准下,除C类(非竞赛型电影节)外,A类(竞赛型非专门类电影节)、B类(竞赛型专门类电影节)和D类(纪录片与短片电影节)均以奖项评定为核心环节,邀请知名电影人组成评委会,对参赛电影的艺术水准做出专业评判。作为短暂而集中的节庆性质的活动,电影节以明星、红毯、大师、首映礼、颁奖等仪式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其中专业媒体与意见领袖的打分与评价对影片与导演在影迷和公众群体里的口碑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新导演若能入围电影节并获奖,意味着其创作风格与导演身份得到了专业电影人的肯定,并将借助电影节自身的广告效应,一举成名天下知。
新力量导演中,刁亦男、杨超、毕赣等导演仍延续了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海外电影节路线,但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第五代导演所依托的国营制片体制及所背负的“东方主义”指摘,亦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第六代导演所面临的西方电影节与国内官方之间“你奖我禁、我禁你奖”[4]的意识形态斗争困境,新力量导演的海外电影节生存置身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入WTO后的新型国际关系体制与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新型市场体制之中,“影片的事实”[5]逐渐剥离对立性意识形态的审视目光而成为衡量中国电影能否在西方电影节获奖的评判标准,《白日焰火》的柏林获奖与市场卖座即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电影场域中新力量导演不同于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海外电影节生存路线。
曹保平、万玛才旦、松太加等导演则借助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于2004年的亚洲新人奖登入影坛,并从本土走向海外。随着专注发掘、推广青年电影人及其作品的“FIRST青年电影展”(2006年)、“平遥国际电影展”(2017年)的设立,越来越多新力量导演被本土电影节挖掘并培养,出身FIRST影展的青年导演有郝杰、王一淳、张涛、李非、张大磊、马凯、蔡成杰、周子阳、仇晟、顾晓刚等;出身平遥国际电影展的青年导演有文晏、刘健、鹏飞、白雪、霍猛、吕聿来、梁鸣、叶谦、杨荔钠等。其中诸多作品在获得国内电影奖项的同时,亦不断入围重要的国际电影节,这一方面证明了新力量导演自身的创作实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上海国际电影节、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等国内电影节所搭建的国际化电影评价平台,吸引了诸多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到此选片,有力推动了新力量导演的海外拓展之路。此间,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全球15个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充分发挥了其与全球各大电影节展的合作优势,与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世界各大电影节开通“国际直通车”,推介“亚洲新人奖”的入围及获奖作品走向世界,并携带正在融资阶段的电影创投项目登陆海外各大电影节,助力新人导演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及合拍可能,以电影节的平台优势与国际影响力扶植中国电影新力量。尽管如此,新力量导演群体中,除了刁亦男斩获柏林金熊大奖之外,较第五代、第六代导演而言,少有在世界三大电影节获得重要奖项,部分原因可能正在于电影节扶持体系所仰赖的资本力量,使得新力量导演电影作品的艺术性相对萎缩。
不同于奥斯卡金像奖只有颁奖典礼的评奖体系,电影节在评奖之外,还拥有完善的展映平台与放映体系,与商业院线形成互补之势,共同维护着电影工业的多样化景观。作为影迷的节日,放映是电影节的立身之本,使得许多无缘院线的艺术电影得以走向观众。上述提及的诸多新导演之获奖作品,部分有幸进入院线,部分则借助电影节巡回展映系统,游荡于国内外各大影展,实现小范围的公开放映,借以收回成本。以FIRST青年电影展为例,其放映体系包括影展放映/主动放映(非电影节期间的线下放映平台),影展放映内部又可分为面向影迷的常规放映与面向公司的产业放映。在产业放映环节,通过征集并筛选入选片单,FIRST为新导演与宣发公司、出品公司、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积极推动新导演的电影作品进入商业院线与国外影展。主动放映分为春秋两季,分别面向高校与城市艺术空间进行巡展,FIRST将策展的权力下放给观众,由当地的策展群体与放映厂牌自主策划放映,不断塑造与培养着乐意接受与欣赏新导演和艺术电影的影迷群体。如此多样化、跨地性、观众自组织的长线放映机制,在商业院线、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之外,打造了一条推广新导演、宣传艺术电影的放映渠道,以此构成了新力量导演电影节生存的重要方面。
创投融资、艺术评判、展映平台构成了电影节网络兼顾资本与艺术、制作与渠道的“垂直整合系统”,选择这一电影节生存模式的新力量导演,在拥有艺术之名庇护的创作自由之时,亦在积极推动艺术电影市场化的新趋势下,面临着艺术与商业的双重考量。尤其是借由电影节创投会实现融资的新导演,更是在创作伊始便面临着“电影节品味”与“市场可行性”的双重期待视野,其电影创作呈现出力图平衡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倾向,显影出“体制内作者”的身份意识,从而使得新力量导演的艺术电影创作呈现出多元样貌。
二、双重期待视野下新力量导演艺术电影的多元样貌
艺术电影是一种独特的电影实践,有其“确定的历史存在,一系列形式传统,以及固有的观赏程序”[6]。电影节作为艺术电影重要的评价、推广、放映场所,其运作体制对艺术电影的生产模式与形式风格具有显在的影响。基于电影节的艺术品位,新力量导演的艺术电影创作呈现出内容上的现实性与在地性,形式上的探索性与创新性;与此同时,基于电影节的产业定位与市场面向,类型化与商业化元素亦开始愈加频繁地出现在新力量导演的艺术电影创作之中,形成了多重面向与多元样貌。
首先,从内容层面来看,关注现实、表达情感成为许多新力量导演艺术电影创作的重要特征。FIRST青年电影展在创办之初以复苏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为宗旨,而现实主义正是艺术电影重要的形式传统之一,在心照不宣中构成了某种“电影节品味”。不论是出于对“电影节品味”的有意迎合,亦或是受制于资金和技术因素,再或是出于导演自身的美学品味和创作初衷,现实性与情感性均成为新力量导演艺术电影创作的典型表征。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观照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表达自我对世界的看法,成为诸多新导演不约而同的创作选择。《八月》《老兽》《春潮》《柔情史》《过昭关》《四个春天》《春江水暖》等电影均是从导演的个人情感与生活体验出发,描绘家族亲情的不同形式;《嘉年华》《喜丧》《中邪》《过春天》《白日焰火》等电影则将目光投向社会,探讨儿童性侵、农村养老、封建迷信、水客、情杀等社会现象。“边缘人物”“底层生活”依然是新力量导演艺术片创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其所占比重与第六代导演相比有所降低,芸芸众生里的普通人开始走上前台,他们是《柔情史》《春潮》里在柴米油盐中掀起生活战争的妈妈和女儿、《过昭关》里坚守乡土社会人伦亲情的爷爷和孙子、《四个春天》里相濡以沫终生共度的父亲和母亲,俯视底层人的悲悯视角转变为置身其中的共情,切身的情感体验成为新力量导演创作艺术电影重要的灵感来源。
在个体性与现实性的基础上,出自某一地域的新导演群体形成了对故乡的多重描述,凸显出典型的地域特色。如万玛才旦开启的藏地电影新浪潮。2005年,万玛才旦的首部电影长片《静静的嘛呢石》问世,成为第一部由藏族人拍摄的藏语电影。此后,万玛才旦以开路者的精神打开了藏语电影的国际国内市场,并从一开始便有意识地培养藏语电影的创作班底,松太加、德格才让、拉华加、达杰丁增等藏族青年导演,均曾是万玛才旦电影剧组的核心创作人员,如今已自立门户,走上了藏语电影的创作之路。此外还有近年集中涌现的各地电影人群体,虽不能像新世纪以来的藏语电影创作一样称之为“新浪潮”,但却在银幕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质,如以顾晓刚(《春江水暖》)、仇晟(《郊区的鸟》)、祝新(《漫游》)为代表的杭州青年导演群体,以毕赣(《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饶晓志(《无名之辈》)为代表的贵州青年导演群体,以忻钰坤(《暴裂无声》)、周子阳(《老兽》)、张大磊(《八月》)为代表的内蒙古青年导演群体等等,更有成立于2016年的“内蒙古青年电影周”致力于扶持内蒙古籍电影新人、展示以内蒙古为拍摄地的优秀影片,以电影节展的形式积极培育地方电影文化,鼓励新力量导演在银幕上呈现故乡的风景,丰富中国电影的空间景观。
其次,从形式层面来看,新力量导演的艺术电影创作一方面秉持着艺术电影革新电影语言、探索叙事手法、推动电影艺术创新与发展的使命精神,另一方面则在电影节体制的影响之下,呈现出类型化的思维倾向与叙事方式。激进与保守、艺术与商业,种种看似对立的矛盾力量潜伏在新力量导演的艺术电影创作之中,使其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电影形态,并于冲突对立、妥协调和中暗含着革新求变的能量。
艺术探索层面,毕赣在《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尝试的超长镜头拍摄与3D技术的结合,杨超在《长江图》中重申的胶片美学,马凯在《中邪》中探索的伪纪录片形式,表现出身处技术大变革时代的新力量导演对于电影媒介属性的反思与电影语言形式的探索;忻钰坤在《心迷宫》中精心编织的多角度限知视角叙事,黄梓在《慕伶,一鸣,伟明》中以人物为主视点的段落叙事,或以智性和匠心邀请观众参与叙事的游戏,或以情感接续视角的转换,体现出新力量导演对电影叙事形式的探索和思考。
在关注当下、革新形式的同时,新力量导演的艺术电影创作也呈现出类型化的倾向。随着《小丑》《寄生虫》在2019年的威尼斯、戛纳、奥斯卡等各大电影节摘得大奖,电影节体系对类型化电影的认可将进一步推动艺术电影的类型化趋势。悬疑犯罪片作为既能满足推理的智性要求,又能展现视觉的暴力奇观,还能批判现实、揭露人性的类型电影,成为许多新力量导演借以观照现实、编织复杂叙事、表达批判立场、平衡艺术性/商业性的重要类型,刁亦男的《夜车》《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忻钰坤的《心迷宫》《暴裂无声》,曹保平的《烈日灼心》《追凶者也》,李非的《命运速递》,董越的《暴雪将至》、徐磊《平原上的夏洛克》等新力量导演的艺术电影,均在悬疑犯罪片的类型框架下展开叙事,有的还融入了喜剧元素,进一步增强了电影的戏剧性和趣味性。此外,《过昭关》对公路片框架的借鉴,《中邪》对恐怖片氛围的营造,《过春天》《嘉年华》《黑处有什么》对青春片叙事的拓展,均体现出新力量导演以其艺术修养提升中国类型电影品质、丰富中国类型电影创作的重要作用。即便是毕赣这样剑走偏锋的艺术电影导演,在创作之时亦选择从类型化思维入手,“我创作剧本有一个习惯,比如《路边野餐》我先是把它写成一个公路片,然后再去‘破坏’它;到《地球》的时候,我先写的其实是一部黑色电影,类似于比利·怀尔德《双重赔偿》。然后从每一场戏开始破坏它。”[7]作为深受好莱坞电影影响的新一代,类型范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力量导演的电影创作,使得艺术电影与类型电影的界限日趋模糊,并在彼此靠近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在增强艺术电影趣味性、扩大艺术电影受众面的同时,亦拓展了中国类型电影的样式与格局,使其在成规与创新之间维持着不断向前发展的动态平衡。
借助电影节体系一举成名的新力量导演,在当下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支持,走向市场、进入主流成为大多数艺术电影导演的选择。而正如许多人所担心的,真正的考验在浮出地表之时才刚刚开始。在由电影节生存向产业化生存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人与制片人的话语权相应扩张,明星策略、类型叙事、宣发营销等商业电影的创作和运作规则,开始渗入新力量导演的艺术电影之中。曾以《光棍儿》《美姐》屡获电影节奖项的郝杰,在走向市场之后,推出了包贝尔主演的类型电影《我的青春期》;以《耳朵大有福》《钢的琴》成名的张猛,也拍出了电视剧质感的贺岁电影《一切都好》,导演的风格在脱离电影节体系之后趋于消弭。即便是如毕赣这般仍保持着强大个人风格的艺术电影导演,在运作《地球最后的夜晚》之时亦默认了宣发方“一吻跨年”的营销策略,致使影片遭遇了跨圈层传播之时的口碑分化和反噬。此间,有意走向市场、进入主流的艺术电影导演如何处理市场要求与个人表达、工业体制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艺术/商业、工业/美学,如何在葆有初心的同时寻求与更大范围的观众相逢,成为其导演生涯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跨界艺术家”与“体制内作者”:电影节生存的两种路径
这一问题同样摆在新力量导演群体中注重市场效应的商业电影导演面前。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升级、质量提升的进程不断加快,观众的观影品位日益提升,“内容为王”成为电影创作的共识。商业电影若想在市场中取得成功,亦需要仔细打磨电影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正如导演金依萌所说,“制片人中心制”下没有风格的导演也能有饭吃,但有风格的导演则能存活地更久[8]。在电影节出身的艺术电影导演向着主流与市场迈进的同时,商业电影导演同样在寻求建立个人风格、提升艺术水准、提高市场辨识度。若将艺术性与商业性作为电影创作的两极,新力量导演群体中的艺术电影导演与商业电影导演将分属两极,且均有向位于中间的“体制内作者”导演群体滑动的趋势。对电影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统筹协调,正是“电影工业美学”的主要原则。作为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电影实践的理论观念,“电影工业美学”要求把电影看作一种核心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在电影工业流程的每个环节都发挥创意和审美的功能,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水准和运作上的“工业性”要求,在电影生产过程中弱化感性的、私人的、自我的体验,代之以理性的、标准化的、协同的、规范化的工作方式,力图达成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统筹协调、张力平衡而追求美学的统一。[9]
不同于自我命名的“第六代”将1990年代“新纪录片运动”的流浪艺术家群体涵盖在内,新力量导演作为官方推介、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导演群体,并不包括主流视野与市场体制之外更加小众与先锋的影像艺术实践,如作者拥有绝对掌控权且不奢求市场收益的部分独立电影与纪录片、地下电影、实验电影、VR电影、论文电影等种种先锋艺术电影实践,这类艺术电影导演更加依赖于电影节的艺术评价体系以建立作者身份,并有赖于电影节的展映平台以获取和观众交流的公共文化空间,独立电影界知名的圣丹斯电影节、国内的中国独立影像展、北京独立电影展、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等专门类电影节为这类艺术电影导演提供了竞赛、评奖与展映的平台。与新力量导演群体中的艺术电影导演向着主流与市场迈进的道路相反,这类更为先锋的艺术电影导演则试图进入另一个可以接受他们作品的体系——当代艺术界,将博物馆空间开拓为银幕与屏幕之外另一重要的影像放映空间,从而将自身身份定位于跨界艺术家,在电影节与双年展的艺术体制中开展影像实践[10]。
与之相反,新力量导演群体中的艺术电影导演,尽管也有着强烈的艺术追求与鲜明的作者风格,部分也采用独立制片的独立电影创作方式,但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电影工业及市场体制并非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更接近于美国独立电影的运作机制与美学风格,与类型电影、制片人中心制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具有“体制内作者”的身份自觉[11]。然而,与美国相对成熟的独立电影理论研究与产业体系相比,中国的“独立电影”在本土化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不同于美国独立电影的理论观念与创作体制,譬如因1990年代独立制片对国营制片厂体制的挑战在西方电影节的误读中被赋予了某种反抗性的政治意味,使中国的“独立电影”具有更多“地下电影”的政治对抗性;而与圣丹斯电影节扶持、培养独立电影导演并积极推动其进入市场主流视野的电影节体制不同,中国的独立电影节展缺少相应的培养体系及商业面向,甚至不见容于主流政治体制,屡屡面临被叫停、甚至停办的局面。此外,中国电影产业体系中也缺少媲美美国独立电影制片人角色的专业性艺术电影制片人,以帮助新导演的艺术电影作品顺利走向市场。令人唏嘘不已的《大象席地而坐》导演胡波的自杀,既是个体悲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电影体制的诸多不完善之处。出身FIRTS青年电影展创投会、并由冬春影业组建项目、面向电影节与院线市场创作的《大象席地而坐》,其融资渠道与创作方式本应使胡波成长为“体制内的作者”,进入新力量导演中的艺术电影导演谱系,但胡波对艺术风格的坚持及对出品方干涉的拒绝,体现出强烈的独立电影精神,力图达到作者导演对电影创作完全彻底的控制,从而站在了资本与市场的对立面,其作者个性更适于创作独立电影,一如毕赣创作《路边野餐》,而胡波的处女作却在电影节体制的推动下走向资本与市场的体系之内,致使作者性/体制性、独立精神/市场要求之间形成了无法调和的冲突。而中国独立电影节风雨飘摇的处境及在观念上对纪录电影和地下电影的偏爱,亦不利于中国剧情片独立电影导演的电影节生存,反观观念更为开放的美国独立电影,则在圣丹斯电影节与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的助力下,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成为与好莱坞互补、互利、共赢的电影力量,其运作模式对中国独立电影与艺术电影的生产与传播具有借鉴意义。
电影节作为一种文化体制,在其艺术精神之外,亦有其商业属性,位于当代艺术场域与主流电影市场的中介地带,为置身其中的新导演提供了可行的两条路径——占领博物馆,或进军电影院,而互联网与流媒体平台的加入则为两类艺术电影均提供了新的流通渠道,为其抵达观众开辟了新的路径。选择做电影节体系与当代艺术体系中相对纯粹的艺术电影导演,成为跨界艺术家;亦或选择做电影节体系与市场体系中的“体制内作者”导演,进入新力量导演谱系,是新导演在践行电影节生存方式之时内心需明确的道路。
注释:
[1]赵宁宇:《导演的产业化生存》,《影视文化》,2009年第1期。
[2]陈旭光:《新时代新力量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
[3]【荷兰】玛莉·德·法尔克:《电影节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肖熹译,《电影艺术》,2014年第5期。
[4]参见王昕:《用艺术抵达现实:当下青年导演的电影观》,《电影艺术》,2017年第1期。
[5]参见戴锦华:《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天涯》,1996年第1期。
[6]David Bordwell:“The Art Cinema as a Mode of Film Practice”,Film Criticism,Vol.4,No.1,1979,p.56.
[7]《毕赣:时间与空间,记忆与罂粟》,CinemAround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QZA3h7qF9RVD ks1Mz5ctEQ,2018-11-20。
[8]参见金依萌,于然:《电影市场成长背景下的中生代导演的自我认同——金依萌访谈录》,《当代电影》,2015年第6期。
[9]参见陈旭光:《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0]参见Thomas Elsaesser:“The Essay Film between Festival Favourite and Flexible Commodity Form”,Brenda Hollweg,Igor Krsti(ed.),World Cinema and the Essay Film,CFAC,Reading University,2015.253.
[11]参见张立娜:《美国独立电影的工业美学:类型实践、“制片人中心制”与作者性表达》,《未来传播》,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