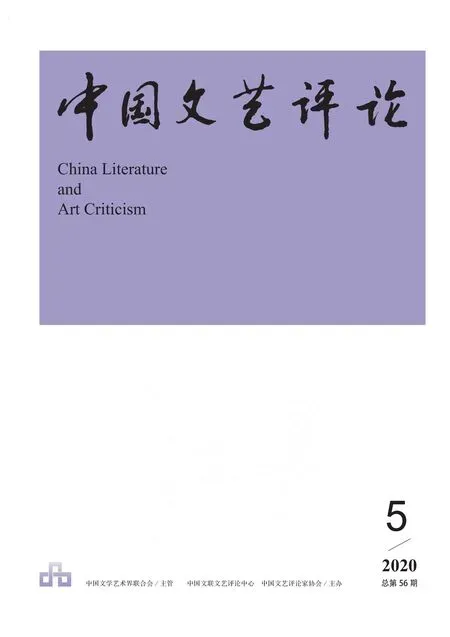点亮英雄主义的文学之灯
傅道彬
一、战“疫”文艺对英雄主义文学的呼唤
2020年开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会让历史永远铭记。面对病毒肆虐的局面,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战“疫”斗争,没有炮火,却险象环生;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困难来临的时候,许多人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流血流泪,献出爱心,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显示了一种不屈不挠、坚忍不拔、正气浩然的中国精神,谱写了可歌可泣、气贯长虹的英雄主义篇章。
文学从来不会在苦难而伟大的生活中缺席。瘟疫横行的时候,广大文艺工作者也以文学的笔、以各种文艺形式表现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英勇无畏的昂扬斗志,描绘了疫情肆虐中不畏生死、奋勇前行的英雄群体形象,用文学凝聚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战“疫”力量。“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战争、瘟疫、动荡、饥荒等苦难之后,往往更能唤起文学家面对苦难、征服苦难、反思苦难的创作激情,从而创作出激荡人心、大气磅礴的艺术作品。文学并不是一味地描写苦难,也不是简单地记录生活,更不是消极地自怨自艾、独自感伤,而是以文学的理性之光、艺术之光,照亮黑暗,点亮心灵,表现人类在痛苦面前愈挫愈奋、不可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在灾难面前高扬起英雄主义的文学旗帜。人类在灾难中更需要文学,在逆境中更需要点亮心灵的文学之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文章合为时而作。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变化,总能激发人的文学创作激情。抗击疫情是一次全民参与的政治活动,也是一场空前的文艺活动,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疫情发生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爱国热情,创作的作品数量之多、人员之众、形式之完备,都是空前的。在形式上既有文学、音乐、摄影、戏曲、书法等经典形式,更有以网络传播为手段的新型文艺形式,而新型文艺形式又有更广大的受众和更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在一个短视频中,一位女护士摘下口罩,满脸印痕,双手皲裂;而另一个视频中,一对老年夫妇面对着自己在疫情中丧命的儿子深深鞠躬,并把儿子的遗体捐献国家,如此等等,现场记录,纯是写实笔法;而唯其真实,更催人泪下,更撼动人心,直指精神深处,从而产生一种悲壮的力量。
战“疫”文艺最鲜明的特征是建立在爱国主义精神基础上的英雄主义精神。许多文艺作品歌颂了以医护人员为主体的英雄群体,他们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慷慨前行,奔赴疫区,完成了从平凡到伟大的精神跨越。一些作品往往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切入,从朴素和平凡中看到非凡的壮举。
冠状病毒落在武汉/像一双黑夜的手/掐住武汉的长江大桥/铁路、地铁、码头、航空/一时间武汉的天空布满尘埃/许多人走了/也有一些人将会离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冠状病毒吞噬着无休止的黑夜/武汉一时间成为围城/而城里的每个人都是英雄/他们不做困兽之斗/只祈求在黎明到来前/又有一颗新的免疫细胞诞生。[1]马济:《“武汉挺住”诗歌专辑(6) |马济:病毒抗争记》,2020年1月25日,封面新闻 http://www.thecover.cn/news/3446509。
——马济《病毒抗争记》
不仅医护人员,那些在病毒肆虐中坚守的武汉民众也是具有英雄主义精神的人。英雄就是面对苦难面对危险面对非常事件时表现出来的坚守、抗争和勇敢。英雄不是天生的,是相对苦难而言的,他们在灾难降临的时候决不丧失信心,在绝境中充满希望。
赞美英雄成为战“疫”文学的鲜明特点。在战“疫”文学中有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就是钟南山形象的塑造。钟南山院士在关键时刻仗义执言,以84岁的高龄奔向武汉这个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他坐在火车上愁容满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老泪纵横,他在医院里疾走如风,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没有专门的号召和动员,许多文艺工作者以各种艺术形式赞颂、描写心中的钟南山形象。歌颂钟南山院士的艺术作品,涉及诗歌、散文、雕塑、摄影、美术、书法、歌曲等门类,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艺术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现象。面对钟南山,一位诗人写道:
那是沉甸甸的四个字/“民族脊梁”——/力拔山兮气盖世/天欲坠时南山擎/一盏仙壶济世悬/国有危难立钟鼎/你是埋头苦干的战士/你是拼命硬干的先锋/你是为民请命的贤达/你是舍身求法的英雄。[1]陈先义:《致敬钟南山》,《雷锋》2020年第2期,第51-52页。
——陈先义《致敬钟南山》
人们将钟南山看成是为民请命的“民族脊梁”,巧妙地利用钟南山名字中的“钟”“南山”,将他描写成天欲坠落时的“南山”和国有危难时的“钟鼎”,灾难的废墟上站立起一个不屈的英雄身影。人们对战“疫”英雄的自觉赞美,反映了一个现象,我们的时代并不拒绝崇高,拒绝英雄,在中国民众的精神深处依然有英雄崇拜的情结,在逆境和灾难出现的时候,我们依然应该点亮英雄主义文学的灯火。战“疫”文艺引发了我们对英雄主义文学的思考。
二、英雄主义文学的主题分类
文学不仅仅反映生活,更照亮生活。文学是光、是灯、是火。英国文学家威廉·哈兹里特认为,如果文学仅仅像镜子那样描写自然,或者仅仅是叙述自然情感,那么它无论怎样清晰有力,都不能构成诗的终极目的。而真正的诗如灯、如光:“诗的光线不仅直照,还能折射,它一边为我们照亮事物,一边还将闪耀的光芒照射在周围的一切之上”[2][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5页。,不被文学反映的人生深深遮蔽于物性而难以自拔。而在艺术世界中,人能够出场,出场就是站岀自身。人从遮蔽的混蒙状态中走出,一方面让人自身的本性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将人带入一种寻常不曾到达的敞开状态。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鲁迅相信,只有文学之光的引领,才能唤醒民众,到达理想的超越世俗的英雄主义境界。
英雄主义文学(The literature of heroism)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世界诞生,荷马高歌”(雨果语)。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就是通过对氏族英雄的歌颂为希腊历史开篇的。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以及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藏族)、《江格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几乎都以一个民族的历史为舞台,展现一个又一个在民族历史上具有奠基和转折意义的英雄形象。英雄史诗深刻影响中国早期文学的历史书写。中国文学中有着深刻的英雄主义精神。中国古老的诗歌经典——《诗经》的《雅》《颂》诗篇中,有多首歌颂民族英雄的史诗,记录了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民族英雄人物带领部族征服灾难和动荡的宏伟历史。屈原、曹操、杜甫、辛弃疾、岳飞、文天祥等,都是在沉重的民族灾难中崛起的诗人。大致说来,英雄主义文学的主题可分为四类:
一是神性英雄主义。原始英雄主义是充满神性的,是与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的。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的阿基琉斯、奥德修斯、普罗米修斯等都是具有神话意义的英雄。中国神话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塑造的英雄形象,是人类陷入灾难时的拯救者,他们具有人的精神,本质上却是神话中的人物。《尚书》也记载和描写了以尧、舜、皋陶、大禹为代表的早期英雄的群像,他们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集人类的真善美于一身,具有“半人半神”的品格。他们高高在上,与神沟通,肩负使命,总是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上力挽狂澜,引导众生走出困境。
二是古典英雄主义。古典英雄主义,也是历史英雄主义。中外文学史上的剑客、侠客、骑士形象,常常充满仗义行侠、匡扶正义的英雄主义情结。中国古代史传文学有尚奇的特征,而所谓“奇”,本质上是超迈世俗的英雄品格。《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讲述的故事,时代不一,神界俗界也各有侧重,但是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英雄主义情结。诸葛亮、关羽——智绝、义绝各逞风采,在世俗世界里建立起忠义与智慧的道德价值追求,也反映了人们的英雄崇拜。《水浒传》中描写的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风雪山神庙、智取生辰纲、景阳冈打虎等,一幕幕英雄传奇,气壮山河,代表了一种江湖热血、敢于反抗的英雄崇拜。孙悟空是《西游记》以浪漫主义笔法塑造的火眼金睛、嫉恶如仇、神通变化的英雄人物,他有神话特征,但他身上的活泼机智、自由乐观的品格,却反映着普通民众心中的英雄追求心理。中国古典小说,如《三侠五义》《杨家将》等,最能代表民间的英雄理想。
三是个人英雄主义。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追溯到神圣的基督教精神。《圣经》贯穿神性,也强调个体的创造意义。耶稣本身也是历经磨难而坚定追求理想的形象。而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个人主义代替神本主义,人的主体精神被发现,个性被强调、被重视,莎士比亚说:“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英]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317页。对英雄主义,中国的辞书往往将其解释为具有高尚品德、才华过人,而无私奉献的精神。而西方的英雄主义写作(a man who is a defender or protector with great bravery and obligations),意味着勇敢强壮、责任担当和捍卫保护,本身强调的就是个人的能力与强悍。美国灾难片中的个人英雄形象是当代个人主义英雄的典型体现。美国灾难片塑造的一个又一个英雄个人主义形象,为当代西方青年所崇拜和模仿。美国灾难片常常描写洪灾、火灾、瘟疫、疾病,甚至海啸、地震、核扩散、外星人入侵等突发事件,而影片中的主人公往往天赋异禀、胆识过人,以一己之力排除万难,拯救众生,甚至整个地球,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与感官刺激。
鲁迅早期的英雄主义主张曾经深受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的影响。他在《摩罗斯力说》《文化偏至论》等理论著作和文学创作中描述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形象。鲁迅心目中的英雄是个性鲜明的,是与“庸众”对立的,是不为世俗的世界所接受的;鲁迅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孤独的复仇者,孤独是因为先觉,是不被理解的寂寞,复仇则是出于革命理想。鲁迅的英雄打破了中庸观念,急切慷慨而不那么温柔敦厚。
四是革命英雄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又称红色英雄主义。中国的英雄主义文学成就卓越,是由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决定的。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革命英雄主义文学及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对中国革命英雄主义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革命英雄主义文学几乎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步,蒋光慈的《短裤党》就描写了1927年上海工人起义的宏大场面,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工人形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革命英雄主义文学创作达到了高潮。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一系列血肉丰满的革命英雄人物的英雄谱,从小说《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青春之歌》,到歌剧《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电影《烈火中永生》《董存瑞》《英雄儿女》,等等,无不洋溢着革命理想主义的昂扬精神,以革命的主旋律唤起民众对革命精神与英雄主义的崇拜。刘志丹、方志敏、洪常青、卢嘉川、刘胡兰、江姐、杨子荣、董存瑞、黄继光、王成等英雄形象,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为崇高理想而不惜牺牲一切,这些英雄形象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壮丽景观。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具有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具有人民高于一切的坚定立场,成为革命英雄主义形象的核心内涵。
三、英雄主义文学的道德高度与冲突模式
神性英雄主义与历史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是一个整体,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别对立,但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构成。以神话、史诗、传说等为代表的神性英雄主义,是原始的英雄主义。虽然远古的历史已经走远,但是神话与史诗对一个民族文学和艺术的影响是根本性的,经过历史的沉淀、变化,这种影响转入一个民族的精神深处,成为潜藏于文化深层结构的心理原型。从神性英雄主义开始,英雄主义文学有了这样的基本特征:
第一,神圣与正义的道德制高点。英雄主义文学的首要特征是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总是从神圣与正义出发的。《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及以色列先知总是肩负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阿基琉斯、赫克托尔等视保卫国家为自己的使命,他们明知自己会死于战争,却不避灾难,勇于牺牲,勇敢前行。历史英雄主义继承了神性英雄主义的这一特点,古典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无不体现着使命的神圣和道德的正义。以《三国演义》为例,历史上的三国之争,本来不具有道德的意义,而在小说家笔下,蜀刘一方却成为皇族正统,带有仁爱、智慧的正义特征,而曹魏一方则大都奸诈、残酷,曹操也因此成为白脸奸臣的形象。作者称美的一方,首先是站在道德高度的一方,所谓英雄首先具有道德的正义感和神圣性。
第二,天使与魔鬼的冲突模式。神性与魔性、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总是充满矛盾的,因此英雄主义叙事总是充满强烈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神性英雄主义中的民族英雄具有天使般的优秀品德,却常常遭遇魔鬼的挑战。英雄在道德上是完美的,而魔鬼则每个细胞里都充满邪恶。古典英雄主义文学将这种“天使—魔鬼”的叙事模式,转化为“君子—小人”式的人格冲突。从屈原开始,中国文学已经建立起“君子—小人”的人格对立叙事,君子的一方追求人间正义、公平,而小人一方,则放僻邪侈、无恶不作,千方百计挑衅道德和正义,使英雄的道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君子与小人的冲突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性矛盾冲突,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也体现为个人英雄主义中的灾难性叙事,表现为革命英雄主义文学的“革命与反革命”“英雄与敌人”的冲突。
第三,艰难与悲壮的故事情节。英雄主义叙事是建立在正义与非正义基础上的,期间充满了天使与魔鬼、君子与小人式的矛盾冲突,因此故事的发展,多是艰难曲折的,英雄形象也常常充满了流血牺牲,甚至是悲剧的。古希腊史诗是悲剧性的,那些为民族而牺牲的英雄往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尚书·金縢》一篇是艰难叙事的典范文献。在中国文学中周公是一个人格完美的“文化使者”形象,但却遭受了流言的攻击。周武王曾经患病不愈,周公则设坛祭祀,祈求先祖:“以旦代某之身”[1]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6页。。周公将誓言锁于金匮之中秘不示人。而武王去后,管叔及群弟散布周公将取代成王的流言,最终在一个“天大雷电以风”的日子,周公与群大夫“以启金縢之书”,使其沉冤昭雪,真相大白,整个故事情节带有悲壮色彩。这种源于正义,发展为天使与魔鬼的冲突,英雄历尽艰难曲折最后终于赢得胜利的模式,是英雄主义文学的基本叙事模式。个人英雄主义文学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革命英雄主义文学斗争的艰难曲折,都是这种叙事的延伸和拓展。
第四,宏大与庄严的审美境界,卓越与非凡的个人能力。英雄主义文学体现为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宏大的叙事是“完整的叙事”,历史的书写者往往以一种俯瞰苍生的姿态出现,对历史作出英雄式的全知全能的判断和预言,其描写的笔法也是史诗式的庄重与神圣。宏大叙事所描绘的历史常常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种群面临胜败存亡关键时刻的非常事件,这个时刻呼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英雄出现。英雄具有卓越与非凡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意志和能力成为英雄战胜一切困难的基础。在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和冲突中,英雄总有一种对立面,或是蒙昧,或是邪恶,或是灾难,或是逆境,而经过重重困难和逆境考验,正义最终战胜一切邪恶和愚昧,从而彰显正义与人性的力量。英雄的形象是庄严肃穆的,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其审美形象也是庄严的,不苟言笑的。
而英雄主义文学一味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庄严的美学特征,也影响了英雄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拒绝世俗,是英雄主义文学的特点,也是英雄主义文学陷入困境的原因。英雄确实具有超常的意志力和生存能力,但是任何英雄都生存于平凡之中。过于强调非凡,远离世俗,使得英雄形象失去了成长的艺术空间。而另一方面,英雄主义叙事,过于强调理念的正确和叙事的宏大,而忽略了艺术的真实与细致,使得艺术表现方法过于简单粗略。
英雄的本质在于当人类面临各种生存逆境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抗争、勇于突破,而决不退缩的顽强精神和意志。英雄的含义就是相对于逆境而言的。中国革命英雄主义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曾经历理论探索的曲折。其明显的特征是把英雄塑造当成了“造神”,所谓英雄成为没有缺点、绝对正确的完美形象。英雄的形象缺少个性,而只是具有某种思想观念和政治符号的代表。由于放弃了典型的个别化要求,忽略了英雄人物作为普通人的真实生命,致使英雄形象走向虚假和僵化。过度地拔高英雄境界,不仅使得英雄的形象脸谱化,也忽略了普通人的描写,人民大众只能作为英雄的陪衬,这实际上已经将英雄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英国小说家福斯特以为:“一个圆形人物务必给人以新奇感,必须令人信服。如果没有新奇感,便是扁平人物,如果缺乏说服力,他只能是伪装的圆形人物。”[1][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68页。失去了典型化的特征,英雄便是扁平的概念化的类型人物,从而失去文学健康的形象,而变得苍白孱弱缺少血色。
四、英雄主义文学的时代书写
出于对英雄主义文学简单化、类型化的反叛,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有一种拒斥英雄主义文学的倾向,强调文学的世俗化、生活化,将平凡庸琐作为生活的全部,刻意地强调个人情趣和内心情感。英雄不见了,崇高不见了,一味地追求小花小草式的审美情趣,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琐屑。其实,平凡是人性,崇高也是人性。历史一方面是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另一方面也是英雄豪杰的叱咤风云、壮怀激烈。海德格尔强调人要站出自身,但这种“站出”,是向着神性站出,向着神性靠拢,而不是相反。海德格尔说:“‘人……以神性度量自身。’神性乃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唯当人以此方式测度他的栖居,他才能够按其本质而存在。”[1][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471页。在海德格尔这里,神性不是偶像,不是宗教,而是人的崇高追求,是人的诗意状态。向神性站出,也就是向着英雄、向着崇高靠拢。人在向着神性靠拢的过程中,获得神性;也在向着崇高的追求中,获得崇高。文学最终还是要有崇高的追求的,失去英雄形象的文学世界是单调乏味的。因此,对一个时期英雄主义文学的缺点,我们确实应该反思,而反思的目的不是摒弃,而是通过修正,建立新的英雄主义文学,建立新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学。
新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学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史诗性书写。我们的时代是历史上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同时也正经历着百年未遇的历史变局。历史发展与未来机遇并存,繁荣兴盛与风云激荡同步,文学家必须与时代同步,记录伟大时代的风云变化,记录我们的苦难与逆境、胜利和幸福,在历史上留下恢弘时代的历史篇章。
新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学是从人民群众的集体环境中产生的。英雄本身意味着对普遍性的超越,但是无论怎样特殊,英雄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历史土壤而生长,英雄性恰恰是人民性的反映,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并为这个利益而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重视集体、重视人伦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新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学中的英雄,自然不是现代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而具有广泛的人民性。英雄出场的时刻,总是在一个民族或集体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是英雄创造了时代,而是时代创造了英雄。因此英雄主义文学要书写的一定不是纯粹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一种民族的、国家的、时代的宏大书写。
新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学是具有鲜明个性的。英雄性并不能脱离人性,恰恰相反,真正的英雄叙事总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英雄更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英雄的丰富性多样性。红色英雄主义曾经陷入概念化、绝对化的泥潭,而丧失了个性和生命力。新时代的英雄主义应当摆脱英雄的绝对化叙事,更注意表现细节、表现个性、表现多样性。在个性上理解英雄,是新时代英雄主义文学面对的重要问题。这次抗击疫情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首广泛流行的歌曲——《等你回家》写道:
除夕的碗筷刚摆下/一声召唤你就离开家/用身体筑防线与病毒厮杀/逆向而行平凡中伟大
(乙福海词,刘臣、刘佳曲,刘臣演唱)
作者选取了除夕夜的典型环境,医护人员听到召唤,慷慨出征,踏上征途。这里有剑气如虹的英勇气魄,也有普通人的儿女情长万般牵挂。歌曲一方面表现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也走进英雄的内心世界——“肆虐的瘟疫在扩大/这次出征真有些怕”。战“疫”英雄不仅有慷慨悲歌的一面,也有内心深处的心灵婉转,使得英雄的形象更真实,更丰满,更有感人的力量。
新时代英雄主义是充满历史反思精神的。英雄主义文学常常要书写逆境和挫折,书写人类曾经历过的苦难,司马迁、尼采、恩格斯等伟大思想家都曾经提出过苦难催生文学的见解。但是,文学家不能仅仅将苦难作为文学的素材,而必须面对历史、反思历史,书写苦难不是歌颂苦难,而是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谴责邪恶,避免曲折,汲取力量。如果将人类的曲折逆境仅仅当作历史材料,缺少批判性的反思精神,这不仅使文学缺少了思想的深度,也徒然耗费了人类曾经的苦难代价。
新时代英雄主义文学是具有崇高美学追求的。康德认为“崇高是一切和它较量的东西都是比它小的东西”。[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9页。英雄主义的文学书写,往往是非凡的事件、非凡的人物、非凡的精神,因此在美学上它也摒弃琐屑与渺小,而追求雄浑深厚、宏大庄严的美学特征。早期的英雄史诗中,英雄人物“半人半神”,英雄首先具有精神的伟大,与众不同。《诗经》中的《雅》《颂》诗篇,在歌颂周民族的英雄人物时,特别注意用大、远、众等语词,运用高山、大河、平原等意象,表现阔大宏伟的审美境界。崇高神圣的审美追求,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英雄主义文学创作。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个人英雄主义,还是革命英雄主义,都基本遵循了崇高的审美追求。当然崇高美学核心是一种精神追求,正如大海不拒细流,崇高也不能拒绝具体,拒绝寻常,而是在具体中体现伟大,在寻常中追求崇高。崇高本身就是相对平庸和寻常而言的,在新时代的进程里,崇高美学精神恰恰是历史需要的。走向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更需要崇高的美学,更需要英雄主义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