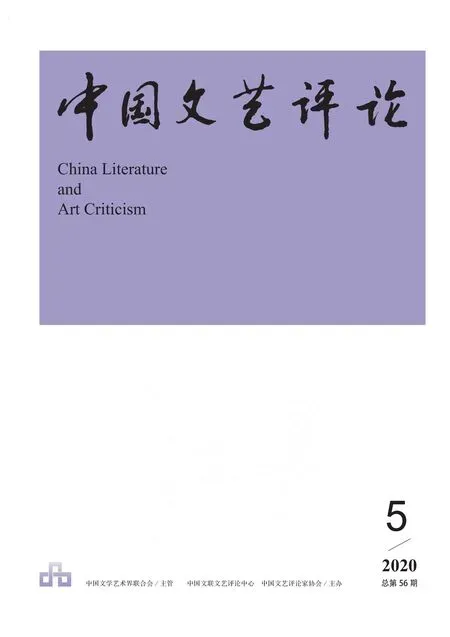中国乡村的文学在地书写
——评“乡村志”系列作品
张丽军 范伊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急剧“加速”。面对当下急速发展变化的新现实,作家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呈现新的社会风貌和人的心理变动。从《苍凉后土》《土地神》《村官牛二》到近期出版的“乡村志”系列小说,四川作家贺享雍的创作始终立足乡村、面向当下,书写乡村发展的新现实,思考乡村发展遇到的新问题。新世纪以来“不少乡土小说,写的不再是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写了一个村庄、一个文化群落、一种生存状态”。[1]雷达:《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概观》,《文艺报》2006年10月26日,第3版。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小说集中描写了贺家湾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变迁,着重表现了贺家湾三代人在改革开放以后物质生活的提高、内心情感和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伦理的冲突与融合。通过描写贺家湾在土地、医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变化,可以寻找到整个中国乡村当下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以及人的内心波动与焦虑。纵观“乡村志”系列的十部长篇小说乃至其早期的乡土小说创作,贺享雍直面乡村现实、反映乡村现状的问题意识,坚持民间立场,吸取传统和民间的叙事资源以及面对乡土文化建设的危机感始终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展现其对乡村、对农民乃至对当下社会整体的关怀与反思,体现出作家的博大胸怀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体现出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书写的新主题、新风格和新审美思考。
一、当代乡村发展新现实的审美书写
“任何一个时代一个伟大的作家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永远带有一种批判和审视”[1]刘卫东:《圪蹴在“形而中”的秦岭》,《文学界》2010年第2期,第16页。,在贺享雍的创作中,作家本人直面现实的创作姿态和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作家从乡村的各个角落、发展的多个方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入手,重点呈现了当下现实社会背景下农村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新时代背景下农民在情感上的变化。有学者说:“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像一个伟大的发现病情并治疗病情的医师一样,诊断现实生活中的残缺和病象。”[2]《现实主义的此岸与彼岸——专家、作家在第八届中国文学论坛上的发言》,《名作欣赏》2012年第3期,第7页。在贺享雍笔下“诊断”的不仅仅是中国乡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更是社会、国民在当下真实存在和不得不面对、解决的现实问题。
1. 当下乡村发展现状的外部描写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给乡村带来重大利好。首先体现在农村的生产力,以及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贺享雍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将这一现实情况通过对农民生活细节的描写自然呈现出来,如《土地之痒》中贺世龙回忆饥荒岁月中家人被饿死的惨状、带弟弟讨要红薯干的情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小说中多次出现“现在谁还缺这口吃喝”“大鱼大肉吃得多了,反而更喜欢吃点清淡的”之类的文字。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村民们有了更高的追求,如休闲娱乐、提升自己赚钱的能力等。但是在农民的休闲娱乐中,一些不良的休闲方式日益流行,在“乡村志”系列中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了贺家湾人对打麻将、赌钱的痴迷。这既是对乡村现状的真实描绘,也是反思乡村文化建设的一大体现。农民在富起来之后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审美等,都是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亟需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农耕器具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农业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使得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更高的经济收益,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城。贺世海进城从事建筑行业后,因工地缺乏人手想要从贺家湾带领一批人进城务工,农闲时的村民们十分乐意再多挣一份钱。而这些人在尝到进城打工收入高的甜头后,越来越愿意进城,甚至开始以打工为主,对种地的热情却日益减退,减免农业税后也没有明显改善这一情况,土地抛荒成为当下农村的普遍现象。在《土地之痒》中,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对土地大量抛荒的描写以及老一辈农民贺世龙面对无人耕种的土地时的痛心和不舍。
“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落差中,作为一个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人的生存本能来说,农民的逃离乡村意识成为一种幸福和荣誉的象征。”[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0页。贺家湾走出去的知识分子,如老一辈的贺世普、第二代进城的贺健,以及第三代研究生毕业的贺华斌,无一不留在了城市中工作、生活,而他们对贺家湾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在《大城小城》中,作家更是集中描写了贺家湾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在城市的生活与工作,他们在城市生活虽不易,但回到乡村却更不可能。一批一批的人走向城市,乡村成为他们回不去或者不愿回去的远方。在这一角度上,作家给我们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考的空间。“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逐步失却了一个中坚力量——乡村精英”[2]林文勋:《历史与现实: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启示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82页。,而留守乡村的主要是“386199”[3]即以“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九九重阳节”等节日的日期来指称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留守乡村的群体。群体。农村不断向城市输送人才和劳动力,老一辈的农民很明显不足以将农村发展向前再推进一步,没有新生力量的注入,乡村的发展势必要呈现萎缩的状态,如何为农村发展提供新鲜有力的力量?这无疑是当下乡村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尽管推行大学生村官等政策,但也远远不够解决乡村发展的积弊。小说中专科学校毕业的贺端阳想要竞选乡村基层干部几度受挫,正说明了乡村问题的难点。这个“难”和根植于农民血液中的传统伦理观念以及价值观有大关系,更与那种膜拜权力的劣根性有不可推脱的关系。对权力的争夺和耍弄、拉帮结派、帮亲不帮理等思想的根深蒂固才是阻止乡村进一步迈向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尽管农民经济收入增加了,乡村新的楼房也接二连三地建起,但村里稀稀落落的人口让村庄显得空荡荡,这种“人去楼空”的景象不仅仅是由于乡村人口流失带来的乡村萎缩,还有村民们在情感上的空虚感。
2. 展现当代农民的心灵情感之变
在生产生活方式得到改变的情况下,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都悄然发生了变化。在上述乡村发展问题之外,更深层次的是农民的精神危机以及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焦虑。“靠土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页。,人与土地的关系的亲密程度决定了情感程度的不同。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靠的是种植农作物,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获取经济收入的途径越来越多,相比之下土地带来的收益却显得微薄,大部分农民尤其是年轻人选择进入城市谋生。其他留在村子里生活的人,也不再是完全依靠种地,如身体不好的贺世凤和妻子开饭店、贺端阳决心种植果树。老一辈农民与第二代、第三代的贺家湾农民对待土地的情感是不一样的,进城离乡的人更希望能够在城市中扎根生活,土地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很重要,而对于坚守在土地上的老一辈农民,比较典型的如贺世龙,深深眷恋着土地,即使不挣钱也坚持种下去。但是在历经多次土地制度改革后的贺世龙最后也对自己是否真正拥有土地产生了疑惑,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痒”也只对真正对土地拥有深厚情感的农民产生影响,而那些早已背井离乡的人已不再将工作、生活乃至情感的重心放在土地上。
“人在改造其与物的关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改造着与世界的审美联系”[1]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7页。。在传统乡村伦理中,血缘亲族关系是维系人们之间情感的纽带,但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现代文明的进入,不仅使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在血缘亲族关系上也发生了变化。尽管人们之间依旧重视血缘关系,但在更多时候血缘关系已经开始让位于经济利益关系。如竞选村主任拉票时,谁能够给选民更高的利益谁就能够获得他们手里的选票;想要跟着贺世海继续在工地务工的村民也在努力拉拢、修复和贺世海家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文明的进入给村民们带来了思想上的革新,使他们能够更加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节奏,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隔膜。如小说中对“人情淡薄”的描写:村民们对“疯子”贺贵的疏远以及对他死亡的冷漠;贺家湾村民在得知村委会没有将制药公司额外补贴村民的钱发放,不顾往日看重的亲情要求查账。在个人利益面前往日的亲情伦理也要做出让步,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思想经历的一个阶段,如何平衡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仍是当下整个社会需要关注和探索的问题。
“我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一个瓶颈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水平问题。”[2]李培林:《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3页。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当下社会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城市谋生,更多是因为城市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更高的经济收入,但进入城市后能够真正融入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就给他们带来了极为矛盾复杂的精神困扰:不愿意回到故乡但是又无法融入城市,于是他们成为城市的“漂泊者”。近年来作家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进城后的农民的生活、情感困境,如石一枫笔下的陈金芳、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等不同类型、以不同身份进入城市的人物形象,展现了进城农民生活上的困顿以及精神情感上的焦虑。贺享雍在《大城小城》中描写了以不同身份进入城市的贺家湾农民的心理状态,一类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农民,如贺兴琼靠在劳动市场打零工、服侍瘫痪病人获得收入,生活较为拮据,还有一类是在城市中站稳脚跟的农民。这里面有的是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如做校长的贺世普;有的是靠最初的资本积累逐渐在城市扎根生活,如依靠承包建筑工程获得资金的贺世海、贺兴仁;还有的则是通过出卖自己的情感和身体留在城市,如出卖情感的贺健、出卖身体的贺冬梅。尽管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留在了城市,但是距离被城市接纳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他们虽然人在城市但心灵却无法真正安放。即使是村民们眼中的“骄傲”的贺华斌,在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城市工作,“可他在这个城市里像个流浪儿一样,别看地方这样大,他却没处可去”[1]贺享雍:《大城小城》,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9页。,狭小拥挤的出租屋、忙碌的工作、靠外卖度日的他在城市中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独,而这一切却无人可诉说。
“文学要面对人生,讲人文精神,讲人道主义,就要关注生活在重重困境中的社会底层的基本群众,满足他们的审美意愿,其手段只能是现实主义。”[2]杨立元:《新现实主义小说出现的历史情境》,《新现实主义小说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32页。贺享雍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表明了他的民间立场,不管是对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揭露与反思,还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心理变迁、精神困境的描写,贺享雍的创作具有很强的“问题小说”倾向[3]此处关于“问题小说”的定义是宽泛的,“任何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反响的文学作品,都或深或浅地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广义地说,思想性和社会针对性强的小说,都可以归入‘问题小说’,在作家以文学参与历史发展的自觉性”。参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这些问题的发掘与呈现的背后不仅仅是作家对当下乡村发展新现实的担忧,更揭示了整个社会面临的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植根于民间与传统的审美形式创新
“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纵观贺享雍迄今为止的创作,坚持以民间立场书写乡村现状是其创作的重要特色。除了大量使用四川方言、俚语营造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在他的创作中,对民俗、民间故事和传说等民间艺术资源的汲取,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让小说的情境更加具有真实感和生活气息,也为读者了解当地人文风情提供了更好的窗口。除了对民俗的书写和民间神鬼传说的引用外,贺享雍还借鉴了“说书人”和章回体结构等传统小说叙事手法,增强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可读性。在上述现实主义手法和对民间艺术、传统小说叙事手法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贺享雍为中国当代文学新乡土小说添写了浓厚的一笔。
1. 地方民俗和民间故事的引用
民俗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生活。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5]钟敬文:《民俗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页。民俗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对民俗的书写似乎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论是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还是十七年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新时期的寻根小说,对民间风俗的书写都有迹可寻,民俗也是小说中表现独特地方色彩的重要部分。贺享雍乡土小说的创作为我们呈现了生动的川东风土人情画卷,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贺享雍所描写的民俗活动中,蕴涵着作家对“人”的关注,将贯穿于民俗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以及人的心理变迁很好地呈现出来,令风俗更加具有人情温度而不仅仅是乡土小说中的装饰品。
小说中既有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民俗描写,还有很多体现地方特色风俗的书写,如川东地区正月里大型游艺——“抬亭子”,小说给予了大量笔墨,从彩亭制作艺术的讲究、人物造型的雅致、表演技术的高难度等多方面向读者展现了这项精彩绝伦的民间艺术。还有婆婆娶儿媳妇时众人对公婆“鲊寒(咸) 老婆婆”和“抬椅轿”、春节期间的“坝坝戏”等都展现了独特的川东风情。除了具体的民俗活动描写,作家在小说中还提及了许多民间的鬼神和传奇故事,增强了小说的神秘色彩。同时,对鬼神故事的描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间的信仰。如贾佳桂因多年与丈夫不睦怀疑是灶神不安造成的,因此特地请村里的风水先生贺凤山来帮助安灶。面对这样的封建迷信活动,贺世普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批评妻妹的愚昧与迷信,而是报以理解和同情:“人活着都要有个精神寄托,我去打破佳桂的梦做啥?”同样,对“灶神”的崇拜体现了人们内心对家庭和睦的一种渴望与追求。此外,还有对“树神”的崇拜。贺家湾村口据说有一棵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老黄葛树,成为了许多村民们的“干保保”,备受村民的崇敬,老树福荫着村民,同时也是整个贺家湾历史的见证,在贺家湾发展的不同时期这棵老黄葛树都以自己独特的姿态参与其中。小说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对村里修公路要砍伐黄葛树时的一段描写,老树仿佛有所感应一般摇晃着树枝,流出“血液”一般的液体。除了对神明的崇拜,作家还写到许多与鬼魂有关的故事,其中多与亲情伦理相关,如贺端阳和贺贵看到鸟儿认为是自己父亲的灵魂、贺端阳母亲梦到丈夫对儿子前途的担忧与忠告、贺世龙欲持刀与人争执时镰刀突然掉落等,这些描述除了增加故事的神秘色彩之外,更多传达的是民间重视亲情伦理的文化氛围,也正是基于以上种种文化和信仰的基础,贺凤山以及他的儿子贺福来能够依靠看风水、占卜等获取生活来源并受到村民们的敬重,这些与长期积淀在人们心中的传统思维方式有着很大关系。
“中式的民俗文化因子深深扎根于广大乡村并占据主导地位,西式的一些文化风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广大乡村。”[1]陶维兵:《新时代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传承与创新路径》,《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1期,第134页。农民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在具体的民俗活动中悄然展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小说中民俗的描写并不仅仅是为了装点作品的“乡土”性,而是有着更大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民俗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的民俗得以出现或者旧有民俗逐渐演变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如丧葬活动中出现烧纸汽车、冰箱等现代交通工具和家电等祭奠先人,婚嫁也省略了一些低俗的“婚闹”行为。贺享雍笔下充满人情味的民俗书写很好地再现了农民心中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及其变迁的过程。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时代,村庄的萎缩乃至消失愈发常见,与此同时依附在乡村生活中的乡土民俗也在大量消失,作家通过对乡村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俗活动的描写,为时代留下了重要的乡村生活风貌的历史画卷。
2. 传统小说叙事艺术的转化
除了对独特民俗的细节呈现,作家在叙事手法上也借鉴了民间说话艺术和传统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叙事结构。小说中“说书人”角色的设定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同时能够很灵活地变换叙述对象,以便于展开不同人物的故事情节。对古代长篇章回体小说情节结构方式的借鉴也使得小说对每个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展开更加清晰。
在贺享雍早期作品《后土》中就鲜明体现了“说书人”叙述视角的特征,小说开头“楔子”中以第二人称“你”为说话对象,通过潜在的说书人视角逐一向读者介绍佘家湾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特征。在《村医之家》中,这一叙事手法表现得更为典型,作家将叙事视角锁定在村医贺万山身上,并让其以第一人称“我”来完成整个故事的讲述,但是在小说中这个“我”却是以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的方式展开叙述的,如贺万山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虽然开头就交代了是自己母亲告诉他的,但是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对很多细节的描述是超越了第一人称视角限制的,如对爷爷、母亲的动作、心理等细节的描写。最为主要的是作为贺万山交流对象的“我”的声音却不曾出现过,二人的对话几乎是贺万山一人自问自答或者自己转移话题完成的,“我把这次进城端‘铁饭碗’的机会给放弃了……我后来后悔过没有?实话对大侄儿说吧,直到今日,我也没有后悔过。为啥?”“既然刚才我说到两小子的事,从现在开始,我就来说说他们的事。”[1]贺享雍:《村医之家》,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27页、165页。在贺万山这些“自言自语”中,小说的故事情节转换自然顺畅,说书人的口吻也给读者做了很好的提示,既交代了故事的前因,又自然过渡到后续来展开,便于读者在众多人物的繁杂故事情节中理清思路。此外,利用说书人的特征还能够对情节的详略做出合理的安排。民间的说话艺术讲究情节紧凑、曲折动人,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展开相对于西方小说来说则较为简略,如《土地之痒》中贺世龙看见儿子贺兴成长大懂事时的心理描写没有展开,而是被一句“心里自然高兴不提”带过,还有李春英和毕玉玲两妯娌闹矛盾后,二人由停止争吵到后面几年又和好,这一过程作者也只用“这已是后话,不提”省略过去。小说中还经常出现一些自问自答的句子,如“郑支书为什么要在他这个大队按老祖业分田呢?难道他不晓得用这种方法分田毛病很多?个中原委其实十分简单……”[1]贺享雍:《土地之痒》,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7页。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出下文。无论是设置悬念、转折过渡,还是进行情节的详略安排,“说书人”的叙述技巧极大地方便了故事情节的展开、提高了文本的趣味性,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除了利用说书人叙述视角的设置串联转换故事情节以外,贺享雍作品中的情节结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我国古代长篇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在小说的回目形式上保留了古代章回小说的神韵。如《村医之家》由“楔子”和13章组成,每一个章节名称概括了主要故事内容,如第一章“我爷爷和我爹都是乡村郎中”;第二章“我治好了自己的病”;第三章“我暗恋上了郑彩虹”,每个章节下面又由不同的小节组成。小说由多个主要情节构成的发展脉络层层递进,每个主要故事情节中通过回忆或者插叙等方式交代人物背景,既丰富了人物形象又能够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在线型叙事结构下,贺享雍将几十年来中国乡村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历史清晰地再现出来,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具有独特地域风貌和生活温度的风景画、心灵史。
三、传统乡村伦理体系的解体与新建
“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2]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41页。如果说对当下农村、农民命运的关注与关怀,以及对民俗的书写和传统小说叙事经验的借鉴是贺享雍乡土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那么在这背后更大的关怀和视野,则是作家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从表面上看作品中对不同农民形象的塑造是在写当下农民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实则是对整个国民性的反思。按照“乡村志”系列小说的出版时间来看,较早出版的《土地之痒》《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医之家》故事的发生地主要在贺家湾,《是是非非》《青天在上》则是以官场政治为书写重点,讲述重心在乡村和城镇之间,而到了后期出版的《大城小城》则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彻底转移至城市。这种“由乡入城”的变化体现了作家创作视野的逐渐扩大,对农民的现实境遇描写不拘泥于乡村,而是扩大到进城的农民。贺家湾人生命轨迹的演变历程展现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人民心灵的变迁史。
乡土伦理产生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和单一的小农经济之中,“是在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时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3]李良、韦潇竹:《传统“乡土伦理”的现代转型与农村基层行政伦理建设》,《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107页。传统农耕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使得人们生产生活主要依靠家庭和家族来完成,对土地的依恋是人们安土重迁心理的重要原因,封闭性和交通的不便使得人口流动性较弱,人们就更加重视家族伦理和熟人社会关系。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价值观念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进入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经济模式,因此传统乡土伦理体系的破裂也在意料之中。“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二元化城乡经济结构类型势必孕育着二元化的城乡伦理结构类型,即城市伦理与乡土伦理之分辨。”[1]王露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土伦理研究及其方法》,《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第80页。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之中如何建构我们的乡土文化乃至民族文化,是作家和研究者们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
1. 现代制度对传统乡土伦理价值的冲击
“现代生活已在世界范围内打碎种种古老传统,中国农村也在开始变革,但观念形态这方面的变化却并不能算迅速”[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现代文明的进入对于传统保守的乡村来说首先冲击了人们心中固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打破了人们以往对于经济、基层管理的认知,同时乡村百姓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也影响了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文化的冲突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的建立与推广打破了乡村小农经济的保守封建。原有的乡村主要是自然经济,人们依靠土地获得生活来源,村邻之间经常互帮互助完成耕种和收获。土地制度由合作社改革为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紧密互助的关系已经有所瓦解,家家户户忙着开垦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土地之痒》中,村民们开荒热情的高度膨胀以至于破坏了当地的环境,村邻之间也经常因争地边发生矛盾,即使贺世龙、贺世凤两兄弟之间也因一垅地而闹得不愉快。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效率和报酬意识受到了农民内心的不满和抗拒,也打破了传统乡土文化中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中互帮互助的传统。
其次是现代法律制度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冲击。过去乡村的“法”主要是指宗族家法和人们习惯性的行为规则,靠的是宗族长老或地方乡绅。在熟人社会中“情”是人们衡量事情对错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而现代法律制度是依照法律条文办事,法理之外再考虑情的部分。“即使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时间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制定法的规则还是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已深深扎入我们灵魂和躯体中的习惯”。[3]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2-184 页。小说中,贺世普和贺家湾村民之间的冲突具体、形象地体现了现代法律意识在基层推行之艰难。中学校长贺世普退休后回到家乡出任村矛盾纠纷调解小组的组长,依靠自身在村民心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贺世普确实为贺家湾村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在很多时候村民们觉得贺世普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比如贺世普在处理贺建华抚恤金时坚持其配偶和女儿的继承权,坚持将妹夫告上法院判刑等,在村民们“就活人不就死人”的亲情伦理观念、乡情大于国法的观念中,贺世普这样的做法是不近人情的。“习惯要服从法律”是贺世普在家乡的处事原则,但在传统伦理价值面前,贺世普一次次碰壁,最终因不得人心不得不回城里去。现代法律制度推广之难还体现在基层政治方面。关于基层组织的民主选举,贺享雍早期在《土地神》中条分缕析地剖析了基层如何应对“民主”。在《民意是天》中则更加深入展开农村基层政治生态的现状,一方面写出了村民对《选举法》相关法律知识的匮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村民们对选举漠不关心的态度。村民们面对选举有着各种人情和利益关系的考虑,贺端阳经历三次选举,每一次选举作家都让读者看到了当下乡村基层政治的缺陷,以及法律规则被无视、玩弄。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贺享雍对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描写与刻画是极为突出、传神的,既写出了官场弄虚作假、权力勾结、玩弄权柄等不良风气,又写出了基层干部的不容易,作者在审视和反思他们性格上的缺陷之外又抱有一种同情,如早期作品中牛二、“乡村志”中的郑锋、贺世忠、贺春乾等人工作中的无奈之处。
2. 现代思想意识的悄然融入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1]秦晖:《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3页。当下的乡村伦理和文化具有转型时代的鲜明特征,既保留了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性的一面。伴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适应,农民的思想也在逐渐向现代靠拢,在“乡村志”系列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公平、效率、交易的意识,贺家湾的村民在请人帮忙时已经习惯了支付一定报酬。同样村民们的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也在悄悄发芽。在描写村民现代法律意识淡薄的同时,作家不仅仅指出了农民的思想现状和后果,而是进一步探寻问题的成因。小说写到的问题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基层干部没有宣传普及到位,甚至根本没有向群众宣传基本的知识。长期以来选举组织者选举投票的不正规操作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中国农民确实缺乏民主的实践,对民主选举制度没有太深的认识,这不能怪他们,只能怪我们这些选举的组织者嘛!”[2]贺享雍:《民意是天》,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16页。尽管在具体过程中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现代经济、法律意识已经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规则和当代乡村伦理体系的新建,在今后的中国乡村发展中如何普及、规范制度操作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乡土文学是百年来中国文学书写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审美主题,由此产生了鲁迅、茅盾、废名、沈从文、赵树理、孙犁、柳青、梁斌、莫言、贾平凹、赵德发等众多名家。鲁迅、赵树理等吸取民间艺术资源和传统小说叙事经验,描绘出一幅幅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风情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何申、关仁山、刘醒龙等作家为代表创作了一批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品,因此形成“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文学创作潮流,反映了20世纪末面对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社会问题和人们所经历的转型期的阵痛。作家们的这种创作姿态体现了他们身上的“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1]陈思和:《就 95“人文精神”论争致日本学者》,《天涯》1996年第1期,第19-25页。乡村生活经验是作家们进行乡土小说创作时不可或缺的生活体验,但是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作家们在创作时多数已经久居城市等现实原因,让作家们在捕捉当下乡村发展的问题和农民的精神情感状态时往往有“隔膜”之感。当下能够像赵树理、柳青等作家深入乡村生活进行创作的作家实在少之又少,贺享雍则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他对农村和农民始终抱着理解和共情,在作品中一直试图为农民解决眼下的困境。
贺享雍“乡村志”系列小说的推出,不仅直指当下乡村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直面农村背后更大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贺家湾几十年来的发展正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许多问题不是农村独有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可忽视的更为普遍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精神危机和文化重建的困境。作家通过小说世界对当下社会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不仅仅是针对过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和我们当下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进行对话。这种直面当下的勇气,以及洞悉一切生活细节和人的心理变化的笔力,为我们呈现了当下乡土小说写作所需要的一种重要的品格,体现出一种“当下现实主义”的可贵审美姿态和建构精神。更为宝贵的是,在当下诸多由作家在城中创作的“缅怀”式的乡土文学作品中,贺享雍通过扎实的在乡写作所捕捉到的同时代人的心路变化历程,为研究者以及后人们提供了一份更具有生活细节和生命温度的文本。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尽管“乡村志”系列小说在叙事技巧上仍有一些不足,但是小说所建构的完整的乡村发展史、农民心灵变迁史,为我们回顾历史、反省当下提供了一面很好的审美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