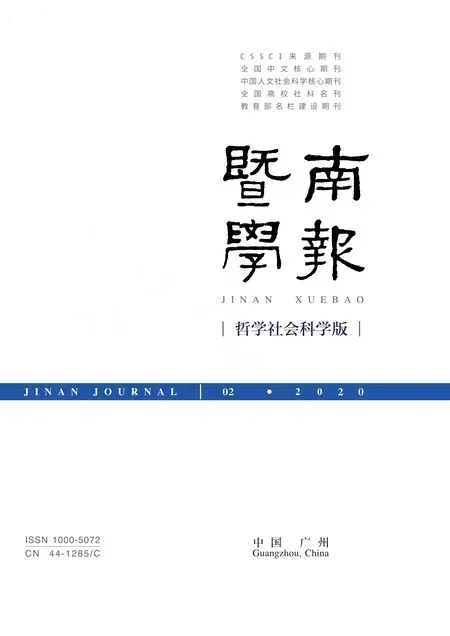平台格式条款的强制披露规制完善研究
宁红丽
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吸引了数以亿万级的陌生用户,传统的企业管理制度无法满足海量用户的治理需求,平台转而通过制定规则与用户签约的方式实现对海量用户的管理,即通过合同来管理用户。为了实现其目标,平台首先制定标准和规则,通过签订注册协议的方式要求其用户遵守;平台规则中包含着了大量的检测手段和惩罚措施,其订入合同获得合同效力的法律支持。平台规则是理解网络空间秩序的重要切入点。在私法语境下,平台规则以其“无磋商可能性”成为最典型的格式条款。各国立法都对格式条款的强制披露进行规制,旨在落实格式条款的制定方向相对人提示条款的具体内容。但强制披露对合意形成和公平交易规制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这一问题在我国学界尚未得到重视。(1)马辉:《格式条款信息规制论》,《法学家》2014年第4期。该文中作者认为,信息规制应与此种决策机制和市场规律相契合。以此来改良我国现有的格式条款信息义务,需增强条款提示的外观和内容显著性, 要求经营者提供通俗化与标准化的条款信息,并运用行政手段创设具体的揭示规则并强化事前监管,构建信息规制的公私法合作机制本文即以电商平台格式条款强制披露为研究对象,在对平台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行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学界争论,旨在反思强制披露的功能与价值,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一、平台格式条款的强制披露: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相关立法及评价
《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201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又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电子商务法》强化了对强制披露的立法态度,设置了数个条款对其进行规制(第15、16、19、32~37条),其第32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
概括而言,基于上述规定,我国现行法上强制披露的效力逻辑体现为:“强制平台披露”相当于“相对人知悉”格式合同的内容;具体而言,强制披露将下述四个情形做了等同处理:符合法律法规的披露=相对人有机会阅读=相对人实际阅读=相对人理解。但是强制披露实际发生的效果却值得探究。本文以下内容即结合“淘宝网”、“京东商城”以及“苏宁易购”等大型电商平台规则的强制披露实践,以及国内外司法实践展开分析。
(二)电商平台格式条款披露实践
在平台格式条款的披露与同意方式上,淘宝网、京东商城、苏宁易购等大型电商平台均采用“不经阅读即可同意”的注册方式。以淘宝网为例,其统一将格式合同公示在其规则页面。截至2019年9月19日,该页面共有1659条知识,用户于“淘宝网”首页点击“免费注册”,即会弹出对话框,显示注册协议,在点击对话框最下方的“同意协议”按钮,即可进入下一步注册程序。淘宝虽然在注册协议中以加粗加黑的方式提醒消费者应当注意“与您约定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与您约定法律适用和管辖的条款”以及“其他以粗体下划线标识的重要条款”,但在主页面上未显示具体的条款内容。《淘宝平台服务协议》、《隐私权政策》、《法律声明》以及《支付宝服务协议》均以词条链接的形式附于主页面的左下方且四个附属文件并不需要分别点击同意,用户不经点击阅读即可进入下一注册界面。
在格式条款的提请注意方式上,提请注意的方式均为下划线加粗字体,内容一般为:“[审慎阅读]您在申请注册流程中点击同意本协议之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协议。请您务必审慎阅读、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免除或者限制责任的条款、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条款。免除或者限制责任的条款将以粗体下划线标识,您应重点阅读。如您对协议有任何疑问,可向淘宝平台客服咨询。”(2)https:∥reg.taobao.com/member/reg/fill_mobile.htm,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6月30日。文本内容一般采加黑加下划线方式。
(三)平台格式条款披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电商平台格式合同的强制披露,普遍存在以下特点:
(1)格式合同规模过长。电商平台格式合同篇幅普遍较长,如淘宝规则、天猫规则均为一万四千字,淘宝平台服务协议内容为一万字,京东商城注册协议的内容为五千字,苏宁易购会员章程篇幅为一万五千字。篇幅长也是国内外购物网站的共同特点,如美国沃尔玛的用户条件和隐私条款总体约一万四千(英文)字,Ebay用户协议总共八千多英文字,(3)https:∥www.ebay.com/help/policies/member-behaviour-policies/user-agreement?id=4259,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8月2日。亚马逊网注册协议也超过两万字。注册协议的内容如此庞大,与一般网络用户的阅读习惯并不相符。
(2)平台服务协议中“显著提请注意”方式过于单一。目前我国网络购物平台服务协议均采用单一的、相似或相同的方式履行格式条款的提请注意义务,即“加粗字体加下划线”的方式,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平台在其服务协议中均采用了此种方式。
(3)“显著提醒”被过度使用。平台规则中“显著提请注意”方式被过度使用的现象十分明显。经过对平台服务协议中显著提醒注意的格式条款的内容数量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淘宝平台服务协议》中显著标识的字数占协议总字数的比例高达45%;《京东用户注册协议》中这一比例为66%。格式条款制定方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显著提请注意的格式条款范围;显著标注的条款数量的不断增多,也导致了“显著信息不显著”的问题出现。
(4)平台规则中专业术语的使用十分普遍,超出普通用户的理解能力。以《天猫服务协议》第7条第4项为例,该项规定:“天猫仅对因其故意、重大过失或其他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导致用户的损失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且金额以用户缴纳的服务费用为限。(4)《天猫服务协议》第7条第4项:“因天猫须向数量庞大的商户提供服务,且服务内容复杂、技术要求高,您认可天猫仅对因其故意、重大过失或其他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导致您的损失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且金额以您缴纳的服务费用为限。”《淘宝平台服务协议》第4.6条“责任限制”(5)《淘宝平台服务协议》第4.6条“责任限制”[不可抗力及第三方原因]:“淘宝依照法律规定履行基础保障义务,但对于下述原因导致的合同履行障碍、履行瑕疵、履行延后或履行内容变更等情形,淘宝并不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出现了“不可抗力”、“合同履行障碍”、“履行瑕疵”、“履行延后或履行内容变更”、第6.3条“赔偿责任”条款里出现了“重大过失”、“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等合同法领域的专业用语。对于此类术语,用户很难准确理解。
二、司法实践:强制披露的效力认定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主流意见承认强制披露制度的效力逻辑。在裁判过程中,法官一般先认定格式合同使用人的披露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然后再认定格式条款能否订入合同。下文即通过一些代表性案例来对此逻辑展开分析。
(一)我国司法实践
早在2001年的“易趣网络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与刘松亭服务合同纠纷案”(6)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1)静经初字第931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辩称,原告的《服务协议》过于冗长,致使用户在注册时不可能阅读全文,故被告不应受该协议的约束。但该抗辩并未为法院采纳。法院认为,原告制订的《服务协议》,经被告确认后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故该份《服务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在“鲁志刚、李峡诉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7)鲁志刚、李峡与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9382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承认曾经点击过服务协议,法院认为,原告未阅读即点击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该服务协议的有效条款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与蔡振文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8)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与蔡振文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2016)粤06民终3872号。中,原告主张“没有打开阅读任何规定或条款,未发现有提示或意思解释”,由于注册淘宝账户必须点击确认同意接受,“阅读与不阅读均无意义”,且原告主张其并不理解协议中的法律专业用语。但该主张未获得法院支持。“施无竞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9)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终字第0914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施无竞作为一名不特定的网络用户,其在注册时已自愿接受《淘宝网服务协议》确定的规则,该协议的约定对施无竞应当产生约束力。“孟静、黄惺与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10)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9048号民事判决书。案中,法院认可纽海电子商务公司以点击合同展示格式条款的行为“符合交易习惯”,以加粗格式字体的形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相关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有效。
上述判决提出了关于强制披露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格式条款制定方所负有的提请注意义务是对披露方式的要求还是对披露效果的要求?“充分完全披露”是否意味着平台企业在践行了强制披露程序后,就进入了“安全港”?更具体而言,平台仅通过字体、字号以及加粗等形式上的提醒,是否就可认定为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有少数判决认识到这一问题。如在“高春梅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俞秀兰网络购物合同纠纷”(11)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14121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被告虽然用红色字体标注但没有对该字条的说明解释,但不能视为尽到了提请注意的义务。对于与消费者权益有重大利害的表述字词没有特殊的解释说明,即使消费者关注到了红色字体,仍足以使其陷入错误的认识。“黄海禹因与深圳市龙华新区锦泉百惠商行、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12)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3民辖终296号民事裁定书。中,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仅通过字体加黑方式尚未尽到合理提请消费者注意的义务,“字体加黑方式能够引起消费者合理注意的前提是与其他条款字体明显不同,而根据寻梦公司提供的《拼多多用户协议》内容共计十二页,几乎每页均有多条黑体标示条款,其中共达五页中的黑体标示条款明显多于非黑体字条款”。法院据此认为,“经过字体加黑的管辖权条款与其他条款并无明显区别,未起到提请消费者合理注意的作用,因此不能订入合同”。
(二)美国判例
对美国法官而言,应对网络用户施加何种水平的注意义务,同样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美国法院一直试图设立一个合理的网络用户的注意标准,以此来判断网站经营者是否达到了合理的提示义务。1967年的Bureau v.Barrett Garages案(13)Specht v. Netscape Commc’ns Corp. 306 F.3d at 30 n.14 (2d Cir. 2002).中,法院认为,合理的注意义务就是“对相关款项用语的实际提醒可以使一个推定的个体达到足以了解其内容的程度。”Berkson v.Gogo,LLC案(14)Berkson v. Gogo, LLC, 97 F. Supp. 3d 359, 366 (E.D.N.Y. 2015).中,Berkson与Gogo公司在线签订的网络服务合同中,包括了一项连续包月自动续期的条款,就该条款是否对消费者进行了合理披露,法院认为,合同的提供者必须确保消费者作为“合理人”就能了解条款的含义。因此,不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条款不发生约束力。在该案中,法院提出了“合理谨慎的网络用户”(reasonable prudent user)标准。但这一标准的具体内涵尚未得到准确界定。法官在该案中认为,不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条款对当事人不产生约束力。2002年的Specht v. Netscape Commc’ns Corp.案(15)Specht v. Netscape Commc’ns Corp. 306 F.3d at 30 n.14 (2d Cir. 2002).中,法官认为网站的提醒注意义务是否达到“典型的网站访问者能够理解网站目的的程度”(typical visitors would have understood the site’s purpose),此外还有“平均的网络用户”(average Internet user)等提法等。但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判例中还未形成一个关于网络用户注意义务的统一称呼,有关注意义务水平的一般标准也无从谈起。美国法院在具体案例中一般会结合网页页面颜色字体设计、条款内容的可读性等因素对强制披露是否符合法律标准作出个别判断。
综上所述,法院对强制披露的做法和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处理方法,造成这一差异化的原因在于,有关格式条款强制披露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适当回应。例如,强制披露是否有助于真实合意的达成?强制披露是否真正改善了消费者的信息问题?在判断网络平台经营者是否尽到强制披露义务时,是否有必要就用户注意标准做认定?这些问题在我国学界尚未得到关注。下文将结合国内外有关强制披露的不同观点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三、同意但不阅读:合意的“假象”
(一)人们是否阅读平台协议
提供阅读机会并不意味着用户会阅读平台协议。格式条款强制披露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提供阅读机会是否重要?阅读机会对当事人全面详细了解条款内容,达成真实合意是否有实质作用?不难发现,即使对平台科加更重的披露义务,在网络交易环境下也很难期待用户仔细阅读交易条款。(16)Robert A. Hillman, Ibrahim Barakat, “Warranties and Disclaimers in the Electronic Age”, Yale Journal Law & Technology, Vol.11, No.1, 2008, p.25.Robert A. Hillman教授在其任教的法学院合同法课堂上所做的调查表明,92个受调查对象中,只有4%的在线购物者在整体上阅读过标准合同;阅读过网站的瑕疵担保条款的仅有15人。(17)Robert A. Hillman, “Online Consumer Standard Form Contracting Practices: A Survey and Discussion of Legal Implications”, in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Age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2006),at 285,308. n.30.而在笔者在法学院学生的课堂调查中,这一数据几乎为零。Plaut and Bartlett在乔治亚大学182名研究生中展开的调查显示,有80%的调查对象根本不阅读条款,而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选择直接跳过协议阅读步骤。(18)Plaut and Bartlett, Blind Consent? A Social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Non-Readership of Click-Through Agreements,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8597/afc0e751737182c4d569516a7748f73c830f.pdf,p.11.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8月2日。Florencia Marotta-Wurgler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使网站提供的格式合同明显对卖方有利,也不会影响用户继续购买。(19)Florencia Marotta-Wurgler,“Does Contract Disclosure Matter?” 2012.这说明,高披露率并不必然导致高阅读率;少数阅读协议的用户也未能作出理性决定。因此,明智的网站设计者都会希望用户作出确定的行为表示其对相关文件的接受和同意,从而使合同的效力得以确认。(20)Ronald J. Mann, “Travis Siebeneicher, Just One Click: The Reality of Internetretail Contracting”,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08,2008,p.993.
(二)人们为何不阅读格式条款
笔者认为,消费者不阅读网络格式合同的原因如下:
(1)基于认知局限放弃阅读。网站格式合同的篇幅过长,不符合一般用户的阅读习惯。“从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角度看,顾客的眼光主要集中在价格或主给付义务上,对于从条件或附加条件,或因根本就未意识到,或因不清楚其效果,或因未想到其重要性等等”,而常常予以忽略。(21)[德]卡纳里斯,张双根译:《债务合同法的变化——即债务合同法的“具体化”趋势》,《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2)格式合同的语言过于专业化,超出消费者的理解能力。在调研中笔者发现,网络交易格式条款的措辞语言远超过普通网络用户的理解能力,其不但内容复杂,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即使是专业的法律人士也难以正确区分其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和风险负担。以“京东商城注册协议”的“合同成立”规则为例,该规则规定:“如果您在一份订单里订购了多种商品并且销售方只给您发出了部分商品时,您与销售商之间仅就实际直接向您发出的商品建立了合同关系,只有在销售商实际直接向您发出了订单中订购的其他商品时,您和销售商之间就订单中其他已实际直接向您发出的商品才成立合同关系”,据此消费者可以将合同成立时间理解为“经营者发出商品时”,但其下方条款又有“当您作为消费者为生活需要下单并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您货款支付成功后即视为您与销售商之间就已支付货款部分的订单建立了合同关系”(22)京东注册页面, https:∥reg.jd.com/reg/person?ReturnUrl=https%3A∥www.jd.com/%3Fcu%3Dtrue%26utm_source%3Dhaosou-search%26utm_medium%3Dcpc%26utm_campaign%3Dt_262767352_haosousearch%26utm_term%3D7945648310_0_d8bfd3a02fb549a8b592f277a8e7fcd9,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2月1日。,即消费者品网购合同的成立时点提前至“支付成功时”。同一规则出现了两种表述,对于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用户,不啻于拗口的文字游戏。
此外,平台格式合同的交叉互引现象也很常见。若用户想详细了解有的格式条款的具体内容,还需二次或多次点开关键词,通过链接查看冗长复杂的解释说明。如在《淘宝规则》中,存在着与《淘宝网评价规范》、《淘宝禁售商品管理规范》的交叉互引;《天猫规则》中交叉引用现象更普遍,其中包括《淘宝开放平台管理规范》、《淘宝供销平台管理规范》、《飞猪规则》、《淘宝游戏市场管理规范》、《淘宝网通讯市场管理规范》等。从强制披露的角度看,将规则设计得更加具体、严谨有利于交易中风险的明晰化,但其负面效果是消费者几乎不可能把握这些条款的含义。
(3)普遍存在的“修改条款”与“将来条款”消弭了事前阅读的价值。由于各平台协议的条款修改十分频繁,平台协议内容存在明显的不稳定性。在各个注册协议或会员章程中,几乎都包括典型的“将来条款”和“修改条款”。如《淘宝规则》第78条规定,“淘宝会对本规则进行不定期修订,并在淘宝规则频道执行公示程序。若修订内容对多数用户的权益构成重大影响,则另行执行征求意见程序。公示期结束后,规则修订内容即告生效。”(23)https:∥rule.taobao.com/detail-14.htm?spm=a2177.7231193.0.0.54c817eaSPx5zd&tag=sel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27日。京东商城《用户注册协议》第一条“服务条款的确认及接受” 即以加黑字体标注了类似条款。(24)“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变化及本软件运营需要,京东有权对本协议条款及相关规则不时地进行修改,修改后的内容一旦以任何形式公布在本软件上即生效,并取代此前相关内容,您应不时关注本软件公告、提示信息及协议、规则等相关内容的变动。您知悉并确认,如您不同意更新后的内容,应立即停止使用本软件;如您继续使用本软件,即视为知悉变动内容并同意接受。” https:∥in.m.jd.com/help/app/register_info.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7月14日。这就说明,平台有权利随时修改其格式条款,这就更进一步降低了使用人通过强制披露获得信息的动机。学者指出,这种广泛应用的“单方修改条款”降低了强制披露的价值。(25)David Horton,“The shadow terms:Contract Procedure and Unilateral Amendments”, UCLA Law Review, Vol.57,2010,p.605.
(三)强制披露有无价值
1.强制披露无价值论
在完全理性模式下,强制披露制度才能发生其期待效果,消费者能基于其占有的充分信息作出理性判断,从而改善自身福利;但在有限理性模式下,强制披露能否实现其预期效果遭到强烈质疑。英国学者阿狄亚早就认为,法律在解决是否产生“合意”的问题上采用了相当宽松的标准,除非高薪聘请律师,合同当事人不可能阅读、理解那些复杂的书面合同,但却被那些没有阅读或不理解其法律意义的条款所拘束。因此许多合同义务并未含有真正的同意。(26)[英]阿狄亚著,赵旭东等译:《合同法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306页。在美国,Victor P. Goldberg教授在1974年就开始质疑强制披露的价值,(27)V. P.Goldberg,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Quasi-Invisible Hand”,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17,No.2,1974,p.461.其后的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指出强制披露并未发挥其规制效果。(28)Robert A. Hillman & Jeffrey J. Rachlinski, “Standard-Form Contracting in the Electronic Age”, NYU Law Review, Vol.77,No.429, 2002. Omri Ben-Shahar, “The Myth of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in Contract Law”, Europe Review Content Law, Vol.5, No.1, 2009; Margaret Jane Radin, “Boilerplate: The Fine Print, Vanishing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2013.芝加哥大学Omri Ben-Shahar教授更是尖锐指出,由于强制披露消除了合同订立中的合意瑕疵与程序瑕疵,使程序上的显失公平没有适用的空间,指出强制披露“不仅无益,而且有害”。(29)[美]欧姆瑞·本·沙哈尔、卡尔·E.施奈德:《过犹不及——强制披露的失败》,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如上文所言,在强制披露模式下,明智的网站设计者都会希望用户有确定的行为表示其对相关文件的同意,从而确认合同的效力。(30)Ronald J. Mann, “Travis Siebeneicher, Just One Click: The Reality of Internetretail Contracting”, Columbia Law Review,Vol.108,2008,p.993.强制披露的反对者指出,鉴于多数消费者根本不阅读长篇累牍合同文本的现实,合同法中的这种“提供阅读机会”规则,应该被摒弃。“强制披露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建立在一条脆弱的因果链条之上。只有当以下三方——立法者、信息披露人及信息披露对象——都能熟练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时,该制度才有可能运行。但各方很少能满足各自角色所需要的所有要求。”(31)[美]欧姆瑞·本·沙哈尔、卡尔·E.施奈德著,陈晓芳译:《过犹不及——强制披露的失败》,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强制披露仍有价值
与上述对强制披露持悲观态度的学者不同,也有不少美国学者认为,在目前提出的全部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制建议中,最可行同时也是最有效果的做法仍然是强制披露。担任过美国白宫信息管制事务办公室主任的Cass Sunstein教授曾指出,管制的首要目标是要确保消费者在获取信息后作出理性选择,而非依政府的指示行动。(32)Cass R.Sunstain, “Informing America:Risk, Disclosure,and the First Amendment”,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20,1993,pp.653,654.因此,强制披露仍有其独特价值。Robert A. Hillman教授则认为,虽然网络经营者的强制披露未必能激励消费者在线阅读合同条款从而实质改善其福利,但与其他措施比起来,强制披露仍然是最可施行的和成本最小的手段。(33)Robert A. Hillman, “Boilerplate in Consumer Contract: Online Boilerplate: Would Mandatory Website Disclosure of E-Standard Terms Backfire”?, Michigan Law Review, Vol.104,2006,p.856.总体上而言,学者认为强制披露制度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强制披露是所有管制手段中最易于实施的,且成本低。(34)Elizabeth Austin Bonner, “Network Neutrality Disclosures: More and Less Inform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Vol.8, 2012, p.188.强制披露由企业而非政府实施,平台企业承担了信息的设计、收集、传播以及维持的任务,相关成本也都由企业承担;与其他规制手段相比,强制披露对“精确性”要求并不严格,而且更灵活,可随着消费者偏好和技术的变化随时调整。
第二,强制披露有利于强化市场竞争。网络市场中信息的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出卖人拥有买方所不具备的信息。规制部门在实现与经济发展同步所需的信息收集处理上也存在结构性的能力缺陷。强制披露有助于提升买方的认知水平,改善其在交易中的地位,从而助其作出更效率的选择。(35)William M. Sage, “Regulating Through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aws and American Health Care”, Columbia Law Review, Vol.99,1999,pp.1701, 1716.在竞争性的市场中,网络经营者追求更大的市场份额,必将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交易条款。即使网页披露实际上没有提高阅读量,基于获取竞争优势的动机,强制披露仍有可能激励经营者起草对消费者更有利的格式条款。(36)Florencia Marotta-Wurgler, Competition and the Quality of Standard Form Contra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s 33-34,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and Economy Research Series, Working Paper No.05-11, 2005,pp.33-34, 这一问题值得分析。Florencia Marotta-Wurgler在其关于市场竞争对标准条款内容的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在交易之前就向用户展示的条款比交易发生之后才展示的条款在内容上更有利于卖方。Robert A. Hillman, “Boilerplate in Consumer Contract: Online Boilerplate: Would Mandatory Website Disclosure of E-Standard Terms Backfire?”, Michigan Law Review, Vol.104,2006, p.853.因此,通过格式条款缔结合同并不必然对消费者不利。美国学者Ronald J. Mann和Travis Sirbeneicher在调查了五百家网站的零售合同条款之后发现,超过一半的格式合同中并没有出现仲裁条款、违约赔偿放弃条款以及其他典型的对买方明显不利的标准条款,其原因在于网站希望格式条款看起来是“温和”而非苛刻的,一旦发生争议,网站也希望其交易条件对消费者是可接受的。(37)Ronald J. Mann, “Travis Sirbeneicher,Just one Click,The Reality of Internet Retail Contracting”, Columbia Law Review, Vol.108,2008,p.1011.
第三,在合意质量上,与传统的纸质媒介缔约相比,电子缔约中的“合意质量”未必更低。Hillman和Rachlinski甚至认为,通过在线强制披露缔约的“合意质量”可能更高。他们在对纸质和电子环境下的缔约过程进行比较后认为,网络交易不受营业场所与营业时间的限制,消费者可以在任何便利的时间和地点(如家庭、交通工具、公园等)进行交易,因此其选择更自由;同时,网购者们还可以借助搜索引擎快速寻找商品,并对同一商品的交易条件进行比较。因此,从逻辑上而言,人们在网络交易时可以作出比在线下消费中更谨慎的决定。因此,消费者并不需要司法干预来保护他们免受商业滥用的侵害。(38)Robert A.Hillman & Jeffrey J. Rachlinski, “Standard-Form Contracting in the Electronic Age”,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77,No.429,2002,p.478.
(四)强制披露的真实效果
如上文所述,强制披露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其的通常期待之间明显发生了错位。从制度初衷来看,强制披露应当致力于促进“合意形成”,但基于消费者阅读的意愿低至可以忽略,这种法律拟制的“合意”与真实的合意关联性极低。作为一项在立法例中被广泛采纳的格式条款规制方式,强制披露到底具有何种价值?笔者认为,应对强制披露的实际效果进行重新评价,具体而言,强制披露在当今具有如下功能:
(1)鼓励竞争。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强制披露的目的是要向买家或者交易相对人提供信息,但实际上这种认识有失狭隘。笔者发现,销售者自愿披露信息以获得竞争中的优势。强制披露的对象与其说是“买家”,不如说成是“同行”和“监管者”;与其说是向交易对象披露,不如说成是向竞争对手和市场监管部门披露。相关理由如下:
第一,平台交易规则具有趋同性。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我国各大网络商品交易平台规则无论在体系、措辞,还是在披露方式上都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平台交易结构存在高度相似性。这说明了平台在进行交易规则的起草时通过竞争对手披露内容互相借鉴。
第二,通过强制披露,平台在消费者普遍关心的核心交易条款上展开竞争。虽然各电商平台基础规则体系虽现出相似性,但它们在消费者较为敏感的交易规则上却存在激烈竞争。以“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为例,笔者发现,几家电商平台在退货期、退货运费以及退货范围等几个方面均设置了不同的做法,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七天退货期的基础上,有的平台主动承诺更长的退货期,如十五天、三十天等;有的平台还设置了更多元具有针对性的退货规则,并主动承担退货运费。规则的竞争有助于改进消费者福利。因此,即使披露无助于提高买家的阅读率,但是却有助于同行之间展开竞争,消费者则可以从中获益。
(2)便于格式条款市场监管部门展开行政监管。平台经济时代,由于经营范围、地域和经营规模的改变,传统的市场监管很难有效发挥作用。有美国学者建议,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应当充当消费者的信息中介机构,对强制披露的内容是否准确有用实行周期性评估。(39)Disclosure and Simplification as Regulatory Tools (June 18,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assets/inforeg/disclosure-principles.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6月24日。Elizabeth Austin Bonner, “Network Neutrality Disclosures: More and Less Inform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8,2012,p.206.我国已有不少地方监管机构开始重视对电商平台格式合同的监管,具体体现为组织第三方评估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和合法性,如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网络市场监管机构均以各种形式组织第三方参与对网络交易规则的评估。
四、如何实现有效规制
如前文所述,网购时代消费者的“同意”建立在“不阅读”的事实上,引发了学界对强制披露制度价值的争议。但如上文所述,强制披露虽然在促成“实质合意”方面的作用有限,但其仍有助于平台经营者在消费者普遍关心的核心交易条款上展开竞争,同时也便于政府对网络市场展开行政监管。但需谨记的是,强制披露的制度初衷是为了改善消费者的信息权,而非为经营者提供一个额外的“商业避风港”。下文即在此基础上,对强制披露提出改善的建议,以促进实现规制的有效性。
(一)升级披露方式
正如桑斯坦所言:“信息披露可能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披露,而非是否披露。”(40)Cass R.Sunstein,“Empirically Informed Regul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78, 2011,pp.1349-1369.设计得当的披露要求,可以增加消费者的阅读机会,作出明智的决策,从而减轻市场失灵。披露主义者建议,强制披露应“简化”、“缩短”以及“标准化”(simplify,shorten,and standardized)。具体而言:
第一,从全面披露转向要点披露。由于消费者只了解自己关心和熟悉的内容,因此针对消费者的强制披露,不需将交易条件事无巨细进行全面披露,要点披露即可满足消费者对信息的需求。对此,美国学者提出“更清晰的提请注意”(clearer notice)标准。Cass Sunstein教授指出,应区分两种披露体系,即简化的有针对性的“概要披露”(Summary disclosures)和提供充分信息的“完全披露”(full disclosures)。对于概要披露,其原则在于要点信息(information of highlight)、简单具体(simple and specific)以及语言准确平时(accurate and plain language)。(41)Disclosure and Simplification as Regulatory Tools (June 18,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assets/inforeg/disclosure-principles.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6月24日。在Berkson v.Gogo案(42)Berkson v. Gogo, LLC, 97 F. Supp. 3d 359, 366 (E.D.N.Y. 2015).中,法官也认为,应当针对不同的格式条款呈现形式践行不同的披露标准。
第二,从专业披露转向平实披露。格式条款应语言平实,降低专业性。法律与商业的专业语言,对相对人的要求较高。结合消费者人像的特点,我们认为,针对消费者的格式合同应当采用浅显易懂的非专业语言草拟并传送。对此,《荷兰民法典》第233条规定,一般条款可因“使用人未给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认知一般条款和条件的合理机会的”而被宣布无效;《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第II-9:402条也有类似规定。
(二)对格式条款内容进行实质干预
1.《电子商务法》第32条的公平性内涵
《电子商务法》第32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此条是关于电商平台自身制定的标准的法律规制原则,其中的“公平、公正”标准是涉及电商规则内容的实质判断标准,应该对该标准作何种理解?公平原则原本意味着合同内容在价值上大体相当。但如何判断其是否“相当”,学说上一直有“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之争。“形式公平”之所以在交易法中具有普遍性,原因在于,“契约价格的适当性也很难客观决定,价格决定一方面跟市场关系有关,另一方面也涉及主观因素,因此,商品或服务的公正价格为何,很难界定”(43)黄茂荣:《债法各论》(第二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239页。。但《合同法》第39条所规定的作为格式条款内容控制标准的“公平原则”,其内容却与“程序公平”标准明显不同。《合同法》第39条应该采纳“实质公平”的标准。这是因为,对格式条款效力的控制,属于对合同自由的实质限制。(44)易军:《民法公平原则新诠》,《法学家》2012年第4期。此时不能根据当事人的意思来确定等价性,而是应采纳“客观的等价标准”。(45)黄立:《民法债编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台湾地区法院也认为,定型化契约“是否符合平等互惠原则,不能主观认定,而应依社会的客观标准,以及当事人双方是否彼此对约定内容有充分的认知来判断。(46)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1年度台上字第1365号判决。“按其情形显示公平者”,是指依契约本旨所生之权利义务,或按法律规定加以综合判断,有显失公平之情形。(47)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3年度台上字第2017号民事判决。因此,《电子商务法》第32条作为平台格式条款的基本原则,其“公平”内涵应当与《合同法》第39条相当,即采纳“实质公平”标准。
2.平台格式条款公平性的具体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对平台格式条款进行公平性判断,可以参照下述两个标准:
第一,平台格式条款不得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比较法中普遍将诚信原则作为格式条款公平性的判断标准。如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也规定:“定型化契约中之条款违反诚信原则,对消费者显失公平者,无效。”《欧洲民法典草案》(DCFR)第II-9:403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第2.1.20条都明定格式条款不得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格式条款违反诚信原则时,不发生效力。(48)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4页。关于格式条款违反诚信原则的认定标准,根据台湾地区消保法第施行细则第13条的规定,“应斟酌契约之性质、缔约目的、全部条款内容、交易习惯以及其他情事判断”。实践中,预先免除经营者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的“概括免责条款”、“自我矛盾条款”(如“广告仅供参考,合同内容以书面为准”)、不合理的风险分配或转嫁条款都应认定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无效。(49)詹森林:《消费者保护法发展专题回顾:定型化契约之理论与实务发展》,《台大法学论丛》2014年第43卷特刊,第1376—1381页。
第二,平台制定涉及消费者的条款不能低于法律的任意性标准。
笔者认为,将任意性规定作为格式条款的实质审查标准,主要是基于如下考量:
其一,任意性规定本身即“合理性标准”。法律设置任意性规定的目的,不仅在于补充契约之不备,而且合理分配契约上的危险,平衡当事人利益,兼具有实践正义功能。(50)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页。任意性规定是立法者基于公平衡量当事人利益而得出的解决方案。立法者允许当事人基于自身考虑,作出区别于任意性规定的约定。若当事人未特别约定而适用任意规定,解决当事人契约关系所生的争执时,任意规定扮演形成契约内容的角色,任意规定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也成为合同关系的内容。(51)陈自强:《民法讲义Ⅱ——契约之内容与消灭》,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17页。
其二,将任意性规则作为格式条款效力的判断标准,也是国外立法例中的通行做法。对此,德国民法典第307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如格式条款在其主旨上偏离了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不适当损害利益。德国法院在对格式条款做内容审查时,首先采用的工具就是法律的任意性规范。(52)贺栩栩:《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规范基础分析:一般条款与法定示例》,陈金钊、谢晖:《法律方法》(第1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8页。《荷兰民法典》第237条b款、日本《消费者契约法》中关于“不当条款”的规定,都是要求格式条款同民法、商法或其他法律的任意性规定相比较,从而区分其中哪些条款限制了消费者权利或加重了消费者义务。通过立法直接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格式条款的判断标准,不仅有利于减轻消费者举证负担,也可使经营者知晓何种契约不得使用,为其提供了事先避免不当条款出现的参照,有助于交易安全。(53)王福华、张磊:《格式合同协议管辖条款之效力》,《烟台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基于此,在保护消费者的范围内,私法的任意性规定可转化为强行规定,契约自由受其限制。学说称此种情形为“任意规定的半强行化”。(54)陈自强:《民法讲义Ⅱ——契约之内容与消灭》,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例如,平台卖方实通过格式条款限制或免除了己方瑕疵责任的规则即为无效。虽然标的物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一般情形中都属于任意性规定,但若在定型化契约条款被排除其适用,则可能因显失公平而被认定为无效。
3.引入“黑名单”和“灰名单”制度
“黑名单”条款,即绝对无效的格式条款,《德国民法典》将其称为“无评价可能性的禁止条款”。“黑名单”中的条款导致当事人合同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甚至违反法律基本价值观念,因此被直接确认为无效,法官对此无任何自由裁量权。“黑名单”在《德国民法典》中有13种情形,《欧盟消费者合同不公平条款指令》列举了17种情形,《欧洲共同买卖法》草案将“黑名单”称为确定不公平条款,有11种情形,它们或者是严重违背法律的基本价值观念,如限制或排除造成对方当事人人身损害或死亡责任的条款,或者是严重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限制或免责条款,如排除或者限制经营者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失或损害责任的条款。
“灰名单”条款即“推定无效条款”,这些条款大多涉及增加交易相对人的负担,或者不合理地排除或限制相对人的权利,或者赋予格式条款使用人某种特权。法官则可结合具体案情判断这些条款是否严重不公平,进而决定是否属于不公平条款。“灰名单”中的条款所造成的合同权利义务失衡并不特别严重,其最终能否被认定为不公平条款,需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
立法例中,1982年的以色列《标准条款法》专门设立了“标准条款法庭”(Standard Contracts Tribunal)这样的准行政机构,对格式合同进行事前审查。这个机构有权力在诉讼程序之外对可能涉及不公平的格式条款进行评价。这部法律对推定无效的条款进行了列举规定,包括“概括免责条款”(waiver of all liability),授与单方设定或者修改价格权条款以及限制消费者法律救济的条款(如强制仲裁条款等)。(55)Sinai Deutch, Controlling Standard Contracts—The Israeli Version, 30 McGill L.J. 458 (1985)1993年欧盟的《消费者合同不公平条款指令》、《荷兰民法典》第6:237条、2015年的《英国消费者权益法案》(ConsumerRightsAct)、DCFR第II-9:410条第一款a至q项也列举了“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订立的合同中推定不公平的条款”。(56)《欧盟消费者合同不公平条款指令》第 3 条第 3 款即确认附录所列不公平条款名单是不穷尽的(non-exhaustive list) 。关于欧盟成员国司法对不公平条款制度的创设与推动,参见[德]海因·克茨著,周忠海等译: 《欧洲合同法》(上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2—206 页。这种规制方式也有其不足,如英国学者休·柯林斯所指出的,如果不存在关于合同条款的竞争性市场,经营者可以仅做细微的改变就能规避开黑名单和的灰名单的规制。[英]休·柯林斯,郭小莉译:《规制合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1997年泰国也颁布《不公平合同条款法案》,列举了推定无效的格式条款。(57)Unfair Contract Terms Act, B.E. 2540 (1997).ThaiLaws.com,http:∥thailaws.com/law/t_laws/tlaw0319.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5月14日。
2015年我国国家工商总局《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工商总局第73号令)第12条列举了七项条款,(58)该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不得作出含有下列内容的规定:(一)免除或者部分免除经营者对其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承担的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赔偿损失等责任;(二)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提出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以及获得违约金和其他合理赔偿的权利;(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法投诉、举报、提起诉讼的权利;(四)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或者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对不接受其不合理条件的消费者拒绝提供相应商品或者服务,或者提高收费标准;(五)规定经营者有权任意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限制消费者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权利;(六)规定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七)其他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这种做法类似于“黑名单”或“灰名单”制度的雏形。结合网站实践和立法例做法,笔者建议,未来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中拟定“黑名单”条款与“灰名单”条款,为平台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判断提供标尺。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格式条款黑名单[确定无效的格式条款]。
网络交易平台制定的与消费者之间的格式合同中,包含下述条款的,无效:
(1)免除条款制定方对其造成的消费者人身伤害的责任;
(2)免除条款制定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失的责任;
(3)免除条款制定方因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
(4)免除条款制定方因未尽到法定审查义务造成的用户人身伤害的责任;
(5)约定合同所产生的所有争议均由网络平台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的;
(6)排除格式条款相对人就格式条款争议提起诉讼的权利;
(7)规定条款制定方享有确定商品价格的权利;
(8)约定特定情形中禁止相对人请求违约金的权利;
(9)约定条款制定方有权任意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限制消费者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权利;
(10)约定仅一方当事人享有选择仲裁机构的权利;
(11)约定条款制定方享有对合同的最终解释权;
(12)其他严重侵害消费者权利的条款。
第二,格式条款灰名单[推定无效的格式条款]。
网络交易平台制定的与消费者之间的格式合同中,包含下述条款的,推定为无效:
(1)约定免除或者部分免除经营者对其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承担的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赔偿损失等责任;
(2)约定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提出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以及获得违约金和其他合理赔偿的权利;
(3)约定消费者承担的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超过法定数额或者合理数额;
(4)约定由消费者承担应当由格式条款制定方承担的经营风险责任;
(5)约定条款制定方享有单方修改权,而并未授予相对人在条款被修改时的解除权;
(6)规定条款制定方享有提价权,但并未授予相对人在条款被修改时的解除权;
(7)其他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三)网络商品市场的行政规制——市场监管机构充当信息中介
1.要求平台提供有效的信息类型
为弥补市场在最低消费信息传播上的不足, 规制机构或其委托机构有义务收集和整理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并促使其充分流动,使尽可能多的消费者知悉。只有如此,信息工具才能发挥起较为有效的规制作用。Florencia Marotta-Wurgler认为,消费者需要的并非数据或海量信息,而是需要有效的“建议”(advice)。(59)Florencia Marotta-Wurgler,“Even More Than You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Failures of Disclosure”,Jerusalem Review of Legal Studies, Vol.11, No.1, 2015, p.65.如美国学者发现,在洛杉矶强制要求食品零售业在橱窗公示标准化的食品卫生评级卡之后,餐厅的评级监督分数普遍得到改善,消费者对餐厅卫生分数的敏感度也明显提升;(60)Zhe jin, G. and Leslie, P. [2003],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on Product Quality: Evidence From Restaurant Hygiene Grade Card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8,No.2,2003,p.402.纽约强制连锁餐厅标识食品卡路里数目,星巴克商店中食品消费热量降低6%。因此,建议我国监管机构调整信息规制的方式,除了要明确监督平台是否尽到了强制披露义务,还要求平台提供的信息类型上实施管制。
2.对敏感条款建立专门的监督机制
在美国,网络购物平台格式条款的瑕疵类型主要包括管辖权条款、免除或限制担保责任和集团诉讼放弃的条款等。(61)Christina L. Kunz et al., “Browse-Wrap Agreements: Validity of Implied Assent in Electronic Form Agreements”, The Business Lawyer, Vol.59,No.1,2003,pp.280-281.而针对这些问题,FTC负有一项职能,即其可要求经营者周期性地证实消费者的合同期待,并对那些不符合消费者期待的可能对其不利的条款提出警示。(62)Ian Ayres & Alan Schwartz, “The No-Reading Problem in Consumer Contract Law”,Stanford Law Review,Vol.66,2014, p.553.Ian Ayresu与Alan Schwartz指出,网络交易中格式合同的“不阅读”问题,造成了“严重误读条款”这一不效率的后果,他们提出建立“意外条款盒子”,通过此机制对交易中出现的那些不利条款对消费者作出警示。(63)Ian Ayres & Alan Schwartz, “The No-Reading Problem in Consumer Contract Law”,Stanford Law Review,Vol.66,2014, p.580.FTC的这项规制措施也类似于“灰名单”的功能。例如,如果格式条款中约定,“无论争议的解决结果如何或者仲裁是否发生非中立的环境中,在发生争议时消费者都需赔偿商家律师费”,这类条款就可能因显失公平而不生效力。(64)Robert A. Hillman, “Online Boilerplate: Would Mandatory Website Disclosure of E-Standard Terms Backfire”, Michigan Law Review, Vol.104, 2006,p.853.
3.对平台格式条款打分评级
美国学者Florencia Marotta-Wurgler曾对十二个网站的软件终端用户协议(EULAs)的重点条款评分比较,从而对协议在整体上是偏向“买方”还是“卖方”及其偏向程度进行评价。其打分的内容包括协议同意(Acceptance of License)、协议范围(Scope of License)、能否转让(Transfer of License)、担保以及弃权(Warranties and Disclaimers of Warranties)、责任限制(Limitations on Liability)、售后服务(Maintenance and Support)以及纠纷解决(Conflict Resolution,如管辖和准据法)七项内容,其中每项内容中又提供了若干评分标准。最终总评分越低,就证明条款内容越偏向卖方。(65)Florencia Marotta-Wurgler,“Does Contract Disclosure Matter? February”, 2012,p.17.而判断条款是否偏向用户的标准,是将条款内容与相关的任意性规定(如UCC第2条)进行比较。(66)Ronald J. Mann, “Travis Siebeneicher, Just One Click: The Reality of Internetretail Contracting”, Columbia law Review,Vol.108,2008,p.995; Florencia Marotta-Wurgler,“Does Contract Disclosure Matter”? February, 2012,p.16. 贺栩栩:《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规范基础分析:一般条款与法定示例》,《法律方法》(第1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8页。将任意性规则作为格式条款效力的判断标准,是立法例中的通行做法。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07条第二款的,德国法院在对格式条款做内容审查时,首先采用的标准就是法律的任意性规范。《荷兰民法典》第6:237条b款、日本《消费者契约法》中关于“不当条款”的规定,都是要求格式条款同民法、商法或其他法律的任意性规定相比较,从而区分其中哪些条款限制了消费者权利或加重了消费者义务。Ben-Shahar 和Schneider也指出,平台应向消费者提供中介型的信息,如评价、排名、打分、标签以及评价等。(67)[美]欧姆瑞·本·沙哈尔、卡尔·E.施奈德著:《过犹不及——强制披露的失败》,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210页。笔者认为,这些评价措施和标准均可为我国网络市场监管机构借鉴。借助这种方式,对各个网站的格式条款进行客观打分和评价,从而向消费者传递出准确信号。
结 语
强制披露是格式条款规制的重要手段。由于电商平台格式条款的强制披露对促成实质合意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立法与司法不应简单地将践行披露行为等同于拟制合意。我国当前实施的强制披露制度并未使消费者的信息权得到实质改善。我们认为,需要对强制披露的运作方式及其实际功能进行重新评价,应谨记强制披露的制度初衷是为了改善消费者福利,强制披露目前的主要功能应体现为鼓励竞争和便于政府主管部门展开行政监管。为了促进市场竞争和改善消费者福利,应从改善披露方式、对格式条款的“黑名单”和“灰名单”进行立法规制以及市场监管机构应充分发挥其信息中介功能三个方面,对电商平台格式条款展开有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