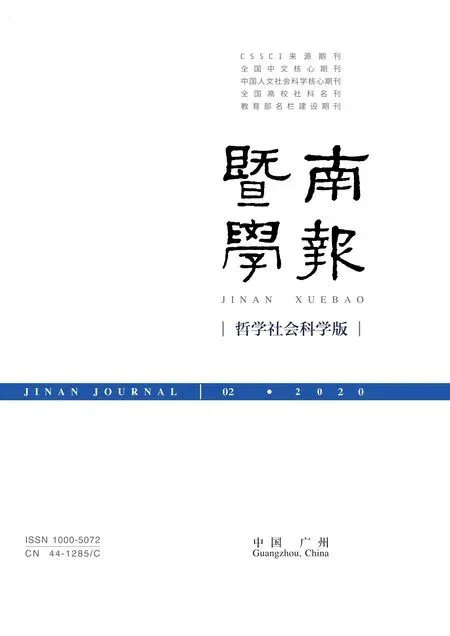虚构死亡:张翎近年来的叙事转向与文本策略
张 娟
加拿大华文作家张翎是近年来海外华文作家中表现出色、成绩亮眼的一位。近年来,其小说曾多次获得重要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七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学界对张翎小说的研究也逐渐繁荣。早期关注到张翎研究的,有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公仲、饶芃子、赵稀方、陈瑞琳等,从空间、历史、性别等角度对张翎的小说进行评价和推介。从2004年开始,随着张翎作品的增多,综合性研究开始出现,从跨文化书写、女性叙事、历史叙事、越界写作等多种角度把握张翎创作的特征。自2010年改编自小说《余震》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映后,张翎进一步获得了大众的关注,在创作上也上了一个新台阶。研究者更是从“交错美学”、“南方意象”、“河流意象”、叙事结构等角度对张翎的小说研究做出了新的拓展。
张翎的早期作品《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等注重描写游走在海内外的移民故事,到《金山》开始将这些移民故事放在移民史架构中,有了叙事转型的尝试。从《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开始,张翎的叙事风格进一步发生转变,不再仅仅关注讲什么样的故事,而是将如何把一个故事讲好作为文学转型的突破。在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中,张翎的死亡叙事逐渐增多,并且成为有效的叙事手段,使张翎近年来的小说呈现出全新的文学图景。《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中的向死而生,《流年物语》中的“物”的视角,《劳燕》的魂灵叙事,《死着》中的死者视角,《余震》《胭脂》中死亡的背景等等,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虚构死亡”的叙事方式。这种死亡叙事开启的并不是“死亡”,而是更为强烈的生存意志,无论在怎样的绝境下都坚韧不屈地活下去,成为张翎的小说中反复回旋的主旋律。这种“虚构死亡”的叙事构型超越了现实主义隐喻,深度关注死亡对人性的拷问,叙事方式的改变带来的是小说格局的廓大和深度的推进,形成了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重要收获。
一、灵魂·自杀·绝境:虚构死亡的不同方式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死”的注解是:“死,澌也,人所离也。”“澌”, 即“尽”,行至尽头,万物寂灭,就是死亡。张翎的小说中大量出现“死亡”意象和虚构死亡的不同方式,但是其用意并不是“万物寂灭”的死亡,而是试图把小说中的人物推向绝境,然后描写这些被逼到命运逼仄处的芸芸众生怎样经受命运的考验,再顽强地活下去。“虚构”死亡成为创设生命的“非常态”的手段,也成为小说的戏剧性和命运感的来源。在张翎的小说中,“虚构死亡”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死亡”为中心意象,形成一系列变体,例如灵魂话语、虚构生死之间的非常情境、把生命推向绝境等,通过灵魂、濒危、绝境、虚构生死之间的意识等不同形式的“死亡”,创造出全新的叙事空间。如《劳燕》就是典型的魂灵叙事,通过死去的亡魂的眼光叙述了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战火悲情,虚设的死亡视角使得整个故事回肠荡气又动人心魄;《死着》是以死亡为开端,将社会的矛盾积聚于一种特殊的死亡状态;《余震》《胭脂》《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则是描写了类似死亡的生命绝境,讲述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这些坚韧的生命如何绝地反击,重新站起来。
《劳燕》中作者虚构了一个灵魂的世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给灵魂下过定义:“灵魂是不可捉摸的虚幻的人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虚无得像蒸气、薄雾或阴影;它是那赋予个体以生气的生命和思想之源。”(1)[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小说一开始就是这一灵魂的自述:“你说以后我们三个人中不论谁先死,死后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里,到月湖等候其他两个人。聚齐了,我们再痛饮一回。”(2)张翎:《劳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活人是无法掌控自己的日子的,而死人则不然。灵魂不再受时间空间和突发事件的限制,灵魂的世界没有边界。千山万水十年百年的距离,对灵魂来说,都不过是一念之间。”(3)张翎:《劳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牧师比利是第一个到月湖践约的人,立下这个约定的三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日本战败,他乘坐“杰弗逊号”,踏上了回美国的路程。在上海等候船期时,因为给一个传教士的厨子动手术,比利被感染而死于败血症。死去之后的每年八月十五日,他都会按时来到月湖,静静地、耐心地等待其他两个人的来临。十七年后,刘兆虎到来,此时刘兆虎应该是三十八岁,而比利则是永恒的三十九岁。他们等待了五十二年后,才等到了美国教官伊恩,他活到九十四岁才死。“亡灵的世界颠覆了活人世界的规矩,在活人的世界里,我长你十九岁,而在亡灵的世界里,你仅仅比我小一岁。死亡拉近了我们的距离。”(4)张翎:《劳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死亡改变了活着的世界。作者不但虚构了死亡,而且对死后的世界进行了丰富的想象,确立了亡灵世界的规则。在张翎的创作世界里,不但人的亡魂世界可以虚构,狗的亡魂世界也可以虚构。《劳燕》就让幽灵和蜜莉两条狗在死去以后对话,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容量。
小说《死着》一开始就是以死亡开端,描写一个正在死去的魂灵的感受。“我不具体积,缺乏形状,所以,我也没有重量。我没有四肢,没有躯干,甚至也没有头颅,我却依旧能看,能听,能闻。”(5)张翎:《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6年版,第3页。“我漂浮在天花板上由两面墙夹筑而成的一个角落里,四下观看。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世界,所以每一样撞进我视野的东西,都让我产生婴孩第一次睁开眼睛猝然看见万物时的那种好奇和惊讶。”(6)张翎:《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6年版,第4页。死亡是至高无上的神,只有死亡可以洞悉一切秘密,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那段著名的独白,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想拿一把小刀了断自己的生命,却陷入了犹豫。张翎在谈到自己为何给《死着》如此命名时,说这个小说的英文名就是这个著名的莎士比亚独白“to be or not to be”,在中文里找不到恰当的翻译,她才选用了《死着》这一名字,而事实上,“着”这一在现代汉语里表示状态的持续的助词,正表现出一种身体在物理上已经死亡,依靠机器维持着医学上的生命的特殊生存状态。也正是这一非常态的境遇,才使得生的本相更加呈现得惊心动魄。
小说《余震》和《胭脂》开篇就是濒临死亡的绝境。《余震》是以自杀为开端。在多伦多圣麦克医院,小灯已经是第三次自杀呼救了。对于小灯来说,一方面是人生的绝望,“自杀昭示了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悲凉意味。当生命的内驱力变成死亡的内驱力之时,死亡便不复是种暧黯不明的生存背景,而直接转化为生存的前景”,(7)陆扬:《死亡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加缪有一句名言“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8)[法]加缪:《西绪福斯神话》,《加缪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24页。,但是小灯一方面屡次寻死,另一方面每次都自己呼救,她生的意志是如此强烈,以致每次都能将自己从绝望之境拉回。《胭脂》的开篇也是绝望之地,贫寒的画家黄仁宽已经病重躺在床上很久了,甚至他已经无力控制自己的身体,“我觉得我的背我的腰我的臀已经在床铺上生出了根须,正如当年的阿娘”(9)张翎:《胭脂》,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他没有了爹娘,地契被改名,房产被霸占,他成为了一个生病无人照看的画家。但是他的绝境被富家女胭脂拯救,绝境成为故事的起点。之后在胭脂的人生中也面临一次次绝望,但她和她的后代们一直柔韧地活着,从来没有丧失生命的信心。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则是以绝境的倾诉为中心。在一次旅游中袁导讲解历史中的茜茜公主,裴多菲、布拉格的生命绝境,现实中的沁园、袁导、红衫女子、徐老师等则分别讲述了自己最黑暗的夜晚,其实也是在讲述每个备受摧残的个体如何向死而生。匈牙利布达佩斯最黑暗的夜晚在1956年11月3日,和苏军的撤军谈判正在进行,但那一夜,苏军的坦克从四面八方开进了布达佩斯,对于匈牙利总理纳吉来说,这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永远没有能够走向白天,两年后他被送上了绞刑架。茜茜公主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发生在1890年,那一年奥地利的头号敌人、茜茜公主的精神伴侣安德拉希伯爵去世,茜茜公主一夜无眠,第二天变成了一位满头白发、一脸皱褶的老妇人。袁导最黑暗的夜晚是离婚的那一夜的巴黎。他本来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最年轻的博导,为了妻子来到法国,并放弃自己的专业成为一名导游,当生活正在走向正轨时,发现妻子出轨,他们以离婚告终。红衫女子最黑暗的夜晚就在她四十五岁生日的当天。她从小供养自己的丈夫,直到他发达并且有了小三,她被丈夫抛弃。徐老师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是她在荒林里挖出丈夫腐烂的头颅,抱着他的头颅过了一夜。五十年前她和自己的爱人从苏联留学回来,在运动中,因为她恍惚中签字的一张纸,爱人被判刑,送到青海的一处劳改农场服刑,三年后,她才知道丈夫已死于肝硬化,被埋在一处荒林。作家沁园最黑暗的夜晚则是在写作崭露头角时被流言所伤。但每个人都没有放弃生的希望,而是在黑暗中挣扎着相互取暖,走向各自的新生。这种最深的黑暗也正如鲁迅所说:“在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在无所希望中得救。”(10)鲁迅:《墓碣文》,《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死亡是一种人类生存的绝境,死亡叙事探讨的其实是生命的限度与反抗。“艺术的起源不仅联结着一个阳光普照的白天,而且深深扎根于无边无际的黑夜——死亡”,(11)殷国明:《艺术家与死》,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西方一直有死亡叙事的传统,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阿尔博姆的《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都是从亡灵的视角切入,近年来余华的《第七天》、艾伟的《南方》,陈应松的《还魂记》,孙蕙芬的《后上塘书》也都是采用了虚构死亡的魂灵叙事,“虚构死亡”指向的其实是对生命的现实关怀,也开启了一个更为全能的叙事视角,借用陌生化的艺术视角呈现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企及的人性的哲学内核。
二、视角·物语·代际:“虚构死亡” 的叙事策略
张翎的“虚构死亡”的另一个重要关键词是“虚构”。从《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开始,张翎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叙事自觉时期。之前张翎的写作基本还是在现实主义层面,关注的是故事本身,而在《流年物语》之后,她更关注故事应该怎么讲。她近年来最突出的改变是实现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换,通过虚构死亡的叙事策略,对灵魂视角、人称转换、线索串联等不同叙事方式灵活使用,形成了故事的形式感、陌生感和间离感。张翎自如地采用不同叙事策略的转换,将故事打碎再重建,打破了读者惯性的阅读视野,通过故事讲述方式的调整,体现出别有意味的故事内核。
首先,张翎通过娴熟多变的叙事视角的转换,打乱线性的故事时间,调控故事节奏。在她的小说里,亡灵可以说话,动物可以观察,生活里的任何物体都可以开口,他们从不同角度讲述故事的不同侧面,展开了一个丰富的叙事图景。如在《死着》中,一开始是魂灵的视角,用第一人称的角度,描写“我”飘浮在空中观察着病房和自己。当他的视线来到医生和小护士身上时,叙述转为第二人称,“我”变成了“你”。接下来,小说进入倒叙,转为第三人称茶妹的视角,回溯了整个车祸和死亡事件的起因。《胭脂》的开篇则是画家黄仁宽的自述,他是个穷苦的画家,父母双亡,家产被亲戚霸占,他病重濒危,甚至连医院的嬷嬷已经给他唱过《黑暗加深》这一给临终者的安魂曲。此时他遇到了胭脂。接下来,转为胭脂的自述,那时的胭脂是师范学校音乐系的学生,正值战乱,她的父亲在英国人的银行里做襄理,忙着给她介绍男朋友,希望通过婚姻把她带离战乱之地,给女儿安排一个理想之路。结果这一天胭脂走错了路,她遇到了濒临死亡的黄仁宽,最终成为了他的女人。然后黄仁宽和胭脂的叙事视角不断转换。到了中篇“女孩和外婆的故事”中,成为了第三人称叙事。作者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描写外婆带着扣扣不断搬家,从谢池巷搬到百里坊,又从百里坊搬到桥儿头,为什么要这样频繁地搬家,作者没有讲。但后文我们从外婆第一人称的角度了解到频繁搬家是为了掩饰扣扣出生的秘密。通过第三人称的视角,作者写到外婆并不是她的亲外婆,而她是在一棵树下被捡到的。接下来作者又用第一人称的叙事,用外婆之口徐徐解谜。原来外婆就是第一个故事里的胭脂,她和黄仁宽的好日子也不过四五年,后来黄仁宽离开上海去了台湾,答应下一班船来接她和女儿,结果这一班船却永远搁浅。她的女儿抗抗重蹈覆辙,爱上了有妇之夫的老师,死于难产。她抚养外孙女扣扣长大。回到现实后,故事又收归第三人称叙事,扣扣因受过惊吓而再也不能长大,直至心结解开。在这一部分,现实故事是用第三人称叙事完成,回忆历史则是用第一人称。下篇“土豪和神推的故事”中,出现了土豪和神推两个新的人物,故事的发生地也转移到了巴黎,作者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对两个人的身份分别进行了介绍,随后又分别让两个人从自己的立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推进故事。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松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让故事从死到生,又由生到死,呈现出复杂的人生况味。
作者不但善于利用“人”的视角转变,还善于利用“物”来开口说话。巴赫金在研究戏仿体的叙事文学时提出了“异常叙述”的概念,认为通过骗子、傻瓜和小丑,更能看清事物的反面和虚伪。《流年物语》从物的视角写人的生活,河流、瓶子、手表、钱包、麻雀、老鼠、苍鹰、铅笔盒等物象都可以开口说话。通过第三人称的物的视角,作者以南方小城为中心,辐射到巴黎、长岛、上海,描写了两个家族三代小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故事。《劳燕》中借助“狗”的视角,让幽灵和蜜莉从自己的眼睛里看到了伊恩和前女友的分手,也看到了伊恩对温德的喜欢,后来温德成为了蜜莉的新主人,看到了温德和伊恩正在悄悄萌发的爱情,丰富了叙事的多面性。张翎还常常在限制叙事中穿插着上帝视角。《胭脂》一书中胭脂刚遇到濒危的黄仁宽时,一开始是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但是在整个故事还没有展开时,作者就插入了一句上帝视角的非限制表达:“可是最终我哪儿也没去。我走了一条让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瞠目结舌的路:我成了一个籍籍无名的穷画家的女人。”这句话更像是作者的声音,在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给出了宿命的结局,形成了一种叙事者、故事人物、作者之间多重叙述的套层结构,构成了多元的复调叙事效果。
其次,打乱了叙事视角和叙事顺序之后,如何让故事讲述更为顺畅,这其实在叙事结构上给作者提出了新的考验。叙事结构也就是叙事作品的文本结构,张翎在她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通过对不同叙事元素的组合,借助不同类型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手段,形成小说的表层结构。同时在故事线索的展开与收束中也体现出了极强的掌控能力。
张翎善于将原有的故事碎片化,将叙事事件、叙事者打乱顺序,然后再通过一个叙事线索将千头万绪的故事收束起来。《劳燕》小说的叙述是从传教士比利开始的。小说一开始就是比利的死,比利死后成为漂泊在中美两块大陆之间的幽魂,每年八月十五日,都来到月湖,等待另外两个人成为灵魂前来会面。张翎从三个人的死和魂灵的会面写起,三个男人都出场后,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女子阿燕才如同风中的传说一样,渐渐显形。在伊恩的故事里,她是温德,在刘兆虎的故事里,她是阿燕,在牧师比利的故事里,她是斯塔拉。小说的一开始,是三个男人从各自的角度分别的叙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与阿燕相遇,产生纠葛和感情。直到战争结束,三个男人的线索汇聚一处,像是抛出去的抛物线,终于有一天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收拢。在比利的叙述中,他在战争结束后,要回美国筹款,在四十一步村建立一座教堂、一间诊所、一个家——一个属于他和斯塔拉的家。他明白伊恩和斯塔拉的感情,但是他相信能够稳稳接住斯塔拉的只有他自己。此时,刘兆虎和伊恩也分别表明了自己的心事,刘兆虎想接阿燕回村,和她结婚。伊恩想到战区事务办公室申请结婚,带她去美国。而下一次叙事线索收归一处,是在阿燕辞世的时候,比利、刘兆虎、伊恩,三个鬼魂赶了三百里路来到一家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阿燕,阿燕得了中风,“中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一种毁坏了原有的感觉系统,打通了阴阳两界的阻隔的奇异病变”(12)张翎:《劳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4页。。阿燕感受到了三个魂灵的到来,她的眼神猝然一变,故事戛然而止。故事由魂灵始,到魂灵终,虚实相生,回肠荡气。
张翎的死亡叙事中还常有一个“三代”的代际构型,在一代代的死与生之间,形成历史的轮回感和人生的宿命感。由于代际的延续,上一代的死亡成为了下一代生的开始,也是下一代生的宿命。《流年物语》描写20世纪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流年中,两个家族三代女人与命运的抗争。《阵痛》则以女人的生育为线索,描写一个家族三代女性因生育而带来的痛苦。第一代女人是吟春,他被日本鬼子强暴,但孩子生出来后,发现是大先生的骨肉,她喜出望外,但是回到家中,却发现婆婆和大先生已经故去,孩子生来就没有了爹。第二代女人是吟春的女儿小桃,“桃”谐音“逃”,她想逃离一切厄运,可是小桃的爱人——一个年轻英俊的越南留学生希望回国效力,与小桃的恋情无疾而终,小桃未婚产子,在几乎毁灭的关口上,小桃嫁给了一直关心自己的学院老师宋书记。第三代女人是宋武生,她来到了美国,但是由于外婆、母亲的惨痛经历,她不愿意生育,当她发现自己怀上了杜克的孩子时,杜克又死于911美国世贸大厦的坍塌。“三”既是历史长河中的三个世代,又是空间流转中的不同背景,通过三代故事的轮回和流转,表达出了生死在历史长河中相似的内核。张翎的新作《胭脂》同样是三代女人互为关联的故事,故事在“三代”构型之外,还插入了胭脂、画等意象作为线索,它们作为代代走向死亡的人生中不变的“物”,使得故事的结构和线索更为复杂,藕断丝连,绵长动人。作者的叙事策略也是一个顺藤摸瓜的线索,看似细若游丝,却最终一一落回实处,带给读者回肠荡气的阅读快感。
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认为,叙事文是由外显结构和内隐结构组成的,叙述的表层结构就是小说家呈现出来的外在叙述结构,而内因则是故事的深层结构,这是产生于文本之前的。张翎近年来的虚构死亡的写作就是打破故事深层的逻辑结构,通过叙事主体、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的多样性的探索,形成独特的叙述形态。从“故事”向“话语”的迈进中,张翎通过多重的叙事话语,利用“虚构死亡”的话语构型,建构起了日渐成熟的文本叙述体系。
三、从形式到哲学:“虚构死亡”的意义
从近年来张翎“虚构死亡”这种叙事上的新变,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创作技法上的转型和努力。这种叙事视角的转型在张翎个人写作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同时也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谱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张翎从《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开始,已经从关注现实的经验写作逐步转换为更注重技巧和讲述方式的写作,向成熟的写作者又迈进了一步。张翎对小说形式精益求精的追求,带来的是哲理思考的深入,使其小说呈现出超越现实人生、直指人性的大格局。张翎的死亡叙事和近年来海外华文作家的叙事转向合流,对于提高海外华文写作的质量、推进海外华文写作的叙事技巧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
著名学者杨义认为,“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把叙事角度看作是 “成功的视角革新,可能引起叙事文体的革新”(13)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95页。。张翎近年来写作上的巨大突破正是由于她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更加灵活的观察视角,而文体意识的增强,也是她的小说近年来颇受关注,并获大奖的原因之一。(14)2017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2017年7月人民文学社出版社出版的张翎的《劳燕》入选长篇小说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利民对获奖作家及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承接现实关怀的同时,作家们也普遍拓展了思想的视界和景深,力图在更为广阔和深邃的审美空间,来理解和把握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包括在今年集中涌现的一批战争题材的小说中,也显示出多元化的人性视野、 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的交织互补。与思想能力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相伴随的,是作家们的文体创造意识的增强。”在笔者对张翎进行采访的时候,她谈到了近几年在作品中大量采用了死亡叙事的内在心理动机:“我始终不认为我真正在写死亡,哪怕《死着》与死亡是最接近的,事实上我在写人,死亡只是一个工具。在我的小说中,死更是一种绝境的象征,而不是我真正在写死亡这件事情,《劳燕》里也没有真正写死亡。亡灵叙事是一种叙事的手段,引入新的角度,然后层层剥开,把每个人的秘密更好地暴露出来。其实也不算秘密,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侧面,每一个侧面都是真实的,只有鬼魂能看到各个侧面,把人整合起来。但是我特别爱描写绝境,这确实是真的。绝境当然与死亡有一定联系,我认为,人要被逼到那样的地步,才能够爆发出来一种东西,让自己吃惊,让周围的人吃惊。如果没有战争,阿燕一辈子都是可以预见到的生活。我们出于怜悯之心,不希望阿燕经历战争,但是她既然经历了,后来她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这些剧变,如果不是经过接近死亡的绝境,我认为是不可能爆发出来的。阿燕被逼得这样紧,她碎了,碎了之后就爆裂出另外的东西,我实际是对这个过程感兴趣。”所以,张翎感兴趣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面临绝境不同的人怎样重新站立起来。从《余震》到《金山》,从《阵痛》到《劳燕》都在探讨人类被灾难逼到墙角时呈现出的某些特殊状态。灾难、战争、厄运这些接近死亡的非常态人生境遇只是小说的起点,张翎着力描写的并不是各种灾难,而是面对这些灾难时貌似弱小的人类,这些不同的个体如何生活下去。张翎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她早年在复旦大学外语系学习,后来出国留学,在北美做过17年听力康复师。她经历了乱世,看遍了世情,她在工作中接触过来自“一战”、“二战”、“韩战”、“越战”、阿富汗战场以及后来中东战争的诸多老兵。现实生活的光怪陆离、人性的深刻复杂、绝境中的挣扎,凡此种种,都成为她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但是如何把这种复杂的感受更好地表达出来,成为张翎孜孜不倦的追求。在对张翎的访谈中,她提到了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君特·格拉斯、库切等人的阅读,这些作家们在叙事方式上的多元和创新令她心存景仰,也让她找到了打开自己的经验宝库的钥匙,通过灵活多变的叙事结构,张翎逐渐呈现出更大的格局,不再仅仅局限于故事本身,而是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结构的调整,在自己的小说中容纳更为深广的社会和人性内涵。
在文学史谱系中,张翎的“虚构死亡”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特别是对于近年来的海外华文文学,她在叙事上的创新和突破引人关注。“文学中的‘虚构死亡’,主要有两种意味,一是借死亡鬼魅世界,曲折讽喻现实,二是借由死亡探讨生命哲学,向死而生。梳理‘虚构死亡’的文学谱系,可为探讨我们的写作在这个谱系中处于怎样的逻辑链条提供依据”(15)张娟:《死亡如何虚构——从鲁迅〈死后〉与余华〈第七天〉的比较研究谈起》,《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8期。。中国的死亡叙事源远流长,虚构死亡的写法在魏晋的志怪小说、唐朝韦瓘的《周秦行纪》、北宋秦醇的《温泉记》、南宋无名氏的《摭青杂说·阴兵》、元朝的《录鬼薄》等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手法也得到当代作家的青睐。方方的《风景》、阎连科的《丁庄梦》、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第七天》等都有虚构死亡的巧思运用。在中国的“虚构死亡”谱系中,大部分都延续了批判现实的讽喻精神,都是将死亡世界放置在一个镜像的现实世界,形成叙述的“他者”。在西方文学中,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阿尔博姆《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则把虚构死亡作为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路径。海外华文文学中,虽然近年来有严歌苓的多种向度的叙事探索,陈河的《甲骨时光》这样的虚构佳作,但总体上还是以经验主义的现实主义写作为主,张翎的“虚构死亡”一方面具有现实的讽喻意义,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叙事转变实现对于死亡的哲学探讨,她的“虚构死亡”在中西死亡叙事谱系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张翎作为一位移民作家,她的“虚构死亡”不仅具有现实讽喻倾向,同时也具有很浓厚的哲学特征和人性探究意味。在中西哲学领域,一直有思考死亡的传统, “不管怎么讲,死亡总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人,并勾连着存在论的所有问题”。但每个活着的人都无法亲历死亡,所以死亡往往是一种想象,而这种想象是指向“生”的,活着的人试图通过虚构的死亡向死而生。从屈原的《天问》到鲁迅的《野草》,从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到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再到伽达默尔的死亡哲学,都在探讨如何在活着的时候领会死亡,从而更加无所畏惧地活下去,“人一旦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暗淡处境,正可以通过同既定命运的不屈抗争,在他生命的重点,因而也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间,显示出人的尊严和自由精神来”(16)陆扬:《死亡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张翎的死亡哲学则是来自于自身生命体验与现实的碰撞。张翎在2018年出版了“生命力”三部曲,包括《余震》《死着》《胭脂》三部小说集。在分享会上她说:“如何把三个故事联系起来呢?就是‘生命力’,有一类女性是在任何大灾大难到来的时候都会挺过去,女人是以柔软的姿势存活的,我是在赞美这样的一种生命力。勇敢也可以是卑贱地活下去。阅历使我对人生有更深的理解,可以宽泛而柔软地活下去。”(17)张翎:《总有一种力量像野草生长》,温州大学第二届文学周开幕式张翎新著《生命力三部曲》的创作分享会上的发言。“此在领会了这一点,就不至于怯懦地逃避死亡,而会在它一路奔向这一终点的过程中,无牵无挂地展开它的全部潜能,即人丰富而自由的本质力量,这就成为光辉灿烂的美的形式。”(18)陆扬:《死亡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张翎的虚构死亡的小说展现的正是这种生的灿烂意志。由于死亡是人存在的规定性,死亡具有不可经验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我们必须对有限的人生进行推入绝境的深度洞悉。张翎的小说中对死亡的思考有不同的层次,面对生命的艰难与黑暗,她会感叹“生不如死”,也会反思战争的残酷,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对死亡世界的虚拟最终穿越绝望,走向了积极的“向死而生”。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这句富有存在主义意味的表达大概就是对张翎“虚构死亡”的叙事方式最好的解释。叙事的突破产生了思维的重组,不同视角的俯瞰、透视、扫描、穿越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也使得作者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有了更深的洞悉,从而具有了超越现实主义走向哲学体悟的可能性。
近年来,海外华文写作群体开始超越最初的经验写作,致力于叙事探索,体现了从写作的客体视角向本体意识的转变。如严歌苓的散点叙事,陈河的迷宫结构等,都使得海外华文写作逐渐向艺术本体推进,其中张翎一系列小说的“虚构死亡”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学现象,这种叙事构型值得关注。 “死亡”以一种非常态的情境带来了叙事的自由,同时,张翎也通过自己的系列“死亡叙事”传达了不同种族共有的强烈的生存意志,灾难面前个体的差异性。基于广阔的中西文化视野,她对死亡的探讨将人性探索和哲理思考推向了更深处,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在艺术本体和思想深度的推进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