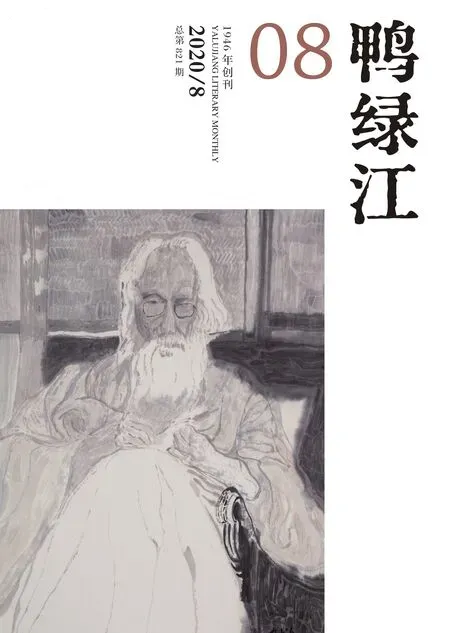满堂光辉(短篇小说)
浩 然
赵洪大伯有十几年没喝酒了,自从生产大跃进起,他破例地喝了三次。今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又打了一瓶子老白干,还让家人每人喝一盅。酒盅挨个轮,儿子、媳妇、女儿一个个领了盅,最后轮到他的老伴洪大娘,可就停住了。
这老婆子,手把着酒盅,两只眼珠子不动地盯着老头子的脸。心里暗想:看这老东西那满脸高兴劲儿,准是社里又出了喜事儿。不然,他不会喝酒,也不会这么高兴。这老两口子和气一辈子了。尤其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娶了儿媳妇,彼此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严肃和尊重。从来不当着晚辈人顶嘴、开玩笑,或说一些不当说的话。因为他们影响,慢慢的成了这一家人朴素的习惯。
赵大娘见老头子一个劲催她快喝,赶忙端起酒盅倒在嘴里,辣的她直掉泪。幸亏儿媳妇夹一筷的菜放在她的碗里,她吃了一口压压,辣劲才过去。
三盅水酒下肚,赵洪大伯那满布皱纹和灰白胡子的脸,变成红灯笼。停了停,他开口说:“大家都快些吃饭,吃完了趁人齐开个家庭会。”
蹲在炕沿上,吃饭象打冲锋的儿子春先,忍不住地说:“爸爸,我建议一边吃一边开。我们炼铁厂今晚上还要出铁哩!”
跨在炕边上的媳妇秋云附合著说:“我同意春先的意见。我还要到乡里监工做水车哪!”
挨着妈妈坐着的女儿小丽,也尖着嗓子说:“就是一边吃一边开,也得简单点儿,我们红专大学再有七天就正式开学了,今天夜里我们还要突击修补教室。”全家五口人,三个人主张一边吃一边开,一向不习惯吃饭讲话的赵洪大伯,也只得说:“好,少数服从多数,咱们就开吧。”
赵大娘本来也有意见要发表,赵洪大伯却没有注意到,就宣布决议了。这使洪大娘心里很不高兴。家庭会我也是个成员哪,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咳,这老东西,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有我好象没我一样,这叫什么民主?不过,她跟往常一样,心里不痛快,也没吭声,把头一低,光顾吃饭。
赵洪大伯说:“今天有件大喜事,先朝大家汇报汇报。”说到这儿,他故意把话收住,眯缝起眼睛,把屋子里的每一个人看一遍,象是观察大家的反映。果然,一家人都停住了手里的筷子,就连赵大娘添在嘴里的饭也不愿得咽,就盯着碗边听他往下讲。他这才接着说:“前几天我出的那张大字报,总社批下来了。立刻拨出三百个棒劳动力到老河湾改造那片沙荒。联合大队指挥部还让我当参谋。你们不要把那片沙荒看简单,那是两千亩上好的黄土地呀!几十年来,我总也不敢去看它一眼,一见它我的心里就象刀子剜的一样疼呵!只有今天咱们公社才有力量让它重见天日!”
赵大娘听罢,不由得乐开了。她猜的不错。难怪老头子高兴,这么大的喜事怎么不高兴呵!这片沙荒的来历,她跟老头子一样的清楚。还是一百年以前,一伙子从青甸洼逃荒过来的难民,在盘山下、舟河边的荒地上安居下来。男的女的,啃草根、吃河水,拼死拼活地开垦,把一片荒地变成了良田。第二年刚要收割,蓟县城里的王家地主派来了一队人马,围着田边跑三圈,插上木牌子,硬说地皮也姓王。王家财大气粗,哥几个都在外边做官,谁取惹他?从此,这群灾民成了王家的佃户。到了赵大娘嫁给赵家(四十年前)佃户们已经把这两千亩土地培植成花园一般。他们的日子却一年比一年苦。那一年庄稼丰收,地主起了坏心,硬说佃户对他不忠诚,把男男女女都赶到堤上替他防风,他亲自带领长工来收割打场。这一下,穷人们再也没有活路了。在一个急风暴雨的夜间,一群小伙子(里边就有赵洪天伯)悄悄地扒开河坝,洪水一下子涌出来,把所有的庄稼一口吞光。以后口子堵上了,那片上好的土地满淤上二、三尺厚的马眼沙。穷人们携老带幼到四周的村子里,这片地方成了荒凉之处,渐渐的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伤心事。今年春天以来,生产大跃进,人人解放思想、力争上游,赵大伯亲眼看见人民力量搬山山能动,掏海海能干,他一下子就想起埋在这片地下的宝贝。为这个事想了好几天,又怕没把握,劳力伤财,就扛着铣,带着干粮,亲自跑到十五里外的沙荒上,挖了一天一夜,沙石果然可以搬走。回来,他让儿子帮忙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鸣放园地。现在,他的提议被批准了,他怎能不喝酒祝贺呢?
这样一来,赵大娘把刚才对老头子的不满,早忘了一于二净。见老头子光顾说话,碗里的饭都凉了,赶忙倒在自己碗里,替他另盛一碗热饭。
小丽这姑娘虽然十七、八岁了,在爹妈面前总好耍孩子气。这时她在一边笑着说:“嫂子,你们看看,我这碗里的饭也凉了,可就没有人管!妈妈光是疼爸爸。”
赵大娘瞪女儿一眼说:“死丫头,什么话都说!你妈妈心眼公道,谁有功劳疼谁。你知道人家这个功劳多大呀!沙子底下那地,你没见过哪,嘿,苏子面一样细,金子一样黄。搬出来,种上庄稼,一亩地打一百斤,就是好几十万斤,咱们就可发了大财啦!”
家庭会就在这样欢乐的气氛里进行的。家里的日常杂事一项一项讨论了,添置过冬棉衣和加入食堂的事情也决定了。大家先后放下饭碗,会议也宣告结束。等洪大娘在后院喂饱猪回来,屋子里不见一个人影儿了。她坐在炕沿上,心里总象有点事儿放不下,翻翻这儿,弄弄那儿,又没什么可做的。她点上油灯,灯光照着那只玻璃酒瓶子。酒瓶子是绿色的,红纸标千写白字。看着空酒瓶子,她的心里荡起一连串关于喝酒的事情。
头一大喝酒,正是春耕时节,老头子披着满身灰土,手里提着那个酒瓶子,大步地跨进院子,活象个小孩子似的对她说:“春先娘,嘿,我给你贺喜了!咱们春先到蓟县城里取经回来,炼出第一炉铁成功了。人家当了工程师,今天一夜就要修起二十五个土高炉。咱们这个穷山村也能炼铁,你说喜不喜?”社里正忙着抗旱播种的吋候,老头子又从外边提来一瓶子酒。一进门就大声喊:“难怪人家是社主任的闺女,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洪大娘停住手里的活计,笑裂着嘴唇问:“你这没头没脑的话,说的是谁呀?”老头子说:“还有谁,秋云呗!你不见她这几日忙的都不愿回家吃饭吗?人家跟着几位木匠,三天三夜发明一架脚踏水车。嘿!一架顶四架,比好几匹棒牲口拉的都快。这回呀,按期完成抗旱播种任务是没间题了!”第三次就是前几天,老头子提着酒瓶子进门,赵大娘就迎上去问:“又出了什么喜事呀?”老头子说:“你猜一猜吧。”赵大娘说:“天哪,社里的喜事一个跟着一个来,你可让我怎么猜的着呀!”老头子说:“告诉你吧,咱们家那个中学生小丽,在社里扫盲有功,明天就到县里开积极分子会。社主任说,要保送她上农业红专大学,咱们这个柴门草舍也有大学生了!”今天喝酒是第四次,第四次酒是为老头子自己喝的,老头子也是对社有功的人了……
赵大娘正盯着酒瓶子想心思,忽然看见老头子气喘吁吁地跑进屋里来。
“快我收拾一下东西吧,衣服、被子,多拿几双跟脚的鞋子。”
“干吗这么慌呵?”
“改造沙荒的事儿,给县里知道了,县委、县长都叫好。社主任刚才指示,要立即突击,争取今年全部种上秋麦。我们马上就出发。”
洪大娘再不顾多问,手忙脚乱地翻开柜子,这个那个摆一炕,最后扯出一件大皮袄,递给了老头子,嘱咐说:“一天比着一天冷啦,野地里住宿,不穿暖和不行。”
“一干活就不冷啦。”
“你那大年纪,还能做什么重活计。不是说让你去当参谋吗?”
赵洪大伯看老伴这份热情,心里早就领受了。最后还是把皮袄打在铺盖里。
不一会儿,街上响起集合的哨子。一个小伙子楞冲冲地跑进来,对赵洪大伯行了个军礼:“报告参谋长同志,战斗团的人马集合齐了。”
赵大娘咧嘴笑了。赵洪大伯跟着小伙子往外走,又转过头来嘱咐赵大娘说:“我们都不在家了,过几天又成立了食堂,家里没有多少事情了。你在社里多揽点工作,咱们全家都得跃进呀!”赵大娘低着头,一声没吭。
老头子走了;儿子住在炼鉄厂;儿媳妇在乡里监造水车每天不一定回来;小丽那个猴丫头,那天也得半夜回窝;家里只剩下赵大娘孤单单一个人。坐了会儿,觉得没意思,索性躺下睡了。翻来复去又睡不熟。往常,虽说儿女们也是这样没白天没黑夜的在外边忙,家里可有老头子给她做伴。年轻人嘛,赶上好时候,应当显显本领;人老了,不中用了,还有什么出息,所以她从来没有感到什么不安。常言说,没有高山不显平地,老头子这一跃进,可就比出自已的干劲实在不足。刚才开家庭会老头子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临走又留下那么几句带刺儿的话,都使赵大娘不痛快。哼,你光是提一个建议,可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小瞧人,你能跃进,我就不能跃进?
第二天起早,赵大娘找到队长,要求增加她的工作。队长说:“赵洪大伯临走也关照过我。我想您年纪大了……”
赵大娘打断队长的话说:“我比你大伯还年轻五岁哩,我什么也能干。”
队长说:“有两件工作都缺人。第一件是到养猪场喂猪,第二件是托儿所看孩子。您就挑一件做吧。
赵大娘速忙说;“不不,我服从队长分配。挑肥拣瘦那还叫什么社员哪!”
最后,队长把赵大娘派到托儿所里。
赵大娘家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槐树上拴着个大喇叭。赵大娘每天下晚班回来,就坐在树下边听社里的新闻广播。赵洪大伯走后第二天,广播说:“沙荒野战团,开始向沙荒进攻,一天使十亩黄土地在沙石底下解放出来……”第三天又广播说:“全体指战员发出冲天的干劲,昨晚一夜奋战,完成十七亩……”到第八天晚上,效率提高到五十亩,社员们都高兴的不得了。这一天,赵大娘搬来凳子,刚刚坐下,就见队长满街找人开会。她赶忙把凳子放回家,正要去会场,忽见小丽从老远跑来,朝她喊着:“妈妈,快到队里去,有电话找你。”
“什么,什么,电话找我?”
“您还不知道哪?咱们队部跟沙荒战斗指挥部接上线了。”
赵大娘踉踉跄跄地跑到队部。屋里没有人,只见电话简放在桌子上。自从社里安了电话网之后,她不只一次看见别人热热闹闹地讲话,她却从来有摸过。这时,她也学着队长的样子,两手颤抖抖地拿起电话筒,轻轻地放在耳朵上,摆弄过来,摆弄过去,总也听不到声音。她当是女儿捉弄她,生气地嘟囔着:“死丫头,那里有电话?”突然,从听筒里传出沙沙的声管:“你是谁呀?”天哪,这不是春先他爸爸的声音吗?她满屋地搜寻着,不见人,更使劲抓着听那筒,唯恐说话的人跑了似的:“我,我,是你吗?你在那儿呀?”听简里又传来赵洪大伯的沙嗓音:“我跟跟你说一件重要事儿。听的清吗?喔,是这样,我们这里已翻出三百亩地啦,那地真好哇!我们保证种下麦子前全部翻完,今年都种丰产小麦,一亩地包它五百斤!眼下出了个大问题,就是缺肥料。社里的肥料都是按着原有土地积的,新翻的地不在圈里。说话就要种麦子,肥料还没有影子,你说急不急?赵大娘连忙回答:“急呀,急呀!”“这问题立刻就得解决,你可要起个带头呵!咱们家不是有三个炕吗,我看可以拆了当肥料,还有锅台……”“好好,这事儿不用你操心了,我一定能办到……”“好,我等着你了们的喜信了。我们立刻又要夜战,有工夫再讲吧。”“行呵,行呵。你们那边冷不冷?我给你捎去的烟叶把好不好?呵?”赵大娘反复地、大声地问了几遍,又把话筒连着摇几摇,再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最后,她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走出院子。
社员大会就是动员积肥。开完会,夜很深了。小丽姑娘在外边奔忙了一天,这时又累又困,躺炕上象一滩泥两只眼皮用手掰都掰不开。赵大娘没有立刻躺上,她在凳子上坐了会儿,推女儿一把说:“小丽,你说,眼下就要开犁种麦子了,最迟过一个月也就不能种了。一个月,这一万车粪积的够吗?”
小丽忽忽悠悠地回答说:“队长不是说了,昨天大突击,三清底吗?”
赵大娘说:“傻孩子,猪圈、茅房、牲口棚,春来都清了一回底,再清一回也没有多少油水了,就算硬着脖子把它挖出来,土里边能有大劲?”
屋里静静的,只有小油灯不时地爆跳一下。小丽的困倦跑的没影儿了,焦意地、瞪着两只大眼珠子盯着妈妈,妈妈也盯着她。
赵大娘想起老头子在电话里说的话,忽然记起来,去年赵洪大伯曾经跟着几个社员搞过一回高温积肥。她找老头子吃饭常去,只恨自己当时没有留心。她回身从柜子里取出一叠子书,对女儿说:“小丽,你给找一找,那本是高温积肥的书呀?我见你爸爸一边装肥窑一边翻它看。”
小丽坐起来,从当中翻出一本说:“这本就是,我们在技术推广站也学习过。这办法好是好。就是把柴草里掺上人粪尿和石灰,一发酵就沤成肥——发酵就是发霉。眼下天气冷了,一窑要两个月才能沤成,那里赶的上?”
赵大娘听了女儿这般讲解,忽然说:“这回我明白了,高温积肥就是石灰跟人尿的热劲儿把柴草搞霉,对吗?喔,我想起来了,要是把窑装好,把窑底下掏个灶,给它加把火,不就发热发霉的快了吗?”
没等赵大娘讲完,小丽就拍着手掌,尖声叫嚷起来:“天神,天神!这个办法准行!一窑出二十车粪,搞上五百窑,那可老鼻子了!”她说着,就要穿鞋下炕。
赵大娘一把拉住女儿的胳膊问;“你这么急急毛毛地干什么去呀?”
“干部会还没散,我去献计,任务算是完成了。”
“你这孩子,办事情总是这么不稳当。”赵大娘把女儿按在炕上说:“大伙儿正在一股劲地找肥源,你冒冒失失地端出这个没准儿的办法,大伙一靠这个,就松了搞别的劲头。倘若这办法不行,人家说咱们娘俩说大话是小事,影响工作是大事。”
小丽点点头,笑着问:“您说怎么办好?”
赵大娘说:“跟你爸爸那样,先搞个试验,有八分成功了,再说出去推广,好不好?”
说干就干没二话,小丽下了炕,拉着赵大娘就往后院走。
晚秋的深夜,月色蒙胧,凉风嗖嗖地削脸。赵大娘领着小丽按照赵大伯搞高温积肥窑那样挖法。娘俩替换着挖哇刨哇的,整整干了一宿。天没亮之前,赵大娘悄悄地从饲养场的草棚里,搬来一把铡刀。回来,妈妈入草,女儿按刀,转眼就把一垛玉米稭铡碎了。沤肥窖装好了,家里有现成的石灰和人粪,拌在柴草里边。蓬上盖好,赵大娘抱着一抱干柴禾走起下地下道。她屏住呼吸,用足力气,擦一根火柴,把柴草燃着,又往洞里一塞,柴草忽的一下子着起来,她的心也跟着一亮。一股浓浓的、乳白色的烟柱,从露在窑顶外的一节烟筒里冒出来,又轻轻地飘上象蓝缎子一般晶莹的天空间。
母女俩白天参加社里突击积肥,夜里烧窑,一天天过去了,她们的心里好紧啊!整整十三天,扒开窑顶一看,肥料沤成功了!
顾不得三更半夜,母女俩分别敲开队长和技术员的大门。
技术员一鉴定,果然是一窑上好的肥料。队长拍着两只大手说:“我的好大娘、好妹妹,你们真给社里立了大功劳!这下子不光一万车肥料,几十万斤小麦是板上钉钉;连运输问题也解决了!”
母女俩连同技术员一时解不开这句话。队长说“你们算哪,我们村离老河弯沙荒地十五里,一万车肥料就算积够了,要用多少车,多少人,多少天才能送到地里呀?有了这个办法,我们就可以到荒滩上就地烧窑,山上有柴草,也有好土,只运一些人尿、石灰去就算完成了?
过了一天晚上,赵洪大伯又从荒地给大娘打来电话。这回赵大娘可有了经验,通话很顺利。
赵洪大伯在电话里劈头就说:“全工地的人都在感谢你呀,你也来个大跃进呵!若不是这儿工作离不开手,我一定打一瓶子白干酒,回去给你祝贺!”
赵大娘听着,满脸笑成一朵花。
赵洪大伯又说:“我们这边对这个火温沤肥方法还掌握不准,打算请你来工地当顾问,你来不来呀?”
第二天早晨,赵家五口人都离开了家,砖房的门子挂上一把亮光闪闪的黄铜锁。只有写着“满堂光辉”的春联。
作者简介:
浩然(1932.3.25—2008.2.20),本名梁金广,中国著名作家。祖籍天津宝坻。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0年到山东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下放劳动,后担任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历任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委,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
1956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喜鹊登枝》。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苍生》《乐土》等。“写农民,给农民写”是他的创作宗旨,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2019年,《艳阳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从1957年12期的《处女地》(《鸭绿江》曾用名)开始到1959年12期的《文艺红旗》(《鸭绿江》曾用名),浩然在本刊先后发表《风雨》《北斗星》《搬家》《过河记》《满堂光辉》《箭杆河边》《朝霞红似火》和《炊烟》等8篇反映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