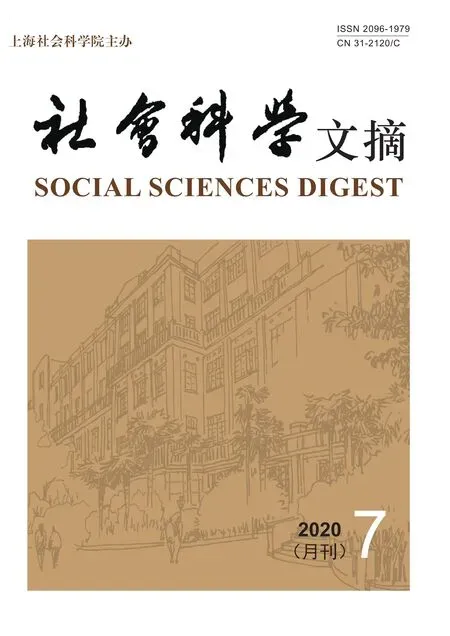“京味”的新声与新变
——想象北京文学的多种方法
研究者们总结京味文学的特征时,通常将其归纳为:北京话、北京人、北京事、北京城。在这里,北京话是重要的存在——它既是语言载体,也是所要表达的内容本身。事实上,当我们想到老舍先生,很难不想到他的北京话。在许多人心中,京味文学首先是“声音优先”的文学流派。
近20年来,京味文学及北京文学创作都出现了“新声”与“新变”。在这里,新声指的是京味文学创作中北京话所发生的变化;新变则指的是,近20年来与北京城市巨变相伴随的文学写作样态的复杂与多样。而潜藏在“新声”与“新变”之后的问题是:一位作家如何改造一种深具传统的地方性语言以适应自我的表达;面对一座“日新月异”的城市,写作如何贴近一座城市的内在精神。
一
今天,老舍这个名字早已和北京话以及深具审美风格的《骆驼祥子》《月牙儿》《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联接在一起了。老舍以他的作品为北京话建造了文学的城堡,这里的北京话洪亮、清脆、好听,有迷人的节奏感,同时也有强烈的平民特征和民间气。某种意义上,新文学史上的老舍和他所使用的语言达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他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地标。
但是,老舍使用北京话,并非自然的选择,其间经过了搏斗、挑选和改造。老舍回忆说,在英国时期,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北平话”。但是,学习英语和拉丁语的过程,促使他重新发现母语,使他逐渐认识到“北平话”才是“我的话”。这是对北京话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意味着对自我的重新理解。发现北平话的过程,是新的创作实践的开始:“因此,我自己的笔也逐渐的、日深一日的,去沾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话的血汁,不想借用别人的文法来装饰自己了。我不知道这合理与否,我只觉得这个作法给我不少的欣喜,使我领略到一点创作的乐趣。看,这是我自己的想象,也是我自己的语言哪!”
当然,重新发现北京话也伴随着他对“冗长的翻译腔的舍弃而选择口语的表达”,这最终形成了他创作的基调:使用口语的、民间的语言,表现最广大市民的生活。要通俗,要简洁,要自然。正如老舍在《我的“话”》中所说:“我写作小说也就更求与口语相合,把修辞看成怎样能从最通俗的浅近的词汇去描写,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来漆饰。用字如此,句子也力求自然,在自然中求其悦耳生动。我愿在纸上写的和从口中说的差不多。”尤其在创作话剧的时候,他慢慢体会到语言选择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我可是直觉的感到,我用字很少,因为在写剧的时节,我可以充分地去想象:某个人在某时某地须说什么话,而这些话必定要立竿见影的发生某种效果;用不着转文,也用不着多加修饰,言语是心之声,发出心声,则一呼一嗽都能感人。在这里,我留神语言的自然流露,远过于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剧中人口里的一个‘哪’或‘吗’,安排得当,比完整而无力的一大句话,要收更多的效果。在这里,才真实的不是作文,而是讲话。话语的本来的文法,在此万不能移动;话语的音节腔调之美,在此须充分的发扬。剧中人所讲的是生命与生活中的话语,不是在背诵文章。”
这是拓荒性的认识与创作实践。在老舍认取他的北平话时,他强调北平话不是官话,他看重的是这一语言的地方性色彩,这也在强调他所使用语言的非主流地位。而这种认知表明,他所使用的语言和所表现的生活并非位居中心和高高在上的,他更愿意站在民间视角,写出三教九流的声音、引车卖浆者的喜怒哀乐。
为什么《茶馆》盛演不衰,为什么《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月牙儿》拥有广泛读者?因为它表现了平民的内在精神,发掘了北平话的内在神韵。当我们想到北京话,我们会想到老舍,想到他笔下的祥子、虎妞、小福子、祁老人等现代文学长廊里的人物,我们会想到独属于他们的声音和腔调。换言之,老舍及其京味作品的魅力在于,他发掘一种百姓语言并使之与广阔的平民生活紧密相随,互为表里;他使北京话深具文学意义与文学光泽。
二
一种文学语言的范式建立之后,需要传承,更需要变革或拓展。王朔语言中有与老舍一脉相承之处,即对民间话语的拾取,但是,也有极强的反叛性——王朔舍弃了老舍笔下老北京人的文雅和“礼”,而对特殊时代所遗留的粗鄙、色厉内荏的东西进行了形象生动的传达。
与老舍的北京话相比,王朔的北京话发生了彻底裂变,他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带有另一种市井气息。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写作者,王朔提取了一种粗糙、粗鄙的、同时也是叛逆的、不入主流的声音,其中包含着调侃、浑不吝以及不驯顺,这是作家对北京话内在精神的重新挖掘,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带来了关于北京文化、北京人的重新认识。而正如研究者们所分析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语言方式,与王朔的大院子弟身份及他的青春经历有关,换言之,这是独属于王朔的、内化为其血液的表达。不过,王朔的叙述也包含了微妙态度,即叙述人之于叙述对象的间离感,某种质疑和嘲弄。
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写的是北京四合院里最普通的百姓生活,乐活、自在、知足,也因此,那些四合院、胡同的消失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幸福生活的到来。刘恒挖掘出北京人生活中的“贫”。刘恒加快了北京话的速度,重现了一种“贫”。张大民简直是“贫”得让人忍俊不禁,但同时又有一种质朴、诚恳和实在劲儿,而正是在通篇的“耍贫”中,张大民和他的家人们战胜生活中的一个个困难而不断向前奔。由此开始,刘恒成为广受关注的深具代表性的京味儿作家——一方面他继承了老舍语言中的平实、质朴、乐观,另一方面也为这种语言提了速,从而更突显了北京人生命中的韧性和达观。“贫嘴”是张大民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生活态度,他以“贫嘴”为乐,也以“贫嘴”表达爱恨,更以“贫嘴”的方式稀释劫难,度过人生困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所以成为当代文学史中重要的中篇代表作,在于刘恒由“贫嘴”入手,挖掘出了张大民身上独有的属于民间百姓的精气神儿。
近20年来对京味语言进行过拓展的作家中,叶广芩是另一位深具代表性的作家。叶广芩的父亲出身于叶赫那拉家族,母亲则出身草根胡同,这注定了她的语言中会有强烈的混杂性。那些皇宫里的太监、宫女、大厨,那些失势的八旗子弟们来到她的笔下。人物的语言及行为方式与人物此间的际遇,形成巨大的张力和落差。一如太监张安达,即使时过境迁,他依然懂“礼”,每逢过节都要带着礼品到“我”家,要给每个人请安,包括孩子、厨子和保安。而在这样的行为背后,则是普通人在时代阴影里的命运巨变。这些人物的语言中包含着话语的变异,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雅的、文绉绉的,但因为失势和乱离,这语言又伴随着低微。有命运感的语言拓展了以往的“京味”,它多样复杂,饱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研究者们注意到,在一系列与京剧曲牌有关的作品里,叶广芩将戏里故事与人物际遇互相镶嵌、互为镜像,使久远的京剧来到了当下和此刻,京白、京韵与京腔由此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了卓有意味的复活。那些民间的、胡同的和大杂院的生活与久远的皇族故事、属于故宫和紫禁城的传说混搭、糅杂在叶广芩的文本里。这独特的、既宫廷又民间的京味,恰合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北京的想象。当诸多研究者慨叹21世纪京味文学后继乏人时,叶广芩和她持续不断的写作令人印象鲜明,念念难忘。
三
北京在发生变化,几乎是一刻不停的。这变化如何进入作家文本,作家如何书写北京之变?这是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多年来研究者们所讨论的热点。
宁肯在《城与年》中谈到过有人不喜欢北京的新建筑,觉得“鸟巢”“巨蛋”“大裤衩”太怪。但这位作家有自己的理解:“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甚至莫如说喜欢。我说过我喜欢巨大的事物,喜欢超现实的东西,故宫在‘巨大’这一点上在全世界也是超一流的,超想象的。”当这位作家不把北京只视为地方性存在时,他打开了认识北京的方法。换言之,当他看到,北京不仅是首都、同时也是被全球化席卷的大都市时,他正视了这种巨变并表示了接纳,由此他有了与众不同的北京想象,从而创作出《城与年》《中关村笔记》等作品。
冯唐则是以“归去来”的方式想象北京,作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去美多年后再回到北京,那些京腔京韵已然消失。1999—2007年的8年时间里,冯唐出版了关于北京的3部作品,《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万物生长》《北京北京》。“三部小说共有一个场景,主人公秋水和他的朋友在燕雀楼门口的人行道上喝啤酒。喝醉,骂人,忆往,铺着塑料布的桌上杯盘狼藉,秋水开始回忆他的往日。在这些关于北京的小说中,总有两个岔道,一条通往少年时代/荒唐岁月,这里有美好的青春爱情;另一端则是成年以后的北京城,朋友暴死,初恋嫁为他人妇,主人公成为跨国公司经理。正是在两条时光隧道里,嵌着两个北京的面向:一个浩浩荡荡充满着大大的拆字,有甜汽水防空洞自行车胡同;而另一个则高楼林立车声鼎沸。”冯唐书写北京的路径与其他作家有何不同?作为没有沉重历史记忆的人,他以一种巨变书写另一种巨变,一种感怀书写另一种感怀。
四
京味文学的固定概念,常常使人拘囿于北京人写北京的认知。其实,以外地人视角书写北京,会为北京文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活力,以及生气勃勃的气息。作为从青年时代进入北京的写作者,邱华栋视北京为梦想的发源地。在他眼里,北京是“梦想的培养基”,它“适合各种梦想像植物和细菌那样的东西,在这样的培养基上茂盛地生长”。因此,北京在他的笔下是敞开怀抱的,是接纳与包容的,是令人惊讶的和令人兴奋的,而绝不是陈旧的、封闭的。事实上,这位作家赋予北京以新鲜与新异之气。于是,在《环境戏剧人》《哭泣游戏》《时装人》等作品中,邱华栋为读者书写了一个极有活力和生机的北京,也塑造了一系列“拉斯蒂涅”式的外省青年形象。在这里,无数青年渴望梦想成真,许多商业大佬淘取第一桶金并写下传奇;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文艺爱好者,有林林总总的新北京人;他笔下也许并没有那么多关于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但有切切实实、热气腾腾的北京生活。当然,这个北京,这既是带给人发展机会的北京,也是带给人巨大生存压力和精神焦虑的所在。
同样作为外地人的书写者,北京对于徐则臣恐怕首先意味着速度,“在北京都得小跑着生活,慢了就要受指针的罪,那家伙比刀锋利,拦腰撞上咔嚓一下人就废了”。在《跑步穿过中关村》中,徐则臣也以“跑步穿过”写出了奔波感,那是陌生的北京,那是低微的、外来的、讨生活者眼中的北京。在《重构人与城的文学想象》一文中我曾经写过,对于北京城里特殊人群的关注使徐则臣的北京书写“脱颖而出”:
他的中短篇小说序列揭示着这个时代社会文化中被我们秘而不宣的那部分特质,那是关于过上好日子而努力向上的生活状态、是关于底层向上层流动的执着的探求。经由这样的人物系列,他的笔下显现出了与老舍那京腔京韵完全迥异、与王朔式京城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学想象。那是作为美好愿景的北京,那是作为攀比对象的北京,是作为奋斗目标的北京,是作为各种欲望搅拌器和巨大阴影存在的北京……关于北京的想象、传说,与许多在黑暗中奔跑着的族群一道,构建了徐则臣关于人与城的陌生想象。
在徐则臣这里,书写北京,不是书写与故乡的关系,而是书写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
五
初登文坛,石一枫小说被视为有浓郁的“京味”,其作品也一度被研究者拿来与王朔作品相比较。但随后,他的写作发生了改变。在与青年读者交流中,石一枫提到他的写作之转变在于,“在新文学传统上多想一步”,并讲述了他对北京话的认知,“北京话我觉得问题就在形象有余,思辨不足”。石一枫抛开了北京话,而认识到老舍之所以是老舍,不仅仅在于他书写了北京人与北京生活。“再说回到那些京味文学的经典作品中去,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老舍之所以是老舍,并非仅仅因为他写了小羊圈胡同和一群形态各异的老市民,更是因为他所触及的往往是一个时代最主要、最无法回避的社会历史问题:阶级分化、民族救亡、旧时代的消失与新时代的来临。”
思考与写作往往是同步的,在《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心灵外史》《特别能战斗》中,北京城及北京气息不再是石一枫作品中着重挖掘和面对的,而变动之下的巨型城市里,人及其精神世界的变化才是他的兴趣所在,由此,他的写作气象一新。
在这位作家那里,北京话固然有吸引力,如何写出人与时代命运的休戚感则更为重要,“作为一个特殊的城市,这里的人和故事天生与时代的走向息息相关并且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命运最典型的代表,也许这才是北京对于作家而言最重要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京味’如果只是作为一种腔调存在,其意义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而足够宽广、深邃和具有总体性的视野和眼界,才是这个地方文学风貌的价值所在”。
石一枫的这些看法让人再次想到本文最初谈到的老舍对北平话的思考,老舍说他所使用的其实是稍稍矫正过的北平话。在其他语言映照之下,他发现了北平话的缺陷,“特别是在腔调上,有些太飘浮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老舍对北京话的清醒认知以及他对北京话的努力改造应该被视为京味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北京文学的发展而言,如何书写北京是一个挑战,而如何寻找到与作家理解更匹配的表达方式也同等重要。北京文学20年来的新声与新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文学世界里,语言是重要而微妙的存在。真正的写作从不只是某种语言的收录机——当语言被书写,它必然要带着作家本人的体温、骨血、内分泌,以及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法。推翻、认取、淘洗、改造,不屈不挠地与陈词滥调搏斗,使汉语永远葆有某种生机与活力,是一位优秀作家的真正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