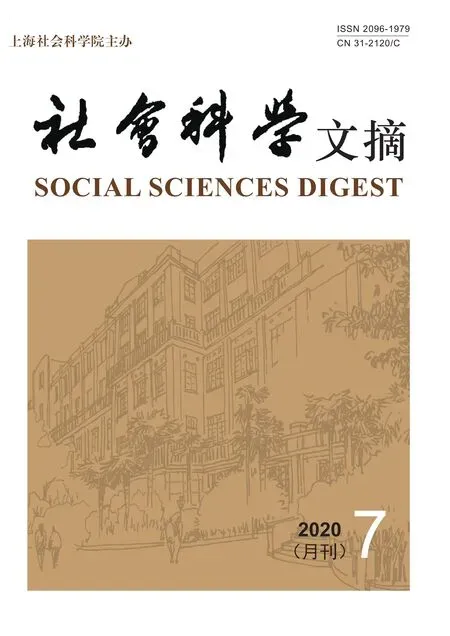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史论
——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始于洪武初年,至洪武八年(1375)基本完成对西藏的全面管辖。永乐时期的明朝,强化对西藏的管理,使西藏成为明代“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终明一世“西陲晏然”的景象。西藏与明朝中央政府之间政治管辖关系的形成,既体现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
明朝经略西藏
明朝建国伊始,明确奉行和平招抚西藏的策略,汉地高僧克新带着“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的重大任务入藏,体现出明朝纳西藏入“中国”的政治意图。从洪武二年至洪武八年,明朝以和平方式将西藏纳入版图,隔断了蒙古残部西入吐蕃之路,防止蒙藏联合,实现了其经略西北、打击残元的战略目的。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北屏蒙古,西扼西域通中原之咽喉,东保陕西,南进四川,进而确保了中国的大一统。明朝在甘青经、川边地区和西藏均设置了各类军政机构,确认了西藏的政治归属;同时任命官员、册封宗教领袖,直接或间接地领有西藏属民,基本上实现了明朝对西藏的统治与管理。
明成祖时期,治理西藏进入新时期。明成祖一方面继承太祖对西藏的统治政策,通过开辟汉藏交通,加强并深化汉地与西藏的联系;另一方面派遣大量官员入藏,参与西藏的行政事务管理。明成祖时期三次大规模的道路修缮工程,使得汉藏间交通道路更为通畅。明成祖也逐渐了解到政教合一、僧俗共治乃是西藏根深蒂固的政治生态,有鉴于这种特殊的政教形势,明朝更为注重文化、宗教的纽带作用。明成祖积极采取“多封众建”的治藏策略,成为洪武朝“尚用僧徒、化导为善”政策的延续,以藏传佛教信仰的纽带力量深刻影响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何以理解明代“中国”西部疆域之形成
明代“中国”西部疆域的确立是当时现实政治与边疆形势共同促成的产物。所以,西藏是否被认为是明代“中国”西部疆域,首先需要考察明朝君臣对“中国”与“天下”的认识。可以说,中央王朝对西藏所持的态度对明代“中国”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消除内忧的同时,明太祖仿效汉武,积极拓边西北,在其诏书中明确提出恢复元朝版图的意愿,西藏未平意味着明朝没有恢复元朝的版图。所以,明太祖及徐达君臣积极地将经略西北、驱逐残元势力与隔绝蒙藏的战略意图合一。明朝君臣在心理上其实已然确定出“中国”的西部边疆范围,这一范围也包括西藏。
与此同时,明朝的“天下中国”观继承了蒙元帝国构建的国家认同,其目的也是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正如姚大力所说“恰恰是天下中国观抑制了对中国内部更小单元的那种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巩固”。所以,西藏是否成为明代“中国”西部疆域一部分,不能以边疆内外底层民众的认同心理为依归,因为无论是明朝内地的子民还是西藏地区的属民,根本无从了解到明朝经略西藏的战略决策,底层民众对于国家大事的知晓程度极其有限。迟至清朝时期,疆域的伸缩变化也只有清政府可以清楚地认识,不但是国内民众缺乏渠道去获知消息,而且欧洲也不了解这一过程。因此,西藏地区民众更多的是遵循于当地僧俗首领的“国家”认同观念,也只有经历长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方面的融通,才有可能使“中国”的观念扎根于底层,并逐渐促使底层民众形成真正的国家认同的心理。诚如葛兆光所言,至少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政治控制、疆域划分、形塑文化、构成认同等重大历史事件,基本是由“国家”或“王朝”主导。
当然,明代“中国”与“天下”是同步构造的。明太祖及其后人尽力恢复蒙元帝国拓展的疆域,并按照“华夷秩序”所确立的圈层结构原则,建立以大明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并以之为纽带,将明朝边疆区域和周边国家按照相互之间的远近关系来确定相应的秩序结构。所以,明代“中国”与“天下”在地域范围上有重合的部分,明代“天下”既包括“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
西藏僧俗势力对明朝的态度更为主动和积极,带有强烈的经济归属意愿。明朝构建的中原内地-“朝贡”区域-周边国家的朝贡圈,凸显出明朝作为东亚朝贡体系圈层结构中央之国的地位。明朝对西藏施政的基础政策是由“分封”-“朝贡”-“优予贡利”三个互相衔接的环节组成。“分封”是最高的政治隶属关系,而朝贡、优予贡利是经济上对西藏的支持和优待,三个环节没有任何的强制性特点。明朝对西藏的内部事务都是听凭其“自治管理”,这种中央政权对边疆区域政治管辖关系的松散状态,需要通过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方式加以弥补和融通,比如明朝与西藏之间长期保持茶马贸易就是一个显例。
西藏地方民众均归属于各僧俗势力的管辖,地方僧俗势力的政治归属就决定了西藏地方民众的政治归属。因此,西藏僧俗势力对明朝是否具有政治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判断西藏是否成为明朝“中国”西部疆域的又一重要因素。在大量史料中,都能看到西藏内部政教势力对明朝的态度是积极的,希望顺应时势成为明朝在西藏地方的代理人,以保全他们在西藏的权力和地位。西藏的帕竹政权和各法王领地重合,共同管理甘青、川边和西藏地区,而西藏各僧俗势力则表现出归属于明王朝的积极态度。比明朝初期崛起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也承认西藏已经纳入明朝管辖。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曾上书永乐皇帝一封书信,在书信中将明朝皇权置于其教权之上,称颂永乐皇帝“政令严明,为各邦所悦服”。他所意指的各邦应为西藏内部各政教势力,显然身居雪域中土的格鲁派也属其中一支,并欣然接受明朝管辖。此后,宗喀巴派遣座下弟子释迦也失入南京进觐永乐皇帝,并在宣宗时被册封为大慈法王,使得格鲁派势力在西藏内部得以迅速发展。西藏内部地方势力的代表帕木竹巴和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政教领袖均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他们与明朝之间的政治管辖关系。以上历史事实反映出西藏僧俗势力对明朝君主的尊奉与忠诚,而且对明朝君主所统系的王朝具有强烈认同感。所以,从根本上讲,明朝和平招抚西藏战略是成功的,而西藏对明朝的归附则是西藏文明东向发展长期趋势的直接反映,与明朝对西藏多元治理模式的确立亦存在密切联系。总之,明朝应对内亚形势的变化,继承元朝治藏之传统,在调整治藏模式的过程中,捍卫和巩固了“中国”的西部疆域,并实现了明代“中国”西部疆域的长期稳定。
另外,明代疆域的历史书写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的认识。明朝建立的东亚朝贡体系反映的“内地-甘青、川边及西藏-朝贡的外国”的圈层结构,容易使后人强化出二元的华夷秩序观念,这可能也成为清人修撰《明史》将甘青、川边和西藏地区放在《西域传》中的一个影响因素。另外,《大明一统志》也把西藏列入《外夷》。这里既有华夷之分的二元秩序在明朝行政区划设置上的体现,也特别强调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特征与中原内地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西藏作为明朝疆域一部分,已经写入《大明一统志》,突出了明朝对“边疆”范围的基本认识。
要之,不论从明朝君臣对西藏的态度,西藏政教势力归属明朝的主观意愿,还是从明朝疆域构成的历史书写,均从不同侧面体现出西藏作为明代“中国”西部疆域的事实。虽然,明中期以后,蒙古势力再次南下扩张,明朝国力由盛转衰,只能奉行收缩防御的战略方针。但是,明朝重新部署和调整了西番诸卫军事体系的战略重心,仍然可以固守西藏,并构建长城九边以及甘青边墙,以抵御蒙古势力的西进与南下。直至明朝后期,明神宗仍明确表达出“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开拓的封疆”的看法,说明明朝构建的“天下中国观”已然形成,并持续发挥着巩固和捍卫明代“中国”西部边疆的作用。
结语
元明易代之际,蒙元帝国的兴衰主导着内亚局势的变化,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与察合台诸王对中亚东部和西域的争夺,使得西藏成为元明两朝控制西域、制约中亚的战略要冲,这种外向发展的帝国形态主导着“中国”边疆的形塑过程。而明朝前期的西向拓展,直至将西藏纳入版图,最终确立了明代“中国”的西部疆域范围。终明一世,明朝西北疆域大体稳定,从而形成了“西陲晏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的历史局面。诚如葛兆光所言,“全球史的视野,淡化了过去固定的‘中心’与‘边缘’,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重新观察过去的历史”。重新审视明朝经略西北、控驭西藏的历史,可以勾勒出多重维度的历史意涵:
第一,明朝继承了元朝西部疆域的一部分——西藏,西藏成为明朝行政版图的一部分,并最终确立了明代“中国”西部疆域的范围,使近世“中国”有了大体的雏形。
第二,明朝采取派遣使臣入藏直接管理和扶植西藏政教势力间接管理西藏的多元治理模式,为清朝调整对西藏的治理策略提供了借鉴,也为清代“中国”西部疆域之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明朝对西藏的经略,促使西藏从明朝的西部边疆变成内亚地缘政治格局的中心,这也标志着明朝与中亚及西域诸国、北方蒙古诸部战略相持局面的形成。
第四,借由“华夷”秩序与东亚朝贡体系共同构建的明代“天下”,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朝贡国家。明代“天下”是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决定了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促使明代“中国”成为内陆亚洲和海洋亚洲的双重地理中心,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