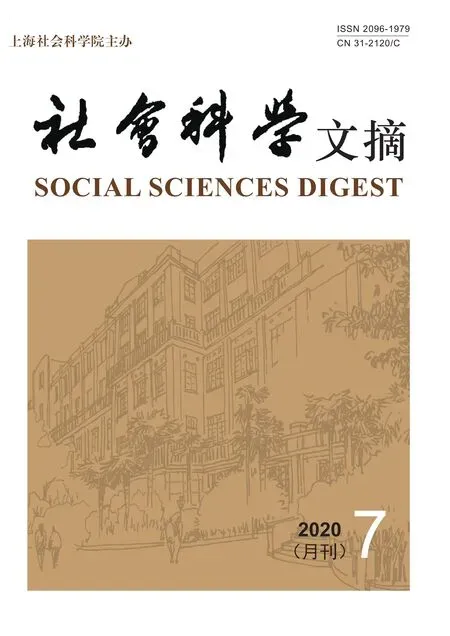历史研究“碎片化”境遇下的西夏学研究
所谓历史研究“碎片化”是指历史研究呈现出了磷片化、杂乱化,甚至远离历史研究主题、无法体现历史研究的功能性、失去了整体关怀的现象。历史研究“碎片化”的风潮也波及西夏学研究领域,近年来,西夏学研究也有“碎片化”趋势。
西夏学研究的发展趋向
西夏学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清朝时期,在清朝考据学兴起之后,部分清代学者开始对各类史料中有关西夏的记载进行收集、甄别,希望能编撰一部较为完整的西夏史,以补二十四史中无西夏专史之缺憾。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产生了一批如周春《西夏书》、张鉴《西夏纪事本末》、陈崑《西夏事略》、吴广成《西夏书事》等西夏专史著作。此时没有“西夏学”一词,学者们也以编撰西夏专史为根本目的,还谈不上对西夏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学界对西夏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主要缘于大量黑水城文献文物的发掘。1909年,俄国的科兹洛夫等从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中盗挖了大量的文物文献,并将其运往俄国。这批文物文献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对西夏历史的研究首先在国外兴起了。如:俄国的伊凤阁、聂历山、孟列夫、克恰诺夫、索夫罗诺夫等,日本的石滨纯太郎、中岛敏、冈崎精郎、西田龙雄等,法国的伯希和、毛利瑟、沙畹等,德国的傅海波等,另外,匈牙利、美国、韩国也有学者从事西夏历史研究。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国外西夏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涉及大历史视角下的语言文字民族国名社会性质等问题。代表性的成果有:著文介绍《番汉合时掌中珠》,出版《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西夏国书说》《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西夏学历史概述》《西夏语研究小史》《关于西夏国名》《西夏语文学》《西夏国家机构》《西夏国史纲》《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早期党项史》《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西夏国名考补正》《西夏建国过程之研究》《关于西夏法典》《关于西夏语之韵的组织》《西夏国书〈同音〉字典的同居韵》等。这一阶段国内从事西夏学研究的人较少,主要以罗氏父子王静如先生为代表,西夏学研究成果主要有:《西夏国书略说》《西夏文存》《西夏国书类编》《西夏研究》《关于西夏国名》《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考》《西夏史籍考》《关于西夏国名二三事》《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西夏是不是羌族》《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论西夏的兴起》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在宁夏、甘肃、内蒙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文物资料。这些资料有力推进了西夏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西夏学研究向着专题史研究方向深入发展,研究成果的专题性更加明显,诸如:西夏国史方面的《西夏简史》《简明西夏史》《西夏史稿》等;考古方面的《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西夏王陵》《西夏佛塔》《西夏官印考》等;语言文字方面的《文海研究》《夏汉字典》《宋代西北方音研究》《同音研究》等;经济方面的《辽夏金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发展中的若干问题》《西夏经济史研究》等;宗教文化方面的《西夏佛教史略》《西夏道教初探》《西夏文化》《西夏文化概论》等;民族关系方面的《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宋夏关系史研究》《宋夏关系史》等;法律方面的《西夏天盛律令研究》等。
20世纪末以来,大量的中国藏、俄藏、英藏、日藏、法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整理公布,使西夏学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西夏学研究成果数量大增、内容更为丰富,大量集中在语言文字与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代表性的专著如:《贞观玉镜将研究》《类林研究》《圣立义海研究》《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西夏文献论稿》《西夏社会》《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西夏经济史》《〈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西夏经变画艺术研究》《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西夏文〈无量寿经〉研究》《西夏文的造字模式》《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研究》《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西夏姓名研究》《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黑水城出土钱粮文书专题研究》等。论文数量更多、关注的问题更具体的代表性的论文有《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区寺院经济研究——基于出土西夏文契约文书的考察》《西夏状元释褐职任窥斑》《黑水城出土5147-1号西夏文典身契研究》《西夏语“罗睺星”的来源》《西夏“只关”考述》《论西夏语的词义移植》《西夏土地买卖租种的价格租金与违约赔付》《西夏水月观音图像研究——以瓜州东千佛洞二窟〈水月观音〉为例》《试论西夏服饰中的植物纹样》《西夏语的副词子句》《论西夏语语素和双音节词的结构类型——以世俗文献为中心》《黑水城西夏医药文献汉字对音研究》《英藏西夏文《庄子》残片考释》《西夏艺术品中对“狗”形象的塑造》等。这一阶段,学界分类别、分专题对西夏文献文书进行整理研究,这相对于以前只依赖于汉文史籍记载对西夏史进行研究而言,西夏文文献资料的使用更有利于我们客观深入地认识西夏社会历史。
综观不同历史时期西夏学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由最初的大历史视角逐渐深入到对专题史的关注,再发展到对更多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研究逐渐深入细化,反映了本学科研究的发展,令人欣喜。但近几年来,我们也注意到在西夏学研究深入细化的过程中,如果对一些小问题的研究把握不当,则会使研究呈现出碎片化。
西夏学研究出现碎片化趋向的原因
第一,研究的深入、细化,增加了研究成果“碎片化”的可能性
从黑水城文献出土到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的西夏学研究主要以大历史的视角探讨西夏历史、西夏语言文字、西夏政权建立及其国名、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虽涉及西夏的信仰、族源、贸易、法律等,但不多,这些研究多属于奠基性的拓荒之作。西夏学研究也呈现出了由最初的语言文字研究、西夏国史研究向经济、宗教、法律、族源等领域延伸的趋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夏学研究是在前一阶段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问题的深入研究带动了西夏专题史研究,内容涵盖西夏宗教、军事、法制、经济、社会、文物等,西夏学研究真正步入了专题史研究的轨道,且逐渐出现了专题下的分支研究,有利于西夏学向纵深化、精深化发展,为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各个层面认识西夏历史奠定了基础,西夏学真正学科内涵得以体现。20世纪末以来,各类西夏文献的相继刊布,尤其是俄藏、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公布对西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西夏学研究成果数量大增、内容丰富,而且使西夏学研究方向也发生了改变——语言文字研究和文献考释成为研究的主流方向,专题史研究方面也呈现出了由某一个专题继续下延研究。如:经济史研究由社会经济关系、土地制度,下延到契约、典当、高利贷、寺院经济等具体经济现象;政治制度史中下延到对文书档案、具体职官制度的考察;文化中下延到对西夏诗歌、文学、谚语、夏译汉籍的详细考证;法律方面依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法律条款反映出的信息,对西夏社会妇女、职官制度、酒业、畜牧业等问题的研究;宗教方面深入到对佛经的考释、对西夏某一区域宗教信仰的探讨;还有对一些零散的社会文书的研究;等等。从整个西夏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西夏学研究由最初的宏观历史问题的探究到专题史研究,再到专题下延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了“点—线、面—点”的特点,这是一个学科研究发展成熟的表现,但同时,这种细化研究无疑增加了研究成果“碎片化”的可能性。
第二,多学科交叉研究与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
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多学科的交叉已是历史研究的显著特点。早在19世纪至20世纪,学界就因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原则、侧重点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史学流派,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德国的兰克学派。兰克学派认为追求历史事实是史学最高的境界,倡导史学家应依史料追求历史真相,史料高于一切,引领了“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风潮。20世纪新史学极具影响力,新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把历史研究对象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把全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历史研究范畴。历史研究渗透到了生态、物质文化、经济社会、社会状态等方面。同时,新史学倡导从叙事史向分析史转变。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促使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越来越普遍。以上诸因素对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对历史研究的细化起到了助力的作用。西夏学研究无不受历史研究思潮之影响,西夏学研究亦是依此轨迹而行,如今语言学、文学、法学、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文献学、宗教学等研究方法早已渗透到西夏学研究领域。利用各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方法去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法律等问题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是推动西夏学研究深入发展的一种必然需求。历史基础知识、边缘学科知识、专门性学科知识相结合是新时期对从事西夏学研究工作者的新要求,我们的知识不能只局限于西夏学领域。这种多学科交叉与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及存世和出土西夏文献的残、杂、碎的限定性都使西夏学研究对象更趋具体化、细化。如:通过语言学研究方法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深入到对其中某一个语言点进行探讨;用文献学方法对出土西夏文献文书残片进行考释;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对某一出土地契、榷场、借贷、抵押等文书进行个案考释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一件佛经残片、一件契约、一个人物、一个职官、一个药方等都可成为研究对象,如果把握不当,也难免有“碎片化”之嫌。
第三,受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后现代思潮在文学、历史、科技、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现代思潮提倡的非理性、多元化、去中心化、去主体性,不相信有宏大、一致的规律性存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多样化形态,人们觉得自己就生活在一个到处充满“碎片化”的环境当中。反映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就是它挑战了传统历史研究的基本模式、方法、价值,对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规律的探求、民族国家的形成、客观展现历史原貌、史料的运用及文史关系等提出了质疑。不再通过逻辑、历史的论证来阐明某个道理或理论,强调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无结构性,注重被传统史学研究排斥在外的“他者”的地位及研究,使研究者更注重从他者的视角对某一具体的历史碎片进行解构。大量的西夏社会文书、档案、碑刻等资料的公布,正好为西夏学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有利于从细节上构建西夏社会历史镜像,然而却也大大增加了宏观把握的困难,这样也不免使西夏学研究呈现出“碎片化”。
第四,急功近利思想和考核机制的影响
现行的教育和科研考核管理机制,要求研究者快速出成果,与快速出成果相伴生的必然是科研成果质量问题。研究者无法在短期内对较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只能选择小而细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都使得科研成果“碎片化”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西夏学研究亦不例外。
如何在细化研究过程中防止“碎片化”
西夏学研究要想有效避免“碎片化”,就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处理好小材料、小问题,做到以小见大,以局部观全局。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或许有益。
第一,研究者要有通史、整体史的意识
碎片化的核心问题是研究者在历史细化研究中如何去把握“局部”与“总体”的关系。当历史研究陷于琐碎、微观,缺乏整体史观念时,就是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体史关怀,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因此,在西夏学研究中对专题史的下延问题研究并不意味着研究成果必然呈现出“碎片化”。对一些人们熟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发掘、考证,也未必会导致研究“碎片化”。研究小问题不是错,真正的问题在于,在研究小问题、边缘性问题时,如何把握“小”与“大”、“局部”与“整体”之关系,研究者有无通史、整体史的意识,有没有将细碎的小问题纳入到专题史、通史的视角下去探究。西夏学研究要走进通史、走进世界史的研究中去,要与回鹘学、藏学、唐宋元史、辽金史等建立紧密的联系,我们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要有通史意识,打破局部与断代的羁绊,在大的视野下去认识小问题,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客观,认识问题才有独道之处。漆侠先生在《怎样研究宋史》一文中讨论断代史与通史之间关系时说:“如果只搞断代史而不同通史密切结合起来,这就必然地如古人所说,‘断代为史,失其陈陈相因之义’,人为地割断了与通史的联系,不但无法说明这一断代史是怎样从前代发展而来,而且也不能把这一断代史妥贴地放在历史发展的巨流中,从而说明这一断代史的历史地位。处理通史与断代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是亦只能是:在专的基础上通,在通的基础上专。搞断代史必须以通史为基础。”西夏学研究亦然如此,若我们在研究中能够把握好“专”与“通”,则无须担忧成果呈现出“碎片化”。
第二,在研究过程中,强化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的积极面,体现历史的功用和价值
历史研究是以求真为目的的,力求达到认识与历史真相的一致。但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们是一个个的独立的个体,在研究的过程中因研究者个体知识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关注点不同,对历史认识也是不同的。任何一种历史理论、学说都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主体的因素和属性。主体性的存在会对历史认识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我们应该强调、强化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的积极功能,即:力求认识与历史真相的统一。新时期,我们可以运用多学科交叉知识和多种研究方法从事西夏学研究,将计量、心理、比较等史学方法运用到研究中,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有区分学科界线的能力,要区分历史学科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的学科界线。另外,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专业立足点,不要遗忘历史的功能。司马迁在撰《史记》时说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体现了历史的功用和价值,历史研究的价值也在于对以往历史经过一定的科学研究,提供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并给人们以启迪的历史知识与智慧。历史是一部人类的社会生活史,而我们所已知者无非是历史的一鳞半爪,往往都是组成历史的碎片。然而,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做到将其置予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作到以小见大,而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