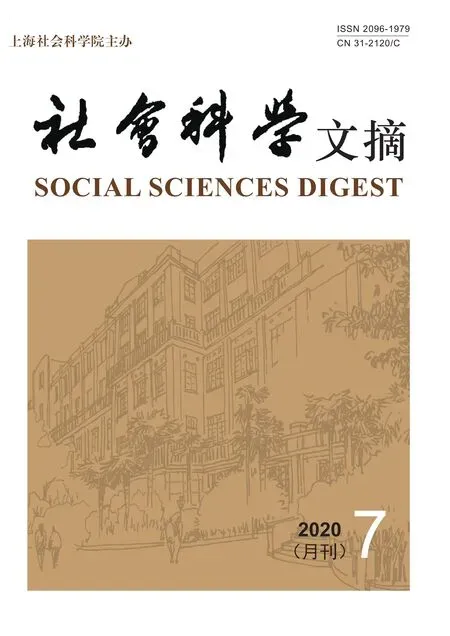让历史人类学的田野有认识论
拙文《历史如何来当下——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观》发表以来,引起了人类学学科内外的一些争论。本文想接续先前的思考,对人类学取向的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学取向的历史人类学就田野调查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所谓“历史学取向的历史人类学”,主要是指大陆这些年高举历史人类学旗帜且有丰厚学术研究积累的一批来自于历史学领域的学者的研究。这一共同体“主要学术贡献是其吸收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变革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限,从而大大拓宽了史学的研究视野,并由此获得了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和地域研究的某些重要发现和突破”。(张小军语)
但是,历史学家借鉴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与人类学家所理解的田野方法仍有一定距离,因而所进入的田野也未必是人类学家心目中的田野。由于“学科化”的本位倾向,历史学界的许多历史人类学家在研究上的落脚点似乎愈加从“回归历史”变成“回归史学”(张小军语)。而本文偏向“回归”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
回不去的历史现场与回得去的历史现场
现代人类学理解的田野有两重语义。第一重语义是指,人类学家离开书斋进入社会中调查。所谓田野工作(fieldwork)是指离开书房等传统知识生产车间而踏入社会获取知识。在此,田野工作是相对于文案工作这一概念而言的。第二重语义是一个学理操作意义上的理解,可以说,有多少种人类学流派就有多少种田野观。比如,年鉴学派和功能论学派就把“田野”理解成一束社会关系系统,因而走进田野就是走进一重或多重社会关系。又比如,象征人类学把田野看作是一个象征或符号的丛林,那么,走进田野就是走进象征的丛林,追寻意义的解释。持有社会文化变迁论或过程主义者,自然会走进所要考察的时间旅程之中。就本文而言,更愿意把田野看作是一个语义场。也许,只有把田野视作一个语义场,才能在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实践之间寻找到共享点以及讨论的起点。
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家是如何走回历史现场的呢?概言之,他们一般是到乡村、庙宇(包含教堂)、档案馆等地方搜集族谱、碑刻、书信、契约、账簿、记事簿等民间文书,然后带回书斋进行阅读和研究。与传统史学相比,他们只是扩大了文献使用范围,在研究上并无本质不同。
当历史学家说能走向历史现场或走进历史现场时,就第一重意义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但从时间物理学来论,则说不通。时间是流失的,是不可逆的,连内卷(involution)都不可能。历史是一种遥远的过去,至少是此刻之前的时刻。人们怎么能身处此刻而又回到此刻之前的状态呢?
田野可以是考古现场,可以是一个乡村,也可以是都市中的某个仪式。这些田野中难免有许多历史因素存在,比如,一件古老的器物,一卷古代书籍或族谱,一件地契或婚契文书,一个古老的仪式,甚至古代的服装,等等。但这些历史因素与身处现在的历史学家是同时在场的。只能说,历史与现在同在于现在,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历史学家回到了过去。就历史学家而言,他们的物理学意义上的身体是回不去的,回去的只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他们的研究是一种出神状态,即精神游离出身体而进入过去。在认知过程中,历史学家造成了身心的分裂倾向。但这种分裂是一种外在的观察,而就历史学家本人而言,当他们处在出神状态时往往遗忘了现实中那个肉体的存在。
那么,人类学出身的历史人类学者又是如何开展田野工作的呢?现代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访谈的技术主张: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一起生活、劳动、休闲、娱乐、审美,乃至参与共同的宗教信仰活动。这种互动使得人类学家能够从与之互动的对象的行为和语言中获取民族志材料。大致有三种:一种是直接观察所得,一种是通过土著人的陈述和解说所得,一种是研究者基于常识和心理领悟所得。由此,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在开展田野工作时只能是观察和理解人们如何面对自己和他人的历史、如何邀请自己和他人的历史来到当下,如何看人们解读并操弄自己及他人的历史。即便是做口述史研究,人类学也是着重口述者都口述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要口述这些内容而不是别的?为什么同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最后口述出来的内容不一样?等等。在此,历史被作为一部意义史来处理。
由于参与其中,人类学家在做历史人类学田野时很少遭遇身心分裂局面,因为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历史是回不去的”,所以,人类学看到的情境是古代遗留物与现在人共处于一个时空结构中。而历史学家将时下的情境与历史遗留物进行剥离或拆解,在想象中重新把古物及其包含的信息放回到过去的历史脉络中或社会结构中去理解,而这样的历史脉络和社会结构必须仰赖大量的历史文献去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大部分学术实践活动把现在活着的人和场景撇下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即使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同到达同一地点进行田野考察,他们进去的根本不是同一个田野现场。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说:“处理与以前一样的同一堆资料,但通过给它们一个不同的框架,使它们处于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了。”因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由于怀揣不同目的,并持有不同的研究信念和视角,最后走进了不同的关系组合和自我意义的追逐中。
从观察者角度理解,今人不是古人,今人怎么可以用自己的心去揣摩古人呢?在此,人类学有一个假设:不同历史时段的人具备不同的历史属性、文化属性,包括感知、认知世界的方式也不同。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认知,要不然,就不会有断代史了。既然历史可以断代,那就意味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状况以及栖存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人群。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历史学家是清醒的、理智的,但是当面对自己这个认知主体时却不能通过反思而认识到身处当下的自己与古人不同了。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可以穿越千古而读懂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群。这种雄视一切的心态在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始自司马迁,因为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一个极具膨胀的认知主体。而人类学从转向“野蛮”社会的那一刻起便认识到:不一定比“土著”更具认知能力。
那么,人们为何还要说“我一下子回到了古代或过去”呢?这其实是谈论的意识活动。当人们与历史因素并置时,他们能部分地感觉到古人的意识和情感。我们在阅读古代诗文、小说、书画,或者听古典音乐时,就常常产生这种感觉。这可能意味着古人今人全都共享一套相同的、根本性的理解范畴。其实,在这里有一个未加证明的假设:有些东西不受时间约束或框定,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某种符号或符码系统而直通古人。比如,语言。
历史学家迷恋于语言,相信语义的连贯性,藉此而进入古人的世界。历史学家默认,相对其他的事物而言,语言是世界上最可靠的东西,尽管语言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是,深受分析哲学影响的人类学家却对语言失去了信任,因为他们已习惯性地思考:文字,何以成了那样的文字?
在精神和情感上与古人共处一个语义场中,这给历史学家造成了一个回到过去和历史现场的错觉。其实,历史学家只是在“语言”或在语言所构筑的世界里漂浮,犹如一根草棒在洪水中打漩。名与实不符,文字材料的世界早已剥离了现实世界。根据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理解,那是一个独立的意义系统。
田野的有限进入与错入
从本质上讲,任何学科(不论是历史学还是人类学)所进入的田野都是有限的,因为不可能百分之百获取对方的信息。问题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哪个更能接近或更容易进入历史的田野?个人以为,人类学可能更胜一筹。造成历史学尴尬的原因不在历史学家本身,而在古人留下的信息极少。
与被研究者心意相通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与对方的心意不相通呢?我们根本就进不了真实的田野。庄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说的就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区隔。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反对理论先行,主张一切从材料出发,由此可以客观地进入历史。但请认真思考:客观地观察事物或世界的方式或处理文献的态度是从来就有的吗?难道不是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发展出来的,以及在现代学术训练体制内获取或被安装的?也许我们一天书没读过,但是能摆脱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集体观察方式及其价值观念对我们的影响和塑造吗?客观观察本身也是一种学术策略,是我们主观意识所选择的一种认知路径。以我观物,故物物皆着我色。最后在学术文本上呈现出来的不过是有我之境耳。学术成果本身很可能是一个集体的表象。既然是时代的集体表象,那么,谈何进入?
面对文字的具体不同态度
无论对于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而言,语言(也包含“言语”)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信息载体。这两个学科都需要赖诸语言分析而开展工作。比如,人类学家到田野中进行访谈或观察,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用语言记录下调查对象的语言,或者是与他们的谈话内容。至于历史学家更是离不开语言,因为历史学分析的主要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献,即一种语言的书面记录。
相比较来说,人类学更多依赖口头语言工作,历史学则更多诉诸文字记录材料。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材料,我们无法想象历史学如何工作。至于人类学,有没有书面材料都可以开展工作,大量人类学研究都是在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社会里进行的。当然,笔者这么言说,并非要降低文字在人类学分析中的价值和地位。
语言是普遍的,在全球任一社会中语言均为全体成员所共享,即人们可以借助它进行思考、交流。但是文字,即使在同一社会内也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因而,文字记录材料不能够被视作全社会的集体意志的表达,它所能反映的仅仅是掌握文字阶层的想法,是一个社会中特定人群的一套象征符号系统,并用以存义与表义。但是,在对中国历史经验展开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人类学和历史学往往对此有着不同的评价态度。
就宗族研究而言,人类学家能够意识到:族谱碑刻上反映出来的宗族观念和实践样态并不是全部宗族成员的态度,它仅仅是儒生集团和男性群体即掌握汉字书写及受过一定儒学训练的古代男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宗族。对于大部分历史学家来说,就学术实践而言,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宗族观念,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里的一套架构。这在逻辑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或者用一个特定人群的文化实践样式指代了整体。
如果没受到任何儒家影响,而自己发育出一套父系或母系亲属制度,人类学家更愿意使用世系群(lineage group)或继嗣群(descent group)这样的概念来指称它。但是,历史学家往往看不到这套亲属制度的东西,因为过去的儒生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即使有,也语焉不详。历史学者应当反思依据文献所得出的那个宗族的概念在解释中国时所存在的巨大漏洞问题。
历史学家研究过去的民间日常生活,同样也应该意识到那是一堆被文字阶层的意识和审美偏好过滤出来的文献,未必就是“民间的东西”。
如何捕捉背景信息
每个人都几乎看到过这样一幅图景,或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人边走路边用手机通话,同时他会做出各种肢体语言,比如手势、肢体扭动、各种面部表情,甚至笑声和哭声。打电话的人仿佛处在一个二人世界中,即他与电话另一端的人构成一个社会结构或情景,完全忘记了现实中的一切,包括自我的存在。对于观察者而言,只是看见他的嘴巴在动,至于说什么内容,如果不是刑侦专家或肢体语言学家,很难猜得出来。当与一个人现实里面对面说话时,我们主要使用听觉器官来捕获他的语言,而其他的非口头语言则容易被忽略。即使注意,也是其次的信息来源。在此,口头的语言成为主体信息,而肢体语言等成为背景信息。对第一个图景而言,由于听不见打电话者说的内容,因而肢体语言成为观察者的主体信息,而口头语言则成了背景信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处田野中时能够做到收取这两方面的信息,而历史学家绝对做不到。古人或过去的人们只是把他们想说的话写在了纸张或刻在了石碑上,有的则把想法型铸在某种器物上或编织在某种仪式里。当历史学家拿到这批资料的时候,只能是单纯地通过视觉来捕获或加工信息(大部分是通过阅读或观察活动)。而这些信息都是主体信息,无法看见古人在写这些话或说这种话时做的各种动作、表情和声调。一般情况下,古人也不会往里面写这些东西。这不是说历史学家拙笨,是因为历史学家无法与已经死亡了的或故去的人对话或互动,或观察他们,无法看见他们语言之外的背景信息。
在田野访谈或观察中人类学家是如何观察、认知并分析背景信息呢?基本上靠的是直觉思维。如果不借助直觉,可同时派遣两位人类学工作者到达田野,一个从事主体信息观察与记录,一个从事背景信息观察与记录。实际上,后者是把背景信息当做主体信息来对待的。这样的人类学家必须是训练有素的,否则,最好携带一名心理学家或认知科学家到场。
每个社会中的人们在长期的交流与互动中,他们每一句口头语言都伴随着一定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而出现,二者构成一个固定的语言结构或陈述句。口头语言和相伴随的肢体动作及表情存在相互表征的关系。因而,要想理解每句口头语言,就不能丢弃相伴随而出现的肢体动作、表情和声调。口头语言不能单独产生语义,是结构赋予了个别语词以意义。历史学家只能从文字记录中提取需要的信息,但这种剥离开具体情境的“语言”其实早已失去了丰富的语义,失去了结构的界定。一但失去了结构的界定,就可能随时扩大历史学家解释的自由空间。只有在结构的框定范围内,我们才有可能限制我们解释的自由性或任意性,从而接近历史的“真相”。
结语
笔者并非看不起部分历史学家所实践的历史人类学,只是想在对比中找出两个学科的历史人类学在田野中的一些差异,思考能不能进入历史现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现场、藉由什么进入历史现场、如何在田野中获取各种信息等问题。在对比的框架中,难免会夸大彼此的距离,从而遮蔽了共享或兼容。同时,当笔者以人类学为本位立论的时候,也会美化人类学而 “黑”历史学,遮蔽了历史学的魅力。对此,笔者深刻地进行自我反思与检讨。在进入田野及获取各种背景信息方面,笔者倾向了人类学,指出了历史学的某些局限性。也许在哲学家看来,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耳,所以笔者提出“有限进入”或“错入”概念。从佛家角度讲,本文也是一种我执。
笔者无意排斥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因为借助祖先留下的有限信息了解过去,可以满足现代人的一种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