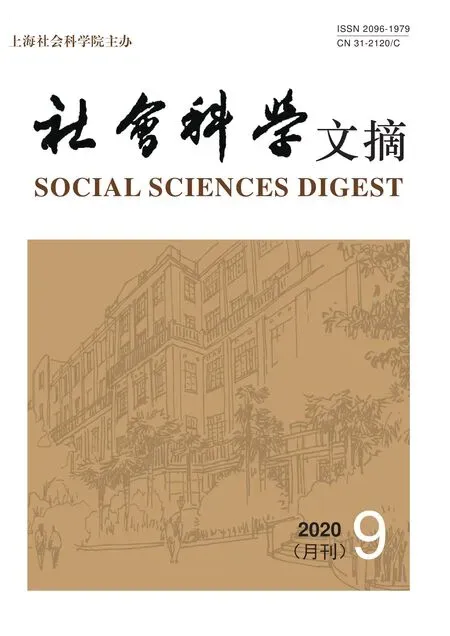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
文/蒋承勇
近期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普遍对跨学科研究的热衷,表现出对文学研究理念、方法和视野更新与拓展的强烈愿望。虽然文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是,处在“网络化—全球化”的新时代,其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与研究,并作出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之展望。
“文学”与“文学研究”
“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先进》中,该篇说到了孔门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里所谓的“文学”泛指所有的书本知识和文字著述,基本上与“学问”一词对等。到六朝时期出现“文、笔”之分,“文”指的是有韵的文辞,“笔”指的是无韵的文字。这时“文”的观念逐渐与现代的文学观念接近起来,但也仅限于有韵的诗文。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literature)观念初步形成于20世纪初叶。直到1935年出版的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才明确把文学称为“美的文学”,并且以这种“美的文学”的观念去梳理文学史。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学界基本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概念。
对“文学”观念的理解,直接影响着作为学术体制中关于文学研究之“学科”的界定。“美的文学”虽然从概念的角度大致上区分了文学与史学、哲学、宗教等相关学科,但是,从文学研究的实践看,在当时我国的学界,学科性的文学研究并没有因此聚焦于“审美性”这一“质点”展开,相反,其重点却落在了文学之外的相关学科上。
在五四之前,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文学研究多属于随感和评点式散论,缺乏理论的深度和体系性,因此,诸如诗论、文论、词论都算不上现代学科和学术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总体上不过是古代文人对自我阅读经验的感悟性表达,其实古希腊时期关于“诗学”的表述也大致属于此类性质;另一方面,其“研究”和“评说”的内容多为文体学和文章学、版本学方面的议论、评述或者考据,而较少作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方面系统而深度的阐发。但是,到了五四以后,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研究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标志,一方面表现在西方式“文学”与美学思想主导下对文学的艺术技巧与审美价值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表现,是对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思想文化内涵的阐释。两个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梁启超与王国维。
与众多囿于诗论、词论、文论和小说评点的我国传统之“文学研究”不同,梁启超的《饮冰诗话》表现出了崭新的观念、视野、格局与气度。他在陆续发表于1902至1907年《新民丛刊》的《饮冰诗话》中提倡“诗界革命”,其间虽然倡导诗歌的新意境、新句法,但更强调诗歌之思想内容的“革命”。正是他的这种不无矫枉过正的文学研究新观念,在当时和后来的文学研究中影响重大而深远,使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成为一种风气和时尚。梁启超的这种不无激进的文学“革命”思想的形成,其实得益于他对“西学”的接受。这是他们这一代学者思想演变之共同原因之一。
与梁启超等人抬高与扩大文学社会功能的观点不同,王国维等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更偏重于文体与审美。王国维接纳了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观念,摆脱中国传统之阐释、评析文学的观念与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新成果。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他以叔本华的生命哲学理论分析小说表现的人生欲望。王国维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其间的哲理与审美意蕴,使文学研究上升到审美的境界与高度。在1908年完成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了“境界说”、“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独到的见解,这基本上是从审美的角度展开文学研究的。王国维式的美学与艺术研究和梁启超式的社会与历史研究,总体上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启的我国文学研究的两种学术理路。
从五四过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长时期内比较充分和普遍地张扬了梁启超式的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研究之传统,致力于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的阐发,并要求文学创作“内容为王”,为现实斗争服务,甚至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服务,有意无意中扼制或者轻视了文学“审美的”研究,某些历史时期还比梁启超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进一步扩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乃至不恰当地夸大了文学的政治功能,并因此抬高了文学的学科地位,使阐释文学之思想政治内容的“社会学”研究,成了文学研究的主导方向。
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角度看,我国现当代的文学研究历史上片面地强调文学之思想政治容及其社会功能的现象,其实是单一性地、简单化地偏向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学科,这种学术理路上的“单一性”偏颇的存在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无需避讳。其实也正是这种学术偏颇的存在,使我国相当长时期内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理论和手段总体显得机械、简单甚至僵化,这便是引发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的“方法论热”的重要原因。
“方法论热”与文学跨学科研究
基于对较长时期内文学研究之观念、方法、理论和手段方面的机械、简单甚至僵化现象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研究领域表现出了强烈的求变求新之愿望,寻求文学研究之理论、观念和方法创新的“方法论热”持续升温。正是这个“方法论热”,很大程度地摆脱了文学研究简单化、机械化和极左思想的束缚,开创了别开生面的活跃而开放的文学研究新局面。事实上,为了寻求文学研究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跨学科研究正好成了当时“方法论热”所追求的重要途径。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角度看,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热”所取得的成效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研究方法由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拓展为多元多层次趋向,美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纷纷涉足文学研究,打破了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一家独大的僵化局面,同时也使人们对文学之本质、文学之功能的认识得以重大改观。文学不再被认为是简单地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文学研究也就在人文社会科学之多学科视阈中展开了跨学科研究。
第二,文学研究除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展开跨学科互动之外,自然科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也是一种别具新意的学术现象,这是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在新时期的一种表征,文学研究也因此展现出更大跨度的跨学科互动研究。
第三,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比较文学生发于19世纪的欧洲,但它在我国兴起得较晚。正是在80年代“方法论热”持续升温之时,比较文学也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新学科应运而兴并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和“中国声音”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如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众所周知,比较文学除了强调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之外,跨学科研究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强调对文学进行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跨学科、多学科、多元多层次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或者说,跨学科研究就是比较文学的重要范畴。在比较文学快速发展的态势中,跨学科研究则进一步走出比较文学本身的学科界阈,成为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和普遍实践的方法。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伦理学研究、文学生态学研究、文学心理学研究、文学人类学研究、文学文化学研究等,都是文学研究界普遍关注的跨学科研究课题,推动着整个文学研究的出新与出彩。尤其是其中的文学伦理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有了较大的影响。总之,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有效地拓宽了我国文学研究的创新之路。
跨学科互涉对文学研究的“异化”
在看到几十年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所取得的十分骄人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实际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过度运用非文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文学,导致了文学研究的“异化”和“边缘化”。所谓的“过度运用”,类似于我国学者指出的西方文论中存在的“强制阐释”现象,指的是非文学的各种理论、知识或方法运用于文学评论与研究,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成了论证某种非文学之理论的材料,从而丧失了文学研究的自我立场,文学研究被“异化”后蜕变为非文学的研究。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把文学研究引入了“非本质主义”的误区。
从国际学界的情况看,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以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为主导,西方理论界出现了大量文化研究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等,一时间它们成了理论时尚,堪称为一种“理论热”或新的“方法论热”。这些理论虽然不无新见与价值,但是,它们明显存在着理论与文学/文本“脱节”的弊端,有“非本质主义”的倾向。
从我国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文学的文化研究可以视为我国80年代“方法论热”后文学跨学科研究之追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但是,这种泛理论的文学文化研究一方面深化了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把文学研究提升到更高的理论与学术境界,但另一方面也明显存在着“喧宾夺主”现象,把文学的研究“蜕变”成了非文学、泛文化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和文学研究本身走向了“边缘化”和“异化”的尴尬境地。正如21世纪初有的学者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突出而普遍的现象:逃离文学。曾经风光无限而被人追逐的文学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弃儿。于是,各种‘转向’迭起,不少文学研究者纷纷转向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和文化研究,不少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也耻于谈文学,甚至出版社的编辑见到文学研究的选题就头疼。‘逃离文学’愈演愈烈,‘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受到根本威胁”。除此之外,比较低级的“泛文化”“泛理论”研究则表现方式虽然五花八门,但基本一致的是牵强地把某种文化理论套用到研究对象上,生硬地“阐释”出某种文化结论,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用文化理论或把泛文化理论套用到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比比皆是。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强调论文必须具备理论(其实是指文学之外的理论,引者注)框架的恶果除了误导学生重理论轻文本、生吞活剥地搬用理论外,还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身心压力……这样就造成了浮夸、狂妄和不实事求是的学风”。所以他们强烈地呼吁:文学研究要摆脱宏大的文化理论“喧宾夺主”而回归文本解读,回归文学研究本身。
学科间性与文学研究的“本质主义”
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除了“审美性”的本质属性之外,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之间都存在着学科间性,因而各学科都存在着与文学展开跨学科互涉与对话的学理依据,这是文学研究的又一本质特征。因为文学描写的内容——人和人的生活——可谓是千姿百态、无所不包,有人的精神—情感世界的生活,也有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自然的方方面面。受文学本身的知识包含的统摄性所决定,文学研究无可避免地也关涉除了审美性之外的与人相关的各种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文学研究就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统摄性而言,就不可避免地决定了这种研究本身的多学科性,也就是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学科间性。有鉴于此,文学研究强调“审美性”抑或“文学性”的本质特性以有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但是仅此一点是不够的,在另外的角度和意义上,强调文学研究的学科间性和跨学科之本质属性比强调审美性更其重要,因为离开了跨学科互涉与对话的文学研究,不仅背离了文学与生俱来的生活内容和学科知识的统摄性,而且会导致文学研究的路越走越窄,导致又一种意义上的文学“非本质主义”倾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追求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新时期“方法论热”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90年代文学的文化研究“热”,虽然文化理论类似于一个容纳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总“框架”,但是,它依然与文学存在着因“审美性”带来的学科间性,文化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毕竟有质的差异性。因此,文学之文化研究的对象虽然可以有多重选择,在“文化理论”的内部也可以有多方面(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语言的乃至科学的,等等)的侧重,但也依然因其间拥有的“审美性”而与其研究对象有学科差异因而有学科间性。所以,所有的文学文化研究都必须认清并把持这种“差异”,在学科“间性”的间隙之间展开多学科对话与互涉,进而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作出独特的阐释。在这种意义上,用任何一种文学之外的学科——包括文化理论和自然科学——对文学进行研究和阐发,都是有意义的和必要的。也因为如此,我们批评文学研究中用当代西方代文化理论过度阐释文学文本的弊病,并不因此意味着排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排斥现当代西方文化理论资源在文学研究中的借用;尤其是对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则无疑应该在更高更宽阔的视野上予以大力提倡,并将其拓展为整个文学研究领域方法论创新的重要渠道。
在“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要寻求文学研究的创新进而摆脱其一段时期面临的种种“尴尬”,一方面需要在跨学科理念引领下更广泛地接纳和借鉴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动态地完善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构架,并且这种研究的核心对象和知识生产依然属于文学范畴,拥有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性”。另一方面,虽然要保证文学研究的“文学性”,但是这种研究也不是囿于文学审美主义的固有原则,以唯一的“审美性”作为学科自主的学理依据,坚守所谓的文学“本质主义”,却无视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学科间性的客观事实,拒斥与文学之外的众多学科展开互渗与对话,致使走向另一种“单一性”偏狭的文学研究。事实上,如果一定要从学科自主性角度谈文学研究的学科本质属性,那么,文学研究的本质属性除了“审美性”意义上的“文学性”之外,还包括学科知识的包容性与统摄性。因为,文学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对人类活动和知识蕴含的无所不包的统摄性,所以文学研究即便是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学科分工愈加细致完善的条件下,也依旧天然地、不可避免地具有学科内涵的包容性、知识生产的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就此而论,无论是中国文学研究还是外国文学研究,都不仅始终离不开学科间性基础上的跨学科互涉,而且这种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提升、拓展与深化,又永远是整个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创新方面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