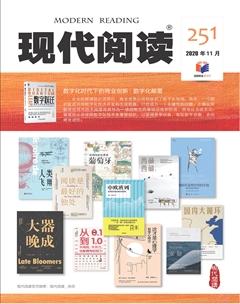女老生王珮瑜京剧学演记

王珮瑜,1978年生于江苏苏州,“余(叔岩)派”老生的第四代传人,被业界誉为“当代孟小冬”。现任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副主席。
入校
1992年,我正值初中二年级,在苏州第二十一中学念书。此前,我已经开始了京剧小票友的“旅程”,学了几个月老旦,又学了老生,并有缘归入“余派”。上海戏校时隔十年再次开设京剧班,面向全国招生。当时我跟随范石人先生学习余派声腔,在复兴中路文化广场的星期天京剧茶座认识了王思及老师,得知戏校招生的信息。王思及、邱正坚、翁思再几位老师在场,随即把“这个苏州小姑娘唱得不错”的消息转达给当时的戏校校长杨振东先生。不久我就参加了戲校的统一考试,有腰腿、形体、声乐、模仿、笔试等科目,我一一通过。但是发榜当天,我榜上无名,并被告知戏校不能录取我,原因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专业戏校没有培养过女老生,上海戏校考试委员会再三斟酌,还是决定不能冒险。
消息传出的当天,我在范石人先生的儿子范文硕老师(著名琴师)家里,范老、王思及、邱正坚、翁思再几位老师也在,大家纷纷出主意,要在正式发布录取通知前最后再努一把力。我当场写下一封信,许下“喜爱京剧,我心已决,不论成败,都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京剧事业”的悲壮愿望,请我母亲带信去找时任上海文化局局长的马博敏老师。
转天上午,母亲把信交给马局。当天的《新民晚报》刊登了由翁思再老师写的一篇题为《上海戏校破格招收女老生》的新闻。王思及老师也在同一时间向戏校领导作出了承诺,由他担任我的主教老师,确保我在专业学习上不出纰漏。主、客观条件都成熟,和这件事相关的所有人都表达了足够的诚意。几天以后,校方回复说,我可以以培养京剧师资后备力量的名义入校,有一年的甄别期,如果跟不上进度,就要劝退。就这样,上海戏校92京剧班一共入校54名学生,我就是第五十四名。
我的“倒仓”
人生最好的老师,莫过于挫折。1992年破格考入上海戏校,受老师们的呵护,一路顺利地学戏、演戏。人在少年得志、过早成名的无限光环笼罩下,还能保持清醒,实在太难。
同班的男生在14岁以后陆续开始倒仓(指变声,嗓子是戏曲演员的本钱,变声意味着“粮仓倒了”,故曰倒仓),这是男演员很重要的一关,倒得回来是老天爷赏饭,倒不回来就只有改学别的行当,或者干脆转行学乐队和舞美的,也不在少数。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无数同行好友艺术命运的起伏悲喜,也阅尽了在京剧舞台上摸爬滚打的艰辛。这些年,我从不在公众场合讲述学戏的辛苦,因为外行人实难理解,唯有亲历者方知其中味。即便淡然如今,想起那9年的点滴时光,“艰辛”二字的确是避不开的记忆。
男生的陆续倒仓,反倒让我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性:老生改了武生,小生改了丑行,之后倒仓倒回来,又可以武生老生“两门抱”。虽然他们经历过痛苦和尴尬,而凤凰涅槃后却可能是一片新天地。我心里羡慕这种大起大落的历程。
也许是对我杂思妄念的一点小惩戒,1998年的春天,我居然迎来了一场“倒仓”。因为一次春游冻出了感冒,引起声带水肿,然而我不知其中厉害,并没有停止吊嗓,加上长年累月不太科学的发声习惯,我患了“声带小结”,导致声带闭合不良。医院五官科专家建议我立刻停止演出、吊嗓,噤声3个月以上。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度令我十分郁闷,不仅失掉了专业上的优势,也不知前路是凶是吉。反思前几年顺风顺水,对演唱技巧自信爆棚,凭借一副好嗓子,几乎不懂得发声科学,一味地追求高调门,一出戏里处处铆上劲唱,所以一遭遇外力作用,声带出问题也是无可奈何的结果了。
关于声带小结,并没有最佳的治疗方案,只能是休养加调理,要做到绝对噤声,按时作息。在那大半年,我接受了各种方式的治疗,包括雾化吸入、针灸疗法、中药调理,也因为不需要上台演出,不需要吊嗓子,倒是腾出很多时间来读书、反思、静默,也开始琢磨更科学的演唱方法。自此,全然凭借天赋唱戏的岁月宣告结束。
半年后,嗓音好转,正值京津沪台几所戏曲学校组团在台北大剧院演出。这是我声带小结恢复后的首次登台,打炮戏就是《捉放曹》。心怀忐忑地上台,唱到陈宫见曹操杀掉吕伯奢,惊愕不已地跪倒在地唱“陈宫哭得咽喉哑”这句嘎调,非常庆幸,我唱上去了。此时在侧幕紧张到不敢呼吸的王校长终于松了一口气,“珮瑜的声带小结基本康复了”。
这次声带小结之后,我在唱法上做了调整,调门降了半个,加强了中低音区的训练。尽管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摸索过程,但毕竟从此前基本处于无意识的状态,蜕变到学着用技巧去演唱,算是一次悄无声息的自我革命吧。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台上见:王珮瑜京剧学演记》 作者:王珮瑜)
——读李如茹《理想、视野、规范: 戏曲教育的实验——北平市私立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中华戏校)(1930—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