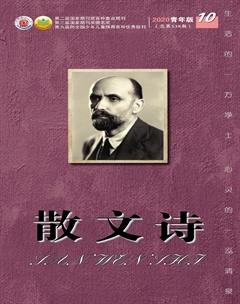残墟
毛阳
那是一个晚秋的黄昏。我爬上了故乡的一座山峦。山峦离家很近,近在眼前,我儿时常在它脚下砍柴、嬉戏,却因为它山陡林密,从来没有上去过。直到那天,我登上山巅,一些不知被时空遗忘了多久的石屋,才在一瞬间出现在眼里。
石屋早已坍圮。深厚的苍苔,缝合了墙基与山石宽窄浅深的缝隙。四面残墙犹如怀抱,庇护的草木繁郁。山巅的秋来得早,也来得深,屋角墙沿随处可见的酸枣刺,荆棵树,已给残墟铺盖上层层黄衣。通红的酸枣无人采摘,在苍老的枝头耗尽了水分,于透进残墟的风中寂寂摇晃、颤动。生满墙头的枯茅,被劲风梳刮得整整齐齐,琴弦一样利落,发丝一般纤细,发出凄清的琴音。高过墙头的榆树,只剩下蓬蓬杂杂的枝丫,划出一阵阵咿咿呀呀的凌厉之声。然而残墟岿然,然而残墟默然,在世人遗忘已久的山巅上,在秋风汹涌凛冽的波涛中,在秋阳稀薄如血的残照里。
它们是何时所建?它们是何人所建?建来是为了什么?它们又是何时被弃?何由被弃?为什么我与它们近在咫尺,却从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也从未听身边的老人谈起?尽管他们也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
无人可以问询。晚秋山风呼啸,从一望苍茫的远方澎湃而来,把残墟的外墙砰砰地拍打,一瞬间破碎出无数声响,形音皆像冲锋陷阵的号角。我恍惚觉得,这凌驾山巅的残墟,曾经是战斗的堡垒,一块又一块巨石,是一个又一个战士,从山巅滚碾而下,让山脚的虫蚁瞬间迸散,迸散成一片茫茫。山风依旧汹涌,高过墙头的榆树迎风摆动,枝丫在高旷的暮空沙沙作响,形如垂天之云,声如二胡弦音。我恍惚又觉得,这藏匿山巅的残墟,曾经是一方巢穴,纷纷杂杂的黄叶瘦枝,在风暴的淫威下,不住地向屋角瑟缩、聚拢,终于雨住风止了,它们摇曳于高高的墙头之上,溅起一抹抹血色的残阳。岁月隐隐,残墟寂寂,幻象皆失,只有枯高的茅草,拨弄着清寂的琴音。哦!尘世嘈杂,这遥筑山巅的陋室,又怎知不是一位高人超然方外的逸举?
阵阵秋风,由起到息,在殘墟的不同部位,演奏出不同的乐曲,时而是唢呐的激昂,时而是二胡的悠长,时而是琴音的清寂。眼前的残墟,也忽而是庇佑良善的堡垒,忽而是滋生传奇的巢穴,忽而是超然凡尘的陋室。残墟之“残”,却让驰骋的想象无拘无束,变幻万端。
这越发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弯下腰来,开始在残墟间穿梭,寻找实实在在的证据,一切历史的遗存,一切烟火的气息,乃至物件、文字和符号、痕迹。然而无果。残墟已经被山巅坦荡的风云雷电,涤洗得内外干净,血色残阳中,一片片鲜艳的苍白,像许多庞然大物,腐烂了肌肉,风化了皮毛,不辨种属,满目狼藉。迷失其间,我仿佛也变得轻盈起来,被秋风的波涛浮起,在亦真亦幻的过往中颠簸,只有被苍老的荆棘牵住了衣角,才感觉到了躯体的存在和有形。
也许只有那些在此寄居过的生命,才能给我以准确的答案。然而,历经时局的动荡,岁月的淘洗,以天地之大,世事无常,他们现今又漂泊何方——是在这山脚一望可见的村子,还是在山巅目不可及的远方?他们又是否还记得这里,记得这些尘封的记忆?这些尘封的记忆,又有着怎样的爱恨、怎样的悲喜,让这些饱历沧桑、顽强跳动的心脏,生出怎样的涟漪?及至物是人非,他们还是否愿意开口把即将凋落岁月深处的故事讲起?就如我身边的那些老人,究竟是不知道这座近在咫尺的残墟的存在,还是全都不愿旧事重提?抑或是岁月的嬗变早已使他们心中一片云淡风轻?
心随着黄昏渐渐沉郁,我怏怏走出残墟,回头一望,却发现答案已经摆在那里。看似僵硬的残墟,早已在山巅反复的日晒风吹中,柔软了石质的躯体。墙头的茅草,是它新生的头发;怀抱中的草木,已然茁壮繁郁,连脚底与山石的缝隙,也被苍苔缝合严密,它们也重新和生自太古的山峦,融为一体。融合的过程,无声无息;融合的结果,无痕无迹,就像随着山峦一同诞生,非由人力,也从无人居。一切消逝的或存在的生命,创造寄身的所有,所有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得失输赢、是非善恶,以及对其无休无止的执著或执迷,超脱或逃避,追寻或迷失,终将湮灭于时空永恒的荒寂,化作一片濡染着血色的景象。暝暝暮色渐起,漠漠残晖淡去,在斑斓的苍穹上,夕照越发浓重、壮观,恰如返璞归真的人生。
如果说默然也是一种诉说,斑斓便是它的回答。罩满暮色的山巅,万象沉静,残墟一如沉入湖底。飒飒秋风吹过墙石间隙,浮起叶影,仿佛有一支断断续续的埙曲,萦绕天际。
临别,我双手抚过它们粗糙冰凉的皮肤。时空无涯,草木一秋,或许,我与它们的相逢,也只在这个晚秋的黄昏。过往,我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余生,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来。明天,我将去往远方的繁华,而它,注定要在遗忘中继续沉默。此刻,暮色已经晦暗了天地,我必须立即下山。一别许是永别,咫尺而又天涯,我不愿刻字记游,以庸俗的徒劳,破坏它始终默然的诉说,然而,我温热柔软的血肉,还是愿意在它冰凉的残躯上,留下自己的温度。
这点温度,来自人性的温暖。
人走后,新月如水,天地间一片澄澈。
残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