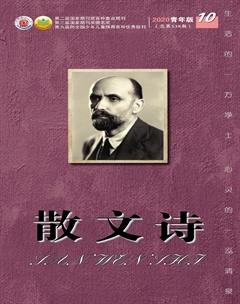静物写生
倪锐
挂 钟
跑了一生,马不停蹄。止住脚步,成了静物。歪斜了,上方的挂钩和下方的衬底,还有钉死的星星,和曾经昼夜不停而此刻静止的指针。椭圓形的脸盘耷拉向一边,像一个老人,坐姿偏斜,扬尘是它喃喃的细语。其实,停驻的那一秒,就注定了它的后半生,只是它善良地以为,有人会让它重新起步。
镜 子
一道墙,斑驳,缺角少块。镜子,趴在墙上,一动不动,唯恐跌下来,被几根蜘蛛网吊住。生锈的铁箍在它的圆脸上绕行一周,就悄无声息了。它用浑浊的双眼看着远处车水马龙的街道,心里却慢慢收拾起满屋的旧家什。
梳 子
墙角,那不是它该呆的地方。它太老了,掉牙了,被遗弃在了这个旮旯。它把灰尘披在身上,以遮挡那黯淡无光的脸面。有飞蛾从头顶飞过,有虫蚁从头顶爬过,有斜阳从头顶照过,有目光从头顶扫过……都是它低到尘埃的头顶。它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它在一瀑青丝飞扬的头顶,咧开嘴笑。梳着,理着,冷不丁掉下乡愁一缕。
软木塞的啤酒瓶
没有标签,仿佛失去了祖籍的孩子,啤酒瓶就那样立在说不出颜色的桌上,泛着绿光。真没有什么值得描摹的,如果非要不可,就只有它的软木塞了。啤酒瓶盖启开的那一瞬间,不知是瓶子抛弃了瓶盖,还是瓶盖嫌弃了瓶子,散了。瓶里的酒原来或许剩了一半,于是有了这个软木塞,就像一个烂苹果,堵住了不停说话的嘴。从此,两个不相干的物件一辈子不离不弃。瓶子紧紧地攥住这个沉默的软木塞,生怕自己再一次失去完整的家。
破 伞
布面七零八乱地贴在地上,没有颜色。沙石三三两两,是眼睛,也是斑点。主心骨已经生锈,再也撑不起那一片无雨的天空。贴着地面,倾听来自屋檐的水声。一辈子为人遮风挡雨,不被需要时,才知道,雨是血化成的泪。
老 屋
在村头立着。歪脖子树,没有。鸡鸭,没有。人烟,没有。有的是,屋顶、屋檐、窗、墙和一扇永远不会再打开的门。盛气凌人的挖掘机和静默的那堆黄土,让老屋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