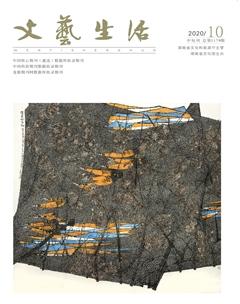饱以老拳
王唯州
摘要:学界对于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不少作家也都以此为题材,创作相关作品,马丁·瓦尔泽的《批评家之死》即是一例。文章从虚构性出发,试辨析作家与批评家若即若离的关系,点出二者间的联系。
关键词:作家;批评家;马丁·瓦尔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獻标识码:A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9.004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9-0007-02
一、作家与批评家
试想,一位作家端坐于房间,四周是剥落的白墙,头顶吊着光秃秃的灯泡,面前一张深色木桌,桌上只一支笔、一张纸。四下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大概有这三种情况:
其一,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作家只是一个人坐在桌前,并且永远一个人坐在桌前。他可能冥思苦想,对着白纸和笔发呆,也可能握起笔奋笔疾书,最后把白纸黑字付之一炬。总之,什么也不会发生。
其二,不远处响起幽幽的脚步声,门打开了,进来又一位作家。端坐的作家看到来者,一惊,一愣,随即又融化了,脸上泛起微笑。进来的作家和他一样的身材、一样的穿衣风格,甚至连举手投足都一样。不同的是,作家看不清他的长相,那人的脸上始终萦绕着一团暗影,久久不散。他手里还夹着烟,不难推测,来人脸上的迷雾就是吞吐的二手烟。新作家的到来打破了屋内的平衡,他们从最开始的沉默不语和陌生,渐渐变得熟络。言语触碰到了某个火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作家和作家之间的交谈,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能聊的境域,赞赏、奉承或是恭维,一派祥和气氛。
其三,门外传来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作家起身开门,却被门外的力量一把推开,一个趔趄摔倒在地。进来的是一位批评家,穿着灰色对襟呢子大衣,肥胖型身材,大衣已经遮不住突起的肚子了。他戴眼镜,秃顶,头戴一顶棉麻贝雷帽。脸上总是一副吹胡子瞪眼的愤怒表情,但实际上他开心快乐得很,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生气了,那他就不是现在这副表情。事实上,谁也没见过他有另一副表情,那都是一个传说。作家见到来的人是批评家,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跟他握手寒暄。但他很尴尬,因为他既没有烟,也没有茶,甚至连杯子都没有,只有一把椅子让他坐,有纸和笔让他写上一几句金玉良言,或者几句对他的写作或某部作品的赞誉。他提出了这个想法,很有些不好意思,但批评家欣然应允,提笔就写。
批评家很快就写完了,把笔傲慢地一扔,还是那副吹胡子瞪眼的表情。作家心想差不离,他开心着呢,于是凑近一看:
一无是处!四个歪斜的大字,外加一个作家们十分忌讳的感叹号。那会儿,作家只感觉被强烈的屈辱感包围,被尖刀一般的耻辱所征服,所击倒了。他低头看着自己在地上蹭了满手灰的双手,那是握笔写作的双手,却被外界的力量推倒,毫无尊严地杵在地上,被灰尘浸染、粉刷,几无还手之力,最后还谦卑地握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批评家——的双手。
作家伸出右手,搭在满脸困惑的批评家的肩膀上。突然间批评家似乎理解了,他闪过一丝笑容,胜利的微笑,就差摆出V字手势了。然后,作家握紧拳头,朝批评家攒劲挥了过去。
二、面对批评家的作家
让作家面对作家很难,然而更难的是让作家面对批评家。作家的天职是面对自己,他们最开心的就是被投入一个小房间,隔绝一切与外界的往来,没有网络,但其他的一应俱全。身处黑暗、独处、安静,是他们最舒服的状态。这是作家的工作,但别以为这就很简单了。翻开《巴黎评论》的采访集,所有作家都在表达面对自我的痛苦,每天他们只能面对自己,而且永远也看不到尽头。
如果作家老是独处,渐生痛苦,那也不可取,久之会消磨笔力。所以,还是得让作家适当地与人交流,获取生活经验。但如果与生活中的所有人往来,恐怕会遭人控诉——看《巴黎评论》里的那些作家,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常人无法接受的怪癖,也不适合与所有人交往。与其引起社会舆情,不如把他们圈养在一个小圈子内部,那就让作家去面对作家吧。然而曹丕的《典论·论文》有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文人互相看不起,那怎么交游呢?好在这样的时代过去很久了,中国当代作家最不见外,热爱与人交游,其中又最喜欢与作家交往。交往的方式,无外乎喝酒、吃肉、聚会喧闹,所以也不难理解各级作协经常组织作家采风活动,到一地游玩,吃一桌餐饭,院坝里共舞一曲,足矣。他们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摆谈,古时候是在星空烛火下,现在则是在KTV频闪灯下畅谈。他们什么都聊,就是不聊文学。
作家不相轻,这是好事,但文学事业总不会就这么一帆风顺、欣欣向荣的,固然有毛病和不足。为了文学事业的进步,也应当合理挑刺。所以不能只让作家和作家推杯换盏,也还应该让作家去面对批评家,去面对他们尖锐的抨击。这是让作家感到最为难的部分,难的并不是接受批评,而是像个犯错的小孩一样坐在圆桌一头,被十几位批评家包围这样一种境遇。听无关的人高谈阔论自己的作品,还不能打断他,是一件让作家脸红心跳的事情。这无关激动或是羞愧,而是全然的尴尬和可笑。所以当帕慕克访问中国时,中方特地举办了一场帕慕克作品研讨会,邀请了各方学者和作家参加,当一位位学者作家发表了冗长的感想,他们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帕慕克——作为备受赞誉的当事人,理应在最后表达一下感谢——却只在桌子那头看到一把孤零零的空椅子。原来在学者发表感想的间隙,百无聊赖的帕慕克溜了出去,畅游北京去了。
这正是当代中国时兴的作家面对批评家的一种形式:作品研讨会。在研讨会中,没有批评,尽是好话。我能想象出这样一个场景:宽阔敞亮的会议室里,作协领导、研究所的学者、大学教授、著名作家一字排开,按级别、座次依序坐在摆有名牌的座位上,头上悬挂的是巨幅红底白字的横幅,上书“某某作品研讨会”。大家都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好似领导讲话的场面。而我们的作家“某某”,灰头土脸的,缩在桌子一角,乖乖地等待批评家们发表完讲话,末了再表示几句感谢,仅此而已。
这是我想象的场景,也是现实中的场景。
三、批评家为何而死?
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的小说《批评家之死》写的就是作家面对批评家的故事。因为故事发生在德国,所以我们也有幸借助这部小说一窥德国文坛中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不同于中国文学界作家和论家一派和谐共生的盛景,《批评家之死》所呈现的德国文坛可谓是乌烟瘴气、矛盾重重。批评家埃尔—柯尼希开有一档名叫《门诊时间》的电视节目,他在某一期节目中尖锐地抨击了作家汉斯·拉赫的作品。某天,警方突然宣告埃尔—柯尼希死亡,旋即逮捕了嫌疑人汉斯·拉赫。显然,他最有理由杀害批评家。但小说的叙述者也是作家的好朋友,研究神秘主义的学者米夏埃尔·兰多尔夫不相信汉斯·拉赫是凶手,于是开始单枪匹马地调查,走访了多位与汉斯·拉赫有关系的出版家和学者,最终迎来了事件真相。
有论家指出,《批评家之死》是对德国文坛活脱脱的影射和讽刺,其中埃尔·柯尼希这一人物,正是直接讽刺了德国著名批评家赖希·拉尼茨基。因为批评家是犹太人,小说中也有侮辱犹太人的话语,所以小说出版前后深陷“反犹”风波,差点胎死腹中,无法出版。
抛开小说的现实影响,单论艺术水平,尽管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却仍旧不失水准。马丁·瓦尔泽的写作是癫狂的,小说某些段落近乎意识流,然而却无比流畅,无论是从写作的角度还是阅读的角度来看,都是一气呵成。在那些呓语般的独白或对话周围,读者甚至能嗅到酒精的神秘气息,如同李白酒后吟唱《将进酒》,瓦爾泽似乎也是在极乐之宴后写下的《批评家之死》。这极乐之宴带来的,是马丁·瓦尔泽在小说最后所作的畅想,于是又带有了科幻小说的意味:在未来的2084年,70%的人口不再阅读,那时的批评家被称作评判官,他们还记得以前的文学是什么样,只有他们还会阅读,他们就是文学教皇,决定着文学的一切好与坏,而作家已经不再重要了。
无独有偶,在西方想象中,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似乎是水火不容的。还记得大卫·米切尔的小说《云图》中有一章题为《蒂莫西·卡文迪什的苦难经历》,讲作家德莫特·霍金斯不堪书评人菲利克斯·芬奇的恶评,在一次酒会中把芬奇推下了高楼,之后写下回忆录《饱以老拳》大获全胜,赚得盆满钵满。
其实,作家与批评家的你来我往并非是个人恩怨,更多的还是出于一种文学策略。一旦达到各自目的,交战双方便鸣金收兵了。汉斯·拉赫和埃尔—柯尼西如此,马丁·瓦尔泽和赖希—拉尼茨基也是如此。个中缘由可以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解释,他将“场域”定义为“自具运作法则,不求诸政治与经济的独立的社会空间”,以文学的角度观之,文学场域就形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权力场。在这个权力场中,充满了竞争和分配,角色则只有二元对立的操控者与被操控者。更关键的是,不同于社会阶级的固定性,文学场域的操控者与被操控者是不断变化的,身份随时会发生转变。
在社会空间里,作为参与者的作家生产了作品,于是形单影只的他们不得不寻求多方支持,诸如以书店、出版社为代表的经济资本;或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凭、职称、社会声誉,是为文化资本;或加入某文学团体,为巩固自己的社会资本。同理,批评家也生产作品,作为文学场域的参与者,他们也占有不同的资本,矛盾就此开始。作家与批评家双方为了积累原始资本,巩固或提升自身的地位,在文学场里大打笔战,以致恶言相向,甚至卷入谋杀案,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毕竟,在当今这个社会,人们大多还是关注于个人利益。
参考文献:
[1](德)马丁·瓦尔泽:批评家之死[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