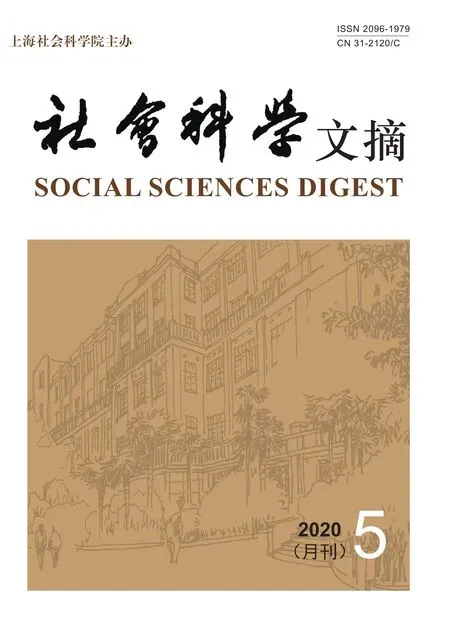情理融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特质
——兼论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之建构
文/张自慧
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有着强烈的时代关照和实践特征,与人们的生活样态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设的“新道德”?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话语体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何谓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多数学者认为西方伦理学关注理性,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关注情感,甚至有学者以情感伦理学为后者命名。这就使得情感常被认为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中国也因此被贴上了“人情”社会的标签。但人们忽视了“情感”一词在中国的多重含义。本文拟从中西比较的视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在区分一般情感与道德情感的基础上,分析道德情感何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主题;通过梳理“敬”的内涵及其嬗变,说明作为诸道德范畴情感之基的“敬”是情理合一的伦理理念;通过剖析孔子及先秦儒家“仁”“礼”统一的思想,揭示“仁”“礼”架构是情理融通之枢轴,从而彰显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情理融通之特质,旨在为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的构建找到出发点和支撑点。
情感: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主题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情感和生命,形成了与西方迥异的主题。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传统伦理的情感主题,我们需要以西方伦理学为参照。
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以世界本源为内容的理性(reason)一直是哲学的主题。一部西方哲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探寻和追求理性的历史。其理性的发展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理性萌芽期。古希腊早期哲学家迫切希望弄清世界的本来面目,极力寻求自然和宇宙的构成、本质、规律。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巴门尼德是古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努斯”既是心灵也是理性,是超然于整个宇宙之外的存在;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皆有“逻各斯”,知识是依靠理性认识获得的。“逻各斯”和“努斯”的提出构成了古希腊哲学对理性的最初规定性。其二,理性发展期。苏格拉底提出了对理性的信仰,认为人都拥有一个理性的灵魂,并开始将哲学的关注点引向理性;构建起理念论框架并确立理性重要作用的是柏拉图,他继承和发展了从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通过将世界分为“理念世界”与“可见世界”,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亚里士多德则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其所构建的宏伟而思辨的哲学体系将古希腊理性主义推向了顶峰。其三,理性成熟期。挺立在现代哲学制高点上的康德和黑格尔,继承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追求理性与自由的精神传统,在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内在张力中,以高度的自觉和卓越的智慧担负起把理性与自由的现代原则哲学化、经典化的历史使命,对推进现代理性与自由的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总之,在西方哲学或伦理学中,理性是贯通和作用于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基本精神和永恒主题。从理论维度看,它是世界的本源,是世界万物背后永恒的“逻各斯”;从实践维度看,它既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建立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原则。与此不同,中国传统社会也重视和强调理性,但理性的内涵和外延都与西方有别。从内涵上说,中国传统理性概念主要是与情感相对应的范畴,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对人的情感和欲望的约束,是与儒家中庸思想相关联的“时中”与“合宜”;从外延上说,中国传统的理性概念关涉的是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关系疏离,即关涉人的生活、人生的意义以及国家的治理,也就是修齐治平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对理性理论层面的思考、探索与争论,但其目标仍是为了破解现实生活的困境,而非像西方那样执着于对“逻各斯”或“努斯”的思考与追寻。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存在是知、情、意的统一。儒家哲学是情感哲学,但“情感”一词的内涵需作深入剖析。在古代儒家那里,情感分为一般情感与道德情感。一般情感指个人的、主观的情感,即处于简单、直观形态的情感;道德情感是通过人的情感意向活动表现出来的经过理性加工的情感,是符合道德目的论的理性情感。儒家伦理中的情感不是纯粹主观的个人感情,而是在社会场域中关照他人和环境后融入了理性成分的道德情感,因此,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题的是道德情感而非一般情感。情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底色和基调。这种情感底色和基调奠基于殷周之际的人文转向,形成于孔子以“爱”“敬”为内核的仁礼学说。其后,孟子的“四端”说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道德情感视为人性的根源,宋明儒学表面上以心性之学为核心,但其“性理合一”思想实质上仍是以情感说明人的存在方式。与西方不同,儒家伦理中的情感不是纯粹主观的个人感情,而是融入了理性成分的道德情感,是来自宇宙的“生生之道”。在儒家那里,情感(道德情感)被视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道德理性不能离开情感而存在,离开情感,无所谓道德理性。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爱”与“敬”体现着道德的“温度”,以这种情感为基础的道德不再是冷冰冰的规矩或规范,道德教化也因之变得生动而鲜活。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教化就是这种情感伦理的范型。然而,纯粹主观的个人情感如何提升为道德情感是儒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孔子关注人的情感,但其情感并非个人主观的情感,他通过“心安与否”的道德诘问,将“人之为人”的理性融入情感之中。同时,孔子追从周公,找到了将个人情感转化为道德情感的重要手段——礼乐。礼乐从“直觉”上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作用于人的生命。具体说,乐能滋养人的情感,“乐合同”且“通伦理也”(《礼记·乐记》);而礼不仅“别异”、“敬人”,而且有节制、中和作用,“礼乎礼,夫礼所以致中也”(《礼记·仲尼燕居》)。梁漱溟指出,孔子思想的要旨有二:提倡孝悌和实施礼乐。在孔子那里,“孝悌——礼乐——仁”是德性成长的路径,礼乐的重要功能是涵养道德情感。从情感伦理学向度对“孝悌”“礼乐”的关系进行阐释,就能够揭示个人情感如何在礼宜乐和的文化场域中达到情理合一的奥秘。其实,礼乐不仅是涵养道德情感的载体和方法,也是社会道德教化的手段和路径。孔子在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礼乐教化模式中,把“兴于诗”放在“立于礼”之前,是因为诗教能使人“温柔敦厚”,意在强调情感是道德的基础。经过后世儒家的持续接力,道德情感作为伦理思想之主题,成为中国传统伦理“形上学”的基石,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特色。
居仁行礼、情理互融:儒家伦理思想之特质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主体,因此,儒家伦理思想之特质亦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特质。在儒家伦理思想中,道德情感是以情理合一为内容和目标的,最能代表儒家情理合一思想的是作为诸道德范畴情感之基的“敬”。《礼记》的开篇之语“毋不敬”被认为是该书的纲领和灵魂,范祖禹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朱熹释曰:“‘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南怀瑾称此语是中国文化之“定慧”,乃“礼之本”。在古代典籍中,“敬”不仅是重要的道德情感,也是立身修己之本、立国兴业之基。
“敬”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其义为严肃、肃敬、恭敬。周初文诰中多“敬”字,从历史维度看,它源于上古的“巫术礼仪”,是原始巫术活动中迷狂心理状态的分疏化、确定化和理性化。从起源上看,敬畏与忠信是祭祀仪式背后最重要的情感。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敬”是主体对客体恐惧、崇拜和敬仰的复合性心理情感,“人们因其崇高而敬,因敬其崇高而畏,即畏己之冒犯崇高也。因此,敬畏重在‘敬’”。从生成逻辑看,“敬”生于忧患。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在中国元典中多有记载。《尚书》《周易》《诗经》中都充溢着忧患意识。“敬”是伴随着忧患意识而产生的道德情感,是忧患意识笼罩下人们精神敛抑、态度恭谨的心理状态。与原始宗教中的畏惧相比,忧患意识是人类对事物产生责任感的表现,体现了人类的理性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敬”是情感与理性合一的伦理范畴,是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规约。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敬”的内涵不断被丰富和完善,从最初的“敬畏”衍变出了“恭敬”“诚敬”“居敬”等意蕴,但情理合一始终是其不变的“底色”。
传统伦理思想以情感为主题,但并不忽视或否定理性,相反,儒家所崇尚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恰恰是理性与情感的合一。今天我们要搭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脉”,就要厘清传统道德哲学“天人合一”的运思方式,掌握古代哲学以“情”为基础、情理交融的道德认知方式。其实,“融通”比“交融”能更恰切地描述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质。所谓“情理融通”是指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情与理有机结合并一以贯之的存在状态。中国传统伦理的情理融通是以“致中和”为鹄的的情理合一。
在先秦儒家那里,情理融通的境界是通过“仁”“礼”统一的思想架构实现的。作为道德情感的“仁”与作为道德理性的“礼”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论语》中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是对伦理情感“仁”的界定和赞许;《礼记》中的“礼者,理也”则表明礼是合于道德理性的规定,即用礼来规约情感就可以走向理性。“仁”与“礼”都建立在“敬”的基础之上,并以“敬”为互通的桥梁。作为伦理范畴,“敬”包含有爱敬、恭敬、肃敬、诚敬、敬畏等内涵,其中爱敬、恭敬倾向于“仁”,强调道德情感;肃敬、诚敬、敬畏倾向于“礼”,强调道德理性。如果说“仁”代表的是“人”“爱人”和“情感”,“礼”体现的是“天道”和“理性”,那么,“礼”与“仁”的统一就是“天人合一”,即情理合一。
儒家伦理兼顾“人情”与“人义”,教化人们做有情有义、合情合理之人。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礼运》)这里的“十义”是指协调人伦关系的十项道德规范。“义者,宜也。”(《礼记·中庸》)这表明,道德规范应与具体角色相连,需以“礼”之合宜性为准则,是情感与理性合一的结果。《论语》中的“三年丧”之礼就是以礼节情、情理合一的典范。
“致中和”是传统伦理思想情理融通的理想境界。传统伦理不仅重视主体心灵的情感意向活动,而且强调基于外部客观环境对主体情感进行理性的节制,使之达至“中和”,这与西方哲学的理智化、智能化的主流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爱”与“敬”是道德应有的“温度”,那么“敬”与“礼”就是道德必有的“适度”。“敬”处于“情”与“理”的过渡地带,也可以说是“情”与“理”的中介,这集中体现在《礼记·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未发”到“已发”是情感的意向活动,从“已发”到“中节”是理性的节制活动,“致中和”是经过“礼”的节制而达到的合宜、适中的情感理性状态,即道德情感状态。它符合“生生之道”,能为社会降熵增序,有助于构建“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世界。
本立而道生:当代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之建构
立足本来,珍视传统,把握特质,构筑中国伦理道德之基。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然而,在当下中国的道德建设和伦理体系构建中,存在着脱离实际、割断传统、照搬西方的现象。为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传统的意义和作用,矫正“西化”派的做法,为伦理体系建构把准方向。黑格尔将传统比喻为联系过去与现在的“神圣链子”,其实,传统并非仅仅具有“链子”功能,它还影响甚至决定着现在和未来。传统是社会的文化遗产,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已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要以“温情”和“敬意”对待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国情,以情理融通的传统伦理思想为出发点和支撑点,奠定当代伦理话语体系的基石,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吸收外来,强化理性,重视方法,补足中国伦理思想之短板。我们肯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优长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缺陷和不足。在全球化使“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孤芳自赏,更不可能置身世外。伦理学的发展亦如此,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夜郎自大,而应以开放的视野、博大的心胸,学习、吸纳和消化西方有价值的伦理思想。中西伦理学有特质之异而无优劣之分,我们要从西方伦理思想之异中,吸纳他者之长,补足自己之短。中国伦理学未来的发展应主动学习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如分析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的方法,将这些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直觉体悟相结合,遵循道德思维的逻辑结构,探索中国伦理学研究科学化、有效化的新路径。当然,也不能盲目学习、东施效颦,乃至丧失自己的优势和特质;不能以移风易俗为借口解构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色和优势。
面向未来,落实“两创”,构建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中国当代伦理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我们转换视角,多维思考。既要做到时间维度上的继承和发展,也要做到空间维度上的开放与融合。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走出传统,但我们又只能生活在传统之中,只能立足于传统才能创造现在和未来。我们既要紧跟历史潮流,又要坚持历史意识,要承继和弘扬传统伦理思想中有生命力的、能跨越时空的东西,以实现新时代伦理学体系建构的超越;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为中国当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伦理和道德支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伦理文化基础;要做好传统优秀伦理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话语体系,不仅关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而且关乎中国伦理学的未来。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上,“立足本来”无疑最为关键,因为“本立而道生”。今天,我们既要像西方那样重视理性,也要像中国先哲那样重视情感;既要让每个人拥有独特的“外在世界图景”和“内在心灵花园”,也要让每个人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这样,才能以“情”为基础,以“理”为节制,用“文明以止”的古代智慧和情理融通的伦理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话语体系,在“天理常明”中走向“圣贤之域”。我们期待着中华文明释放出绵绵不绝的上升力和崇德广世的辐射力,期待着中国伦理学摆脱“学徒”状态、提出“自我主张”时代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