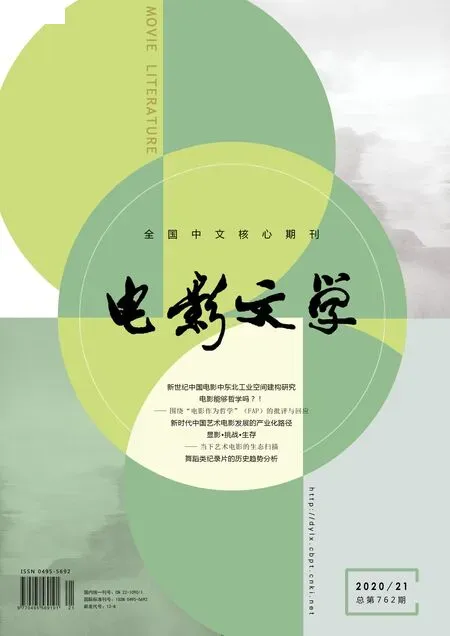革命与乡土的变奏
——以《红旗谱》及其电影改编为中心的考察
闫东方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0)
梁斌的《红旗谱》出版即广受赞誉,其中,周扬认为小说写了“老一代的革命农民向反动势力冲锋陷阵的悲壮历史”,尤为值得注意。在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三代农民群像中,周扬尤为重点地指出了小说对于老一代——朱老忠一代农民形象的书写,这与青年一代农民在保二师学潮大展身手、带领众人取得反“割头税”胜利等书写中的主体位置似乎存在某些偏差,如常明就曾在《红旗谱》的座谈会上指出过“书里写的骨干是江涛”。但是,到了电影《红旗谱》,随着叙事内容的精简,朱老忠的形象突出了。探讨小说原著和改编电影的差别,重审小说和电影对革命历史的不同塑造,反观革命如何改造乡土是本文的中心内容。
一、改编策略:取与舍
改编最为明显的变动在于,将小说第40~59节所写的保二师学潮删去,止于反“割头税”运动的胜利。不同于梁斌对小说创作有着全景式的宏大愿景,改编者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有限的电影长度内将小说的中心内容有效表达出来,这也意味着对于小说内容的再度审视。其结果,删去保二师学潮,以反“割头税”为重点,也就决定了不同人物在改编中的不同命运。主要可以分为三类:(1)农民形象序列突出了。朱老忠成为电影的绝对主角,大闹柳树林的朱老巩与朱老忠都由崔嵬扮演,反抗的性格父子相继;另外,朱老明作为拥护革命的群众代表多次出场,但是其他农民的身份差别,如贫农朱老明、雇农老套子的区分不再强调。(2)知识分子形象序列。随着保定二师学潮的删除,知识分子形象序列急剧压缩,代表不同知识分子类型的严知孝、严萍、冯登龙等都未能出场;小说重点人物江涛的相关信息也删去不少,在其青年学生和农家子弟身份之间,后者更为重要。(3)地主形象序列。以冯兰池为主,冯贵堂三兄弟改编为冯贵堂一人,小说在第8、34节对冯贵堂改良村政、调整经济结构的设想有过详细书写,但是电影中仅以冯贵堂着西服出场显示其曾上过新式学堂,定位是旧式地主阶级。
大幅改动的内容包括:(1)人物关系。主要是朱老忠与贾湘农的关系,虽然电影中沿用了运涛与贾湘农雨天相遇的情节,但是后续的重点,并非小说中贾湘农引导运涛、江涛走向革命的书写,而是多次突出贾湘农与朱老忠的直接交往。“四一二”政变之后,贾湘农鼓励朱老忠革命终将胜利,并把钱和信直接交给朱老忠,希望能对朱老忠、江涛去济南见在狱中的运涛有所帮助。朱老忠在济南看望过运涛后,也是贾湘农接收朱老忠入党,改变了原著中由江涛发展朱老忠入党的情节。(2)矛盾的激化方式。除去沿用砸钟和“割头税”两个核心矛盾,还增加了坐车过冯家大院要下车的规矩,朱老忠驾车扬长而去,宣告了复仇或曰革命的开始;此外,卖宝地一处更改为严志和卖了宝地才知道是冯兰池所买,突出冯兰池之奸诈。(3)革命方式。原作中花了不少笔墨写江涛动员反“割头税”运动,以反映革命青年逐渐进步;电影中,突出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动性,除了对朱老忠这一主要人物革命的自觉性进行阶段性提升之外,朱老明的形象也较原著更为突出,多次呼喊,正是农民自觉要求革命的表现。
整体上看,改编中删除的主要是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一支,着重突出了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革命。电影开头出现的江水拍岸空镜在朱老忠重回故乡之时再度出现,朱老巩与朱老忠形象的同一性与主体性正如戴锦华所言:“甚或在序幕中、父辈故事里,朱老忠(朱老巩)已然是历史的主体。”
二、错位:重审题材与叙事
把三卷本的《红旗谱》划定为革命历史题材是无疑的,尤其第二部《播火记》和第三部《烽烟图》对高蠡暴动和七七事变前后北方农村的书写,与第一部风貌颇为不同。凌子风曾言:“后来还想接着拍第二部《播火记》,因写得没第一部好,放弃了。”那么,第一部好在哪里?小说叙事与题材、小说原著与改编电影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错位?错位又是如何形成的?是接下来所要探讨的内容。
在小说《红旗谱》的内容提要中,不难发现颇为复杂的信息。首段以“人民的革命斗争”定位小说;第二段重点情节“反割头税运动”和“二师学潮斗争”对称出现;第三段指明的主要人物不仅包括朱老忠等农民形象,还包括江涛、张嘉庆等知识分子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对江涛这一农民出身的革命青年,突出的正是其青年革命者而非第三代农民的身份;第三段末尾单独提出知识分子群像的书写,第四段又特别指出严知孝的复杂心理。此外,第三段特别提到“作品里充满了醇厚的生活气息和浓重的地方色彩”,是对小说艺术特色的提示。不难在小说中发现这一提示,甚至这一提示的内容是随处可见的,滹沱河的景致、方言改造的小说语言、农民对于土地的珍重、捕鸟和看瓜等民俗……构成了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构成《红旗谱》叙事关键的,其实并不是所谓‘阶级斗争’主题,而是那个被作家视为辅助性的、处在第二位,但却是如此自然的‘民族形式’”。具体来说,“它包含着人物性格、人民风貌、民俗、地方风光和特定地域的语言”几个因素。也就是说,叙事上的民族形式,事实上是以乡土的自然、文化形态为基础的,但是题材却并非乡土的,而是革命历史的。此外,在乡土情调之外,华北农村的经济现状,也是梁斌的“意外”之笔。小说详细书写了冯贵堂在家族经济上的设想,为第二、三部冯贵堂从封建地主转身为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做铺垫,囊括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平原经济转型的重要信息,侧面泄露了华北农村经济的崩溃不可挽救。可以说,主观上,梁斌意欲书写的是乡土之上的“革命”,事实上,却是乡土生活(农业生活、爱情生活、经济生活)、地方色彩等使其作品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别具一格,在主题与叙事之间有着明显的错位。
对改编者来说,似乎也存在着小说主题和叙事的错位理解。较之《红旗谱》,《播火记》所呈现的矛盾显然更为复杂,反映的革命斗争更为尖锐,层面更为丰富,但是凌子风却认为《播火记》没有写好。电影对小说优秀部分——乡土情韵——的转化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如朱老忠一家在火车站的情节始终以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鼓书说唱为背景,瓜田、河景、农忙耕作、新盖房屋等情节又试图刻画朱老忠一家在故乡如何重新扎根。但是,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形成电影的独特风貌,反思其成因:一方面,尽管电影在某些镜头的处理上有破格之处,但是未能真正形成风格化的镜头语言;另一方面则是对小说主题的集中化处理,结果是影片的叙事始终以朱老忠为中心,即使在捕鸟这样以青年一代为主的情节中,也是以朱老忠的反应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在电影里,人们从形象中获得思想;在文学里,人们从思想中获得形象。”在朱老忠的形象里,革命的要义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了。或者说,这并不是改编者理解的错位,而正是由于其领会了梁斌而非《红旗谱》所要传达的主要精神,才使得电影对小说的主题做了更为集中化的解读。
对小说来说,还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从地方革命中升华出民族革命的起源。其方式是不断通过贾湘农指导来自农民行列的青年来增强党和农民革命的联系,使传统意义上的复仇行为,转换为现代意义上的阶级革命。电影中,升华的主体也变成了朱老忠,贾湘农直接肯定朱老忠阶级观点的进步,反“割头税”中,朱老忠带领众人从反冯兰池一路到税务局和县衙,作为斗争对象的私权和公权顺利衔接,宣告了革命的胜利。主题与叙事在电影中得到了统一。
三、或隐或现的乡土世界
从小说《红旗谱》到电影《红旗谱》,隐匿的不只是乡土情味,也包括乡土既有的结构与秩序。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反对冯兰池霸占河神庙前的48亩公产,事因在公不在私,他所要维护的乡土社会秩序,恰是朱老忠等革命的最终目的。问题是,在朱老忠等人的革命胜利后,旧乡土世界就彻底被摧毁了吗?对朱老忠在小说与电影中的身份和功能进行比较,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乡土权力结构的变迁,以及革命愿景中乡土秩序的存留。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基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产生“无为政治”,基于“教化权力”产生“长老统治”,“长老统治”常见于家族内部,但是也不限于家庭内部,并不是强制性的,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定性。在小说中,如果说江涛、运涛身上所携带的威信是由革命真理所赋予的话,那么,朱老忠所携带的威信更多来自乡土本有的“长老统治”。朱老忠之所以能成为“长老统治”的代表人物,与其父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在农民群体中树立的威信有关,在虎父无犬子的观念中,朱老忠正是朱老巩热心道义的继承者。此外,朱老忠从关东返回故乡,与冯兰池势不两立,并依靠双手重立家业,无疑都显示了他侠义、能干的性格。他所进行的“长老统治”最典型地表现于对朱、严两家子弟“一文一武”的出路设计,不是严志和,而是朱老忠,支持运涛多接触贾湘农,并借机参军;也是朱老忠,在严志和因经济问题想让江涛辍学的时候支持江涛继续读书。小说中,革命的火种不是由朱老忠扩散的,但是朱老忠却以最普遍的后代能够“一文一武”的期望将运涛、江涛推向了革命。
电影中,朱老忠的威信最早也来自“长老统治”。朱老忠一家返回故乡,朱老明等人来严志和家院子看望,之后,朱老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举手抬头大喊“当年大闹柳树林的朱老巩的虎子回来啦……”较小说中朱老忠看望各家的情节,朱老明的大呼更能集中展示朱老忠因主持“公道”而具有的威信。接下来的情节中,贾老师以“地主、老财背后还有军阀和帝国主义”道理启发的也是朱老忠,而非运涛,正是朴素的乡间道义与革命道义共同附着到朱老忠身上,使其带领众人反“割头税”的运动具有主持乡间公道和农民革命的双重意义。所以,后续《播火记》《烽烟图》中分田地财产、建立武装等组织行为,显然不再等同于旧有的士绅统治,侧面反映了乡间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
不过,乡土权力结构的变迁并不意味着乡土秩序的其他部分也就随之变迁。运涛还在教育江涛珍惜土地的时候,冯贵堂已经在琢磨改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并将其卖到天津,不仅参与国内市场,也参与世界市场,但这只是极为少数的大家族才能完成的转型。小说中透露出的有关土地的愿景,正反映了多数人革命的动力。然而,这并不足以支持农耕经济持续发展,乡土经济结构转型在当时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甚至在当下始终面临一定困局。另外,对春兰的书写尽管写出了妇女解放的一面,但是春兰在家等运涛同时帮运涛娘料理家庭事务显然未能变动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传统。这两方面是小说和电影都触及到,但都未能有所变动的部分。
重新考察小说《红旗谱》及其改编电影,有助于我们探究一定程度上被作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所遮蔽的乡土世界,以及革命改造乡土秩序的范围和限度,进而理解现代社会与乡土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思乡土世界中是否存在某些值得普遍焦虑的现代社会转换运用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