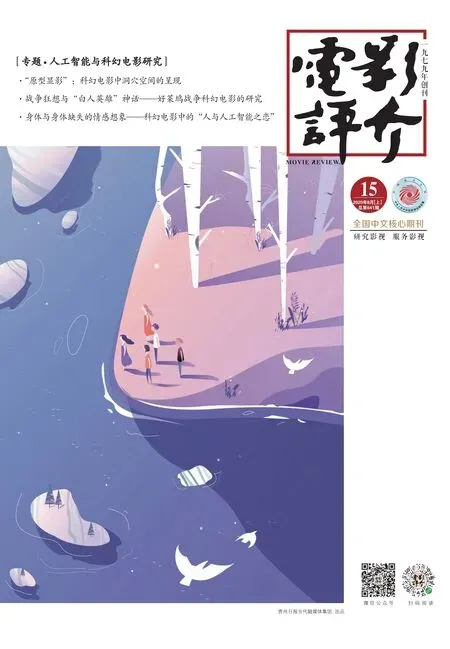消费文化与娱乐政治:中国电影市场的多方博弈(1945-1949年)
林吉安
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人们热切期望重建起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电影也深深地被卷入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当中。这种博弈既体现在商业层面的利益争夺,也触及文化和政治层面,成为管窥1945-1949年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鉴于此,本文将从电影检查、电影税收和票价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分析1945-1949年中国电影是如何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商业、媒体与观众等多方力量相互博弈下生存和发展的,从而管窥当时中国社会的某些切面。
一、存废之争:被抗议的电影检查制度
抗战胜利后,随着全国电影业的重组,国民党政府迅速恢复了对收复区电影业的管理。尽管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国民党政府自1945年10月1日起就废止了《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但要求“电影戏剧检查仍继续办理”。在这一规定下,国民党中央戏剧电影审查所很快就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并于同年10月15日宣布从次日起对收复区电影进行审查,从而正式恢复全国统一的电影检查制度。
正如有学者指出:“1945-1949年的电影检查,在制度、组织体系和检查标准方面,大体沿袭了战前和战时的一套组织系统和若干条文规定。”其中,道德风化问题是检查的重点。据资料显示,截至1947年,被禁映的影片有17部,其中国产片8部,外国片9部,“全属神奇怪诞或诲淫伤雅之旧片”。然而,随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白热化,1947年5月内政部要求电影检查处对“过分讽刺政府”的影片“依法予以严格检查”。由此,电影检查力度明显加强,且尤为注重思想意识方面。即便是古装历史题材影片,“只要其情节和对白被检查当局认为有涉时局或引人联想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亦被严格检查与删剪”。对于现实题材影片,检查则更为严厉。据统计,在1945年10月到1948年9月这3年间送审的162部国产影片中,遭到删剪的就多达48部,约占三分之一。
这种严厉的检查遭到电影界人士的激烈抨击。在1948年上海《大公报》主办的时事问题座谈会上,阳翰笙便提出中国电影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检查制度”,并控诉电影人“在剪刀下生活”的创作窘境:“我们往往有好作品,怕通不过检查,自己先就忍心剪掉。有时一个电影,什么都好……却只有一样不好,就是通不过检查官的剪刀”。为此,他强烈呼吁“检查制度要放宽”。另外,也有评论建议改革电影检查制度,放宽检查尺度,“除了有伤风化的猥亵镜头要被检去,思想上都可以比较自由”。甚至当时还有废除电影检查制度的呼声。1945年12月31日,应云卫、马彦祥、宋之的、潘孑农、沈浮、阳翰笙等戏剧电影界人士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座谈会时,就提出取消审查、演出自由等意见,并推举应云卫、马彦祥等五人起草意见书,以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
其实,人们对电影检查并非从一开始就持抵制态度。事实上,在电影勃兴之初,由于市场乱象频生,一些有识之士有感于电影的巨大社会影响力,要求政府对市场上流通的影片“严加选择,去劣留良”,并呼吁“迅订检阅取缔之章程,颁行全国,以挽薄俗”。甚至有评论指出,要想发展民族电影业,“第一急务,是设立电影审查会!”尽管当时电影人对审查也不无意见,但大多只是对审查的方式和方法不满,而并不反对审查本身。譬如,孙师毅就曾撰文指出,尽管江苏省教育会“在组织的方法上,不能令人无言;在审查的方法与态度上,则殆属刺谬百出”,但“省教育会之发起审查,在原则上,我予以同意”。可见,对电影进行必要的审查是当时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到了20世纪30年代,电影人也大多只是“要求它本身健全的合理的组织和运用”,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质疑审查的合法性。战争期间,出于抗战宣传的需要,电影审查更成为时代的必需,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那么,为何到了1945-1949年电影人对检查制度这么不满,甚至要求从根本上废除电影检查制度呢?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知识分子普遍追求自由、民主的时代氛围分不开。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新闻界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经过两个月的抗争,1945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十次常会最终通过了废止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这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文化界。由此,广大电影人也应声效仿。1946年1月,当国共两党及各民主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重庆电影戏剧界发表了《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意见书》,要求政府“废除对话剧、电影、旧剧、新剧的一切审查制度”“保障戏剧电影业的营业自由”。这种主张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所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随着政治协商会议谈判的破裂,以及国民党政府对和平建国纲领的撕毁,这种“废检”抗争以失败告终。
二、税率之辩:高额税赋下的影院抗争
抗战胜利后,尽管国民党政府曾试图进行经济恢复与重建,但成效并不理想。加之蒋介石挑起内战,军费开支巨增,导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愈加严重。为增加财政收入,国民党政府决定大幅征税。由此,包括电影在内的各行各业被迫承受沉重的税赋,使得当时社会民怨四起。
1946年1月4日,上海市政会议通过《上海市筵席税娱乐税征收规则》,规定娱乐业中除有特殊规定者外,一律按价征收30%的娱乐税,其征收范围涵盖戏剧院、电影院、音乐场、说书场、歌场、舞场、赛马场、溜冰场等一切“以营利为目的”的娱乐场所。但两周后,上海市政府为了加强保卫力量,又于1月18日开会决定在娱乐税中加征20%作为保卫团经费,使税率提高至50%。同样,成都市政府为筹集自来水公司第二期经费,也决定自1946年8月起将电影娱乐税从30%提高至40%。这种税率的大幅提升,无疑会大大增加影院的经济负担。况且,影院还需缴纳其他多种税赋,如印花税、营业税、特种营业牌照税、所得税、利得税等。在这重重税赋下,当时已涨为800元的票价,除去所交税额后,最后只剩下不到一半的钱(300多元)由影院方和制片方平分。除法定税赋外,政府还经常以摊派、募捐等名目向影院临时征收额外的税捐。如重庆市政府为了征召青年军就曾要求影院摊派二千万元,在七七纪念时又募捐一百万元。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影院的负担。
这种高额税赋和苛捐杂税,不仅远超战前的征收标准,甚至比抗战时期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1935年北平市颁布的《娱乐捐征收章程》,“娱乐捐按票价或入场费价百分之十征收。”1937年广州市电影院所需缴纳的所有税捐也才20%。即便是抗战时期,娱乐税也仅提高到30%。然而,到了和平时期,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减税以休养生息,反而大幅增加税率,这无疑会招致电影从业人员的强烈反对。
面对沉重的税收负担,各地影业纷纷发声抗议,甚至以停业示威。例如,成都市影剧业公会就对政府增加娱乐税的政策“深感不满”,甚至连“舆论界人士(也)甚望市府能体恤商艰,收回成命”。重庆市各大影院更于1946年元旦全面停业,以示抗议。然而,经过协商后,最终结果却并非降低税率,而是提高票价,将原来的350元涨至600元。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经济负担转嫁给观众,而这无疑会抑制观众的消费,进而影响到影院的营业。当时有报道指出:“看电影已成为高贵的享受,而经营电影业的人,也叫苦连天,在重税和生意冷淡下,纷纷亏累与停业。”如重庆的“升平”“一园”和“国泰”三家影院在1946年就亏损了三千多万元。其“亏累停业的原因虽是有两种:税重、生意淡,其实根源只有一个:因为税重,院方收入少,也因为税重,票价订得高,票价高,看的人就少,生意自然冷淡了。”可见,过重的税赋已给影院造成了极大负担。
在上海,这种抗议之声更是此起彼伏。1946年初,上海市政府决定加征20%的娱乐税时,广大戏剧电影界人士便发出强烈抗议,批评上海市政府违反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有关“分别减轻电影、戏剧、音乐之娱乐捐与印花税”的规定,提出“除要求将新增的百分之廿撤销外,并呼吁百分之卅依旧太高,要遵从决议,再加减轻”。同时,上海《电影周报》也发文批评这是一种“挖肉补疮的方法”“对于观众也是过重的负担”。然而,面对电影界和社会舆论的批评,上海市政府并未理会,仍旧强制执行。
在娱乐税的重压下,上海各大影院于1946年7月1日起全体罢市,以示抗议,同时向社会各界公告,要求减低税捐。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上海市政府被迫决定于同年8月1日起将娱乐税降为40%。但不久后,上海市参议会又决定从同年11月1日起恢复50%的娱乐税率。对此,娱乐界代表以“营业情形不佳”为由,数度前往参议会请求撤销原案。在据理力争下,经市府财政局和参议会财政组商议后最终决定暂时维持40%的娱乐税率。然而,即便如此,立法院在讨论修正娱乐税法时,多数立法委员仍认为40%的税率“未免过高”。最终,在同年12月4日公布的修正版娱乐税法中,明确规定“税率不得超过原价百分之廿五”,且政府“不得以其他任何名目增加附加税捐”。然而,上海市政府并未执行该项政策,仍以40%的标准征收。对此,上海市电影院业同业公会于1947年1月6日和7日在《申报》上并排刊登两则启事,提出“中央法令不容不遵,市民权利不容忽视”,并声称“减低税率事关全市民众福利”,从而试图借助中央法令的权威和社会民意的力量给上海市政府施压。最终,在电影界的抗争下,上海市政府决定从1947年2月1日起将娱乐税减低为25%。可见,在此斗争过程中,作为电影行业组织的上海电影院业同业公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民间力量的顽强抗争。
三、票价之战:通货膨胀下的政府管控
由于内战等原因,国民党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诸如提高税赋等财政手段,但仍无法填补军费这个“无底洞”,于是只好增发法币,而这又引发了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情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强制推行金圆券改革。然而,这一政策并未扭转局面,反而使形势急转直下,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在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下,电影票价也随之不断上涨。以南京的四家首轮影院为例,其票价在1946年1月初时分为200元、300元和350元三个等级,仅半个月后就分别涨至300元、375元和450元;3月11日起又涨为420元、560元和700元;4月4日起涨到800元、1000元和1200元;7月1日起又进一步涨到1200元、1400元和1800元;11月1日起更涨为1500元、1800元和2500元。也就是说,仅在1946年,南京首轮影院的票价就涨了七八倍。而随着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电影票价更是飞速上涨。即便是后来政府强制实施限价政策,也无济于事。1948年6月18日,政府将上海市首轮影院的限价座票价定为6万元,其余70%座位的票价分别为15万元、20万元和30万元三种。然而由于物价上涨过快,电影票价几乎每隔一两周就要上调一次,且涨幅不断加大。就在限价政策实施仅一周后,限价座票便从6万元涨至10万元。随后又从7月2日起再次上调,将限价座票涨为20万元,其余座位则分别涨至30万、40万、50万和60万元。仅半个月后,上海电影院业同业公会又决定自7月17日起将各级票价一律增加九成,最低限价票也从20万元涨至40万元。像“大光明”“国泰”“大华”“美琪”等首轮影院,则将最低限价票提高至45万元,其他座位则按时段和影片质量进行单独定价,其中日场分70万元、100万元和120万元三种,夜场分90万元、120万元和160万元三种。如果是质量较好的新片,票价则高达200万元。可见,此时电影票价已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一般而言,电影票价理应按照市场规律,由影院根据市场的供需情况进行自主定价,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受到来自政府、影院、片商乃至观众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影响和制约。其中,从片商的角度来说,中西片商当然“希望票价最好能节节提高”,因此他们“对于票价的调整尤其积极主张”。但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则希望票价越便宜越好,因而普遍反对涨价。对于影院而言,他们一方面当然希望适当提高票价,以保证影院经营,但另一方面又不愿因票价过高而抑制观众消费,因而倾向于在片商和观众之间寻求平衡。例如1948年8月17日,当片商要求将票价提高90%时,影院因“顾虑观众购买力”,最后决定西片影院上涨70%,国片影院上涨20%。
除了市场因素外,这一时期政府在电影票价的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电影“实负宣扬文化,普及教育的两重任务”,因此为了满足人们的观影需求,国民党政府对电影票价实施严格管控。然而,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无论是影院还是片商均有强烈的涨价诉求,因此它们往往联手向政府施压。譬如1948年5月,电影院业同业公会以职工薪金、电费、广告费、外汇等各项费用激增为由,要求将电影票价提高55%,但社会局最终只准许增加20%。西片片商则在多次要求上调票价而未果后,最终决定停止供给新片,以示抗议。同时还与影院公会共同派出10余名代表向上海市社会局请愿,要求将限价座的数量从30%降为15%,或者是提高限价票价格。但这一诉求遭到时任社会局局长吴开先的拒绝,其理由是“设限价座之目的,在使经济能力稍差者,亦有看电影之机会,如将限价座减少或将限价票价格提高,则失去设限价座之本意。”为保障这种限价政策的实行,上海市社会局、警察局和电影院业同业公会还共同派员到各大影院核查座位数目,划定限价座位区域,绘图呈报并将限价座位表张贴在各影院门前。同时,为了打击黄牛党抢买限价票,或是与影院卖票人员勾结等不良现象,政府还规定“限价席票不准预售,购票后即须入座”,并对擅自减少限价座位或提高票价的行为予以惩罚。然而,仅仅半年后,由于金融改革失败,物价彻底失控,这种限价政策于1948年12月底正式取消。
由此可见,当时的电影票价是在市场力量(影院、片商和观众)与政府力量(社会局、警察局)相互博弈下的结果。正是在这种多方博弈尤其是政府的强力管控下,电影票价变得相对便宜。尽管从面值上看数目很大,“但较之战前增加之倍数,则远不如其他物价之高也”。与其他文化娱乐消费相比,看电影已是相当的经济实惠。如1947年,电影票价仅是京剧票价的15.6%,舞场票价的42%。而到了1948年,电影票价变得更便宜,甚至“几支纸烟,也足抵得上四流电影院中的票价了”。这种相对低廉的票价对扩大观影群体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1945-1949年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
结语
电影从来就不只是纯粹的艺术,也不仅仅关乎商业和娱乐,而是与社会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电影场域”的核心力量之一,电影放映既要受到制片和发行的影响,也要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制约,如社会环境、政府、观众和媒体等。这些力量背后均有着不同的话语和诉求。大体而言,影响电影放映的话语主要有商业话语、大众话语、精英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
对于1945-1949年的中国电影而言,电影被深深地卷入到官方与民间、政治与商业、媒体与观众等多方力量的相互博弈当中。尽管电影人的力量微薄,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抗衡,但他们依旧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懈抗争,从而在多方力量相互博弈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虽然当时中国社会整体呈现出“国家权力上升,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式微”的发展趋势,但电影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大众文化依然展示出蓬勃的生机,并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社会开拓了一片重要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