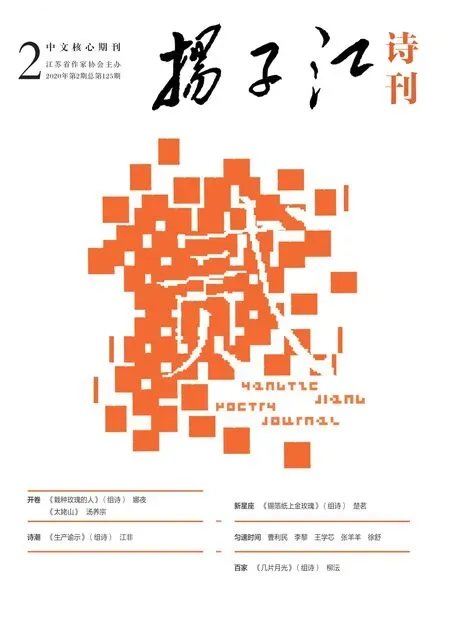局外人(外二首)
2020-11-12 04:49量山
扬子江诗刊 2020年2期
量山
她被小叔叫去后,表情更淡漠了。
我想起我们关于加缪的谈话。
瞧,妈妈在叫我了。
她穿着红色睡衣,和我外婆
完全一样,先后被剥夺读书的权利。
外婆的葬礼上,她没有哭
她觉得葬下的还会继续。
我们继续各讲各的故事,
火车开往不同的方向。
像诗,有不同的地域性和时代背景。
甚至来不及有交集,
杯沿上啤酒的泡沫不断地上升——
我坐在田埂边的石磙上看流云,
和石磙没有多大关系。
不像大海——给Z和M
当李叔同《送别》的歌声响起
三个人陷入不同的回忆
在瓦库
像是高速途中短暂的停顿、相交
怀旧,但不可能逆行,而前方的未知
埋伏着无常
是的,我们不像大海,像小溪
随时面对断流的危险
他大病初愈。麻醉药和手术刀
让脊椎不介意里面的钉子
迫使物化的生活正常化
她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怪人,把自己藏在
大海潮涨潮落的泡沫中
她不断地冲洗自己,重新获得完美
我感到冷冽
十八岁的夏天,我们绕过墓地
提前来到麦苗中间
多少年过去了,他们一茬茬倒下
香气仍在持续
在水利博物馆
我从水利博物馆往回走,
心中有一头铁牛镇守。
巴赫曼正在给策兰写信,信纸上,
有一辆水车经过多瑙河。
她的话语缠住了我,楼下的橘树,
果实低垂。早晨的光线里
火车的体内快递了一道闪电。
云层和涵洞包裹住它,
短暂的黑暗后,车窗上
重新镶嵌高山峻岭。
在水利博物馆,
我经过一条又一条的河流。
像一块铁,锈迹斑斑
仍竭力咬合着齿轮的中心。
猜你喜欢
今日农业(2022年1期)2022-06-01
作文周刊·小学一年级版(2022年20期)2022-05-07
建材发展导向(2021年19期)2021-12-06
意林·少年版(2020年16期)2020-08-31
新作文·小学低年级版(2020年6期)2020-07-09
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9年9期)2019-11-10
人民黄河(2019年6期)2019-09-10
特别文摘(2019年12期)2019-07-19
动漫界·幼教365(中班)(2019年1期)2019-06-11
创新作文·初中版(2014年2期)2014-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