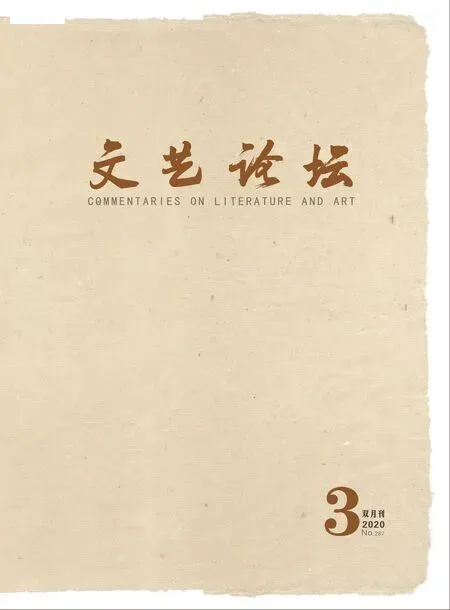历史、存在与人性
——论郑小琼见证叙事的意义
◎ 罗小凤
自2007 年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以来,诗歌界、媒体界、学术界对郑小琼的关注与研究便不绝如缕,这些评论与研究对郑小琼其人其诗进行了各种阐释与挖掘。然而,对于郑小琼自己反复强调的“见证”,众多的评论与研究文章却论之不多,即使偶有提及,亦只是蜻蜓点水式地一笔带过。事实上,郑小琼认为文字都是软弱无力的,无法介入任何问题发挥实际作用,但可以作为见证,记录一代人的生活与情绪。因此,郑小琼心怀自觉而强烈的见证意识,以个人的经历、体验与书写对历史、时代进行见证,而且她的诗歌诉求不仅仅是见证,她是在此基点上对人的存在、人性都进行深入思考,使其诗不仅仅停留于“见证”层面,而承载着更深广的诗歌意义与美学价值。
一、见证意识
郑小琼大力倡导“见证意识”,在她看来,文字并不能改变现实,但可以“见证”现实,见证时代:“很多时候,文字对现实来说是无能的,也是脆弱的。但至少,我认真地记录了我周围人群的感受,他们的幸福与不幸,虽然无力改变,但是作为见证者,我们需要认真地记录与思考。”因此她曾反复强调诗歌的“见证”作用:“一个没有勇气见证现实世界中的真相的写作者,肯定无法把握活在这种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内心。文学是因为人而存在,它应该关注人的丰富性,而‘见证’意识正说明了写作者在贴近了人,贴近真实的人,而不是虚构的人,想像的人。”在她看来,是否具有见证意识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重要素质,因此她“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可见,郑小琼具有极其自觉的见证意识,不强调“介入”,而强调“见证”。所谓“见证”,原本是一个法律术语,是惯常法律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其作用是为既有的事实信息进行核对,并提供公众都看得见的公开凭证。郑小琼在诗中自觉为时代作证,见证了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时代过渡转型过程中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经历、经验和精神状貌。
见证者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担任,其基本条件必须是亲历者。郑小琼显然拥有做“见证者”的资格,她自己便是打工生活的亲历者,她对打工生活的各种悲惨遭际、景况、感受、情绪和心路历程都非常熟悉。郑小琼2001 年从卫校中专毕业后曾在重庆一家诊所做过短期的护士,不久便转去广东汇入打工行列,曾在鞋厂、家具厂、毛织厂、玩具厂等工厂待过,后来进入东莞黄麻岭一个五金厂工作四五年,她在这家工厂的编号是245,她的工作是每天重复着从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最多的一天曾打过一万三千多个孔。在打工生涯中,毫无疑问,郑小琼亲身经历过打工者的辛酸血泪生活,黑工厂、流水线、出租屋、暂住证、欠薪、失业、饥饿、孤独、断指等各种打工经历、经验她都有过,她将这些经历和经验都写进诗歌。亲历者的身份角色可以让她更接近她所要见证的本相,郑小琼对此体验特别深刻:“作为一个亲历者比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会更真实,机器砸在自己的手中与砸在别人的手中感觉是不一样的,自己在煤矿底层与作家们在井上想象是不一样的,前者会更疼痛一点,感觉会深刻得多。”郑小琼亲身经历了机器砸在自己手中的感觉,亲身体验了打工生活带给她肉体和精神上的多重疼痛。因此她的许多诗都呈现了她打工生活带给她的各种疼痛、耻辱,如:“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还忍耐的孤独与疼痛”(《生活》),“我置身的,是广泛的失声的人群/是沉默中的疼痛与愤怒/ 是暴虐的石头与铁,是文字/是秋天,是思想改造或者/肉体毁灭,是军队或者坦克/是纸上的失眠,是罚款与暴力/是贫穷与职业病……我们的人生正被时代删改或者虚构/我不敢说出,只能隐匿人海”(《耻辱》),“却无法改变/时代对他们无声的冷漠与嘲讽”(《在电子厂》)。见证苦难,不仅仅是为了让苦难不再发生在见证人自己身上,更是为了让苦难引起大家关注,寻求解决的办法,从而不再发生在任何其他人身上。这是见证者的使命意识,郑小琼正是肩承这种使命意识坚持她的诗歌书写向度。她一直心怀做见证者的角色和使命,她为了保持见证者的身份角色,当东莞作家协会及多家媒体向她伸出“橄榄枝”时,她都一一婉拒,因为她不愿意脱离流水线,脱离对打工现场的敏感,脱离做见证者的资格,她“需要保持这种在场感,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没了疼痛感,诗歌就没了灵魂。”这是一种见证者自觉的角色意识。她曾花了大量时间去做女工的调查,深入女工中间做调查达六年多时间,其间她走过很多乡村,访谈过很多人,她有意识地租房子在打工者聚居的城中村,尽管那里复杂、脏乱,她为了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为了近距离接触打工者的生活,她就居住在她们旁边,做她们生活的见证者,以获得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正如她自己所陈述的:“我有意识租住在混乱的城中村,每天都会碰到抢劫的、卖淫的、嫖娼的、做小贩的、补鞋的、收购废品的、做建筑工的、失业的、偷盗的、贩毒的……各种各样的人出没在我的周围,我也出没在他们其中”,正因为如此,她“目睹被拐骗的女工如何变成娼妓,目睹一些男工变为吸毒者,沦落为抢劫犯”,甚至目睹女工被吸毒者谋杀。正因为她是这些女工中的一员,她才能见证“真实的”生存状态。2008 年,郑小琼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失业,她利用这段时间去江西、河南、重庆等地调查,她去过很多村庄,见过很多女工,认真倾听她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人生及她们未来的打算,随后便有了《女工记》这部见证一代女工打工生活遭际与命运的诗集。可以说,郑小琼一直在以见证者的角色和使命意识目睹、经历并用文字见证底层打工者的沧桑生活,对于打工者们所经历的苦难、受伤、失业、残疾、堕落、欠薪、耻辱,她在诗中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展示和见证,如“他拇指的伤口/无法虚拟机器时代的命运,他被动地融入/机器中,成为某颗紧固的螺钉”(《木棉》)、“她们在异乡出卖肉体”(《周红》)、“我们已经被降解得面目全非”“我们只有视而不见才能避免痛苦”(《竹青》)、“时代逐渐成为/盲人十四岁小女孩要跟我们/在流水线上领引时代带来的疲惫”(《凉山童工》)。郑小琼用诗歌见证了工业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民由乡村进入到工业时代的基本生活面貌和情绪感受,“为我们时代的变迁保留一种内心的见证”。即使后来她进了广东作家协会《作品》杂志,及至她做到《作品》杂志副主编,她依然未曾放弃做见证者的身份和角色。
特伦斯·德普雷曾指出:“作见证不只是人的语言行为,更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显然,见证已成为郑小琼的一种存在方式。
二、以个人的方式想象历史
然而,如果郑小琼见证叙事的意义仅仅在于“见证”、记录和呈现,那就跟以前的伤痕书写、苦难书写区别不大,毫无突破之处了。在郑小琼之前,已有许多诗人在写打工生活,如许强、刘大程、罗德远、谢湘南等;在她之后,则有更多人跟风大批量地写打工诗歌,他们的书写都带有“见证”作用,但最有影响的为什么是郑小琼?其重要原因便在于她的作品决不仅仅在于“见证”打工生活的生存境遇和命运,而是在呈现这些个人生活遭际的同时,她其实都在以个人的方式想象历史,见证历史与时代。她一直在超出时代与年龄地思考历史、时代、国家与存在,这正符合陈超在上世纪90 年代中期提出的“历史想象力”的概念,陈超后来呼吁新世纪诗歌要有“历史想象力”,这种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对生存、个体生命、文化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深度的理解和自觉挖掘意识,能够将诗性幻想和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地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郑小琼将真切的个人生活与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同步展示,将历史和时代的重大命题揉入打工生存经验的呈现之中,在个人的细节经验中隐藏着历史品质,她在加班、职业病和莫名的忧伤里“摊开一个时代的幸与不幸”(《钉》),让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相融合,让个人化的形式技艺与生存关怀、人文关怀彼此激活,形成其诗歌对历史的想象力。
郑小琼构建了一套独属于自己的诗歌话语,形成了自己的主题向度和隐语世界,她在许多诗歌中都频繁使用“祖国”“国家”“人民”“百姓”“山河”“历史”“真理”“万物”“时代”“世界”“人生”等与历史、时代相关的宏大词汇,而与这些宏大词汇相关的,是郑小琼在她的诗中几乎摊开了时代的所有不幸,如乞丐、蛆虫、蚊蝇、妓女、尸首和性病,她所呈现的世界是肮脏、腐败、腥臭,布满孤独或饥饿、悲伤或悒郁、痛苦或惶惑、贫穷或困苦的“悲惨世界”,如《人行天桥》中郑小琼捕捉住“人行天桥”这个场景作为时代展览的舞台,这里展览了工业时代和市场经济下各阶层形形色色的本相:算命的、传销的、办假证的、走私的、吸毒的、卖假药的,扒手、贪污犯、二奶、桑拿女、娼妓,三角债、失业率、性病,红头文件、法院通告、刑事案件,她将膨胀异化的欲望、无处不在的暴力、善与恶的冲撞、人性的挣扎都通过“人行天桥”呈现出来,呈现了她“对社会现实、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及对现代都市文明及生命的困惑、混乱和颓败的挖掘”。谢有顺曾分析道:“她的写作意义也由此而来——她对一种工业制度的反思、对一种匿名生活的见证,带着深切的、活生生的个人感受,同时,她把这种反思、见证放在了一个广阔的现实语境里来辨析;她那些强悍的个人感受,接通的是时代那根粗大的神经。她的写作不再是表达一己之私,而是成了了解这个时代无名者生活状况的重要证据;她所要抗辩的,也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一种更隐蔽的生活强权。”此言显然抓住了郑小琼诗歌写作的真脉。
见证时代就是见证历史,历史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旦过去则成为历史,但每个人对于“历史”都只是想象,历史无法重来,每一种叙述都是一种“说故事”的方式在言说历史。郑小琼的诗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的历史进行叙述和言说。诗歌的“见证”其实是一种想象,对于时代、历史的一种想象,以她的视角、角度进行的想象。历史是无法介入的,每个人对于历史的描述都是对于历史的想象,历史一直都在进行之中,而郑小琼善于在诗中将巨大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社会现实内容置放在个人体验、个体化表达中,由此展开她对个人、社会、历史的思考。张清华认为:“她的词语不只深及生命与个体的处境,同时也插进了时代的肋骨”,陈劲松则将郑小琼比作“时代的镜子”,都充分肯定了郑小琼的历史把握能力和历史想象力。
可见,郑小琼的诗都不是小情绪、小感伤,而是如海上曾指出的:“郑小琼的大情绪是一般女性所装容不了的,她为当代民生、民意、民权在独立思考在独立分析,在独立地去接受生命赋予的苦难。”郑小琼的可贵不仅在于揭示出全球化背景下后工业时代的底层打工者生存样态,而且“她以自己的经验和感受,验证其切入时代与社会背景下的疼痛感与正义感。从她的写作里,我们能看到一种对现实的质疑,对存在主义精神的探寻,这是不易的。”郑小琼善于将个体遭际与生存经验放置在广阔的时代语境中,既呈现出个体生命最幽微的体验,又呈现出历史的症候。对于郑小琼而言,历史是诗歌的背景和素材,她将经历、存在和痛苦深刻地切入到最基本的历史境遇中去,她通过诗歌对历史产生思考和认知,历史性与个人性互相耦合,审美想象与历史真实完美融合。正如江腊生曾指出的:“郑小琼的诗歌创作不仅仅记录下一个中国特色时代的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心路历程,更重要的是其中青春的激情流淌与存在的理性思考。其中,不仅有个人身体、物质层面的书写,也有国家政治、历史层面的呈现。郑小琼的诗歌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工业化进程中,打工者生存的空间与心灵世界,又扩大到社会政治与历史层面,承载了传统诗歌的忧患与责任意识,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个体情绪与思考。”
郑小琼还在自己的诗歌中创造了自己的一套隐喻话语。许多评论家注意到的是“铁”“风”“流水线”等,笔者注意到的是“她”。郑小琼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符号:“她”,在郑小琼的诗里,这个人称符号不是泛指,不单纯是人称的指代作用,而既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也是一个具有足够承载力的“历史符号”,象征着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过程中一支未被注意到的独特力量。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几千年历史中,没有其他任何年代的农村女性如这个时代这般大批量走出家门涌入城市,她们构成打工队伍的主力军,是各个工厂的主要劳动力,成为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农业时代,男人是主力军;在工业时代初期,男人同样是主力军;但工业时代进行到一定进程后,工业发展方向由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工种由需要男人作为体力活主力的重活转向偏“轻”偏“细”的工种,因此更需要“女工”,需要“她”而非“他”,在许多城市,年轻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找工作,因为轻工业的工种需要的是大批女性,因此成千上万的“她”涌入工厂。在此情境下,郑小琼在其诗歌中创造一个“她”的系列,其意义自然是不言自喻的。这是一个女性长廊,《女工记》的诗歌中就有91 个“她”,这道女性风景线是当代诗歌场域中不能不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在特殊年代的诗歌中,“我”都不是我,而是人民、民族的代言人,是集体化的无限放大的大我。郑小琼诗中的“她”,不是小我,也不是大我,而是“她”,一个个具体的她,一个个作为人存在的她。郑小琼试图通过“她”的人物群像展览,呈露出她们所遭受的苦难,从而引发关注,改变处境,如“她日子平淡而艰辛,她要习惯/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卡钟与疲倦/在运载的机器裁剪出单瘦的生活/用汉语记录她臃肿的内心与愤怒/更多时候,她站在某个五金厂的窗口/背对着辽阔的祖国,昏暗而混浊的路灯/用一台机器收藏了她内心的孤独”(《剧》),这个“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女工的缩影,是郑小琼的一个创造,是诗歌史长廊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特写,是一个时代的隐喻,背负着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广阔含义。
可见,郑小琼一直在自觉地将自己的叙述话语织入一张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谱系中。难怪张清华认为从郑小琼的诗中读到了现在所处时代的“所有秘密”,“我说从郑小琼的诗歌中读到了这个时代,确乎不是夸张。”
三、不只是“见证”
郑小琼自己强调其诗歌的“见证”意义,但如果只是停留于见证,即使是见证历史,其影响力依然是有限的。其实,她的诗歌已经不知不觉地超越了见证,而试图抓住时代的病根,挖掘人性。郑小琼的诗不仅仅见证苦痛、伤害,由此见证历史,还在此同时呈现了她对存在与人性的思考,这是其见证诗歌的重要内涵与意义。见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见证者说出个人的苦难,更在于站在人类普遍的立场上,思考人的存在,见证其中呈现出的人性,见证被苦难扭曲的人性。
郑小琼非常可贵的是,她在其诗歌中提出了“她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这是一种哲学维度、终极层面的思考。“名字”是郑小琼用诗歌构建的一个表征人作为存在个体的重要符码。在她看来,“一个名字背后,意味着一个人的尊严、责任、权利”,她看到现实中“很多人无法享受到法律赋予她们的权利,她们的利益不断地被损害,正是她们的故事让我感到我们更需要尊重个体的权利与利益,不要用庞大而虚无的集体或者国情来搪塞个体应有的权利与利益,捍卫每个个体的尊严与利益,就是捍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利益”。“我在流水线上做过许多年,深深了解在流水线上叫一个工友的名字,而不是叫她从事的工序名称所带给她内心的感受。叫我的名字我感到的是温暖,人性的尊严,而用工序名称替代我的名字,我感受到的是冷漠与隔膜。名字饱含了一个真实的人的体温与感受。”其实,这是对人作为存在的一种思考。郑小琼感触最深的是流水线上的女工们都被隐匿掉了名字,她们都被以工号、工种或地域重新命名,都成为一个个符号,而不再是她们自己,郑小琼觉得名字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与尊严,名字的失去是对她们作为人的存在的遮蔽,对此,她自己深有感触,她在五金厂工作时,被人称呼代号245,或工种“装边制的”,这让她感觉到自我的丧失和存在感的缺席:“在人群中,我感觉我正在消失,我变成一群人,在拥挤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挤成了一个失踪者,在人群中丧失了自己,隐匿了自己。”因此,郑小琼试图将流水线上被简化成地域、工种、工号、工位的女工还原成她们的真实身份,还原她们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她“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掏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她们的柴米油盐、喜乐哀伤、悲欢离合……她们是独立的个体,有着一个个具体名字,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在她心中,“在她们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她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与她之间,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命运”。女工虽然渺小卑微,但也是作为人的存在个体,可是工业文明却抹灭了女工及其他打工者作为存在个体的存在性,这是最不公平的地方,因此,郑小琼努力“深入到女工中,把这个‘们’换作她,一个有姓名的个体,只有深入到她们中,才会感受到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和她们的个人经历”。郑小琼在诗中关注人作为存在个体的普遍意义与境遇。她关注的是打工者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如何实现,是对普遍人性和存在境遇的探索。加缪曾指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最迫切的问题”,人不能没有意义地存在,但意义却始终不在人的掌握之中。因此,“人不能不面对非理性。人的内心向往幸福,向往理性。在人的(内心)需要和这世界非理性沉默之间发生了冲突,于是荒诞便诞生了。”郑小琼在诗中直指这个问题。打工者不能没有意义地存在,但他们无法自己掌握自身作为存在的意义,因此需要有见证者将他们无法作为“人”存在的境遇呈露出来。《女工记》中有91 首诗是直接用女工的名字命名,如田建英、黄华、竹青、谢庆芳、刘美丽、兰爱群、李娟、熊曼、伍春兰、阿蓉等。《黑暗》一诗中,郑小琼对“存在”“生命”“世界”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进行思考,触及对人类普遍的生存本质的认识。
而在思考人的存在的同时,郑小琼呈现了她对人性的思考。人的存在与人性息息相关,由于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特征,因而也是“人”是否存在的基本条件。徐贲曾指出:“灾难见证承载的是一种被苦难和死亡所扭曲的人性”,“见证文学所呈现的是邪恶的灾难和被苦难和死亡扭曲的、绝境中的人性”,希望“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灾难邪恶的希望和信心”,其实,任何见证文字背后所承载的都是在苦难中被扭曲或被保留、挽救的人性,见证文字的意义在于通过他人的阅读和联系找寻共同抵抗苦难的希望和信息。郑小琼的见证意义便在于此,她通过叙写打工者、女工们悲惨的生活遭遇和命运,其实是为了有人关注他们,有人能够在知道这些苦难之后如犹太哲学家费根海姆(E.Fackenheim)提出的“修补世界”。这就是见证文学的终极意义。遭受苦难的不是某一个打工者,而是一拨人,一代人,这些人身上呈现的全人类的共同人性。郑小琼看到了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对人性的抹杀,她在诗中对此进行了呈现与思考。《女工记》中最令人痛心的是《黄华》,断臂的女工黄华对自己的伤残没有半点悲伤,反而平静得“让我有些不适应”,“我深知律法与赔偿/你却用人情与良心来回答‘老板是好人/出了全部医药费还赔了四万块钱’/‘是我自己不小心不能怪老板’你陷入/深深的自责反复地唠叨/仿佛某部影片中犯错误的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工/庆幸断的是左臂庆幸断的是自己/——一个女人的手臂如果是男人的——/自己丈夫的手臂将变得更难些”,这诗中所呈现的人性内涵极其复杂。女工不知道用《劳动法》保护自己,却相信了老板的伪善,庆幸四万块钱的赔偿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庆幸断手臂的不是丈夫。郑小琼对她无疑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女工们对自身命运无法掌控,无法用法律保护自己,而在四万块钱的赔偿面前满足甚至感到愧疚,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女工记》中另外两个女童工的经历与心理更是让人扼腕叹息,“有时她黝黑的脸/会对她的同伴露出鄙视的神色/她指着另一个比她更瘦弱的女孩说/‘她比我还小夜里要陪男人睡觉’”(《凉山童工》)。女童工对自己同伴的鄙视和对自身命运的无知,呈现出城市文明对青少年的毒害与侵蚀,更显示出人性的泯灭,正如郑小琼在诗中感叹的“为什么仅有的点点同情/也被流水线的机器碾碎”,碾碎的不仅仅是同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是人性。郑小琼颇为敏锐地挖掘了这一人性的缺口,同是女工,同是弱者,同处于被碾压的境地,但她们却彼此嘲笑、鄙视、挖苦,对自身处境与命运没有任何意识,更别说反抗,呈露出她们作为“人”的尊严的丧失殆尽,于她们而言,尊严已经是一个极其奢侈的词语,人性则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人行天桥》亦暴露出城市文明对人性的抹灭:“人行天桥上三个来自江西的少女在等待有人收购她们的初夜权”“三个下岗女工唱起了‘下岗女工流汗不流泪’,不卑不亢走进夜总会,陪着局长市长睡。”在郑小琼笔下,城市就是一个人性缺失的荒原,郑小琼以诗对人性进行了深刻思考,明显超越了“见证”层面。
可见,郑小琼的诗是她作为个体与历史、时代相遇的碰撞,是她对个体存在、历史、时代境遇和人性深入思考的结果。正如《2008 年庄重文文学奖授奖词》中评价郑小琼:“她的诗与散文,既是对声音微弱的无名生活的艰难指认,也是对自我、世界和工业制度的深刻反省。她通过对自身经验的忠直剖析,有力地表达了这个时代宽阔、复杂的经验,承担生活的苦,披陈正直的良心。她痛彻心肺的书写,对漂泊无依的灵魂深怀悲悯,她的作品因而具有让失语者发声、让无力者前行的庄严力量”,惟愿她继续超越“见证”层面的呈现与指认,创作出更多具有“让失语者发声、让无力者前行”的灵魂震撼之作。
注释:
①⑲小哑、郑小琼:《中国女工:一种更为现实的现实》,《法治周末》2012 年3 月6 日。
②何言宏、郑小琼:《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山花》2011 年第14 期。
③郑小琼: 《疼痛着飞翔:打工妹问鼎“人民文学奖”》,《劳动保障世界》2007 年第10 期。
④郑小琼:《写诗与打工一点也不矛盾》,《深圳特区报》2007 年6 月21 日。
⑤郑小琼于2007 年在人民文学奖领奖台上的发言,转引自:《打工妹爱写诗获人民文学奖》,《南方周末》2007 年6 月7 日。
⑥⑦⑳㉑㉒郑小琼:《女工记·后记》,花城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9 页、第250 页、第254 页、第254-255 页、第253 页。
⑧金莹:《郑小琼:<女工记>,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文学报》2013 年5 月16 日。
⑨Terrence Des Pres,The Survivor:An Anatomy of Life on the Death Camp,NewYork:Pocket Books,1977,P.32.
⑩陈超:《诗的想象力及其他》,《山花》1996 年第5期。
⑪杨清发:《历史与现实间现代精神的见证——读梁平的长诗<重庆书>》,《南方文坛》2007 年第2 期。
⑫谢有顺:《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南方文坛》2007 年第4 期。
⑬⑱张清华:《词语的黑暗抑或时代的铁——关于郑小琼的诗集<纯种植物>》,选自《纯种植物·代序》,花城出版社2011 年版。
⑭陈劲松:《工业时代的恶之花——郑小琼诗歌的现实意义及其精神内蕴》,《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2011年第2 期。
⑮海上语,《郑小琼诗选·封底语》,选自《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2008 年版。
⑯刘波: 《“80 后”文学的另一片风景——评郑小琼》,《新作文》2011 年第4 期。
⑰江腊生:《底层见证与超越——郑小琼诗歌的整体观照》,《创作与评论》2012 年第4 期。
㉓Albert Camus,The Myth of Sisyphus,New York:Random House,1955.P4.
㉔徐贲:《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文艺理论研究》2008 年第2 期。
㉕Emil Fackenhaim,To Mend the World :Foundations of Future Jewish Thought.NewYork:Schochen Books,1982.
㉖郑小琼获得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时的获奖评语,见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10-26/784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