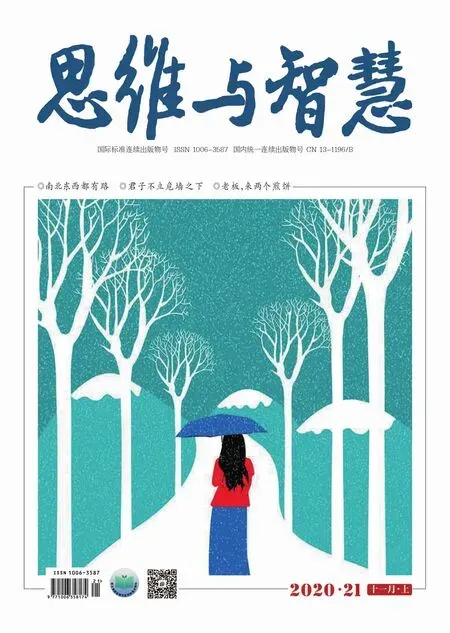半条腿的母亲
● 高云红

小学三年级的春天,山上的杜鹃花开得正艳,小草也刚刚冒出嫩芽。我坐在教室里,大哥向老师请假把我带回家,路上大哥告诉我,母亲出事了。懵懂的我不知道“出事”二字的意思,回到家不见母亲,她穿的薄棉裤带着血渍晾在栅栏上。
第二天,我们兄妹四人被父亲厂部的解放车拉到30公里以外的镇医院。很多人拥挤在医院的走廊里,不知谁说了句,“孩子来了。”堵在走廊的人们自发让出一条道,目光像舞台的聚光灯投向我们,还听到有人窃窃私语:“孩子这样小,真可怜!”
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是来给母亲献血的,因为母亲血型比较特殊,当时的小医院不具备存储血液的条件,父亲的厂部去了很多人等待验血,抽血。
进了病房,母亲躺在那里,见了我们,嘴唇哆嗦成一团,泪水无声地流下来,枕巾湿了一片……我们兄妹老老实实把后背贴在墙上,木然地看着母亲,不知该安慰她还是陪她一起流泪。
这时进来两个男大夫,其中一个询问母亲术后的一些情况并掀开她身上的被子,我看到母亲左腿仅剩的残肢染红了缠在上面的白纱布,那红色在雪白床单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心上,每次回忆仍在流着血……
母亲遭遇了车祸,保住了命,却失去了一条腿,她左腿膝盖以上截去了三分之二。母亲说出事的时候,她是清醒的,被汽车撞击拖碾后她爬起坐在地上,为了防止出更多的血,她把受伤的腿拧成麻花样。母亲讲自己经历的时候,不曾流泪,把天塌地陷说得云淡风轻。
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半年后母亲戴上了假肢。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假肢有十几斤的重量,而且行走的时候都是伸直的,只有坐下的时候,搬动膝盖处的卡环才得以弯曲。
母亲开始不习惯,戴上假肢也要拄着双拐,慢慢母亲试着扔掉双拐,虽然走路很慢,但半个月后她逐渐适应。并不停地忙碌,好像弥补她曾失去的光阴。
每天放学回家,桌子上的饭菜冒着热气,夜晚我们写作业,母亲陪在一边织毛衣,或纳鞋底,只有睡觉的时候,母亲才摘下十几斤重的假肢。假肢把母亲的腿磨出很多血泡,她用做活的针,在蜡烛的火上烧一下,挑破血泡。母亲说,等磨出茧子就不疼了。
一夜终究无法让破损的皮肉愈合,第二天母亲照旧戴上假肢,走路缓慢而且一顿一顿的,那该是一种怎样的钻心之痛?母亲从未抱怨生活赐给她的苦难,反而倔强地走在疼痛的路上。
一茬接一茬的血泡历练着刚强的母亲,我们心疼母亲,劝她皮肤痊愈了再戴假肢。母亲却说,这个过程必须经历,如果闯不过去就只能拄拐或坐轮椅。
母亲想出各种方法,用软布把残肢缠住,软布不能打褶还要紧实,因为她经常活动,软布很快就松懈,试了几天,母亲觉得浪费时间而且麻烦。放弃了软布,母亲又在假肢腔体边缘涂一些爽身粉,还是因为母亲活动量大,汗水让爽身粉很快失去功效。最后母亲放弃一切,用皮肉对抗着身体的另一半,接受着假肢带给她一次次的磨炼,她没有服输,终于母亲的腿生出了老茧。
母亲右脚踝总是肿的,像半个馒头大小,从清晨睁开眼她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她从未把自己当成残缺的人,相反她比健全的人更出色。母亲不仅照顾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还养猪喂鸡,侍弄菜园子。假肢已然成为她最贴心的朋友,没有它,母亲已寸步难行了。
临近春节,母亲用一只脚蹬着缝纫机,一忙就是半夜,我们兄妹每人一身新衣服,都在年三十穿在身上。
时间在母亲的忙碌中流进我们的身体,我们脚上的尺码逐渐加大加宽,母亲脸上的皱纹也加长加深……
母亲七十五岁那年,她觉得走不动了,说自己真的老了。但每天仍坚持拖着十几斤的假肢下楼去走一走,和邻居打牌聊天。
如今母亲七十八岁了,躺在床上,她再也不用负重前行了。可是假肢,已然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即使不再戴了,也放在自己身边。它和母亲一样,都累了,都想歇歇了。可是我们知道,母亲不再奔走,母爱却停不下来。她换了一种方式,比如不厌其烦的叮咛,不管你在哪儿,都会穿越程程山水,破空而来,在你耳边萦绕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