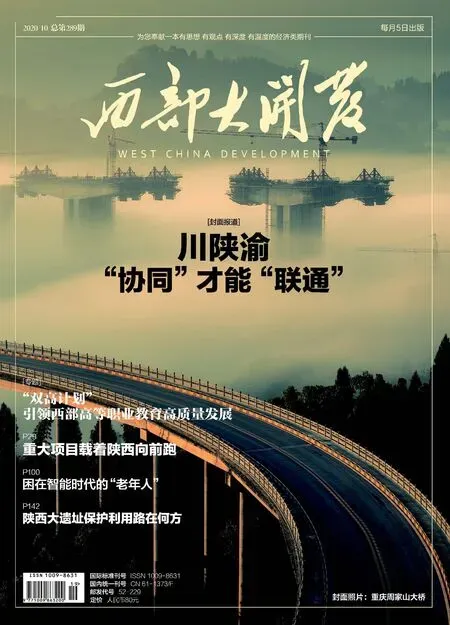困在智能时代的“老年人”
文/本刊记者 王薇

社工在一家社会福利院指导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在许多还在用着只能接打电话的“老年机”的老年人面前,老王甚至能被冠以“技术宅”的称谓——他会用淘宝买机器配件,会用微信收付款,会用手写文字聊微信,会用百度搜索各类新闻……
“手艺人”,是老王从事家电维修行业40余年积攒下来的“褒奖”,他热爱钻研新事物,并对自己乐于钻研的精神津津乐道。但尽管如此,在日新月异的智能场景的强势入侵背后,老王分明感觉到自己“拥抱智能时代”的信心正在被消磨殆尽……


数字生活的“局外人”
今年3月,正是疫情猖獗的时候,老王在程序复杂的健康码申请界面“败下阵来”,繁琐的步骤要求与庞杂的信息输入,不小心退出便找不到再次进入的路径……居家隔离的女儿打来的微信视频还在小窗口亮着,老王无奈地对女儿叹了口气:“要不……我以后还是随身携带身份证吧……”
现实是,像老王这样拥有互联网学习热情的老年人只是凤毛麟角,而更多的老年人正在互联网发展的迅猛速度中力不从心。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3月份,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6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为6.7%。
而今年1月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底,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经过计算不难得出,在我国,未搭上信息化快车的老年人占据着绝对普遍的比例。
疫情来临之前,我国连年增长的网络支付规模已有了突飞猛进的趋势。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7.68亿,较2018年底增长1.68亿,占网民整体的85%。
而如今除却消费端,网络信息化覆盖的范围正在向各个领域蔓延,疫情催生的个人健康二维码系统便是个很好的例证。
不可否认,我国能在较短时间内将突袭的疫情掌握在可控范围内,健康码功不可没。在区域范围内,“一码通行”在阻断传染源和方便人们出行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点,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标准化、直观化的管控方法。
数字化带来的便捷立竿见影,健康码几乎成为疫情之下公共场所的“唯一通行证”,拒绝使用健康码无异于拒绝进入疫情下的公共生活。
而健康码对于任何一个熟稔智能手机操作的年轻人来讲,无非是一次生活走向便捷化的亲身体验,“一部手机走天下”在我国7亿的移动支付规模与9亿的网民规模面前,只能算是“稀松平常”的场景,但却给老年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出行困难。
过去的几个月里,关于健康码的新闻屡见不鲜,而其中“健康码与老年人出行”间的矛盾便占据了“半壁江山”——《老人没有健康码被赶下公交车》《农民工没有健康码进不了小区,跪求保安放行》……而新闻内容也几乎如出一辙。
6月份,有媒体报道,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因无法出示健康码,半月徒步千里露宿公园。
8月8日,大连地铁车站内,因无法出示健康码或纸质的疫情通行证,一名老人被挡在了进站口外,其视频一度在网上热传。
8月17日,哈尔滨一老人没有手机扫健康码,被公交司机拒载,因迟迟不下车,遭乘客谴责“为老不尊”,最后由民警将老人带离公交车。
作为疫情防控的“利器”,健康码的出现让我们见证了数字变革带给社会的意义,但积极作用之外,社会伦理困境也逐渐显现,而以老年人为代表的“网盲”则是困境人群中的一种,财经作家吴晓波将其称之为“科技边缘人”。
“科技边缘人”,顾名思义,首先是一个“边缘群体”。在媒介语境下,“边缘群体”是指因经济结构、文化基础等差异,被主流所排斥的群体。
吴晓波表示,健康码的出现,把这种差异与不平等无限地放大开来。健康码只用来满足主流群体的利益,当疫情来临之际,规则粗暴地用统一的健康码将边缘群体拒之门外,而全国的每座城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去保护这群弱势群体;即便有,复杂的操作和流程等同于一记“闷棍”,经常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重大偏差。
这也加剧了老年人抵触网络的负面心态,于是有老人自我调侃道,健康码不但没能使我“畅行无阻”,反而令我“寸步难行”。
“触网”的困惑
在没有智能手机便“寸步难行”的当下,网络是万物互联的基础,是生活与工作的基础。但与年轻人不同,多数老年人“触网”更为被动。
疫情之下,许多医院为避免人群聚集,将所有的挂号业务转为线上,这让身体欠佳的崔大爷深受其扰,“以前我带着病历卡直接到窗口排队就可以。疫情一来,要网上预约了。”
崔大爷的孙子曾教会他用微信,但崔大爷网上预约时并没有绑定自己的医保卡,到了医院才发现预约的是自费号。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他取消了之前的预约,又绑定医保卡重新预约了一次,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小时有余,崔大爷想预约的专家也排满了,只能第二天再跑一趟。
“我感觉看病比以前麻烦多了”,崔大爷感慨道。他的很多老伙伴也深有同感,有一位老伙伴自己预约好了,结果到医院才发现看错了预约时间,白跑一趟。
这样的乌龙事件发生在数字时代的各个角落。无数像崔大爷这样的老年人感慨自己被时代“抛弃”了。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表示:“老年人长久以来习惯的现金购物、排队挂号、在窗口购票等生活方式,疫情之前尚能维持,疫情出现后服务业窗口作用削弱,为减少接触改为线上服务,点餐、挂号、政务……不少老年人蒙了,跟不上社会变迁的节奏,在‘数字化生活’中被‘代沟式’淘汰。”

志愿者指导老人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挂号

一位老人通过直播向网友推介自家的土鸡蛋
清洁工李大爷的一天,是从老年手机的整点报时开始的。每天早上8时至18时,他的老年机都会准时进行整点播报。2019年5月,他以240元的价格购得这部老年机。对于年近70岁的他来讲,字号大、功能简便、自动报时,老年机的优势不是功能繁琐的智能机可以替代的。
两年前,儿子曾给李大爷购得一款智能手机,用了不到2个月,便被他搁置了。智能机功能繁琐,每次接打电话,都要滑动界面、翻过各类软件,“经常没注意就点进别的地方,电话一直接不起来,着急。”
但有老年机,他也心满意足了,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春天,健康码开始成为大家的出行必备。李大爷突然发现,没健康码,不会网上预约,出行、就诊、购物……都成了生活难题,没有智能机不仅沟通不畅,而且剥夺了他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
互联网迅猛的发展速度,正在令越来越多以李大爷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失去使用智能终端的“权利”。而很多老年人即便能够感受到数字智能时代带来的便利,但偶尔力不从心的数字生活场景也会像一盆从天而降的“冷水”,瞬间将他们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热情“浇灭”。
张阿姨和老伴独自生活,虽然都用智能手机,但手机上常用的软件并不多,也几乎没用过。“现在不用智能手机都出不了门,但拿着手机我又担心自己点错了什么出现问题,孩子叮嘱我不要乱点,怕钱财被盗。”
谨小慎微并没有带给张阿姨足够的安全感,有一次去银行办理业务,需要配合手机银行APP上的操作,张阿姨眼睛不好,反应也跟不上,尽管有工作人员在一旁指导,但她还是感觉到了背后排队人群的不耐烦,“有时候真感觉自己赶不上时代了。”
疫情为数字化升级提供了舞台,也粗暴地剥夺了许多人晚年体面生活的尊严。新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也让许多老年人成了“数字贫困户”,数字鸿沟带来的问题早已远远超出家庭范畴,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时代不等人,但人要等人”
在被互联网“侵袭”的时代,相较于被动接受数字生活“洗礼”的老年人,年过六旬的李教授对待无处不在的智能生活的态度则是“主动拒绝”。
微信诞生的前几年,李教授便将微信归入了知识碎片化“罪魁祸首”的范畴,因此,他不但拒绝阅读微信公众号,他还卸载了微信,并专门写了一封信,公开抵制微信,此事在当年曾轰动一时。
两年后,记者在某一公众场合碰到了李教授,并问他:“你现在还不用微信吗?”他很骄傲地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只几乎已经在市面上消失多年的诺基亚键盘机,说:“我现在最多就用用这个东西,绝不上网,绝不使用智能手机。”
但在连纸质货币几近消失的今天,主动选择退出智能生活并非易事。
早在2018年,一条拒收老年人现金的新闻一度引发网络热议。67岁的谢大爷在超市买了8.8元的葡萄,排队交款时,被收银员告知不收现金只能用微信。交涉未果,谢大爷赌气拿着葡萄走到门口,被保安拦下。最终,在保安协助下,谢大爷才成功用现金结账。
谢大爷作为老年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其遭遇之所以能引起热议并非偶然。近年来,消费者在旅游景区、餐饮、零售等场所消费时被商家拒收现金的事件时有发生,部分零售点更以“找不开”“没零钱”等理由要求消费者“扫码支付”。
相关部门调查显示,在受访的2万多个商户中,近四成表示过去1年中曾“拒收现金”,而在受访的3万多名消费者中,超三成反映在过去1年内遭遇过“拒收现金”的消费场景。
2014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仅2.15亿,即10个人中只有不到两个人会使用移动支付,而爆发式发展就此开始。2019年,我国移动支付规模已达到7.33亿,以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为主要渠道的移动支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场景。
购物不带钱包,手机就能“买买买”;手机下单点外卖,半小时送家门口;直播间1亿人在线,只为拼手速抢好物;网约车成为日常,最远4600公里都能去;卖房还能直播卖,方寸小屏就能获取最新资讯……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这一切不过6年而已。

大学生志愿者帮助社区老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老人用手机淘宝扫码参加商场活动
而以老年人为代表的“科技边缘人”也是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的。吴晓波说,“科技边缘人”的出现,是科技本身未到成熟形态的缩影,应当引起我们对当今人文、商业和制度关系的深刻反思。
如果智能时代带给我们的困惑在加剧,那么反省与改善便不能缺席。不被人工智能“操控”,曾是许多科幻故事的主要题材,如今竟成为涉及社会民生的现实问题。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张国新提交了《关于缩小数字鸿沟、维护老年公民公平权利的建议》。《建议》中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有不少人因为不会使用网络而产生被时代“抛弃”的负面情绪,进而发展成为焦虑、失落、沮丧等,有的甚至因此质疑自我价值。
张国新表示,受地区、地位、能力、素质等的限制,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接触范围与掌握程度会存在明显差异,这可能会造成甚至已经造成了新的“数字鸿沟”和机会不均,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部分社会群体更加边缘化。
智能技术带来诸如安全隐患等问题又往往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上。为此在渐渐步入老龄社会的中国,全社会都在体验着互联网便利之际,互联网如何公平服务全体公民,值得思考。
而互联网时代的诸多现实问题与其说是技术缺陷,不如说是人文关怀理念缺失导致的价值冲突。社科院研究数字化驱动劳务的研究员孙萍表示,“加强程序员的培训和价值导向很重要。但目前国内的情况是,程序员大部分都是理工的直线性思维,很少有社会科学的这种思维,所以,他们对于公平和价值的这些问题,理念上都比较欠缺。”
而在吴晓波看来,科技本身没有不公平,它提高的是全社会的平均效率,最终普惠大众。而且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谁都可以去学习,去融合,然后得到进化。而科技进步中的不公平来自于科技形态尚未成熟之下的制度和规则缺陷,这使得落在后面的人在科技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彻底失去了追赶的希望。
时代不等人,但人要等人,互联网时代友好的“规则设计”已然“呼之欲出”——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如何坐地铁;医院预约、扫码,能否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专门服务;没有热情学习使用智能设备与移动支付的人能否被平等对待;除子女的帮助外,面对对智能设备颇有学习热情的老年人,能否有专业社会组织为其进行实践教学……
身处被电子产品“裹挟”的互联网世界,或许与我们理想中的人工智能时代还相去甚远。现状之下,有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恐怕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填平”,但让其“浅一点,再浅一点”,是我们始终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