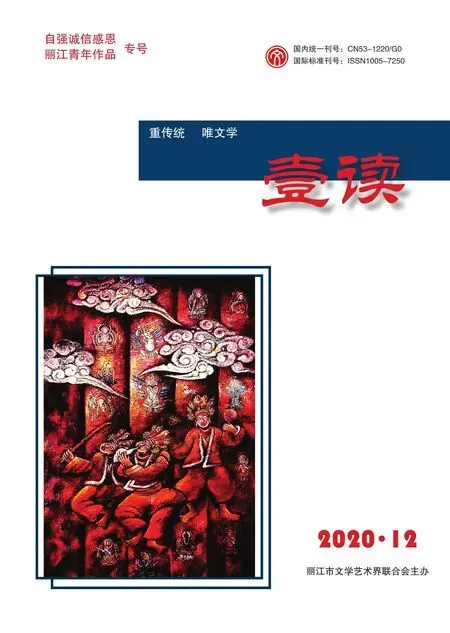又是一枕秋凉(组诗)
◆马海
香格里拉
卓玛转身的时候,草绿了
植物长出一寸寸阳光
大地饮着露水浸泡的早茶
风是一把梳子,高原开始柔顺
咀嚼时光的牦牛,目光
穿过古朴的木栅栏
静立的马匹,倾听
昨夜星辰遗落路旁的一盏情歌
荒原的独树上,谁种下第一粒鸟鸣
佛陀双手合十的缝隙里
乌鸦穿过吉祥的阳光
指尖,一朵净界的云缓缓滑过
薄薄的流水,把村庄洗了又洗
山寨一角,颤音的野蜂
写着一行袖珍的诗
高悬蜂巢的崖壁,岩画斑斓
雾散,雾散
绿野上一只鹰驮着家园飞翔
岩壁上的鸣蝉
走进虎跳峡的人突变为千年哑巴,他们清楚
在翻卷的巨浪中,说什么都是多余。唯有
绝壁上数万的蝉,那些小虫,不肯罢休
伏身险境,一刻不息地嘶声高叫
于是在巨大的洪水轰鸣声中,始终
有另一种尖锐的声音不绝于耳。仿佛
一群民间歌手,在与十万铁甲的呐喊对峙
游人忘情山水的同时
无法忽略那些蝉的鸣叫
我被浪花打湿睫毛,却被鸣蝉打湿内心
在回程的路上,虎跳峡洪水的轰鸣渐渐停息
那些蝉,还在虎跳峡深处叫绿一个夏天
牦牛背上的风
藏地。香格里拉。秋日草甸。
阳光和雨水,同时到达。高地啊,
不是岁岁可以登临。
脸庞,岁月的攀爬,步履,如胡须样密。
虔诚,有如僧侣。掌上,有花,静放如佛。
来了,不戴墨镜,不着风衣和帽。任乱发,
随风曳动。
走过湿地,有一份野马的心情。
哦,牦牛。一个个高原的标点。沉默,隐忍,彪悍,
大地的断章,在此铺开。
牦牛就是不须呐喊的斗士,
一对尖锐的角,在呼啸的高海拔上屹立。
逝去的青春,就要返程。我喝了一口雄心。
牦牛背上的风,来自蓝天。从月亮那边吹来。
我只有用赤裸的胸膛来装,装一壶风。
不佩戴藏刀,不喝烈酒,已经是男人。
狼毒花,在脚下。伸展腰,到天涯。
今晚,我不宿店,
等一个少女,骑着牦牛过来。
又是一枕秋凉
秋天,说来就来了
回老家的路被稻子的熟黄包裹
凉意梳理着我步入中年的心情
何时,这条路渐渐荒芜
几枚文字,怎么也码不出故乡的样子
凌乱的草垛,堵住回乡的路口
一年年在土地上寻求荣光的爸妈
蓄满岁月之铧的犁痕,笑容里
点着如月的豆和晚景的瓜
我用歉意编织的篮,无法装下
因为有爸爸在,故园还是园
因为有妈妈在,老家还是家
只是爸妈给我一生的爱
我却给他们孤独的晚景
在我背离的这片故土上
面对说来就来的秋天
一生忙于收割的爸妈,毫无还手之力
午夜,一辆入城的马车
月光在午夜惨白,如水流泻
一地银色河流。树影,那水草
等待鱼的贯入。工业的犬子
纷纷睡去,金属的鼾声渐起
农业的虫鸣,仿佛失忆的人
在月光下苦苦寻找精神故乡
这是午夜两点,一辆马车
一个十九世纪的闯入者
仓惶驶进城堡。踢踏之声
溅在我脑上,梦被踏碎
我想到马背的汗味,和车上的
一两个酒瓮,破落贵族的后裔
龟裂的油画,他们随着马车
驶入一个不安的城市。我推窗
一阵蹄声和轱辘,已远去
满地碾碎的影子,在如水的月光下
惨白,如一个失忆者的记忆
陈家院子
陈家院子,是民国遗留到今天的旧物
居住着镇上的鳏寡孤独
我在院外度过半饥半寒的童年
每天收集嵌进墙体的铜钱和瓷片
王谢堂前燕子,在百姓头顶做窝
深宅不深曲巷太曲,拴着的老犬
吠一片草根的天空。防火墙的流线
举起衰草,落些琐碎的雀,念着民谣
我家四口从陈家院子迁出
已是三十多年,总有一些民国书声
传进我耳里,像是陈家院子遛出来的
一声雀唱。我的文字,染指了那些旧
旧的乡人,旧的灯,旧的院落
我的味蕾,徒增了一步荒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