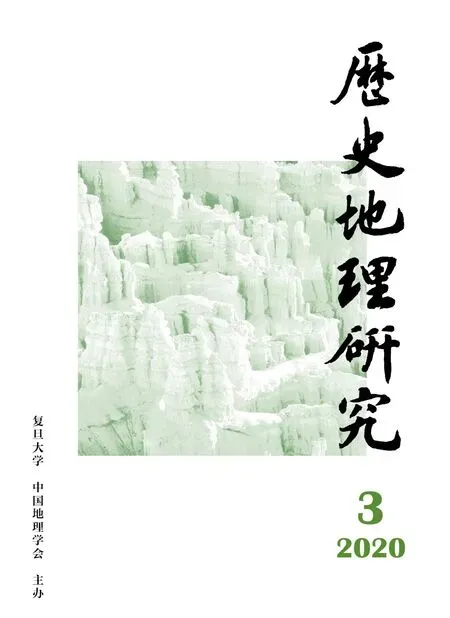南京博物院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藏本之诠注
阙维民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1949年以来,有关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已有研究成果,尚无探讨南京博物院利氏《坤舆万国全图》藏本(以下简称“南博本”)(图1)的专文。本文从8个方面略述“南博本”的公展记录、摹本比较、现有刊版、图幅尺寸、成图形式、成图底版、摹绘底本、独特价值。
一、 公 展 记 录
“南博本”于1922年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1933年尚存于北平历史博物馆(1)《北平历史博物馆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3年第45期第1版(前2幅)、2版(中2幅)、第46期第2版(后2幅)。,1936年前(2)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1—50页。移藏至南京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
1923年4月13—15日,“南博本”公展于北京故宫午门大殿,这是该图首次公布并展出。此消息最先由中文刊物《时报》(3)《利玛窦所绘地图之陈列》,《时报》1923年4月14日,第4版。报道,其后《圣教杂志》(4)《利玛窦在华所撰绘之地图》,《圣教杂志》1923年第12卷第6期,第277—278页。《青年友》(5)《三百年前之古地图: 明万历年间旧物,利玛窦在华所撰绘》,《青年友》1923年第3卷第5期,第11页。《史地学报》(6)《三百年前之古地图利玛窦在华所撰绘》,《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5期,第14—15页。按: 该刊转载时将“十三、四、五等日”误为“十三、四、五等月”。相继转载(文字略有出入)。这份报道在有关利氏世界地图的所有研究成果中迄今未被引述,故录《时报》载《利玛窦所绘地图之陈列》全文如下:
近世天文大家利玛窦氏于明万历年间,由欧来华,现在极负盛誉之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即为该氏及徐光启诸人所手创遗留迄今者。闻日昨午间历史博物馆(7)“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度工作报告》,谓旧藏本系于民国十二年访获入藏”。参见曹婉如、薄树人、郑锡煌等: 《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得该氏摹绘“世界坤舆全图”六帧,一幅长七尺宽三尺,图作球形,经纬度数俱全,各地均附注解,五色绚烂,古雅可爱。第一幅及第五幅有该氏题句,款(8)“款”,《圣教杂志》与《青年友》误为“欵”。用大明万历壬寅年(距今三百余年),他幅复有李之藻祁光宗等跋语。李等与氏为挚友,亦科学界著名之士也。图中南北亚墨利加洲已标出,而所述则为印地安土人之生活,盖氏作图时,约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八九十年,而距合众建国时期,固甚远也,其他欧洲诸国译名,均与今大异,中国幅员亦不相同,如满洲东三省之地,统标名女直(9)图上标为“女直”,《时报》原录,但《史地学报》《圣教杂志》与《青年友》均称“女真”。,黄海称为大明海,此其尤显著者,图内海洋空隙,绘有怪异鱼类多种,陆地则加绘猛禽厉兽若干,状貌悉狰狞可畏,大抵现时灭种者居多,大洋中复间绘十六世纪船只十余艘,作乘风挂帆之状,形式虽不一,均奇特出人意表。此图原在厂肆某古玩铺(10)经查,“民国十一年悦古斋铺主韩德盛收购一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旋经人介绍卖给了北平历史博物馆。‘九一八’事变后,此图运往南京”。参见曹婉如、薄树人、郑锡煌等: 《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为某外人所见,将购送海外,有成议矣,该馆据北京教育会会员孙君报告,急俛(11)按: 《圣教杂志》作“挽”,《青年友》作“浼”。人向某铺磋商,以重值购得。现定于十三、四、五等日河南赈灾会(12)检索民国期刊,1923年中国的赈灾省份有山西、广东(汕头)、陕南而无河南,故此处“河南赈灾会”疑为“陕南赈灾会”。期内,悬挂午门大殿,供人观览。并函商前意大利公使钱念劬君,请将其旧(13)原文为“售”,据《史地学报》《圣教杂志》与《青年友》更正为“舊”,即“旧”。藏利玛窦氏绘像,暂借该馆,与地图一同张挂,以引起参观人兴趣,且寓表扬前贤之意。钱君已函复照办。想届期前往参观者,必不在少数也。
自1924年首次公展以来,“南博本”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据检索,国外展出记录有: 198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史博物馆的“中国五千年的发明与发现”(Chine Ciel et Terre 5 000 Ans d’inventions et de decouvertes)(14)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1995, Volume 47, Issue 1, pp.94-117, Note 16.展、2014年6月27日—10月19日英国爱丁堡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明朝: 黄金帝国”(Ming: The Golden Empire)展、2014年9月18日—2015年1月5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明: 盛世皇朝50年”(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展(15)秦川: 《英国两大博物馆举办明代文物展》,《中国日报》中文网[2014-8-12], http: / /language.chinadaily.com.cn /bbc /ent /2014-08 /12 /content_18293618.htm。(该展主要阐述1400—1450年改变中国的50年历史(16)郭婷、徐立恒: 《反思灿烂和多元的时代——回顾大英博物馆明代大展“1400-1450: 改变中国的50年”》,《书城》2015年第4期。按: 成图于1608年的《坤舆万国全图》何以随展不详。)。国内展出记录有: 2019年4月16日—6月16日浙江美术馆馆庆10周年的“心相·万象——大航海时代的浙江精神”(17)《“心相·万象”大航海时代的浙江精神群展》,雅昌展览[2020-05-01],https://exhibit.artron.net/exhibition-63279.html。特展。2020年6月19日—8月23日中国丝绸博物馆“一花一世界: 丝绸之路上的互学互鉴”(18)本文即应中国丝绸博物馆为此展之约而撰。展。
二、 摹 本 比 较
现存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藏本有刻印本与摹绘本(包括“刻印+摹绘本”),迄今已知世界各地所藏摹绘本共有9份:“南博本”,南京博物院藏本(彩绘,1—6幅);“首大本”,韩国首尔大学藏本(彩绘,1—8幅)(19)《〈坤舆万国全图〉(彩绘)韩国汉城大学藏本》,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大阪本”,日本大阪北村芳郎藏本(彩绘,1—8幅)(20)《〈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日本大阪北村芳郎藏本》,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51页。;“凯达尔本”,美国凯达尔捕鲸博物馆藏本(Kendall Whaling Museum)(彩绘,仅第3幅)(21)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1995, Volume 47, Issue 1, p.95.;“理格本”,法国人理格(G. Nicolas)藏本(彩绘,1—6幅)(22)此图现只转载于德礼贤《利玛窦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一著所附黑白照片,《〈坤舆万国全图〉(彩绘)理格藏本》,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53页。;“国图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彩绘,仅第4幅)(23)《坤舆万国全图局部(中国部分)》《坤舆万国全图局部(东亚部分)》,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编: 《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注: 该图集未标注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通常被误导为南京博物院藏本,如《南京版坤图上的船》(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54页),实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龚缨晏也已指出了这一问题(龚缨晏: 《关于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的几个问题》,张曙光、戴龙基主编: 《驶向东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239页)。;“奉先寺本”,韩国奉先寺藏本(彩绘,1—8幅;已毁,首尔大学奎章阁存有黑白照片(24)杨雨蕾: 《〈坤舆万国全图〉朝鲜彩色摹绘本及相关问题》,《历史地理》第2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343页。,韩国实学博物馆藏有复原图(25)赵敏住: 《明清西方天文学对朝鲜时期地球研究的影响及其视觉表达: 以韩国所藏〈坤舆万国全图〉为中心》,《中国美术研究》2019年第4期。);“鲁德曼本”,美国鲁德曼古地图商店49843号(彩绘,仅第1、6两幅)(26)龚缨晏、梁杰龙: 《新发现的〈坤舆万国全图〉及其学术价值》,《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1期。按: 据鲁德曼商店网站显示该地图目前已售出。;“历博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本(墨线仿绘,1—6幅)(27)《〈坤舆万国全图〉(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墨线仿绘本)》,曹婉如、薄树人、郑锡煌等: 《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比较分析9份藏本,可获以下几点结论:
(1) 所有摹绘本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图版拼幅(6幅与8幅之异)、图识图说(图面布局之异)、图面文字(缺漏变更之异)、图本内容(陆域或岛屿的大小缺漏之异)等几个方面。
洪煨莲认为“意大利人理格君所存之绘本和历史博物馆原藏之本尽相同”(28)“北平交民巷台吉厂理格洋行之主人,意大利理格先生(G. Nicolas)亦藏有彩色旧绘本一图。承他示我以十分清晰的照片。我见得原图第四幅的上端纸颇残缺,然其图中所写的文字,所绘的地形,和船,鱼,禽,兽,等等,全与历史博物馆之原图一致。理格君且告我: 他的原图之尺寸,设色,尽与博物馆本相同。因此,我姑定: 这两图同属一个时代,且同出于一源,不必请他费神去取原图相示,亦未尝向他借照片来研究。”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3、27页。,即指“南博本”与“理格本”完全相同,但比较两图还是可以分辨出差异。主要差异之处是第4条幅“地南极线”上方圆圈内“看北极法”的文字排列形状,“南博本”呈近正四方形,而理格本呈矩形。事实上由于摹绘本是手工摹绘,摹绘本与被摹绘之本、各摹绘本之间多少都会出现差异之处,当属正常现象。
(2) 除“历博本”为墨线仿绘本外,其余8份均为彩绘本。
(3) 除“凯达尔本”与“国图本”两藏本外,其余7份均为完整藏本。
(4) 所有藏本中,“南博本”保存最善、品相最佳,地理内容及图题图识与1602年李之藻的刻印本最为接近。
(5) 在7份完整藏本中,除“南博本”与“历博本”(墨线仿绘“南博本”)两藏本外,其余5份藏本均有版识:“钱塘张文焘过纸 万历壬寅孟秋日”,相当于今天正式出版书籍版权页标明的出版印刷单位与出版日期。“过纸”,是木刻印刷过程中一道重要技术工序的术语,包括把握刻版的上墨深浅、调试印纸与刻版的吻合程度等,在裱画、绘画与拓碑前对纸张也有类似的整理工序(29)阙维民: 《伦敦本利氏世界地图略论》,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中心编: 《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25页。,可以解释为今天的“刊印”。“南博本”不用1602年的“过纸”版识,正说明其版是1608年呈贡万历皇帝的原图。
三、 现 有 刊 版
“南博本”1923年首次展出后不久《东方杂志》即以三整页的篇幅刊载了全图(30)《利玛窦之坤舆全图》,《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9期。,对此图的各种学术研究也由此开启,尤其激发了中国学术界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热情。
《东方杂志》刊载之后,随着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逐步开展,“南博本”又被多次刊载引用,分别为: 1928年,法国传教士裴治堂的研究小册《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利玛窦之世界地图》附图(31)[法] 裴治堂(化行 Henri Bernard): 《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利玛窦之世界地图(法文)》,北京政闻报出版社1928年版(Augustin Bernard, La Mappemon de Ricci au Musée Historique de Pékin, Collection d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1928)。“册子内附有一小张缩影历史博物馆藏图”,参见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5页,尾注17。;1933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的分幅刊载(32)《北平历史博物馆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3年第45期第1版(前2幅)、2版(中2幅)、第46期第2版(后2幅);分幅刊载。;1938年,德礼贤著《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之附图(33)Pasquale M. d’Elia, Il Mappamondo di Cinese dell P. Matteo Ricci, S. J., Rome: Vatican Library, 1938, Fig.29 (Copied by 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1995, Volume 47, Issue 1, pp.94-117. Fig.3).;1940年,《东方画刊》刊图(34)《中国第一部世界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东方画刊》1940年第3卷第8期,第6页。;1983年,研究论文附图(35)《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南京博物院藏彩色摹本)》,曹婉如、薄树人、郑锡煌等: 《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1995年,《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刊图77(36)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编: 《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第77页。;1988年,《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图92(37)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编纂: 《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2004年,《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图版四(38)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图版四。。
上述所有“南博本”的刊载本,以1988年《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的刊载图最为清晰,色彩度最接近于原图。
四、 图 幅 尺 寸
关于“南博本”的图幅尺寸,据笔者检索,共有五种记录(纵×横,厘米): ① 192×675; ② 168.7×380.2(39)“纵168.7厘米,通幅横380.2厘米”,见曹婉如、薄树人、郑锡煌等: 《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高168.7厘米,通件长380.2厘米”,见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47页;“高168.7厘米,通幅长380.2厘米”,见龚缨晏、梁杰龙: 《新发现的〈坤舆万国全图〉及其学术价值》,《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③ 168×382(40)“纵168厘米,横382厘米”,见《九大博物馆入选〈国家宝藏〉的27件国宝》,搜狐网[2017-12-04],https://www.sohu.com/a/208257382_488370。; ④ 192×380.2(41)“纵192厘米、横380.2厘米”,见庞鸥: 《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国测绘》2002年第5期;“纵一百九十二厘米、横三百八十点二厘米的整幅”,见万方、周宏伟: 《中国古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书屋》2006年第12期。; ⑤ 192×346(42)“纵横192厘米×346厘米”,见孙果清: 《利玛窦在中国编制的“世界地图”》,《地图》2008年第5期;“纵192厘米,横346厘米”,见《〈坤舆万国全图〉说明》,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编纂: 《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第126—127页。。
记录①为1923年中文《时报》记录:“……六帧,一幅长七尺宽三尺”(43)《利玛窦所绘地图之陈列》,《时报》1923年4月14日,第4版;《利玛窦在华所撰绘之地图》,《圣教杂志》1923年第12卷第6期,第277—278页;《三百年前之古地图: 明万历年间旧物,利玛窦在华所撰绘》,《青年友》1923年第3卷第5期,第11页;《三百年前之古地图利玛窦在华所撰绘》,《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5期,第14—15页;《利玛窦之坤舆全图》,《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9期。,洪煨莲解释:“可惜我未得绘本之尺寸。据《东方杂志》影图后之说明云:‘宽三尺,高六尺’。此尺如为营造尺则是192×96 cm。不知这是如何量的。我疑绘本和李之藻刻本大小相同。”(44)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1—50页,尾注146。
笔者认为“……六帧,一幅长七尺宽三尺”,当作“……六幅,每幅长七尺、宽三尺”解,这样整幅地图的尺寸即为: 纵7尺、横6×3尺,即: 纵192厘米、横675厘米。
由于原图有裱衬底纸,而裱衬底纸的宽度往往大于原图,因此,原图尺寸与裱衬底纸尺寸的量算结果,往往存在差异。记录①中的横675厘米远大于后4种记录的原因,应当是量算6幅裱衬底纸宽度之和的结果。
以《时报》“……六帧,一幅长七尺宽三尺”为据推测:“南博本”在1922年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是6分幅,1923年4月在午门展出时,将6分幅裱合成完整一幅。而墨线仿绘“南博本”的“历博本”,分为6幅收藏(45)《〈坤舆万国全图〉(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墨线仿绘本)》,曹婉如、薄树人、郑锡煌等: 《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第61页。,可作旁证。
在未实际量算的情况下,笔者倾向于出自南京博物院管理人员(46)在《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一文的作者中,有曹者祉,时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约翰·D·戴在其文(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1995, Volume 47, Issue 1, pp.94-117)尾注20、22、23中的“Cao Zhefu (Nanjing Museum)”,当为“Cao Zhezhi曹者祉”之误。的记录(记录②),纵168.7厘米、横380.2厘米。
五、 成 图 形 式
在有关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已有研究成果中,多少都涉及利氏世界地图的成图刻板、成图颜色、成图材质、成图方式。具体如下:
1. 成图刻版
成图刻版主要分为石刻底版与木刻底板,未发现金属刻板。石刻底版有1598—1598年间赵可怀在苏州的石刻《山海舆地图》,既是石质地图,也是拓图的底版。木刻底版共有5版: 第一版为《舆地山海全图》(肇庆,1584年,王泮刻板);第二版为《山海舆地全图》(南京,1598年(47)汤开建、周孝雷: 《明代利玛窦世界地图传播史四题》,《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按: 普遍认为是1600年,汤开建、周孝雷经考证认为是1598年。,吴中明刻板);第三版为《坤舆万国全图》(北京,1602年,李之藻刻板);第四版为《两仪玄览图》(北京,1603年,李应试刻板)(48)Pasquale M. d’Elia, 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 (1938-1960)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 S.J., Monuments Serica, 1961, Volume 20, Issue 1, pp.82-164.注: d’Elia仅列前四版。;第五版为《坤舆万国全图》(北京,1608年,梓人秘造本(49)张宗芳: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考》,《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3年第46期第2版;第47、48期第2版、第50、51、52、53、54期第2版。)。
2. 成图颜色
成图颜色主要分墨色和彩色。墨色,包括2种形式: 木刻版墨印(如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1602年李之藻刻印藏本)与墨色摹绘(如“历博本”即为墨线仿绘藏本)。彩色,包括3种形式: 木刻版彩印(尚无实例)、“木刻版墨印+彩绘”(如辽宁省博物馆《两仪玄览图》藏本)与彩色摹绘(如“大阪本”)。
3. 成图材质
成图材质主要有三种。纸质: 凡用纸张进行墨(彩)色木刻版印、石版拓印或摹绘而成的图,其材质均为纸质(绝大多数利氏世界地图现存藏本的材质为纸质)。绢质: 凡用绢进行墨(彩)色木刻版印、石版拓印或摹绘而成的图,其材质均为绢质(绢质利氏世界地图尚无实例,但有史料记载证明其或曾存在(50)利玛窦《入华记录》:“皇帝自内廷下谕,令备六幅世界地图绢本十二付”,转引自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25页。)。石质: 凡用石进行刻绘而成的图,其材质即为石质(如前述苏州的石刻《山海舆地图》)。
4. 成图方式
成图方式主要是三种形式。刻印,即用纸或绢,在木刻或石刻版上墨(彩)印或拓印而直接成图的方式;摹绘,即在纸或绢上,进行墨(彩)色摹绘而直接成图的方式;“刻印+摹绘”,即先刻印成墨色底图,再墨色或彩色添绘而分步骤成图的方式。
“南博本”为利氏世界地图的木刻第五版,即该图以残留的刻工私刻底版为主体并加补刻而墨色印刷成底图,再在底图上彩绘图像而成图(详见下节)。即: 该图中的线条与墨色文字均为刻版墨色印刷而成,然后在需要的部分渲染设色,书绘彩色文字;图中的绘画图像(10艘海船、8头陆生动物与15条海洋动物)其颜色当由制图者挑选,但据构成图像轮廓的、粗细均匀且清晰明辨的线条,可以推测该图是在木刻版墨色印制的基础上再经彩色描绘而成的。伦敦英国地理学会的《坤舆万国全图》藏本虽然没有彩绘图像,但图上的彩色部分也是在木刻版墨色印制的基础上再经彩描而成(51)阙维民: 《伦敦本利氏世界地图略论》,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中心编: 《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第314—325页。。确切地讲,“南博本”不是纯粹的摹绘本或“彩色绘本”(52)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3页。,不是彩绘绢本(53)邹振环: 《神和乃囮: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在华传播及其本土化》,《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注: 感谢邹先生相告:“我把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与南怀仁《坤舆全图》两者的彩绘本混淆了,后者有彩绘绢本。”或彩色绢本(54)邹振环: 《殊方异兽与中西对话——〈坤舆万国全图〉中的海陆动物》,《海洋史研究》2015年第1期。,也不是纯粹的木刻印本,而是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
六、 成 图 底 版
关于“南博本”的成图底版,有利玛窦本人的两份史料可资考证。一份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七月十三日利氏寄罗马耶稣会总监信(55)“今年年初,有以世界大地图献皇帝者。皇帝欲印多本。然原板已不在京,而副版已毁。于是有旨召窦,命窦印若干本。诸太监既知窦无版可印,则大惧,恐皇帝不肯信也,窦告以如得一月期限,愿别刻一更佳之本以应。诸太监具以覆奏。然皇帝不欲使窦破费,乃命彼等依照原样,在宫中刻版。既就,印本遂满全宫”。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期,第24页。;另一份是利氏《入华记录》的记事之一(56)利玛窦的《入华记录》:“一日皇帝有旨召吾等,其急。利玛窦及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二神甫既至灵台诸太监住所,见掌印太监及其他近侍等,颇甚张皇。皇帝自内廷下谕,令备六幅世界地图绢本十二付,盖指昔李我存在京所印之本。此图利神甫所制,每付共六幅,幅宽如肘之长,高过其倍,印就,装裱之如纸窗,系其边以带,使可舒合,置于室中。图中有利玛窦神甫之名,太监之给役内廷者,或指以示皇帝,故命就利神甫取图也。诸神甫曾以世界地图多付赠太监若干人。此中不知何人竟以一付添绘彩色,而献之于皇帝。皇帝见此佳制,繁列众国,广载异俗,中国人前此所未见者也,则大悦;故欲多图,殆拟以分赐皇太子及其他亲族者也。诸神甫未曾以此图献皇帝,且亦未尝欲他人为之,盖深恐皇帝或将误会图中中国所占地位之小,而以为吾等有意侮辱中国也。中国人素以为中国占天下之大半,中国士人且多谓吾等缩中国,伸外邦,而引以为憾者矣。然皇帝固自聪明,彼知此图所绘者实得世界名地大小之真,非有意轻视中国也。此本地图曾两度刻于北京,二本尽相同。一本为李我存所刻,李回籍时已将版片带去。又一本乃刻工等所刻,印之以求售,所卖印本颇多,且得善价。然北京大雨之年此本版片适在一旧屋中,夜中屋塌,压毙工人二,且毁其板焉。诸太监闻此,知不能应皇帝命,则又疑吾等言妄,既遣四人至吾等住所再询,复派人至刻工处取零碎版片之尚存留者,以为证。吾人之天主教徒李保禄曾刻八幅而更大之地图。吾等亦遣取此版至。然诸太监不敢以此本献皇帝。皇帝所指索者非此本,而两本中之注释亦间有不同也。彼等不知所为,踌躇不决者两三日。吾等乃告以愿得一月期限,自费别刻一更佳之地图,吾等意欲于图中多加若干更有益于天主教之宣传也。诸太监闻此,甚喜,即具以所闻奏复。然皇帝雅不欲多扰吾等,遂命就旧有之板,补刻以成六幅之世界地图,此事旋即办妥;其后宫内所需之地图,即在宫内印之”。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期,第25页。。两份史料均收录在《利玛窦全集》(57)Opere stort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uorauze Naziouali, cou prolegomeui, note a tavole dal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 I.; Volume I, I Commentars della Cina (Macerata, 1911); Volume II, Le Lettere dalla Cina (Macerata, 1913).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42页尾注11。中,细读这两份汉译史料,可总结如下:
(1) 利玛窦及其他神甫曾向多位太监赠送过1602年李之藻的木刻墨印版《坤舆万国全图》。说明在未进献皇帝之前,1602年版《坤舆万国全图》已在宫内流传。
(2) 收赠地图的太监之一将墨印版《坤舆万国全图》添绘彩色后献于皇帝。是仅添绘了色彩还是添绘了彩色图像未详,但无论是添色还是添图都说明: 一、 在1608年刻印彩绘《坤舆万国全图》之前,利玛窦本人刻印的世界地图以墨色素图为主,没有彩绘,也未绘图像;二、 1608年版的添彩绘图是被动而为。
(3) 皇帝见此繁列众国、广载异俗、前所未见之图后大悦,令索更多份以分享皇族。说明《坤舆万国全图》所展示的地理新知识,已撼动了中国皇帝头脑中固有的地理观念。
(4) 因图中有利玛窦之序,故指名要利玛窦提供。1602年版图中有多人的题识序跋而皇帝唯独指名利玛窦,说明皇帝(或太监禀告皇帝)知道此图“版权”属利玛窦,最佳被索人选非利玛窦莫属。
(5) 1602年版图的原刻底版已被李之藻带回杭州,刻工私刻底版虽被大雨塌屋毁坏,但仍有部分留存,说明此版的《坤舆万国全图》私刻底版并未完全毁灭。
(6) 利玛窦建议以《两仪玄览图》的8幅木刻底版作为取代版,印刷进献。但因其版非皇帝索要版本,太监不敢。
(7) 利玛窦再建议以一月期限自费另刻一版,皇帝不允。利玛窦能够保证在30天内完成《坤舆万国全图》的刻版印刷任务,说明他必定娴熟于地图底版的刻制与图中图像的摹绘。有学者也倾向于这一认识(58)邹振环倾向于“彩绘本上的动物形象之设计者应该是利玛窦”,参见邹振环: 《殊方异兽与中西对话——〈坤舆万国全图〉中的海陆动物》,《海洋史研究》2015年第1期。。
(8) 皇帝“遂命就旧有之板,补刻以成六幅之世界地图”,此事旋即办妥。说明1608年版《坤舆万国全图》是以1602年版私刻底版残留部分为主体加以“补刻”而成。且从补刻到完成制印的过程,时间很短。再次说明利玛窦在刻印地图与摹绘图像方面的娴熟程度。
(9) “其后宫内所需之地图,即在宫内印之”。说明利氏《坤舆万国全图》1608年版(即为前述的木刻第五版)的木刻底版保存在宫中,还可根据宫内对该图的需求量而添印之。
(10) 皇帝谕索绢本世界地图(“令备六幅世界地图绢本十二付”),但“南博本”为纸本而非绢本,这是一个遗留问题。有三种假设: 一是当时印制的进献图实际是纸本;二是当时在印制绢本进献图的同时,添印了纸本;三是在进献“绢本十二付”之后,添印了纸本。无论何种假设,“南博本”的底版都是1608年版,即木刻第五版。
洪煨莲考证认为:“我更疑宫中并无刊刻此图之事”故将“南博本”视为“诸太监摹绘李之藻本”(59)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26、28页。按: 洪氏述及7刻板,但未述此版为刻板,仅述为“摹绘李之藻本”。。笔者认为: 完整刻制新版,与在残留版基础上补刻,是两个概念。“南博本”的木刻底版显然不是完整刻制新版,但据利氏记载分析,当为在1602年私刻版残留部分的基础上补刻之拼版。
洪煨莲又认为:“历史博物馆旧藏的那本(即“南博本”)也许即是这样的摹绘本之一,该本的内容与李之藻本,除了几点外,完全相同。”(60)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26—27页。但对照梵蒂冈藏本(1602年李之藻原刻木版墨印)与“南博本”(1608年据补刻1602年刻工偷刻私版“墨印+彩绘”),去除后者图中的绘画图像,仅就图面大洲岛屿的封闭线形状与题识序跋的文字布局而言比较两者: 粗看,极其形似;细究,多有差异。故两版之间非洪氏所述的“完全相同”或“二本尽相同”(61)“此本地图曾两度刻于北京,二本尽相同。一本为李我存所刻,李回籍时已将版片带去。又一本乃刻工等所刻,印之以求售,所卖印本颇多,且得善价。然北京大雨之年此本版片适在一旧屋中,夜中屋塌,压毙工人二,且毁其板焉。诸太监闻此,知不能应皇帝命,则又疑吾等言妄,既遣四人至吾等住所再询,复派人至刻工处取零碎版片之尚存留者,以为证”。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25页。,而是利氏所述的版幅尺寸“大小尽同”(62)“此图之刻工又私梓一版,大小尽同”。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16页。。
七、 摹 绘 底 本
利玛窦在编制世界地图暨《坤舆万国全图》所依据的地图参考资料,是利氏世界地图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洪煨莲认为: 利玛窦献于皇帝的贡品之一《万国图志》就是《坤舆万国全图》所据底本,并据金尼各《中华传教记》(DeChristianaExpeditione)考证为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年)(63)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有多种汉译: 奥提力阿斯(洪煨莲译)、奥代理(方豪译)、奥特里乌斯(黄时鉴译)、阿伯拉罕·奥特吕(李旭旦译: 《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28页)。本文译据: 新华通讯室译名室编: 《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064页。的《地球大观》(TheatrumOrgisTerrarum)(64)《地球大观》(Theatrum Orgis Terrarum)为方豪所译,他认为:“洪氏译奥代理所著书名为《舆图汇编》,完全不合原义,Theatrum本作舞台解,故译为‘大观’。”(方豪: 《书评: 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上智编译馆馆刊》1947年第2卷第2期,第170—173页)若译《寰宇概观》更雅,但为了不引起混乱,本文沿用方豪译名。。从百科全书的介绍中可知,该著有各家所绘地图五十三幅。他还利用利玛窦全集的记载,证明利氏还参照了意大利地图学家鲁瑟利(Girolamo Ruscelli, 1500—1566年)编制的地图。限于各种原因,他自叹:“关于十六世纪意大利派或比利时派的地图,可惜我现今都未能得而将与利氏的地图细校”(65)“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利氏所献与皇帝的贡品内有《万国图志》一册。据金尼各的《中华传教记》,这即是奥提力阿斯的《舆图汇编》;其中有各家所绘的地图五十三图。至于意大利地图家法,则利氏本是意大利人,况他亦得用鲁瑟利Ruscelli(卒1566)的地图。关于十六世纪意大利派或比利时派的地图,可惜我现今都未能得而将与利氏的地图细校。”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18页。。
洪煨莲考证但未亲睹的著作《地球大观》就藏于北京西什库天主堂图书馆(方豪称“北堂图书馆”),且有1570年与1595年两版藏本,由于利氏1578年即启程赴印度,1582年抵达中国澳门,因此利氏制作世界地图所参照依据的当为1570年版。美国汉学家德礼贤在其著《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出版(66)宠光: 《利玛窦地图在罗马影印出版》,《天主公教白话报》1939年第22卷第3期,第44页;《利玛窦地图在罗马影印出版》,《公教进行》1939年第11卷第4、5期,第130—131页;《利玛窦地图在罗马影印出版》,《图书季刊》1939年第1卷第1期,第99页。前五年的1933年曾赴北堂图书馆翻摄了《地球大观》全著。1946年,方豪也赴北堂图书馆调阅了该馆珍藏的“利玛窦《万国舆图》所依原书”(67)《北平西什库天主堂内发现珍本古物,有利玛窦万国舆图原书》,《新闻报》1946年7月22日,第2版。,并于次年撰文评述道:“利玛窦绘《坤舆万国全图》,必有所本;十余年前,外国学者早就注意这一点,并认为利氏必本于”奥特柳斯的《地球大观》。并考证出如下事实: 德礼贤翻拍的《地球大观》,错将1595年版认作1570年版(68)方豪: 《书评: 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上智编译馆馆刊》1947年第2卷第2期,第170—173页。。
有关彩绘摹本《坤舆万国全图》(包括“南博本”)中的绘画图像,洪煨莲未考证其摹绘来源。他叹述:“这殆是从他处摹抄来的,西人旧图往往有这些玩意儿,可惜我现今不能证明其从何书,或何图中搬来的。”(69)“历史博物馆旧藏的那本也许即是这样的摹绘本之一,该本的内容与李之藻本,除了几点之外,完全相同。在其相同中,如名称之同为《坤舆万国全图》,各序跋之完全相同,地形及注释之相同,皆足以证: 绘本乃以李之藻本为蓝本,而摹写的。至其不同之最显著者,则绘本中独有船只,奇鱼,异兽之图。这殆是从他处摹抄来的,西人旧图往往有这些玩意儿,可惜我现今不能证明其从何书,或何图中搬来的。”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26—27页。真是一大遗憾!如果他看过了北堂图书馆所藏《地球大观》中的地图,就知道《坤舆万国全图》中的绘画图像即直接仿摹于《地球大观》中的多幅地图。
比利时制图学家、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于1570年出版了《地球大观》第1版,共辑地图70幅(欧洲56幅、亚洲与非洲10幅、四大洲各1幅),堪称世界第一部完整的构想地图集,被一再重印再版至1612年止,并被翻译成欧洲各主要语种。(70)“Abraham Ortelius 1570”, in Phillip Allen, The Atlas of Atlas: The Map Maker’s Vision of the World, London: Marshall Editions, 1997, p.36.注: 洪煨莲称《地球大观》载“各家所绘的地图五十三图”,则一定不是第一版。仅笔者所阅就有1570年、1573年、1584年、1585年、1587年、1589年、1590年、1595年、1598年、1606年版中的被转载图,这些图几乎多少都绘有海陆动物与海船图像。但在已有研究中很少引载《地球大观》所辑地图,就笔者所阅仅有展示伪圆柱投影的椭圆形世界地图(1570年、1587年版)(71)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图版十一、图版十二。、展示绘画图像的冰岛图(1590年版)(72)Map of Iceland from Abraham Ortelius’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1590, Map 8), in 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1995, Volume 47, Issue 1, pp.94-117.与中国地图(1584年版)(73)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图版十三。数幅。
除奥特柳斯的《地球大观》所刊地图外,为了说明“南博本”的地图伪圆柱投影及在地图上描绘图像的现象在16世纪的西方十分普及,再展示4幅世界地图: 西蒙·格里诺伊斯(Simon Grynaeus)的世界地图(1532年,木版刻印)(74)Simon Grynaeus, Typus Cosmographicus Universalis. Woodcut. An elegant world map first published in 1532 in a collection of voyages by John Huttich edited by Grynaeus, in Carl Moreland and David Bannister, Antique Maps,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89, p.15.(图2)、贾科莫·加斯塔尔迪(Giacomo Gastaldi)的世界地图(1546年,刻板)(75)World map by Giacomo Gastaldi, 1546, the progenitor of a sequence of maps continuing through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Thomas Suarez, Early Mapping of the Pacific, Singapore: Petiplus Editions, 2004, pp.42-43.(图3)、保罗·福拉尼的(Paolo Forlani)世界地图(1565年,铜版刻印)(76)World map on an oval projection. Universale descritione di tutta la terra conosciuta fin qui, by Paolo Forlani, copper engraving, Venice, 1565. A close copy of Giacomo Gastaldi’s map of 1546, in John Goss, The Mapmaker’s Ar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Skokie, IL: Rand McNally, 1993, pp.11,132.(图4)、安东尼奥·拉弗雷里(Antonio Lafreri)的世界地图(1580年,木版刻印)(77)Antonio Lafreri 1580, in Phillip Allen, The Atlas of Atlases: The Map Maker’s Vision of the World, London: A Marshall Edition, 1997, p.50.(图5)。

图2 西蒙·格里诺伊斯(Simon Grynaeus)的世界地图(1532年,木版刻印)

图3 贾科莫·加斯塔尔迪(Giacomo Gastaldi)的世界地图(1546年,刻板)

图4 保罗·福拉尼的(Paolo Forlani)世界地图(1565年,铜版刻印)
这4幅世界地图都是西方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成就的地图再现,它们具有以下共性: 第一,地图投影均为呈椭圆形的伪圆柱投影;第二,地图内容均有绘画图像;第三,出版年份均在1582年利玛窦入明之前;第四,地图投影与地图内容均与“南博本”形似。可以认为有绘画图像的椭圆形世界地图在16世纪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十分流行。生长于那个时代的学者型耶稣会士利玛窦,对于这些地图必然烂熟于心。
利玛窦编制《坤舆万国全图》(包括“南博本”)时,虽然国内外学术界都认为他利用了奥特柳斯的世界地图,但并不意味他只利用了奥特柳斯的某一幅世界地图(78)龚缨晏: 《〈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驳李兆良的相关观点兼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更不意味他没有参照与奥特柳斯同时代的其他世界地图的编制成果,尤其是有绘画图像的椭圆形世界地图。
八、 独 特 价 值
“南博本”除具有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暨摹绘本《坤舆万国全图》的共性价值与意义(79)《利氏世界地图共有的学术价值》,阙维民: 《伦敦本利氏世界地图略论》,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中心编: 《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325页。外,还另具独特性。
中国学术界对于利氏世界地图的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
(1) 明末清初汉文化圈的吸收学习阶段。代表研究者分两类: 一类是参与利氏世界地图刻版印制的学者,如《坤舆万国全图》中题识序跋的作者吴中明、李之藻、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等;另一类是编录利氏世界地图及其序跋的学者如章潢(著有《图书编》,收录《舆地山海图》与《舆地图》,1613年)(80)④ 转引自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20页。、周于漆(著有《三才实义》,收录《舆地图》,康熙、乾隆年间)④、冯应京(著有《月令广义》,收录《山海舆地全图》,1602年)(81)⑥⑦ 转引自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29页。、王圻(著有《三才图会》,收录《山海舆地全图》,1609年)⑥、游艺(著有《天经或问》,收录《大地圆球诸国全图》,1675年)⑦、程百二(著有《方舆胜略》,收录《山海舆地图》,1610年)(82)转引自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46页。、徐敬仪(著有《天象仪全图》,收录利氏部分地图,明末)(83)⑩ 转引自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47页。、潘光祖(著有《汇辑舆图备考全书》,收录东西两半球图《缠度图》,1633年)⑩、熊明遇(著有《格致草》,收录《坤舆万国全图》,1634年)(84)转引自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59页。、熊人霖(著有《地纬》,收录《舆地全图》,1638年)等。
(2)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基础研究阶段。代表研究者有陈观胜(85)陈观胜: 《论利玛窦之万国全图》,《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7期,第19—24页;陈观胜: 《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31—72页;Kenneth Ch’en and Matteo Ricci, Metteo Ricci’s contribution to, and influence o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9, Volume 59, Issue 3, pp.325-359.、洪煨莲(86)洪煨莲: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1—50页。、方豪(87)方豪: 《书评: 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上智编译馆馆刊》1947年第2卷第2期,第170—173页。、王庸(88)王庸: 《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07—109页。等。
(3)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外地图研究阶段。代表研究者有曹婉如等(89)曹婉如、薄树人、郑锡煌等: 《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金应春与丘富科(90)金应春、丘富科: 《中国地图史话》,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20页。、卢志良(91)卢志良: 《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177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9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332页。等。
(4) 21世纪以来的东西文化交流研究阶段。代表研究者有黄时鉴、龚缨晏(93)黄时鉴、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等。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时间间隔近300年,意味着利氏世界地图曾带给明代中国的世界地理新知识没有得到传承,而是中断了近三个世纪。正是1922年被发现、1923年公开展出的“南博本”,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利氏世界地图研究的现代新篇章。在目前各地现存的所有利氏世界地图藏本中,这一特殊意义唯“南博本”独有。
综上所述,本文有以下五个要点:
(1) “南博本”的价值:“南博本”的被发现与公展,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利氏世界地图研究的现代新篇章。
(2) 新发掘两类相关史料: 一是有关“南博本”1923年第一次公展的4份史料;二是可证明“南博本”编制摹绘的参照底本,即4幅16世纪欧洲编制的、图中有绘画图像的椭圆形世界地图。
(3) “南博本”的成图形式: 已有研究基本公认“南博本”是非刻印的摹绘本,即无刻印底版;但本文认为“南博本”的成图形式是: 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其刻印底版是在1602年私刻版残留部分的基础上补刻之拼版。
(4) “南博本”与“理格本”之异: 洪煨莲认为“南博本”与“理格本”两者“尽相同”;本文认为仔细比对两图仍然存在差异,即不尽相同。
(5) 李之藻刻版与刻工私刻版之异: 洪煨莲认为1602年李之藻刻版与同年刻工私刻之版(即1608年补刻拼版之主体)“二本尽相同”;但据1602年刻版墨印的“梵蒂冈本”与据1608年补刻拼版墨印+彩绘的“南博本”相比较,1602年的李之藻刻版与同年刻工私刻之版两者仅尺寸“大小相同”,内容则相似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