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徙·僭越·坚守
赵光鸣是新疆作家中的实力派,被刘俐俐教授称为“是西部流浪汉小说的扛鼎作家”(《流浪汉小说:由浪漫到深沉——立足于西部流浪汉小说的历史回顾》,见《小说评论》1996年第2期)。他的作品常常聚焦漂泊在社会底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被称为“盲流”。赵光鸣写他们的流徙、挣扎、欲望、奋斗和坚守,有破败不堪,也有温情微光,在光与影的斑驳中画出时代的剖面,也画出了这些流浪者们的生存世相。
“盲流”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概念,主要指1953到1989年30多年间,脱离当时户籍管理自发迁徙到城市去谋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称“盲目外流人员”,简称“盲流”的时候带有一定歧视意味。在有正式新疆户籍的人眼里,“盲流”约定俗成的涵义是来到新疆谋生、暂时没有固定工作和本地户口的“口里人”,这个群体并不一定全都是农民,也未必一定全都流入了城市。作家鲍昌说,“不知从什么年月开始,无数的人自东徂西,来到新疆这块亚洲的腹地探险。他们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名称,而在新中国建立后,被起了个政治化的名称——盲目流动人员,简称就叫‘盲流。这名称颇带贬意,仿佛比穷光蛋、流浪汉、叫花子高不了多少,有时更被看成了‘罪犯。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他们实际上是开拓新疆的有功之臣。几十万人‘流进新疆,像是撒向旷野的一把草籽,有的被风吹去了,有的却生根发了芽”(何镇邦《瑰丽的色彩刚健的风格——简评长篇小说<盲流>》,见《小说评论》1985年第6期)。尽管“盲流”为开发新疆建设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获得当地社会认同的过程却极其艰难。赵光鸣于1980年代后期敏锐地将“盲流”人生纳入文学视野,既是对新疆文学创作题材领域的开拓,也是对当时主流文坛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主潮的呼应。
一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为什么而活,人该怎样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本质性的追问是困扰一代又一代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形而上的命题。而对永远行进在流徙之路上的“盲流”们来说,每一步脚印、每一寸光阴都是答案。赵光鸣借他笔下的流浪者告诉读者,“我这样漂泊天涯,一定是命运早安排好了的”(赵光鸣《云游》,见《远巢》,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
赵光鸣所书写的“盲流”,是一个包容了三教九流的复杂群体,其中每一个人走上盲流之路的原因千差万别,每一个人的流寓人生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带着对改变生存现状的期望踏上征程的,不可知的远方有不可知的坎坷,也有更多改变身份与命运的可能。
被称为西部文学发轫之作的中篇小说《石
坂屋》(见赵光鸣《绝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谷发是为了改善贫困的生活,带着凉西戽三十个乡邻组成的工程队,来到1300多里外的卡卡斯雅矿盖房挣钱。工程尚未结束,所在县政府已通令所有外出的施工队、副业队限期返回,施工所得全部收入还要没收充公。“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把一屋人都打懵了”,谷发甚至做好了被押被批判的准备,他要遵守对矿上的承诺,让矿上的工人有房住。同时,他也抱着希望,“因为呼延矿长和老朱再次重申了施工队的辛苦费由矿上代存,绝不食言。”这样,辛苦所得就不至于平白无故地被没收。对于“盲流”来讲,活着殊多不易,贫穷、漂泊、辛劳,如此种种,都是卑微人生之中的常态,他们要承受随时可能到来的打击和挫败,常常陷于不能自主的境地,而特定时代的政策律令则进一步冲击着他们的生存自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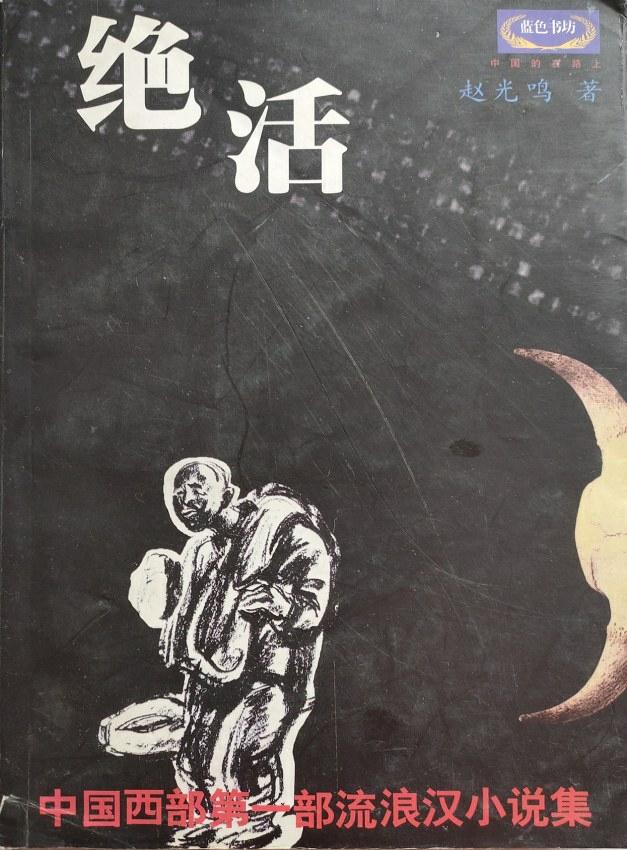
然而,“盲流”看似微贱的生命却有着强悍的生存意志,其漂泊辗转的人生意义便在于对既定命运的全力抗争。“盲流”们通常比处于稳定生活状态的人更能吃苦,更加坚韧,生命力更为旺盛。赵光鸣《蚂蚁与耳朵》里写代尔维什乡为了解决贫困户脱贫致富问题而办起砖厂,“乡里招的贫困户民工干了不到一个月人都跑光了,嫌砖厂的活儿又苦又累,还要起早贪黑。于是,四川盲流司文通瞅准机会把厂子承包了,从喀什大街上招来一帮内地民工,干了几年,这些人都挣了不少钱。有的人,在老家把楼房都盖起来了。”(见《人民文学》2009年第7期)原住居民——哪怕是贫困户——的生活因未臻于绝境,还可以吃救济粮、穿救济衣,退到一个不温不饱但也不寒不饥的角落里,生命在惰性中变得委顿。而“盲流”们选择流徙生活本身就是对常态生活的抗争,他们没有退路,也不会退却,反倒在勇往直前的道路上爆发出生命的强力。所以《鼹鼠》(见赵光鸣《绝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的“河南人”即便“饿得垃圾堆里找食吃,大冷天冻得没处躲,就去钻人家的菜窖、睡候车室。有时候被人当贼抓了,打得皮开肉绽,半个月走不动路”,也要“凡事不愁”,因为“人只要遇事不愁,就能腾出脑瓜想办法。只要愿意想,办法总是有的。”
如同《石坂屋》中的知识分子“我”所感悟到的,“活着,而且在梦想着,期待着,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活着”对个体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虽然能否活、如何活常常是个体无法左右的,但渺小如“盲流”,在无法掌控的流徙路上,也总能在无限的希望中感知自己的生。
二
赵光鸣关于“盲流”人生的书写常常与性、欲望、男-女关系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性爱出自人的天性,到发情期不论男女都会产生性欲冲动和性幻想……性和吃饭一样,都属人的本能。”(《赵光鸣访谈录》,见《绝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因此,他以平常的、轻松的、漫不经心的方式来写“盲流”的性,将它呈现为漂泊人生中的自然存在,甚至僭越了正常社会中的伦理规范。车厢里(《逃亡》)、工地上(《石坂屋》)、苞米地(《絕活》)、美容美发店、出租屋、豪华套间(《乱营街》),性无处不在,成为“生”的形态和意义。
性对个体的吸引与“活着”对个体的吸引是一样的,赵光鸣倾向于表现“盲流”们原始状态的、纯粹生物属性的性需要和性快乐。如长篇小说《乱营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对“我”(李豹公)与菜农的女儿、经营色情业的美容美发店老板娘康彩凤之间的性关系的描写:
我把书从她手里拿开,扔到一边。就势把她拥进怀里。这次她没有拒绝,好像早有准备,顺从地迎接拥抱。然后就是长时间的站立紧贴,互相抚摸,试探性的浅吻,到热吻,深吻,最后变成狂吻。
我们都脱得一丝不挂,我的进入让她快乐无比,她的疯狂妙不可言。
这类性过程的详细叙述和对欲望目光凝视下的女性身体的描写,在整个作品中不时出现,强化了读者“性无处不在”的阅读感受。不谈爱情,只有性本身的快感。在性过程的展开中,叙事者与行为者共享着来自欲望满足之后的感官愉悦。
在赵光鸣笔下,爱是很难把握的。《石坂屋》中花儿铁与寡妇石牡丹相互爱慕、相互关照,但是因为石牡丹的犹豫、花儿铁的自卑、人们的起哄,情到深处反而不知所措,只好在“胡骚情”的笑闹中掩饰尴尬,最终在别别扭扭中错失良缘、阴阳两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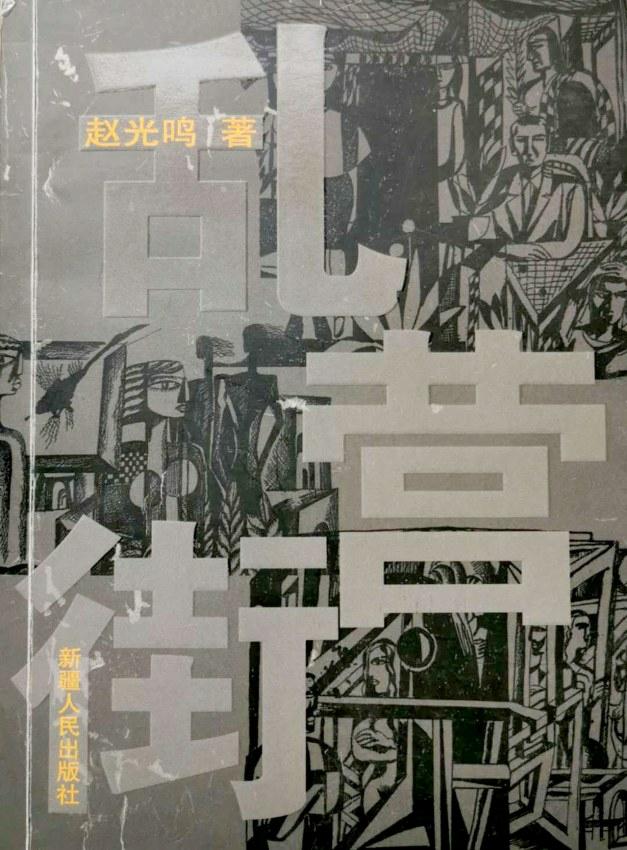
能够抓住的只有原始的、粗鄙的性。小说《逃亡》(见赵光鸣《绝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在小说集《远巢》中又名《乐土驿》)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流亡新疆的火车上,河南卖艺人郅二,趁任英子丢盹之机,“装着瞌睡,一点一点往英子身上靠”,进而把英子揽在怀里,这位跑江湖的便“如久旱逢甘霖,偷眼看她身边的男人也昏昏而睡,便放心搂住她,手挨到那柔软处,禁不住心花怒放,神魂颠倒。他将两眼挤成一条缝,俯视她颈子上毛茸茸雪白丰润的肌肤,灯笼裤里跳得厉害。只可惜一切只能到此为止,这猥亵动作倘再做下去,怕连这点短暂的享乐也要鸡飞蛋打呢……”
赵光鸣并没有对这种不堪的性进行道德上的审判,郅二这种于他人无伤、但有悖文明人道德的、对陌生女人的猥亵,给他带来的是飘零人生中的些许温暖。读者尽可以对郅二的猥亵之举嗤之以鼻,或要为英子的遭遇担忧,但作者笔锋一转,英子与路上邂逅的阎泰娃因被疑偷窃枪支而受到审问和拘捕,却是这位行下流之举的郅二冒险救了他们,并赠送“两个馍、一盒饼干”给英子,助他们逃跑。作品中郅二对性的“窃取”与阎泰娃对性的尊重形成鲜明对比,但郅二的义气与阎泰娃的“不义气”也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无法谴责阎泰娃在生死关口将任英子抛在沙漠独自求生的行为,也难以谴责郅二通过与异性的肌肤接触获取精神慰藉的猥亵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都不过出自别无他途的流亡者的本能。
赵光鸣写“盲流”脱离了“爱”的性,并不是为了谴责这个群体道德的缺失,而是为了揭示他们生存的窘况。当“盲流”们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时,“爱”只能是奢侈的美梦,性才是可以抵达的现实。因此,性的意义不是在身心结合中对“爱”的完成,而是在空茫中对可怜的快乐的享用、对生命的真切感知和对生活的实在把握。李银河在谈到对虐恋的态度时曾说,“有些人总是要把人的快乐与道德连在一起,其实,在多数情况下(无论是虐恋还是换偶),性只不过就是一个快乐的问题,是人们在短暂的生命当中的一种游戏而已,就是这么简单朴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可怜的小小欲望而已,用不着那么危言耸听……”(见《李银河性学心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对于“盲流”未卜的、充斥着苦难的人生而言,性也许不仅仅是快乐,很多时候它还可能是慰籍,是力量,是希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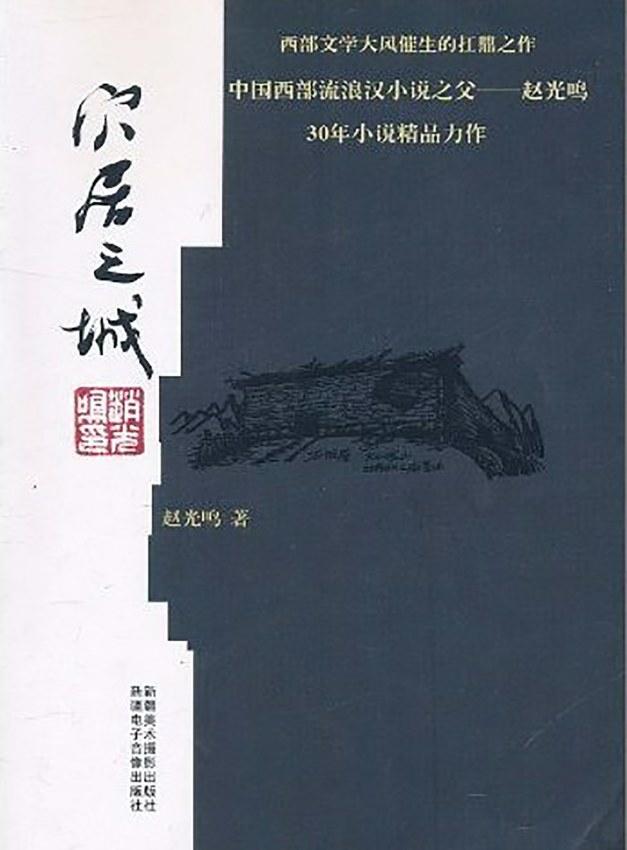
“盲流”的社会是文明秩序之外的世界,人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又为着共同的生存目标杂处在一起,常态文明社会的观念礼仪都在这里发生变异,“盲流”们遵循的是人性原初的善与恶。关于性,关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盲流”们的态度和认识自然也是混杂多样的,秩序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几乎失去了评价能力和现实意义。难堪或愉悦、丑陋或尊严、有爱或无爱,性是“盲流”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越轨之处正如同“盲流”的人生——生存是无奈的,性也是无奈的。
三
当然,在这个混杂的群体中,有一部分人通过并不光彩的性来感受活着的快乐,也有一部分人受所来自的文化系统的制约,仍保持着关于性、关于人生的严谨态度。赵光鸣中篇小说《西边的太阳》(见《当代》,1991年第5期)里,陇西南农民赛麦堆的家乡塬顶村太贫穷,“他是实在待不下去了,才决定携家带口外边世界谋生的。”贫穷让他变得卑躬屈膝、失去尊严,但是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打他婆姨的主意时,他愤怒了,“我赛麦堆给人下跪磕头,脸皮掖到裤裆里做孙子都行哩,那是我把自己不当个人把你当个人,你当个人就该像个人,你神气威势你还是个人,你趁人之危占人家老婆的便宜你就不是个人,是个驴!是个畜生!”他放弃了落户的可能,走上了更漫长的流亡之路。《石坂屋》里东乡族的穆生贵海成子夫妇还恪守着最保守的性禁忌,海成子连给花儿铁洗补裤子都犹豫着不敢做。
如果说赛麦堆们是借两性关系的纯洁性坚持着“盲流”最后的自尊,那么另一些“盲流”则借性的征服力来坚持自己生存的合法性。
带有寓言色彩的小说《绝活》(见赵光鸣《绝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以沙洲流落来的延寿强大的性能力来隐喻“盲流”顽强的生命力。延寿“长得英眉俊气,笑得很可人”,“他会唱秦腔、郿祁戏、花儿、莲花落、武都、康县、礼县山曲儿也会,还会说古,封神榜、瓦岗寨、刘关张、窦尔敦,他让人听得如醉如痴。”因此赢得了芳甸所有女人的青睐,而他那令村子里的男人们“倒抽了一口气”的性器官更让女人们神魂颠倒。在“盲流”延寿的性征服力面前,芳甸的男人们失去了原住居民的优越感,显得那么卑怯和委琐,他们合起伙来用延寿劁鸡的“绝活”把他劁了。但是被阉割了的延寿依然顽强地活着,他那被埋在碱土里的性器官长成了一棵能遮阴凉的大树。芳甸的男人女人们都来看这棵树,“延寿压根儿没有走,他成了女人们心目中的一处风景。”
弗洛伊德说:“人体从头到脚皆已顺着美的方向发展,唯独性器本身例外,它仍保持其属兽性的形象,所以不论在今日、在往昔,爱欲的本质一向总是兽性的。”(見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林克明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延寿的性器官就是富有生命强力的兽性形象,它不受道德约束,不听“人”(王顺)的劝阻,不顾已知的威胁,奔突在芳甸女人身体和灵魂之间。他为自己赢得了不亚于甚至超出原住民的认可度,以参天大树的形式扎根在了异乡。作品关于延寿的描写,颠覆了原住居民与“盲流”二元结构间天然的中心/边缘、优/劣的关系,“盲流”越来越成为不容轻视的外来力量,吹皱了保守的地方主义的一池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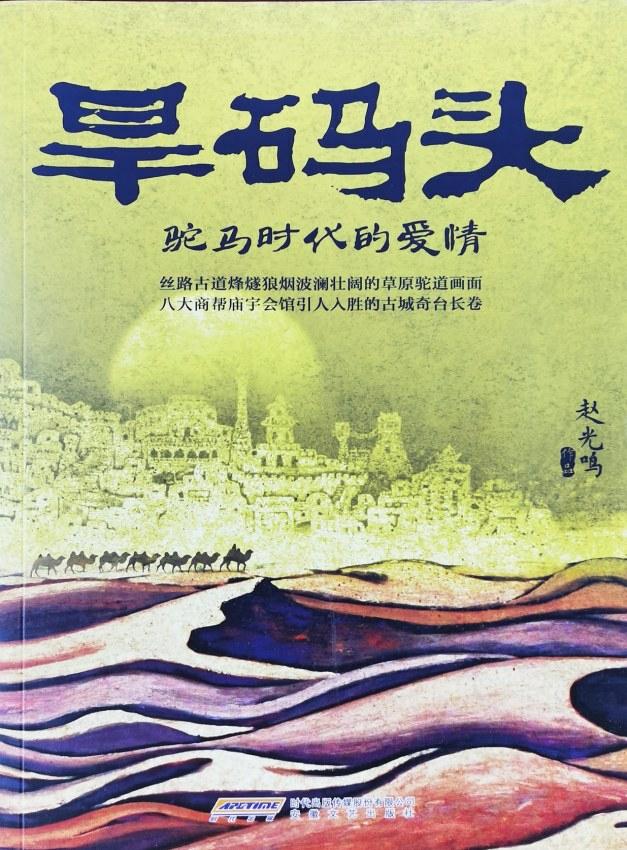
性是人的本能,生存也是人的本能,赵光鸣敏感到生存与性在“盲流”生命中的同质性,通过男人-女人关系的书写,倾诉其对人生和人性的理解。恰如兩性关系的胶着与无奈,“盲流”的人生在缠绕不清的外在压力和内心向往中亦主动亦被动地行进“在路上”,“盲流”的人性在粗野中有真诚,在良善中有鄙俗。“盲流”们的欲望滚动在原始的动物性与文明时代的道德律令之间,似乎与现代的、文明人的所谓“浪漫”爱情相去甚远,但却暴露出“性”最本真的丑陋与美好。它可能是他(她)们被迫背井离乡的动因,可能是他(她)们旅途中的痛苦深渊,但某些时候又会成为这些沦落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荒寒”的漂泊旅途上彼此温暖、汲取力量的方式。“西部的自然、气候比较荒寒,西部的人生也可称荒寒,但大西北的性爱并不荒寒,因为发生在荒寒的环境里,它比温柔之乡的南方或东边更加炽热。压抑得越厉害,爆发得越猛烈。”(《赵光鸣访谈录》,见《绝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生存百态就像性,或美妙、或肮脏、或亢奋、或凄楚地铺展在每一个“盲流”的生命之中。
赵光鸣洞悉“盲流”人生,将自己对“盲流”(以男性为主体)人生的理解和同情附着于一个个微小的故事之中。撒谎、偷窃、粗鄙、卑微和勤劳、坚忍、豁达、自傲,都不过是“盲流”对“活着”的坚持,坚持活下去,坚持活得更好一点,坚持在承受苦难的同时享有快乐,坚持在一片冷眼中获得认同。
从性别批评的视角来看,赵光鸣在书写“盲流”的两性关系时,是存在男性中心的性别偏见的。他在不经意间将女性描绘为他者化的存在以使男性“盲流”们满足“男子汉”的自我想象。比如,《石坂屋》中魏生贵穷困潦倒,落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因为有海成子对他噤若寒蝉的依赖和畏惧,他也便仍然不失为一个强者。《绝活》中的延寿可以在漫不经心中就扰乱整个芳甸所有女人的心,控制了女人们的快乐和忧伤。《乱营街》中有太多将女性作为生物性的欲望对象的画面。但不管怎么说,赵光鸣的书写为我们审视底层群体的生存经验和性别经验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学文本。
有研究者认为,“流寓小说”中垦荒者的流寓心态和情感体验与流寓者从文化中心的东部向文化边缘的西部迁移时潜在的“文化降格”体认有关(李兴阳《从文化想象到重新发现——近年西部小说作家群及其创作综论》,见《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但赵光鸣的“盲流”小说打破了这种刻板认识,他在对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以谋求生存的“盲流”进行书写的过程中,并没有表达“盲流”们因“文化降格”而产生的失落之情,相反,始终在场的东部或中原家乡是盲流们千方百计要逃离的灾难地,而远在天边的新疆却是冒险家的乐园和蒙难者获取新生的希望之乡(“乐土驿”),性有不堪中的温暖,生亦有艰辛中的坚韧,“盲流”们的流寓心态源自由流动生活状态朝向稳定生活状态奋进道路上的失望与希望、磨难与收获,“盲流”们的生存意义也便坚实地体现在永不停歇的行进之中。
作者简介
王志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理事,新疆昌吉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昌吉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性别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曾获中国妇女研究会第四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二等奖,新疆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奖优秀奖。
[栏目编辑:马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