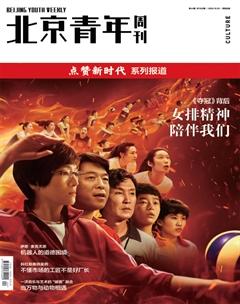伊恩·麦克尤恩机器人的道德困境
王雅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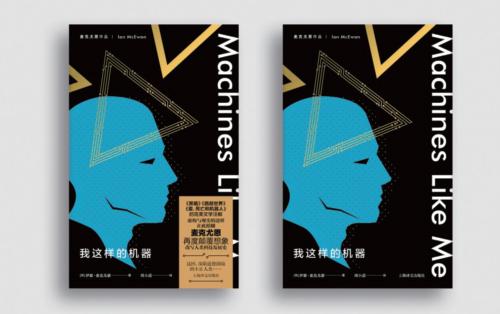
《我这样的机器》
1982年,平行世界的英国伦敦,彼时人工智能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前的发展水平。在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英国在马岛战争中落败,举国哗然之际托尼·本恩当选为英国首相。“人工智能之父”图灵也没有自杀,麦克尤恩给了图灵他应得的生命,而非受到审判、监禁、自杀。图灵得享高寿,活在世人的尊崇之中,他的作品创造了技术奇迹。与此同时,32岁的伦敦人查理开始了两段新的关系……事情也慢慢开始失控。麦克尤恩在小说中探讨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我们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在的生命?机器人能够明白人类的心吗?对于那些人类无法掌控的技术,这部小说将带给读者深入的思考。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早已为世人熟知,关于人工智能,如今人类面临更为复杂的一系列道德难题: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我们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在的生命?机器人能够明白人类的心吗?机器人出轨人类该怎么办?在《我这样的机器》一书中,英国国宝级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探讨了机器人道德困境,其本质最终还是引向了他对人类内心世界、人际关系的密切观察——所谓的邪恶或残忍往往是缺乏同理心的表现。近年来,除了文学领域,麦克尤恩越发热衷于社会热点话题的关注和讨论,经过长期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和研究,麦克尤恩以小说《我这样的机器》交出了一份特殊的答卷——回答了他本人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看法和期待。以下文字摘自本书后记《好机器人必须死》。
小说男主人公查理,是个自由自在的宅男,不上班,他只要电脑、网线,和一小笔钱。股票、期货或者房地产,他每天就在各种投资投机市场上找机会。有时赚有时赔,基本能满足温饱。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青年,他接受了一种价值中立的道德视角。因为进化心理学、因为文化人类学,它们的初级课程往往会让人获得一种相对主义的伦理自由感。这种道德相对论让他在税务上闹了一点小麻烦,上了法庭。政治上查理有点保守,支持撒切尔对马岛的远征,他的女朋友米兰达则绝不认同,为此他们争论起来。那是他们第一次吵架,造成了让人吃惊的后果。
仿生机器人亚当夏娃们上市时,他正好继承了一幢房产,卖掉房子得到一大笔钱。宅男们总想比别人抢先一步进入未来世界,如果能力有限,就买下可能通向未来的新潮电子产品。尽管只是测试产品,beta版,而且要花8.6万美元,他也毫不犹豫下单了。公司统共只推出了25个,12个亞当,13个夏娃。他买到亚当,虽然他本想买一个夏娃。
女主角米兰达,社会史专业博士、查理楼上的邻居、比查理小10岁。她也算亚当的半个主人,查理自己向她让渡了这个权利。他一直不知道如何向米兰达表达感情,也许希望这个机器仆人能成为某种联结象征。亚当会进入他们俩的生活,查理觉得当他和米兰达一起关注亚当,创造亚当后,就会自动成为一家人。
亚当确实需要他们“创造”。因为查理把它领回家时,它仍是原厂设置,亚当可以按照说明书,在个性化设置上“自由创造”。他决定了,自己只完成一半,另一半让米兰达勾选。如此一来,他和米兰达那种看起来有点不切实际的关系,就能够凝结在有形实体上了。但这个慷慨的举动将会成为日后所有困扰的起点,此刻他并未预料到。
在小说中,这批测试版仿真机器人于1982年面世。把人类目前远未实现的科技能力设定在过去历史时间当中,是常见的科幻故事装置。让一种未来技术通过时间装置穿越回过去,或者索性立足于现代物理学观点,构造一个平行世界。作者由此可以技术决定论地设问:科技发明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命运?但这部小说并不关心此类问题,让亚当在1982年来到查理家中,或者让它在2032年出现,看起来没什么差别。
我们猜想起来,麦克尤恩让故事发生在1982年,更可能是出于——作为一个小说家,对有关机器人的大众叙事历史和观念变迁的关注。有一个历史统计数据,到1981年,日本汽车装配生产线上已使用了6000多个机器人,同一时间英国只有370台工程机器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是大力鼓吹广泛使用机器人作业,此举或许也是首相对各地不断出现罢工浪潮的冷酷回应。当时英国失业率常年徘徊在10%,撒切尔推广机器人的言论得罪了工人大众。本来憎恨机器的卢德派在英国就有久远历史渊源,政府和工人们两相激发,机器人成了那个年代英国人最热门的话题。
事实上,如果你在谷歌图书词频(GoogleNgramViewer)上检索“Robot”(机器人)和“AI”(人工智能),就会看到这两个词在80年代初异军突起,在整个80年代形成一个高峰,到90年代反而渐渐下落。事实上,最令人难忘的机器人电影就是此刻拍摄的——1984年上映的《终结者》。显然,智能仿真机器人是那个时代极其广泛的大众话题。那时候,麦克尤恩刚搬家到伦敦没几年,出版了几本小说,开始创作剧本,与同道友好交往,参加午餐会讨论热门话题,也许这个有关“比人更聪明的人造人”的想法,在这个30岁出头年轻作家(正是小说中查理的年纪)的内心,一度掀起过极大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