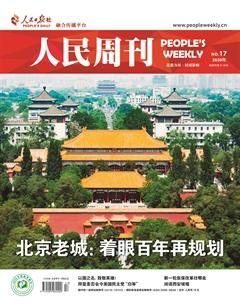旗袍情结
吕易欣

前阵子收到了一件旗袍。不用想,便知道是姥姥做的。
姥姥一直是爱旗袍的。年幼时没有条件,年轻时没有机会,等到年老,她才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旗袍情结系到生活中去。伴着阳光的温暖,听着缝纫机嗒嗒的伴奏,一件旗袍便在姥姥手下成了形。这时,姥姥总会把旗袍捧在手中,在阳光下眯着眼细细欣赏,端庄而虔诚。
姥姥不仅爱做旗袍,还爱在跳舞时穿旗袍。年过花甲,依然挡不住她对美的追求。曾有一次,母亲带我看姥姥的舞蹈演出。姥姥身着得体的旗袍,手持轻罗小扇翩翩起舞,朴实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没有半分忸怩作态,仿佛一枝清荷随风摇曳,摇落一地芳华。姥姥跳舞,激起了我的憧憬,似乎在我的心里系上了一缕憧憬的丝线。演出结束后,我摇着她的手央求道:“姥姥,我也想有一件旗袍。”她摸摸我的头,笑意漾出了眼眸,“好。等你再大点,姥姥给你做啊。”时光如白驹过隙,我早已将这句话忘在脑后,没想到,姥姥却一直记着。
我举起这件旗袍,它看上去是那么平凡。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精致的盘扣,没有名贵的布料,一如它的制作者,朴素而真切。我学着姥姥的样子,眯着眼睛细细地看,才发觉这件格子旗袍做工精细,布的拼接、缝合十分仔细,没有一处粗大的针脚。立领处的盘扣盘得妥妥帖帖。刹那间,我仿佛听到缝纫机嗒嗒的声响,姥姥踏着缝纫机的景象又出现在我眼前。
她在裁剪好的布料上先是车缝省,要做出收腰,却忽然停下来,若有所思地用手拈着布,嘴里还念叨着什么。反复几次后,终于做好了恰如其分的收腰。然后她把衣片一点点地缝起来,细小的银针在其间不断穿梭,姥姥神色庄严,不见一点疲惫的神色。她将她的旗袍情结一点点地缝进了衣服里,好像只有这样,她才会心安……
再次见姥姥时,我特意穿着这件旗袍。姥姥那一天竟像小孩子一般欢愉,忽地快步上前,又忽而后退,从不同的视角审视着自己的作品,不时转头对母亲说:“多好啊!多好啊!”霎时,她好像发现了什么,眉头微蹙,轻轻地叹:“这盘扣是不是钉歪了?”她很执着地要修改,我和母亲怎么都拗不过她。几天后,姥姥将改好的旗袍送了过来。她看着我穿好,眼睛不住地打量,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忽然认识到了这件旗袍的价值。它的样式是平凡的,但是这件旗袍里装着的,是化不开的浓浓亲情,是一种工匠精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不天从人愿,姥姥却依旧在心里装着对旗袍的喜爱;外表不天生丽质,她却敢于追求自己心中的美;手艺不无与伦比,她却极为虔诚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作品……这件旗袍,它平凡而又普通,但是它庄严、它真诚、它隽永!这便胜过一切。
我好像明白了姥姥为什么对旗袍情有独钟。一种崭新的感受注入心田,仿若一泓清泉。喜爱也好,震撼也罢,这旗袍情结,就这样在我的心里系上了。
一个下午,夕阳西下。我、母親、姥姥,三人身着姥姥做的旗袍漫步。夕阳无限好,但我只觉得,夕阳再美,也抵不过我们三人身上的旗袍耀眼。我们爱它的平凡,爱它的真诚、隽永,这是我们的旗袍情结,这是山川可以为之而失色,繁星可以为之而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