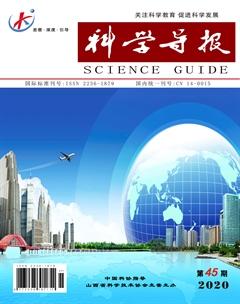聚焦1980年代农村题材话剧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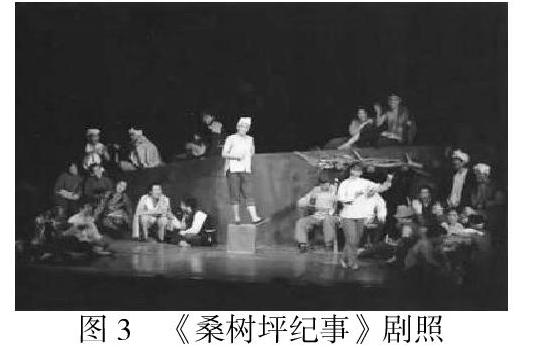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应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自1907年《黑奴吁天录》上演标志着中国话剧诞生起,110多年来中国话剧始终把自己的发展命运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为警醒国民意识、激励民族斗志、凝聚民族力量、启迪大众思想贡献着自身的力量。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文艺作品创作中对农村题材的深刻关注和对农民群体的人文关怀具有源远流长的时代传承,话剧更是自诞生初期就始终保持着对于农村题材强烈观照。创作于“五四”时期的话剧《新村正》、1924年的话剧《获虎之夜》,着眼于揭露农民悲惨的生活境遇;1930年时期熊佛西在河北定县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戏剧试验、李健吾创作的话剧《村长之家》、洪深的“农村三部曲”:独幕剧《五奎桥》、三幕剧《香稻米》和四幕剧《青龙潭》,关注农民和地主围绕权威和利益的抗争,这些作品以深刻犀利的视角关切农民的生存疾苦,批判现实、启蒙民智,促成了中国话剧农村题材创作的第一次艺术高峰。抗战时期,话剧作为最容易被大众理解接受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一,承担着在斗争中宣传思想和凝聚民众的重要政治功能,这个时期虽然基于农村生活创作的剧目众多,但核心要义并非是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本体的关注,更多是为抗战的政治目的而服务。新中国建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时期,农村题材的话剧发展相对缓慢,多数作品集中塑造了一批“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创作思路偏向概念化和公式化,直至“样板戏”达到标准化创作的顶峰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题材话剧作品再次呈现出旺盛的创作热情。脱贫致富是新时期的时代最强音,也是话剧作品创作的一大主要内容构成,这部分的作品聚焦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和农民产生的影响,展现乡村巨变。进入新时期,农村面临着城市化进程的冲击,城乡关系更为复杂,话剧创作也更广泛地涉及到留守儿童、打工人群等新的农民群体,传统的“乡土文化”在现代精神文明冲击和消融下人性的复杂困局等新的农村问题上。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之年,这对于我国的农村和广大农民群体而言尤为意义重大,笔者创作本文的目的正是希望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话剧作品中农村题材的创作、农民典型人物的塑造,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从话剧作品的角度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农民群体的奋斗史、变迁史,通过舞台的空间触摸农村在新时期蓬勃的时代脉搏。
一、1976年-1990年
1976年10月,打到“四人帮”拉开了全新历史时期的大幕。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全新阶段,众多话剧创作者把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思索转化为创作实践,话剧舞台呈现出许久未见的繁荣景象。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得到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给予文艺工作者创作上的自由空间,“解放思想”成为戏剧领域响亮的口号,出现了一大批写实主义作品,集中关注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形成“社会问题剧”的创作潮流。具体到农村,1979年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登上历史舞台,土地由集体制度转向个体制度,这是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历史性的转折,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改变不仅仅是分配方式的变化,更是影响到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在中国农村一贯的精神传承,在经济和精神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变革。这种现实大环境的改变,为戏剧创作者带来了丰富的创作基础。
以1984年探索戏剧兴起为分割线,这个阶段农村题材的话剧创作呈现出两个阶段。其中1976年-1983年的第一阶段,主要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一方面聚焦“文化大革命”以及十年动乱岁月后续的影响,表现“伤痛和黑幕”;另一方面聚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表现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和冲突。主要作品有:1976年湖南省话剧团创作,展现韶山灌区建设新面貌的七场话剧《银河曲》,编剧陈健秋、吴继成、钱公乐、吴仲谋;1980 年江苏省话剧团演出的《带血的谷子》,编剧蒋晓勤、韩勇,讲述七十年代中期,革命干部马震山为保卫南方山区农民利益,与“四人帮”的殊死战斗;1981年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在成都演出的四幕话剧《赵钱孙李》,编剧栗粟、李佩、庞家声,通过“赵钱孙李成一家,父子、母女雙拜堂”这一喜剧性情节,展现了由于党的新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一个普通生产队由穷变富的过程;1981年河北省话剧院在石家庄演出的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六场喜剧《张灯结彩》,编剧宋凤仪、孟瑾,导演宋英杰,以喜剧的形式讽刺了农村买卖婚姻、大要彩礼的陋习;1982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歌颂农村新气象的喜剧《龙飞凤舞》,导演贺昭;1982年长春话剧院演出的四幕话剧《高粱红了》,编剧李杰,导演王常俭,剧情围绕县长郑毅军的起伏命运展开,以浓厚的生活气息展现了“四人帮”覆灭前夕到八十年代初的东北农村生活,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我国农村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以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讲述八十年代初贫穷的东北山区如何脱贫致富的七场话剧《落凤台》,编剧房纯如、杨舒慧,导演肖汀。
话剧导演胡伟民在《开放的戏剧》一文中提出:“我以为应该突破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狭隘理解。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至于用什么手段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应该允许艺术家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开放的剧作,要求开放的戏剧观。要求高度重视并深入表现人的精神生活。因此我认为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处理诸如再现与表现、情节与人物、说理与抒情、客观与主观、感情与思考、事件与哲理等矛盾方面时,不应忽视或削弱后者。我们可以融百家所长,不拘一格,别具一格,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深入揭示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借此表达对现实的深刻思考。”[2]而谭霈生认为戏剧真正应该解决的事戏剧自身的特性与规律、戏剧与社会、生活、政治诸方面关系的问题。在《“形式革新”小议》中他提出:“不应丢掉这些问题孤立地考虑表现形式的革新。原因在于,其一,把‘形式革新看得高过一切,很可能在形式探索的热潮中掩盖了这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其二,由于忽视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存在,孤立地考虑表现形式的革新,很可能在探索新形式的过程中,使这些具有根本性的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这些,对振兴戏剧艺术都是不利的。”[3]胡伟民导演和谭霈生先生的这些观点,体现了当时社会问题剧创作在一段时期的繁荣之后,快速地进入瓶颈期,而在改革开放的整体氛围下西方哲学思想、艺术思潮以及戏剧表现手法和戏剧观念迅速地进入我国,国外现代演剧形式与国内单一演剧模式的碰撞,话剧从业者们对于戏剧创作的深切思考。这个阶段,戏剧理论界在关于戏剧本质、戏剧功能、戏剧创作的发展趋势、戏剧表现形式、戏剧民族化等多个角度就戏剧观展开激烈的讨论,黄佐临的《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徐晓钟的《在自己的形式中赋予自己的观念》、高行健的《我的戏剧观》和《论戏剧观》、童道明的《也谈戏剧观》和《戏剧革新和戏剧假定性》、林兆华的《戏剧观要在实践中革新》、谭霈生的《<当代戏剧观念的新变化>质疑》和《“形式革新”小议》、丁扬忠的《谈戏剧观的突破》、胡伟民的《话剧发展必须现代化》和《话剧艺术革新浪潮的实质》、陈恭敏的《戏剧观念问题》等文章都是期间理论探索的重要文章。戏剧观点的碰撞很快激发了戏剧创作的全新领域,探索戏剧兴起,农村题材的话剧创作也在展示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展开了更深化的探索和思考。
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0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戏剧观讨论的不断推动,农村题材的话剧作品在这个时期呈现出形式新颖、思想深刻、人物饱满等特征,不仅生动地反映了彼时农村的现实生活和农民的心理状态,而且还深层次的观照到农村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农村“乡土文化”在新时期的变化,融入了话剧创作者个体对农村、农村问题的理性思考。这个时期的话剧作品百花齐放,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第一次农村题材创作高峰之后又一次的创作巅峰。主要作品有:1984年长春话剧院演出的二幕七场话剧《昨天、今天和明天》,编剧郝国忱,导演吕贵、宋惠萍,故事围绕技术员指导养殖户科学养鸡展开,而核心却是关注新旧观念交替之时农村的现实问题,通过描写“今天”农村社会中遗留的“昨天”的阴影,来表达对“明天”的期待和憧憬;1984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演出的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四幕风俗喜剧《红白喜事》,编剧魏敏、孟冰、李冬青、林朗,导演林兆华,戏剧通过展现80年代农村的日常生活,关注在新农村的变革中封建意识、陈规陋习留下的浓重阴影;1985年年底长春话剧院在长春市演出的四幕话剧《田野又是青纱帐》,编剧李杰,导演王旭,全景展示了青纱帐深处一个叫三棵柳的小屯从黎明到黄昏一天生活的实录,散文化的戏剧结构是该剧的主要艺术特色;198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多场现代悲喜剧《狗儿爷涅槃》,编剧刘锦云,导演刁光覃、林兆华,剧情通过狗儿爷的坎坷经历,刻画了农民追求土地和致富的心态,舞台表现上融合了写实与象征、体验与表现等多种艺术手法,被认为是北京人艺新时期艺术发展的代表作;1986年长春话剧院演出四幕话剧《榆树屯风情》,编剧郝国忱,导演蔡洪德,剧情围绕老榆树下吴老铁和刘三两家人的对抗展开,聚焦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贫富变化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变化;1988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86届干修班在北京演出反映我国西部农村题材的话剧《桑树坪纪事》,该剧根据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小说”改编,编剧陈子度、杨健、朱晓平,导演徐晓钟、陈子度,舞台创作手法上兼容并蓄地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多种表现方法,被学术界认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88年郝国忱编剧的话剧《扎龙屯》,剧情展示了1953年到1983年之间的四个场景,关注30年间农民群体的命运;198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多幕剧《背碑人》,编剧刘锦云,导演田冲,故事聚焦60年代的农家子弟大学生运生坎坷跌宕、起伏变幻的命运;1989年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的实验话剧《蛾》,编剧车连滨,导演肖致诚,以大写意的手法描写了农村女性悲惨的命运;以及1984年演出的《女儿行》、1984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正月十五雪打灯》(编剧:魏敏、李冬青、孟冰)、1989年演出的《乡村轶事》、1989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演出的《娲皇峪》等等。关于这个阶段话剧创作的艺术特点和探索,笔者想着重对《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这三个代表剧目进行分析和讨论。
四幕风俗喜剧《红白喜事》首演于1984年6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故事发生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村,一户典型的农村三代共聚一堂的郑家:82岁的郑奶奶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二儿子是普通的农民、外号“一根筋”,三儿子是党员、小学教师,四儿子从小过继给申家、现在是申家庄党支部书记,五儿子是党员、大队副业组组长兼片长,孙子热闹党员、复员军人,孙子金豆党员、公安民警。剧情从郑奶奶与齐老贵做主叫热闹和齐老贵的孙女凤蓉订婚开始,早已和齐老贵另一个孙女灵芝私定终身的热闹反对这门婚事,引发两家人的轩然大波,得不到家人支持的二人只好選择私奔。期间还穿插着金豆和寡嫂的爱情,无叔夫妻二人为了不绝户一定坚持要生个儿子等支线情节。最终灵芝为了获得郑家人的认可,在郑奶奶病危之时,同意热闹父亲“借寿”的请求。从人物的设定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是一个颇为“进步”的家庭,郑奶奶抗日战争中积极投身革命、土改时又被选为“评议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革命”;大儿子为革命牺牲;除了二儿子之外,几个儿子和孙子都是党员,可以说这个家庭是经过革命考验接受过党的教育的家庭。但中国农村又有着它特有的“乡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是“礼治”而不是“法治”,是“家族治”而不是尊重个体。这种独特的“乡土文化”不仅是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传承,也造就了中国农民普遍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郑奶奶是郑家说一不二的“老家长”,她重男轻女,迷信算命先生,包办婚姻以及要求睡在自己的棺材里也不同意家人把自己火葬,这些鲜活的生活细节是乡土伦理观念在农村土地延绵的生动例证,也是彼时农村发展过程中乡土伦理观念和现代伦理、法治的直观冲突。话剧《红白喜事》整体而言是一部较为朴素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它最突出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卢卡契认为:“典型的描写和富有典型的艺术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社会的普遍性都结合了起来。因而在典型塑造中,在对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的揭示中,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向就得到了充分的艺术表述。”[4]“老革命”、“老家长”郑奶奶,她的身上还残留着许多封建的思想和迷信的落后观念,但是当听说孙子热闹要退党然后给自己“借寿”时,她怒斥道:“你小子要退党?别看我没动过你一指头,你要敢干出这种事儿,我,我扇你两脖子拐!”[5] 82岁的郑奶奶,她出生于旧社会,经历战斗岁月的磨难,喜迎新中国的建立,并在新时期逐渐衰老,即将死去,变革的现实社会在她身上的烙印正是她内心性格中相互矛盾的部分,这恰恰就是彼时农村社会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问题。话剧《红白喜事》整个舞台的观感很喧闹,这种喧闹中正是用喜剧手法展现的讽刺态度,作为农村题材的作品,笔者认为该剧的处理方式是非常可取且值得借鉴的,因为情节上“红白喜事”的生活细节是农村观众非常熟悉的,导演力求展示的戏剧的生活化拉近了舞台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可以说这种舞台风格是农村观众“喜闻乐见”的;而略有夸张的表演营造出喜剧讽刺的效果,远远胜过枯燥的宣教,我们所说的话剧所承担的文化启蒙作用,正是要通过观众在笑声中的自我观照和反思去实现。
话剧《狗儿爷涅槃》首演于1986年10月12日,主要演员有林连昆、谭宗尧、王领、梁冠华和王姬等人,该剧一经上演就引起了观众和评论界的轰动和热议。陈可雄评价狗儿爷形象“可以和阿Q相提并论”,是“大作家、大导演、大表演艺术家奉献了一部我们时代的艺术精品”[6]。童道明先生评价这部戏是“新的戏剧现实主义”[7]。戏剧大家曹禺先生认为:“两个小时的戏让人过了一生。这个戏既是悲剧,让人看着狗儿爷的一生而感伤,又看到了80年代的发展,令人悲喜交加,感慨万分。”笔者认为,话剧《狗儿爷涅槃》可以说是探索戏剧成就的代表作,它不是简单的描写农村生活,而是从生活和历史的脉络中提炼出深层次的思索和规律;不是单纯地追求形式的创新多样,而是把现实主义创作与现实主义的表现元素有机地融合一身,以独特的现代审美角度,将再现与表现很好地统一起来。编剧刘锦云在和谈及这部戏的创作时,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创作的设想:“在构思《狗儿爷涅槃》这个戏时,我确实是想寻找一个最适于表现这种复杂多变的生活内容的形式。这个戏时间跨度比较大,前前后后二十多年,经历了从土改、合作化、文革、责任承包等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弄不好就会演绎事件而把人物淹没了。所以,我当时想尽量把时代背景推到后面,这种虚化环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集中笔墨塑造人物,刻画主人公狗儿爷的心理。另外,我对传统的中国戏曲比较熟悉,对现代派作品也比较喜欢(比如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 等)。这使我在构思《狗儿爷涅槃》时,一方面吸收了中国戏曲在时空表现上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借鉴了现代派作品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的许多长处,象幻景、回忆、人物心理活动外化形象等等。”[8]
话剧《狗儿爷涅槃》的剧情围绕着农民狗儿爷(本名陈贺祥)跌宕起伏的命运展开。狗儿爷给地主祁永年当了半辈子长工,父亲和人打赌,活吃了一条小狗,才赢了两亩地。狗儿爷坚信一个道理:“庄稼人地是根本,有地就有根,有地就有指望,庄稼人没了地就变成了讨饭和尚,处处挨挤兑。”[9]由此,故事以狗儿爷和土地的纠葛为核心,描述了狗儿爷“三起三落”的人生。第一个起落是土改时期,狗儿爷冒着子弹不惜性命收了地主祁永年二十亩芝麻,分到了土地,买了大菊花青,续娶了19岁的年轻小寡妇,还用三担芝麻便宜换来了三亩村东大斜角的肥田,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但合作化,所有的土地都归集体所有。“酒净了,人醉了,菊花青没了,气轱辘车没了,地没了……”狗儿爷在父亲的坟前哭诉着,失落感和不甘把狗儿爷的精神逼迫到了疯狂的边缘。第二个起落是文革时期,神思恍惚的狗儿爷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土地”,独自一人在风水坡开垦了一片荒地,儿子陈大虎娶的媳妇刚刚怀上身孕,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丰收让狗儿爷的生活似乎再次燃起希望。然而这片狗儿爷独自辛苦开垦的荒地成为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所有的希望再次成为泡影。第三个起落是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度,土地和小菊花青终于回到了狗儿爷的手中。满头白发,暮年沧桑的狗儿爷已经丧失了年轻时“庄稼人有闲死的,没累死的”的斗志,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孙身上。而儿子陈大虎已经不打算继续“土里刨食”的生活,一心打算拆掉门楼,在自家的土地上兴建白云石厂。狗儿爷一生的希望再次落空。
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农民问题的根本就是土地问题。话剧《狗儿爷涅槃》一剧中,正是运用意识流和倒叙穿插的手法,深刻地反思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现实问题。土改前的狗儿爷是悲惨的,半辈子做长工,被祁永年吊在门楼上抽打,而土改后获得土地的狗儿爷,面对祁永年时高高在上,写契约时很得意可以让祁永年“伺候”自己一回,想把祁永年的印章据为己有,“把‘你磨了去,重新刻上‘我——陈贺祥”,甚至梦想着“姓祁的,哪天老天也把你挂在这儿门楼上打打秋千。你狗儿爷有这么大权力?有!谁给的?咱政府!”可以看出,狗儿爷内心深处对“地主梦”的渴望,这是几千年传统农业生存模式刻在广大农民心目中无法磨灭的印记,其中既包含着农民渴望生活富裕的期望,也有着“小农经济”深层次不可忽略的历史局限性。作为被剥削者,狗儿爷无比仇视并痛恨着地主,但在他的灵魂深处,他做梦都想着能过上祁永年那样的地主生活。剧中,老年狗儿爷对自己青壮年生活经历的回忆、内心独白以及与祁永年灵魂思辨的幻象交替出现,突破了现实时空的桎梏,省略了大量生活化的现实细节,让剧作者的创作意图即狗儿爷这个人物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形象的复杂性得以清晰呈现。编剧刘锦云在采访中介绍道:“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我是对农民的不幸遭遇想的比较多,但是后来,我漸渐感觉到,仅仅去歌颂他们的纯朴善良或仅仅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是不够的。做为一个作家,不仅能够在生活的血泪浸泡中“有所感”,还要能够“有所悟”,就是说,要超越自己的表现对象,去思考形成这一切的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社会的诸种复杂根源。这样,当我和我笔下的人物(当然,也是我生活中的人物)拉开一定距离的时候,便不仅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可爱、可怜之处,也看到了一些可恶、甚至一可憎之处,这些历史积淀于他们身上的复杂因素引起了我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思考。我感到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不经过“蜕变”亦即“涅槃”是没有出路的。我写狗儿爷这样一个复杂的农民形象,就是想表达我对生活的体验与思考。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农民比较熟悉,另一方面,我觉得,写农民更能表现我们的国民性。”[10]笔者认为,以核心人物的一生去透视一个时代,而非让时代去影响人物,是话剧《狗儿爷涅槃》的独到之处。人物是命运真正的主角,人性是决定人物命运的根本,而狗儿爷人性中的复杂性正是植根于农民身上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剧作者对农村题材深层次的反思。最后笔者还想谈一下剧中象征手法的运用。狗儿爷和地主祁永年既是活生生的人,亦是农村两个阶级的象征。高门楼是高门大院富裕生活的象征,是“地主梦”的象征,亦是狗儿爷内心深处欲望和憧憬的象征,是“小农意识”思想的象征。剧终时,狗儿爷和地主祁永年在火光中渐渐隐去身形,轰鸣的机器声中高门楼在火光中逐渐坍塌,象征着旧时代农民悲剧宿命的终结、新时代农民崭新生活的开启。
话剧《桑树坪纪事》剧本改编自朱晓平三部中篇小说《桑树坪纪事》、《桑塬》以及《福林和他的婆姨》,展示了桑树坪——这个被大山层层包围、贫困封闭的西北小山村的村民,在1968年至1969年前后的生活和命运。大幕拉开,远处传来雷声的滚滚轰鸣,塬上金黄的麦子眼看即将被暴雨冲毁,桑树坪的村民敲锣打鼓声势浩荡的走上黄土高坡,要把暴雨赶到隔壁的陈家塬,而陈家塬的村民站在他们对面,高呼着把雨赶到桑树坪。两村的村民由赶雨变为了对骂,大雨在雷声中倾盆而下,对峙双方紧张的人群四下逃去。桑树坪的故事在歌队沉重且激昂的歌声中,娓娓道来。全剧以“围猎”这一桑树坪村民的集体舞台行为,贯穿讲述了四个悲剧事件。第一个悲剧是“捉奸”,李金斗为了将彩芳嫁给自己的小儿子仓娃,带人打断了麦客榆娃的一条腿,榆娃被迫离开桑树坪,彩芳最终在李金斗的逼迫下跳井自杀;第二个悲剧是“失贞”,“阳疯子”李福林疯疯癫癫,新过门的媳妇青女只能期望用情爱来唤醒他的本性和良知,而李福林在村里闲后生的撺掇挑逗下,高喊着“我的婆姨!钱买下的!妹子换下的!”,残忍、但却天真无邪地当众撕下了青女的裤子。第三个悲剧是“夺产”,上门女婿王志科是桑树坪李姓氏族中唯一的外姓人,妻子死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在桑树坪,为了得到他的自留地、口粮和破窑,李金斗组织村民以“杀人嫌疑犯”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送到了公安局。第四个悲剧是“杀牛”,耕牛“豁子”是“一村人的命根根、心尖尖”,平日里不舍得犁下太深、上坡也不能只靠牲口拖,生怕会把耕牛累坏,更不允许任何人打牛一鞭子。为庆祝公社成立革委会,大队点名要求宰杀“豁子”张罗宴席,被激怒的桑树坪村民亲手打死了“豁子”。剧终时,歌队从舞台纵深歌唱着向台前走来:“中华曾在黄土地上降生,这里繁衍了东方巨龙的传人。大禹的足迹曾经布满这里,武王的战车曾在这里奔腾。穿过一道道曾紧锁的山峰,走出了这五千年的梦魂。历史总是提出这样的疑问,东方的巨龙何时还能猛醒?尽管前面有泥泞的路程,尽管有多少山峰需要攀登。总是这样不断地自问,总是这样苦苦地追寻。”[11]表达着导演对历史、文化及民族性格的批判和反思。
桑树坪在空间上是封闭的,层层叠叠的大山围困在它的四周;桑树坪在精神上也是封闭的,极度的贫困、封建思想的桎梏和传统“礼治”的落后观念将村民们紧紧捆绑着,“它使桑树坪人盲目而麻木地相互角逐和厮杀,制造着别人的也制造着自己的惨剧”。[12]这里生活的人愚昧落后、麻木不仁,为了维持活下去这个基本的生存欲望彼此野蛮地撕咬和伤害,抛弃了道德和文明的底线。李金斗作为剧作的核心人物充分体现了这些特质。李金斗有善的一面,为给村民多留点粮食苦苦央求,挨了耳光也不生气;他是不讲情面的专制老家长,为了省下彩礼,让彩芳改嫁给自己的小兒子仓娃,为解决李福林父母给儿子娶媳妇的难题,把月娃卖去做童养媳,换回了青女,一切都只是为了延续香火的目的;他也是冷漠的统治者,恪守宗族的刻板观念,不择手段驱逐“异姓人” 王志科。不同于多数文学作品中,农民形象的愚昧、陈腐以及一点点的狡猾,“围猎”这一舞台行为的贯穿使该剧中的村民更具有残忍和麻木的特性,且这种特性还是群体性的、无法对抗的。导演徐晓钟谈到剧作对人物的选择和刻画时认为:“他把自己的焦距对准桑树坪这些默默无闻的小民,是要通过他们来认识我们的历史和今天。他写的是小桑树坪,观照的是大桑树坪,桑树坪人身上有的某些性格基质、文化心态,我们身上有过,或者现在也还有;桑树坪人的命运,我们有过,或许也还可能有。《桑》剧全体创作人员怀着对我们民族——苦难母亲的赤子之爱,来改编这部小说并把它呈现在舞台上,希望通过李金斗和他的村民们的命运引发人们对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激发自己的民族自强意识,希望《桑》剧的演出能折射出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3]
从舞台的表现看,该剧集中体现了1980年代戏剧形式探索和实验的成果,导演徐晓钟在继承现实主义演剧方式的基础上,采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并融合了音乐、舞蹈、祭祀仪典等多种艺术语汇元素于一身,形成了该剧独树一帜的舞台风格。在导演手记中,导演徐晓钟介绍道:“我一直想通过一台戏的演出甚至包括剧本创作表述自己这几年对戏剧发展的思索继承现实主义戏剧美学传统,在更高的层次上学习我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原则,有分析地吸收现代戏剧(包括现代派戏剧)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辩证地兼收并蓄,以我为主,孜孜以求戏剧艺术的不断革新。”[14]表现与再现两种不同的美学概念,在本剧中通过舞台有机地结合起来,导演将生活幻觉和非幻觉共同营造出诗化意象的情境,尤其在杀牛和青女化身这两个场景尤为清晰。这种诗化意象的情境会同时激发观众理性思考和情绪激荡两个层面的情感波澜,超越了以往单纯现实题材创作的瓶颈。笔者认为这种艺术探索的“实验”,在彼时话剧出现冷遇的危机下,是特别有价值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2] 胡伟民:《开放的戏剧》,《文艺研究》1985年第2期,15-17页
[3] 谭霈生:《“形式革新”小议》,《戏剧报》1985年第8期
[4] (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页
[5] 《红白喜事》:《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第14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4月版,第406页
[6] 陈可雄:《“农村生活沤出了我”──记〈狗儿爷涅槃〉 编剧锦云》,《文汇》月刊 1987 年 第 1 期
[7] 童道明:《新的戏剧现实主义——话剧〈狗儿爷涅槃〉观后》,《光明日报》1986年11月13日
[8] 《<狗儿爷涅槃>的创作及其它——剧作家锦云答本刊记者问》,《戏剧文学》. 1987年05期 第48-49+52页
[9] 《狗儿爷涅槃》:《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第15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4月版,第166页
[10] 《<狗儿爷涅槃>的创作及其它——剧作家锦云答本刊记者问》,《戏剧文学》. 1987年05期 第48-49+52页
[11] 《桑树坪纪事》:《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第16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4月版,第417页
[12] 徐晓钟:《在兼容与结合中嬗变(上)——话剧<桑树坪纪事>实验报告》,《中国戏剧》1988年04期
[13] 同注12
[14] 同注12
作者简介:潘晓曦,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专业,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