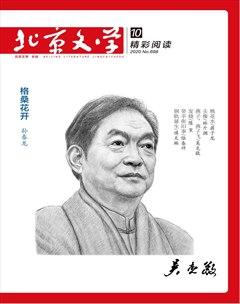将进酒
蔡勋建
最美的风景,原来是自家的屋檐。
——题记(引自文友“金句”)
一
离我结婚前一个月,县里清退“亦工亦农”。亦工亦农,这是个打着时代印记的字眼,20世纪70年代,一种农民合同工,说白了就是也工也农,工人职业农民身份。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我这个吃“背背粮”与临时工没啥两样的合同工司机,被县汽车队坚决地清退了,我无法面对这一现实,为什么要以粮食的属性来分彼此、定去留?事实上我更难面对的是,马上就要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年轻美丽的准新娘——萍。一个“亦工亦农”的“土饭碗”都丢了,我真是尴尬极了,遇见熟人亲友我回避躲闪如小偷一般……
变故突然发生,我没有思想准备,十分错愕。而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这婚还能不能结?我心事重重很难为情地对萍说,我现在都这样了,原来还有一个“亦工亦农”的“护身符”,指望着三五年能转正,可如今一下子成了一个什么也没有了的“裸男”,你可是肉食站响当当的国家职工,咱俩相差太远了,还是拉倒吧,不然你会很尴尬。我说不清这是自卑还是自尊,没想到萍却神情坚定地说,你就是在家种田“打土块”我也跟着你,现在不是有很多“半边户”吗,我们就给洞庭湖区再新增一户。“半边户”,也是时代新词儿,可当年也是丈夫吃国家粮、妻子吃农村粮者居多,像我这样“倒装”的少。萍毫不犹豫一锤定音,很快成了我的妻子。几年后,我终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招工机会,还调换了几个单位,置换了几次身份,也算没让她将尴尬进行到底。然好多年,我很不喜欢与人扯什么“国家粮”“农村粮”,特别忌讳别人提起“亦工亦农”这个字眼。
俗话说,人不轻狂枉少年。我曾经就这样想,男人要么胸怀大志,要么腹有良谋,要么身藏绝技。后来我渐渐觉得昔日的年轻气盛、心雄万丈是何等的幼稚,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按说,我是1970年底16岁入伍的正宗汽车兵,在部队我超期服役三年,本来我是有可能提干的,可父亲的“历史问题”最终成为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1977年3月,我惆怅地离开军营,离开南疆边城凭祥,坐上绿皮火车一路向北,回到湘北华容河畔的家乡。一身刚刚摘去帽徽领章的绿军装着在一个二十啷当岁的小伙子身上,军人气质未褪。应该说,此时我有着三个身份,退伍军人,共产党员,还是一个持军照(待换地方执照)的汽车驾驶员。可在当时,这三个身份还抵不上一个国营单位职工。眼看着一次次的招工机会与我无缘,我迫不及待地去县商业车队干“亦工亦农”,开货车,“山寨”国家职工。
老实说,回乡的那几年,汽车驾驶员还是挺吃香的,尤其在国营汽车队里开货车,跑岳阳、荆州、武汉、长沙是常事。每天清早,车队停车场没准会来许多搭便车的妙龄女郎。等到早餐完毕,司机们都纷纷登上驾驶室发动汽车,这时车队管理人员或修理工师傅给你“推荐”乘客来了,有的“女神”干脆毛遂自荐、笑容可掬地喊着“师傅、师傅”蹭车来了。平心而论,那时天天都有这种“艳遇”,你不可能乱想的,更何况车队领导天天都在给你念着“安全经”。然可怜的是,虽然也有搭车女子一时春心荡漾的,可一听说我是一个“亦工亦农”,有的就立即“勒马”站住,所有的语言都在眼神里表达;有的则忽然像只高视阔步的孔雀不无优雅地走了……萍看上我的那一刻,我不知丘比特的神箭是怎样射出的,我怀疑爱神那时候打盹了,作为当年很体面很自豪的国家职工,据她说当时她就是对我“感觉挺好”,至于什么“亦工亦农”想也没想,于是一种“感觉”为我俩当了“红娘”。
二
我发誓绝不让妻子把尴尬进行到底。然而没有捷径可走,唯一可能的就是让自己彻底“翻边”,再创一个全新的自我。
1981年,《山西青年》杂志创办刊授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据说学生多达52万人。我跻身其中,选学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十几门功课,历时四五年。我在汽车等渡时的洞庭湖边,在冷水当空调的蜗居斗室里,啃完了几十本书,系统地读完了一系列文学史籍、创作教材和中外文学作品。其实,此前我已经悄悄地开始文学创作两三年,自我感到要亟須“充电”才报考刊大的,老实说那时我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新婚不久,我又在另一家汽车队里谋了一个代班司机当——没有余钱剩米让我用于创作。我一直用着读小学时的一本《新华字典》,实在太小儿科,太浅,我好想拥有一本《辞海》。我几次在县新华书店里盘桓,那一部1979年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缩印本《辞海》真的太具吸引力了,我拿起又放下,又拿起再放下,辞书明码标价:22.20元(几乎占去我一个月一多半的临时工工资),可我的兜里只有18元多钱。几天后,我一狠心,向人借了5元钱,如获至宝地将它买了回来。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很难过,她自己领取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我把那借款还上。
我是真正的“妻管严”。妻管我的一切,票子、帽子、鞋子、袜子、衣服裤子,甚至连头发胡子也不放过,买什么穿什么,她会去为你选择安排,什么时候要理发要刮胡子了,她都一一“管”着。有时候散步,她看见某个男人不修边幅、很邋遢地走过,她会鄙夷地对我说,这男人的老婆肯定只顾自己玩。一种轻轻的责备中流露出她守夫有责的自豪。我有时就想,一个人被一个人“走”进心里,一旦生“根”,就不易抹去。我不知为什么让妻子这般宠着,有时候我就觉着“爱屋及乌”这个成语有些霸道与暧昧,而妻子在这个词上有着她独有的话语权。作为丈夫、男人,这个我当然求之不得而且幸运。但我又窥到,作为妻子的女人,她的心里也有不能触碰的地方。
1998年,岳阳长江大堤沿线和洞庭湖区战胜旷日持久的高洪。1999年初,东方歌舞团受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的委托,由党委书记李谷一等率队,专程为全国抗洪救灾主战场之一的湖南岳阳慰问演出。正月十二,东方歌舞团来到我的家乡华容,慰问演出在黄湖山下华容一中广场举行。听说李谷一来了,这个能纳十万之众的大广场人山人海,周围教室里、阳台上,甚至屋顶上、树杈上,全是“谷粉”。李谷一老师深情演唱一曲《乡恋》,现场掌声雷动。后来她又与观众互动演唱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补锅》,更是全场沸腾。我的朋友县文化馆青年摄影家王绮平在台下一跃而上与李谷一搭档配戏,同台演出《补锅》。作为“铁谷粉”,王绮平不但为此“三生有幸”,而且也给了我另一个意外的惊喜。他有意事先备好相机,早在李谷一莅临华容的当晚就抓拍了许多照片。王绮平知道我也是谷一老师的粉丝,照片晒好后特地送我一张。老实说,这张照片真的很漂亮,李谷一老师一袭玫瑰红装,至少又“年轻”了二十岁,乍一看,不定认得出。我当然视为珍宝,腾出一个小镜框,将谷一老师的照片置入其中并放在书桌案头。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发现谷一老师的照片不见了,问妻子她摇头说不知,我书房里到处找遍不见,再问妻子她仍说没见。偶然想到一个敏感问题,于是我对妻子说,你不会以为……把它丢了吧,那可是歌唱家李谷一。远远看到妻子脸上泛红,避开我的目光匆匆走进了厨房。这“案子”再不能深究了。后来,文友们知道了这事,居然成了我的一段“绯闻”,当然也是我们夫妻的一段佳话。
三
2010年接近年底,我的身体上出了大问题。有天中午,午餐毕,正想小眯一会儿,忽然感到腹中不适想如厕,赶紧进卫生间,没想到刚上坐便器,便哗啦啦地拉了一便池,上面也呼啦一声吐了一地,用眼一瞧,上下喷涌而出的全部都是粉红色的液体,天!这是咋啦?妻子和小姨子吓得手足无措,我当时也有点心里发毛,但我马上镇定下来,凭我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过赤脚医生的经验,这是胃出血无疑,至于是不是胃穿孔还不得而知。我赶紧穿好衣裤冲出厕所往楼下跑,妻这才反应过来,说赶紧打120吧。我说不用,我自个儿打的上县人民医院,你们随后赶到就行。
急诊科医生马上送我到住院部病房,立即为我打针止血,紧接着一系列临床检验与预约检查次第跟进。妻子赶来了,一脸的惊恐,我想她肯定是吓坏了。当晚,北风呼啸,寒冷异常,病房里患者满员没空床可用,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旧门板,向护士租来被子,与小姨子在病房就地躺下,两姊妹轮流陪护通宵达旦。
妻子她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也许是她心理过度紧张压力山大,第二天一下子头疼脑涨,走路也如腾云驾雾一般,赶紧让护士量血压,呀,舒张压过100,收缩压过200,医生说别是脑梗吧。好在那天有病友出院,于是就在我旁边的病床上挂瓶吊水,两口子并“床”战斗抵抗病魔。我这里还出血不止,妻子又跟着染病,夫妻双双出问题,那架势真是让人心里发怵,况且女儿远在上海,急坏了小姨子。我想决不能“躺”以待毙,必须有一个镇定的心态,我对我身边病床上打点滴的妻子喊:老婆,你千万不能为我紧张,我没事的,放心。如果我们两个都紧张都害怕,结果就会是你的血压继续升高,我的血压也跟着上升,那最后我们就有可能都走不出这病房。
由于处理及时,胃出血的问题很快得到遏止。但我的家人却仍处在高度的惊恐之中。首先,是胃的检查结果让人惊恐,医生说胃镜检查时“咬”了三处胃黏膜做了活检,寄到长沙检验一周后来了结果,有一处发生病变,疑似胃癌。医生说我25年前胃曾做过部分切除术——准确地说,切除了三分之二——现在忽然大出血,不能排除恶变的可能。医生的推理不无道理。其次,是家族内有胃癌病史——我的在这家医院当过护士长的小姑妈就是因患胃癌去年故去的,至今刚满周年。胃癌会遗传吗?我也弄不清,1969年时期的赤脚医生当年根本还不懂得什么叫癌,记忆中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这种推理足可以让人惊恐万分。当然,我没有见到这个结果,家人也没有人给我看病理报告单,我是从医生办公室经过时隐约听到内科主任与医生们作病例分析,从妻子小姨子的脸上“读”到的,他们有意在回避着我,可能是怕我紧张。好在我那时一点儿也不紧张不害怕,就像一个新兵上了战场,进入了阵地,看见了敌人,居然不害怕了。后来,我自我总结:怕有用吗?怕能解决问题吗?如果这个时刻你怕死,只能死得更快!再说,医生说的那个结果不是“疑似”吗?
出血止住后,病情基本稳定,医生动员我再做一次胃切除手术。我没吱声,但我对妻子说,这个决定让我们到省城长沙湘雅医院后再做。说走就走,我让最小的妻弟高勇请假陪我去长沙,妻子要去我不让,我对口眼歪斜的她说:我怕你太紧张,会害了你,一次胃出血就害得你中风面瘫,我于心何忍。妻子说,你不让去长沙我就不紧张了吗?后来,她还是赶到长沙医院,说不看到我人她不放心。
像是一场诀别,我在妻子无限忧郁的眼光里离开家迅速赶到了湘雅。几天后,胃肠专科主任医师亲自给我做了胃全切除手术,术前周教授征询我是部分切还是全切,我说听您的。周教授认真地说他的意见还是全切的好,万一那个疑似的家伙是個真的,怕会坏事。不过部分切除还留点胃根,还可以慢慢长起来——人体所有器官,唯胃可以再生,全部切除就意味着胃彻底消失了。考虑到胃切除25年后再大出血,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我毫不犹豫地对他说,不留了,永远消除这个祸害。
手术很成功,至今我得以幸存十年。湘雅出院那天,周教授笑着对我说,以后再不会有胃癌来困扰你了。我想那是当然,胃都没了。他又说,你以后可能会瘦一点点,所以回家后最关键的是你今后要少吃多餐,防止营养跟不上而缺血而发生低血糖。周教授告诉我,胃体切片活检结果还真是那个坏家伙作怪,只是刚刚发生癌变。他说,你是因祸得福,幸亏这次胃出血发生得早,再晚个把月,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我当然很庆幸,与死神擦肩而过,我还庆幸,我没有搞过什么化疗放疗,后来一直平安无事。然而我在湘雅住院最初的20来天里,妻子在洞庭湖西天天给我打手机,那份牵挂,那个担忧,无以复加。
接下来,我就要过着“没人胃”的日子,遵医嘱每日“少吃多餐”,全靠肠子消化来保命活命。这对我是莫大的考验,胃没了,一只胃肠吻合器连通上下,医生要求术后半个月这吻合器需要“撑”,不能一味地吃流质,而是面条馒头轮着吞,强行通过,为今后食物通畅练功。这就忙坏了妻子,起初进食我经常噎着,妻子便用空心掌在我后背轻轻拍打,或者用手给我从上而下捋背,嘴里还叨叨着:坚持坚持,闯过这一关就好了。
妻子起早贪黑伺候我,从一日八餐而七餐而六餐而五餐而四餐,直到如今的一日三餐,从稀饭到包子馒头到面条米饭,都是亲手为我操弄。有时上街,不能回家弄餐,她就会过个一时半晌去买只热乎乎的灌汤肉包给我吃下。出院回家当月,已是严冬,我只能半躺着休养,晚上她服侍我躺下,然后在我的脚头挨着我睡下——为了照顾我起夜,她居然打破了我们因鼾声互扰而已然“分居”的约定。妻在那头用手搂着我的双腿,她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我因失血太多而回暖很慢的冰冷的双脚。
我很失败,为人一世就是没养护好胃,胃动过两次手术不说,最后还是丢了胃,差点就丢了命。我逢友人便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算自我解嘲自我安慰吧。想想也许不是我命大,可能是我不怕死,敢于面对,我常常夜思,假如我当时总是惊恐不安,恐怕早已骨头敲得鼓响,假如不是妻子日夜伺候,我也不知能够苟延残喘几天。可是,妻子还未从那惊恐中走出来,一次她对我说:老倌子,当时你病来得那么陡急,那么危险,你可是什么都没跟我说哦!我怪笑着说,跟你说什么,我又没有准备走(人)。
四
我与妻子相濡以沫近40年,眨眼间她也在走向暮年。她才20出头嫁给我,而今已是皤然老妇,她的青春她的韶华她的芳容去哪儿了?我仔细想过,首先时光是掠夺她青春芳华的始作俑者,其次疾病才是戕害她身体容颜的职业杀手。
我不知她的身体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病痛,刚至而立之年,一次输尿管结石引发肾积水,那一次手术简直像一顿杀威棒,几乎剥夺了她的丰腴美丽。及至不惑之年,又一次罹患子宫肌瘤,差点让她崩溃。记得那是2002年秋,我们送女儿去武汉上大学,陪女儿到纺织学院报到完毕,我们就在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住下,医生动员她做子宫摘除手术,她只是不吭声,一切全由我来做主。我知道,作为一个壮年女人她是浑身上下都不愿做这个手术,但医生说她的子宫肌瘤已经有“鹅蛋那么大”了,而且是两个,如果不做子宫全切手术,将来癌变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命她含泪点了头。子宫摘除后,她一直闷闷不乐,有天晚上,我们在医院里散步,她忽然问我:“一个女人,连子宫都没有了她还算是女人吗?”我一时无言以对。少顷我怅怅地说,咱中国没有了子宫的女人恐怕已是千千万……算是我对她的安慰。
翌年三月八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单位工会主席提前一天通知:所有干部职工家属明天都去妇幼保健站免費检查身体。我回家高兴地告诉妻子,没想到妻子一时像触了电一般猛然反弹,她大叫:“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去!”如此反复两遍。我吓了一跳,两眼迷惘地望着妻子,她手里举着一只茶杯,没有摔下去,眼圈红了,有晶莹的泪花闪烁。唉,一个伟大的、与生俱来的、营造人类的巢说没就没了,我理解她的悲伤。
接踵而来的还是不顺。先是更年期的提前到来,焦躁、失眠,无端的发热、出汗,如此折磨十多年。再是下岗,被单位买断工龄,失业。好在女儿女婿争气,他们从深圳“双飞”到上海,结婚又生孩,买房又买车,给我们带来了喜悦,带来了希望。2011年9月,女儿待产,我与妻子先期赶到上海,从小外孙女呱呱坠地到上小学读书,我们一待就是六七年,家里没请保姆,妻子就是保姆。外孙女曈仔出生那年,我正好是大病全休之际,所有家务都由妻子承担。妻子那时膝关节病发,上下楼都困难,在市六医院打了针,疼痛减轻,依然要去买菜购物,日子还真是难熬。然最难熬的还是那个小把戏曈仔一岁多的时候,那个哭闹很邪乎、很准时的,午夜凌晨她就又哭又闹,怎么也止不住,我们叫她“半夜鸡叫”。特别是在三九严寒之夜,妻子抱着小家伙在房间走着,嘴里咿咿呀呀哄着,整宿整宿不睡。有时候小家伙根本就不让你上床,只能抱着走步;有时候她“批准”你上床睡,但你必须抱着她睡,而且还必须让她睡在你的胸脯上。有时候,我不得不想办法换个“新招”,我接过小把戏,一步一步走动,哼着电影《地道战》里“鬼子进村”那一桥段配制的音乐,抑扬顿挫,阴阳怪气,弄得妻子哭笑不得。有时这招儿还管用,有时竟哭闹更凶。想想,养一个小孩子真是不容易!
曈仔闹得更凶了,而且夜夜不休,妻子连最原始最传统的“招儿”都使出来了。妻子很认真地对我说,写几张“招魂贴”吧。我知道她的意思,对着她苦笑,说有这个必要吗?妻子说试试吧,就算是救救我的命吧。我写了几张“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的小贴,夜深人静时,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偷偷贴到临路的大树或墙壁上。妻子一天天憔悴,可她很少生怨。好些时候,我“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为使“半夜鸡叫”不叫,妻子将所有的法子都用尽了,包括改善饮食补锌补钙。等到曈仔午夜不再哭闹,妻子发病了。有天早晨,妻子照例为一家人煮好鸡蛋、蒸好包子馒头、熬好米粥。自从胃切除后,我就有了一个怪毛病,早餐只能吃面条,妻子为我煮好面条外加一个荷包蛋。妻子看着我一边吃面条一边对我说,她昨晚就有些胸闷,这时候好像更厉害了。我用手触触她的额头,没发热,但有点出汗,我知道胸闷又出汗不是什么好现象,赶紧几下吃完送她上医院挂急诊。医生几经检查诊断为“心包积液”,马上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又经痰液培养血液化验乃至专家会诊,排除了肺结核病,但医生告诉我一个很坏的消息,说妻子是心包后面积液,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抽去积液也很困难。我背着妻子偷偷地哭了,为什么会这样啊?自己都病成这样了,还在为全家老小弄一日三餐!我的心情没有瞒过妻子,她看到我的眼窝有泪痕,问我怎么啦?我说没什么,她又问是不是她身体有大问题?我岔开话题,对她说:老婆,你什么时候不吓我呀,上个月你突发急性会厌炎,急诊科医生说再晚会儿来可能有生命危险,赶紧让你进抢救室打点滴。那一次虽然有惊无险,但也让我不敢回望。我望着她,心里暗暗为她祈祷:老婆,这一次你一定要闯过这一关!
许是上天眷顾,奇迹出现了,就在医生正考虑如何进针抽水之际,妻子在服用一周药物后,心包积液居然消失了。我们喜极而泣。
出院后,妻子心情很好,她对我说:老倌子,喝点酒吧。我见她很高兴忙迎合说要得要得。我知道她能喝酒,年轻时候她以白酒回敬“贶杯”,把肉食站主任怼得钻过桌底。她知道我不能喝白酒,且早戒了烟酒,她特地拿出高脚酒杯和女婿孝敬的红酒,一人倒上一杯,我一时兴奋竟而迂阔,端起酒杯说:将进酒。她没听清连忙问什么什么?我笑着说,我敬你。我碰了她的酒杯。我曾在深圳沙头角中英街为她买过金项链金手链,在云南买回过翡翠手镯,她似乎都不稀罕,这些东西没戴几天就进箱入箧了。此刻,我只想对她说一句祝贺祝福的话,还想说一句感激感恩的话,她却夹上一块我最爱吃的红烧猪脚往我的碗里送,然后她很绅士地举起酒杯靠拢我的酒杯,莞尔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责任编辑 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