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转型与戏剧感投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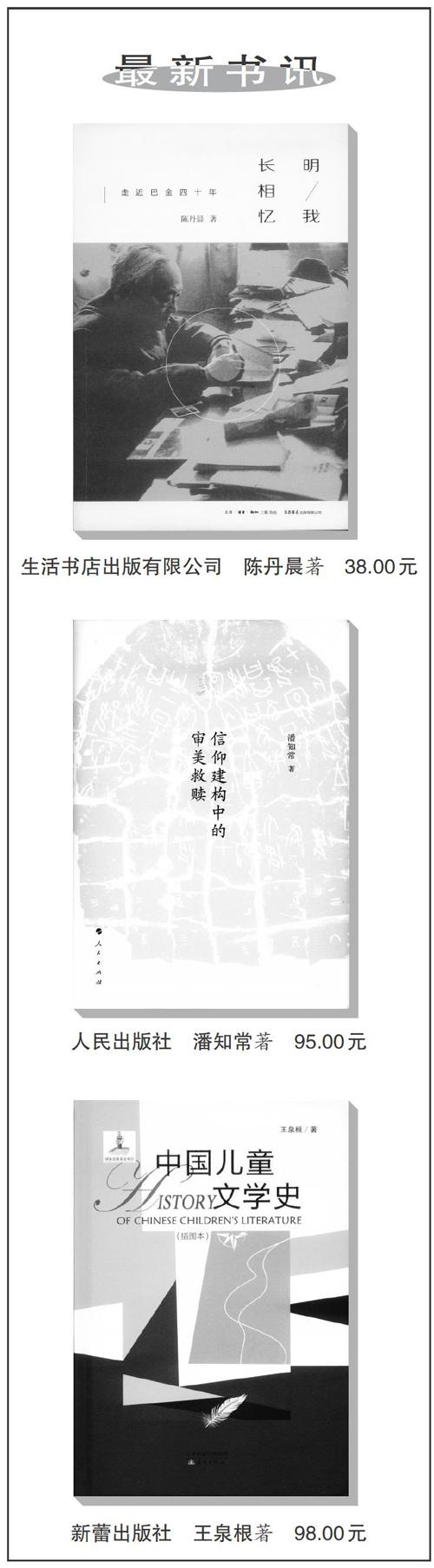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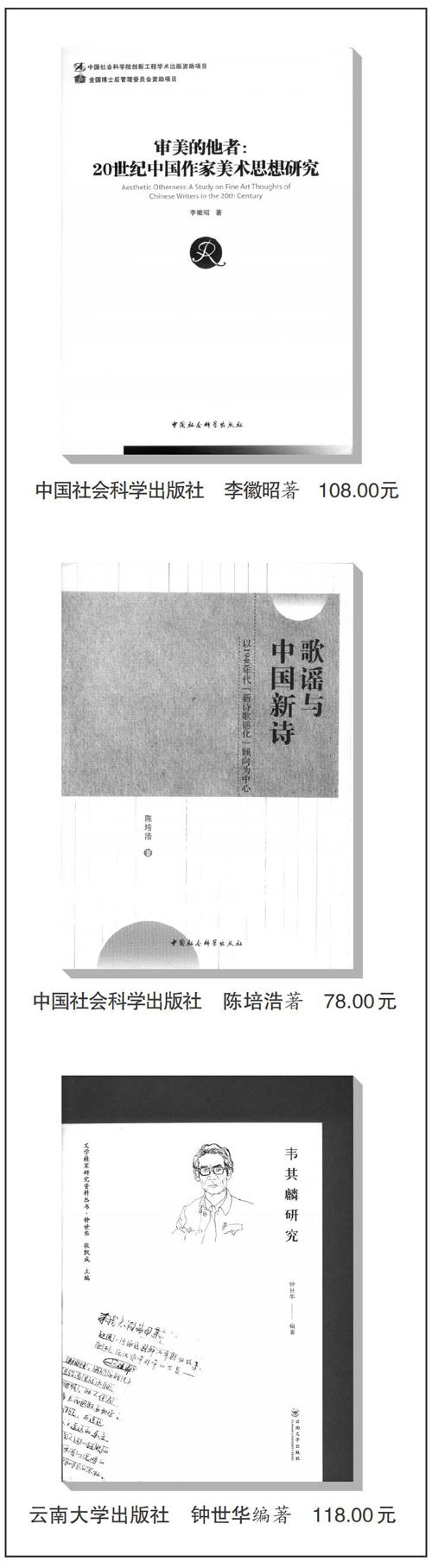

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日战争史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重要的题材资源。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时小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抗战题材小说在国内大文学史景观中已基本完成了经典化过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通过不断地再解读,深化自己的理解和研究层次。进入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创作在原本深入人文价值腹地、重塑民族形象、复原历史本貌、检省道德人性等创作诉求的基础上,在叙事视角、叙事风格、情节戏剧感等写作发生学的技术层面也期冀有所突破,进而确立起本土性和世界性相互交融的艺术风貌,以及多元化、极富张力的创作个性。
近八十年的抗战小说创作发展史也积累了一些创作顽疾——当思维禁锢在某一个苑囿中,不仅想象力疲软,而且其现实焦虑感亦会陡升。陈晓明教授曾在《鬼影底下的历史虚空——对抗战文学及其历史态度的反思》一文中指出了中国抗战小说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书写具有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甚至是鬼化的特点,原因在于这些小说缺乏对时代、对民族、对人性的反思,希望中国作家全面检讨对历史的认知态度,尤其是对邻国日本的认知和理解①。近日,张学昕教授再次明确指出:“1980年代以来的‘抗战叙事,显然还缺乏更宽广、更阔大的历史、民族、文化背景,在精神深度和人性烈度的发掘方面,也还缺少哲学底蕴和理性张力。”②从近二十年的抗战题材小说来看,作家们已意识到思维拓展和叙事转型的必要性,另参考了西方经典战争作品,如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等。除此之外,新世纪抗战小说更为重视创作前期的实地考察、采访幸存者,从民间口述史、地方志等途径收集创作资料,例如熊育群《乙卯年雨雪》、范稳《重庆之眼》等。这样的创作理念既能拉开创作与官方历史文献的距离,又能使民间话语成为最宝贵、最广泛的资源。还有一部分新世纪抗战小说与影视传播媒介有相互成就的关系,“先影视后出版”的新型抗战小说文本,通过强大的戏剧感投射迎合了当下大众立体阅读的要求。总体而言,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创作的个人经验越来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前抗战小说的一部分缺陷,强调了文本叙事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和传奇性,解构了以往的英雄特征与文学的教化功能。本文将从叙事技术层面重点探讨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转型和对戏剧感的把握,以及突破范式规约的艺术价值。
一、“赋予内容以形式”的陌生化叙事
大历史景观的宏大史诗叙事是20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主流书写方式,而后,直面正面战场的血腥暴力美学和死亡书写,呈现抗战历史的惨烈和艰苦卓绝,成为中国抗战题材小说的常规化叙事手段。而新世纪抗战小说更倾向于回避正面战场的血腥暴力与死亡,另辟民间小人物叙事视角之蹊径,通过重视文本的技术构造而强调小说的写作发生学意义。
突破常规的陌生化叙事策略,有非常强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必要性。同一个主流性话题内容,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反复淘洗摘选,可以选择的有新意的内容已经十分有限了,那么如何还能激发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如何能够在已知历史大背景和总结局的前提条件下继续阅读?如何能给读者输出一个有个性的、不雷同的故事体系和人物形象?如何能够给抗战历史一个有新时代意义的文学归属?这些问题都要求抗战小说在叙事方面有转型突破,这既是面对多种文艺形式和传播媒介极速扩张的自身发展要求,也是后现代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创作基础的绝佳场域。近廿年的创作在陌生化叙事方面已经交出了一份不俗的答卷。张翎的《劳燕》即是有意避开抗战情节的正面书写,在正文本中交错引入了书信、日记、新闻报道、地方志、戏文等多种应用文体,通过加强叙事的技术性而创造了一个奇妙的、完整的、有逻辑意义的、更有深度的人物故事。张翎本身十分享受叙事游戏的快感,她把结构、时间、空间和视角形态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叙事不断生成谜团,铺垫悬念,通过读者的猜测和想象前后照应逐一得到验证。
陌生化的叙事策略还体现在对非虚构情境的营构。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尽管小说家可能只能与想象中的事件打交道,而史学家则只与真实的事件打交道,但是把想象与真实事件融为可理解的整体并使其成为表述客体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想象的过程。“作为现实具体的真实与凭借虚构的想象性真实已杂然并存。不过即便是在非虚构写作中,现实具体的真实一旦进入文学创作主体的笔下便必然被赋予一种美的意义,成为心灵感受的真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记者层面‘被表现为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新闻报道式的真实。”③熊育群的《乙卯年雨雪》、范稳的《重庆之眼》、王树增的《抗日战争》,都是在叙事中假借非虚构的外衣而营造了文学想象的幻境,滲透了作者从民间口述史、地方志等途径收集的创作资料,一方面形成了尊重历史事实和官方历史文献的写作伦理,另一方面也营造了极富个性的叙事风格——寄非虚构于虚构中。读者很容易从《己卯年雨雪》中读出一种非虚构性:“60年后,我动员屈原管理区的朋友易送君对‘营田惨案做田野调查,二十多个人历时一年,寻找到了一百多个幸存者,记录了那一天他们的经历。”④这是作者力争还原历史真实状态,竭力复原细节的努力。《魏特琳日记》真实记载了日军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妇女们为躲避强奸更是费尽心机,包括削发、女扮男装、抹锅灰、假装重病等不一而足⑤。小说《金陵十三钗》作者严歌苓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金陵十三钗》描写的“秦淮烟花女子诉国殇”正是受到了《魏特琳日记》的启发。哈金在《南京安魂曲》中也描述了日军索要妓女事件——谷寿夫的第六师团后勤部中佐带着翻译和一百多名日本兵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找妓女。这些史料和文本创作不禁令读者肃穆,相信历史事实比任何虚构想象创造都更有戏剧性和感染力。
当然,还有一种“陌生化叙事”来自远距离观照——抛开受害方立场的滤镜以及国内文化气氛和舆论环境,用一种独立的、既不期支持庇护也不受限制的书写态度来创作。远距离,包括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新世纪抗战小说创作实际上已经存在时间距离,经过了历史沉淀,创作者们对战争本质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而空间距离则比较集中地针对海外移民写作,海外华裔作家力图探索区别于内地很多现实主义抗战小说的叙事模式,试图将中外文化差异融化在人的情感沟通中。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而对于大多数移民华裔作家来说,抗战历史记忆书写似乎又加工丰满了一步——“离去、流浪或是受难、死亡,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对于战争,这类作家群体拉开了与受难症候群的距离,突出了异质特征,产生了文本张力和陌生化的叙事效果。
马尔库塞认为,借助审美形式,艺术具有与日常言谈针锋相对的疏离和异质感。这个想象的、可能性的、梦幻的世界,保存和提供着另一种真理性抉择的记忆和意向。“美,是一种与艺术所有传统形式相联系的性质。美的表现即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当下与将来的统一。美是审美形式中涌现的决定性因素。”⑥对于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来说,叙事之美正可以充分利用“赋予内容以形式”的策略呈现,进而通过审美回顾历史记忆。
二、非典型性叙事的戏剧性张力
可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时小说、“十七年”的战争题材小说以及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战争小说,已然没有给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创作留下太多的“自留地”,因此,很多作家选择创作非典型性叙事作品——这些特殊的、不具有常规或普遍价值的文本创作,反而补足了中国十四年抗战史在艺术作品创作方面的完整性。徐贵祥在千禧之年出版了《历史的天空》,如今看来,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两点极为突出的艺术价值:一来,它的情节推进速度疾快,每一个小事件的发展转折结局都不拖沓,这种叙事节奏很有好莱坞影视的美学特征,但是这也带来了小说文本语言粗糙的缺憾,一些人物语言和心理描写禁不住推敲咀嚼,情节之外的气氛酝酿与营造缺少了回味意境和字里行间的内蕴;二来,它塑造了一个“泼皮无赖”似的人物梁必达(梁大牙),并将其作为中心人物,这个初令人大跌眼镜的构思似乎开启了一个历史战争写作的新纪元——“人性”走在“形象”前面,“性格”走在“身份”前面。这两个方面的美学价值使这部作品成为新世纪初非典型性叙事最为成功和启发性的作品。
在非典型性叙事中,事件和人物是重中之重。一般来说,作家为了构建人物的性格特征,将事件的戏剧冲突性、人物的欲望放置在一个极为重要醒目的位置,但是实现目的达成欲望的过程却极为艰难,跌宕起伏,因此,完成这一过程既是完成叙事,也是塑造人物、构建庞大复杂人物关系网的铺排过程。若想由真实历史作为叙事大背景而成就一个出色的故事,重点在于要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激励事件”,它能够形成后续的连锁反应,就有可能让一个个小事件形成多米诺效应,叙事情节愈演愈烈,人物性格戏剧性发展也明晰起来。《历史的天空》中,每一个小事件的发展都以梁大牙的阶段性转变为结果;同时梁大牙这个人物不是孤立存在的,作家配以张普景这个善良正直的政委作为人物的戏剧行为阻力,当然也是协同梁大牙成长的辅助力。矛盾、冲突、成长,加上叙事延宕与转折,经历意外拐点,使故事本身充满了戏剧感投射,更是一个有逻辑性的叙事游戏。抗战英雄形象由“高大全”式的“神性英雄”,到普通平凡的“平民英雄”,再到“贩匪痞贼”,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完成了英雄的人性回归。
从“伟岸英雄”转向“贩匪痞贼”,是新世纪抗战小说强调人物形象个性化和传奇性的主要手段,也是基于现代史观构建和反思式写作而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进行辩证思考。《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抗日,《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兵痞抗日,《和平饭店》中的土匪抗日,都是通过“反英雄写作”而加强情节的戏剧感投射。或者可以这样说,“表现怎样成为英雄”要比“表现英雄”更有价值感。《和平饭店》中,王大顶在陈佳影的带领和感染下最终成长为“民间英雄”,其传奇性和趣味性阻断了受众对其真实性的追问,而浸入作者营构的独立、合理的抗战叙事范式。密集的矛盾推动,悬疑的铺排埋伏,离奇曲折同时具有生活感的情节故事,大景观多层面、多线索交叉的叙事框架,明确的故事发生场所(和平饭店)以及高密度的叙事时间(九天)——这些具有戏剧性张力的叙事要素和蒙太奇手段,促成了王大顶的快速成长,完成了叙事的目的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兵痞孟烦了以“消解大众印象中抗战士兵一切崇高感”的功能性身份出场,颠覆了以往战争回忆录的崇高写作美学,历史图景在孟烦了的独白中充满了滑稽和反讽。孟烦了的个人主义意识十分突出,这严重消解了以往抗战士兵以国为先、以集体为重的大义精神。他既愤世嫉俗而又尖酸刻薄,因为性格和腿部溃烂残疾,他也比别人更清醒、更绝望。他的绝望在于:他找不到可以归属的带番号主力部队,打不到像样的胜仗,治不好自己的瘸腿,不知道死亡是在明天或是未来的哪一天,他只能徘徊在国门边缘,无法真正尽一个士兵的卫国职责,却又没有胆量死亡。孟烦了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西南战场的关注与反思,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抗战叙事的正常推进,造成叙事的波折与延宕,是典型的以人物性格打造宏观叙事风格的叙事策略。
既涉及《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平饭店》等作品,就不能不提及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中一个特别的类型,即先播出影视剧后出版的小说。21世纪初,《历史的天空》《风声》《潜伏》《我的团长我的团》《旗袍》《刀锋1937》《红色》等制作精良的抗战历史影视剧蜂拥而至,社会文化影响力极大,因大众想通过文字阅读再回味影视作品中稍纵即逝的人物神态、隐晦的悬念机关和明暗交错的复杂人物關系,出版社积极出版了这些影视剧的小说文本,满足了大众阅读需求,形成了文化市场二次推广。影视画面感输出和市场效能转化深刻地改变了作家的思维模式,甚至可以说,为了营造更有戏剧性张力的情节文字,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将影视剧本的写法纳入小说创作。当下许多作家兼有小说家和编剧的身份,例如国内的阿来、麦家、海飞、金仁顺、郑执,国外的彼得·汉德克、马克·扎斯洛夫等,可见,小说家与编剧的创作技巧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影像语言都能够与文字对等转换输出,文学性的聚焦还是更倾向于小说本体,作家在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中更适于找寻一种“平衡感”。
三、注重记忆伦理和道德感的完整性表达
“十七年”及之前的抗战小说在描写日寇暴力伤害的时候,叙事情绪是异常激烈的,人物性格棱角也十分鲜明,表明了意识形态上的立场。进入新时期,作家的书写逐渐变得冷静,接近于客观的零度写作,这对于作家创作和民族观来说无疑是成熟的。情感的输出方式可以通过很多方面,而不局限于用近乎自然主义的写法描写血腥、暴力和死亡等伤害场面。对暴力伤害的叙事表达发生转变,连带着对汉奸和日寇的描写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低能的咆哮、无差别的杀戮、单一的残暴等特性表现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日寇多面性格展现、对所谓“圣战”的执着和忠诚,以及汉奸的矛盾复杂心理,等等。人物变得立体有复杂性,情感输出富于变化,并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弱化了对暴力血腥死亡近乎自然主义的镜面式重现,这一变化更突出了作家的“克制”以及由克制而直接引发的伦理道德感。“新世纪以来,由于世界范围内整体伦理秩序的失范,传统道德休戚与共感的消弭,逼着人们重新思考人类存在伦理的问题,文学伦理问题才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⑦道德感中理性和感受的平衡关系,是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在加强叙事形式审美价值的同时着力攻克的难点。在这方面,西方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和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战时小说给了当下写作者以最大程度、最广泛多样的启发。
老舍的《四世同堂》在战争叙事思想方面达到了空前高度与深度。在文本中,日本老太的两个儿子在中日战场变成骨灰,两个儿媳妇被军部调去充当“营妓”,她发自内心地向中国人(瑞宣)忏悔。日本老太的悔悟,其实是老舍借其口而对战争所作的国际性的深刻反思,老舍先生用极为包容的态度精神给予了这个人物温度,从“人”的角度讲述战争中发生的故事,超脱一般的民族国别意识,使其具有柔软的人情味。这样的大民族意识人道主义写作和伦理学营构,在老舍先生《四世同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退化了,究其根本原因,是大量主题先行的文本创作者对美的实践和道德的象征没有深入准确的认识,而在政治、历史、革命、军队、英雄、民族伤痛等意识形态元素的作用力下书写迎合时代需要的文学作品,美学实践表达也相应符号化、机械化了——直到2008年,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发表问世。
可以说,《小姨多鹤》的叙事逻辑和视角完全冲击了已适应革命历史传统书写方式的中国读者,它不仅以民间立场取代了宏大叙事,完全采用侧写视角叙述战争,还超越了战争本身所蕴含的阶级性、人民性和民族性。中国人的记忆伦理和道德感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得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观照和洗礼。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当年从日本远迁至中国东北的日本平民被抛弃,原代浪村村长要求村民一起自杀,名曰“尊严地死去”。十六岁的少女竹内多鹤凭借着求生本能逃过生死劫,而后被张家买来用以传宗接代。她无力反抗现实,只能不断地用自己的子宫为自己创造亲人,她只能用自己的勤劳、含蓄、善良、感恩和隐忍被动适应“张家小姨”的身份和生活。严歌苓仅在小说开头用最为隐晦的方式揭露了日本战败之后惨无人道的弃民政策,而后面所叙写的竹内多鹤坎坷苦难的一生,都是对这一简省开头的因果敘事展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与殖民中国的十四年时间里,普通日本民众同样经历逃亡、杀戮、自杀、被杀、饥饿等种种苦难,作家选择用这一个特殊的夹缝式人物审视战争对双方国民的长久伤害,极大程度地拓宽了抗战题材小说的想象范畴,更新了叙事逻辑。
“让艺术作品借助审美的形式变换,以个体的命运为例示,表现出一种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的力量,去挣脱神话了(或僵化了)的社会现实,去打开变革(解放)的广阔视野,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也可被认为具有革命性。”⑧用民间话语形态书写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战争中的浮沉命运,一方面是反思战争本质,审省民族情感和伦理情感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满足了当下国人对历史个人化阐释的社会需求。进入新世纪,面对中国目前精英化阅读与历史个人化阐释的社会需求,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逻辑倾向于逃脱艺术生产的工业性,而更直接地对接在想象力这个基点上,令现实与想象竞放。
若把抗战文学创作以命题的方式呈现,那么作家的创作主旨从最初告诉世人“抗日战争应该是怎样的”,发展至今已转向“抗日战争究竟是怎样的”以及“抗日战争为什么是这样的”。作家们在苦思冥想如何能用最为新奇、新鲜、新锐的叙事手法表达抗战故事时,这一个个血色的命题也向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叙事功能要内化,反思并重新建立抗战小说的叙事逻辑。国人需要以大民族意识的文学伦理角度反思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抗战双方的损失也应有更为客观及人道的认识,并以大同情感化解狭隘民族仇怨。熊育群言:“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不仅仅是从自己国家与民族的立场出发,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而是要看到战争的本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寻找根本的原由与真正的罪恶,写出和平的宝贵,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⑨在近年抗战叙事中,以大民族意识为主轴的叙事观逐渐成为主流话语,而大民族意识中又包含灾难、命运、民族、国家、英雄、救世、人性、道义等关于哲学、历史学、人类学、伦理学和艺术美学等多方面的深刻母题,每一个都值得作家们发现与剖析。
【注释】
①陈晓明:《鬼影底下的历史虚空——对抗战文学及其历史态度的反思》,《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②张学昕、鲁斐斐:《“抗战小说”的叙事伦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4期。
③晏红:《文学的真实性与真实的文学性——关于文学的虚构与非虚构》,《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
④⑨熊育群:《己卯年雨雪》,花城出版社,2016,第365、387页。
⑤[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杨夏鸣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100页。
⑥[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17页。
⑦李占伟:《“文学伦理学”建构刍论》,《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9期。
⑧[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205页。
(周珉佳,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