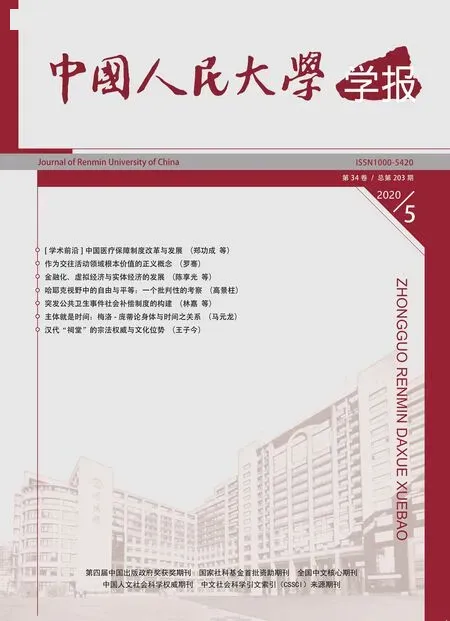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
——兼论“脱实向虚”问题
陈享光 黄泽清
经济金融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伴随经济金融化,虚拟经济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却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出现了“脱实向虚”问题,从而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正确认识经济金融化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解析金融化是通过何种途径和机制影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揭示经济发展中“脱实向虚”的形成原因,探讨强化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机制和金融政策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早在20世纪60年代,巴兰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就已经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剩余流入到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的现象。(1)Paul A.Baran,and Paul M.Sweezy.Monopoly Capital: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6.自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进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始,金融部门的力量迅速上升,以此为基础的金融化研究也大量出现。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Aglietta和Boyer就曾指出,金融主导的增长机制始于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率下行的回应,随着后福特制的到来,凯恩斯理论主导下的经济开始转向金融主导的经济。(2)Michel Aglietta.“Shareholder Valu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Some Tricky Questions”.Economy and Society,2000,29(1):146-159;Robert Boyer.“Is a Finance-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 A Preliminary Analysis”.Economy and Society,2000,29(1):111-145.杜梅尼尔、莱维认为,现在企业对于利润率的维持依靠的是利息和股息而不是投资,流向金融部门的现金流并未回到原来的非金融性公司。(3)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与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载刘元琪主编:《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代表人物福斯特认为,在“垄断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尽管金融化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财富效应,但资本积累所增加的金融资产往往并不能导向产业投资,为增加投机工具而产生的债务杠杆远超过投资于实体经济所需要的程度。(4)约翰·B·福斯特:《垄断资本的新发展:垄断金融资本》,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3);约翰·B·福斯特、弗雷德·马格多夫:《当前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停滞趋势》,载刘元琪主编:《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Lin和Devey认为金融化改变了社会结构关系,资源从工人和生产者手里被分配到金融单位和金融市场之中,降低了企业的潜在增长力和稳定性。(5)Ken-Hou Lin,and Donald Tomaskovic-Devey.“Financialization and U.S.Income Inequality:1970—2008”.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3,118(5):1284-1329.
Lazonick和O’Sullivan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视角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金融化不断发展,“股东价值导向”成为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公司的经营目标变为缩小投资规模以获取利润,即缩减生产性投资的规模并将收入的大部分分配给股东。(6)William Lazonick,and Mary O’ Sullivan.“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A New Ideology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Economy and Society,2000,29(1):13-35.Orhangazi也发现,金融利润的增多改变了公司经理的激励,公司投资策略转为关注短期股价的提升而不是长期的生产性投资。(7)Ozgur Orhangazi.“Financialis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US Economy:1973-2003”.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32(6):863-886.不仅如此,国民经济中制造业份额的下降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制造业向金融行业转移的程度,因为很多非金融公司经常通过一些不用单独上报信息的金融手段来获取大量利润。(8)Michael Perelman.“The Corrosive Qualities of Inequality:The Roots of the Current Meltdown”.Challenge,2008,51(5): 40-64.Wolfson和Kotz发现,金融化背景下的金融去管制的确使得金融部门将资金转向了投机活动,而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生产性投资活动。(9)Martin H.Wolfson,and David Kotz.“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1(2):209-225.
后凯恩斯主义学者Stockhammer发现,在股东价值导向下,公司越来越像食利者,将利润用于购买金融资产而不是生产性资产,降低了积累率。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出现了两种增长模式,一是消费驱动型,二是出口导向型。前者的信贷消费会伴随着大规模经常账户赤字,使得资本流入国内刺激信贷泡沫,引发危机;后者的消费不足需要净出口来拉动总需求从而刺激实体经济。(10)Engelbert Stockhammer.“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Slowdown of Accumulation”.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4,28(5):719-741;Engelbert Stockhammer.“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y”.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240,2010;Engelbert Stockhammer.“Financialization,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Crisis”.Investigación Económica,2012,71(279):39-70.Palley认为,金融化可能导致经济陷入债务型通货紧缩和长期衰退的状态,实体经济的增长将面临长期放缓的趋势。(11)Thomas I.Palley.“Financialization: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525,2007.Hein等将现实经济体制视为一种“有利润无投资”的体制,其中金融化挤出实体投资是该体制的关键。金融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并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在长期中会恶化实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带来系统的不稳定性。(12)Eckhard Hein,and Till van Treeck.“‘Financialisation’ in Post-Keynesia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and Growth:A Systematic Review”.IMK Working Paper No.10,2008;Eckhard Hein.“A(Post-)Keynesian Perspective on‘Financialization’”.IMK Studies,2009(1);Eckhard Hein,and Nina Dodig.“Financialisation,Distribution,Growth and Crises:Long-run Tendencies”.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No.35,2014; Eckhard Hein.“Finance-Dominated Capitalism and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A Kaleckian Perspectiv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5,39(3):907-934.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国内学者特别关注经济金融化转型及其产生的经济影响。高峰认为,金融化使资本不再通过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分配,而是直接再分配已经创造出的财富,从而产生了新的资本积累方式。(13)高峰:《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12)。陈享光认为,金融化改变了资本和收入的积累占有方式,强化了货币资本积累、虚拟资本积累的独立性,造成脱离现实积累的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积累的扩张和收缩运动,使得金融的繁荣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脱节。(14)陈享光:《金融化与现代金融资本的积累》,载《当代经济研究》,2016(1)。张成思、张步昙,杜勇等以及彭俞超等则从实证角度分析了金融化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15)张成思、张步昙:《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载《经济研究》,2016(12);杜勇、张欢、陈建英:《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7(12);彭俞超、韩珣、李建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1)。他们发现,金融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业投资率,并弱化了货币政策提振实体经济的效果。金融化所引致的金融资产的增加不仅没有缓解企业投资的不足,还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性投资,损害了实体企业的未来业绩,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
基于我国出现的“脱实向虚”问题,一些学者研究了金融化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刘骏民讨论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三大定律,包括货币直接创造GDP、金融创新创造GDP以及虚拟经济介稳性或“成氏定理”。(16)刘骏民:《经济增长、货币中性与资源配置理论的困惑——虚拟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4)。杜厚文、伞锋认为虚拟经济是从“虚拟资本”的概念中演绎而来的,马克思时代的虚拟资本仅表现为收益性,而当前的虚拟经济包括流动性、风险性和收益性三个特征。(17)杜厚文、伞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载《世界经济》,2003(7)。李扬则把虚拟经济看作是金融,他认为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实体经济有着促进作用,但同时又酝酿着经济的虚拟化。(18)李扬:《关于虚拟经济的几点看法》,载《经济学动态》,2003(1);李扬:《“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辨》,载《经济研究》,2017(6)。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金融化的发展使得经济进一步虚拟化了,在金融衍生品上这种关系被彻底割断了,伴随“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金融与实体、虚与实的边界将越来越模糊且彼此渗透。王国刚虽然也认为虚拟经济主要就是金融业,但他进一步指出,虚拟经济不仅存在于金融部门,还存在于从事虚拟经济活动的产业部门甚至政府部门。他认为金融的“脱实向虚”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资产证券化强化了金融“脱实向虚”的维度,包括货币载体、金融交易对象、金融服务网点和资金的“脱实向虚”等多个方面。(19)王国刚:《关于虚拟经济的几个问题》,载《东南学术》,2004(1);王国刚:《金融脱实向虚的内在机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7)。易纲等则认为“金融不是虚拟经济”。(20)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金融不是虚拟经济》,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1)。张晓朴、朱太辉也反对将金融体系视为虚拟经济,他们认为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做出直接贡献的一种服务业。(21)张晓朴、朱太辉:《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载《国际金融研究》,2014(3)。叶祥松、晏宗新认为,虚拟资本采取了更加多样的形式,包括衍生品、艺术与高档消费品以及品牌专利等无形资产,这些形式的虚拟资本逐渐绕过实体经济的再生产过程而只为当事人创造货币收入,因此,财富创造和积累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从原先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领域转向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领域。(22)叶祥松、晏宗新:《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9)。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从货币到资本虚拟化发展的逻辑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货币的存在使得商品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货币变成价值的化身,在发展过程中,货币的交换价值又能够获得一个脱离货币材料,脱离货币实体的存在,如纸币,但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权并没有消失。(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货币,一方面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另一方面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而作为价值尺度需要货币的物质实体,作为流通手段则注重货币的符号数量,就后者而言,它“作为一定量的金和银的那种基质是无关紧要的”(24),从而产生了货币基本职能的矛盾。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矛盾统一体,货币必须通过激发其他职能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扩张。在货币职能的发展过程中,货币一方面在本质上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而不断积累自己,另一方面却在形式上不断脱离物质实体的束缚。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商品(即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体的商品)进入市场交易,与货币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由于不是真正的商品,它们自身没有社会劳动凝结形成的价值,所以,在同它们的交换中,货币成为表现这种所谓“商品”虚拟价值的“价值形式”。由于这种所谓“商品”的不断增加,作为其虚拟价值存在的货币虚拟性越来越突出,特别是随着资本商品和虚拟资本品不断增加,货币虚拟性及货币形式代表的价值和财富的虚拟性不断发展。
货币不是资本,但资本是以货币作为自己出发点的,“货币是资本借以表现自己的最初形式”(25),分析货币自身的演变是理解资本运动,特别是生息资本扩张的前提。货币在其规定性上,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规定”(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65、208、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资本主义之前就出现了高利贷资本形式的生息资本。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高利贷形式的生息资本已经逐渐被借贷货币资本所代替。借贷货币资本或者生息资本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同于产业资本,借贷货币资本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为中介的运动”(27)。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货币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28),且这种资本商品“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只是被贷出”,也就是说,货币资本家让渡了对它的占有权却保留所有权。生息资本的利息并不像产业资本的商品那样存在一个客观的“价值”,从而使得“需要决定的东西就是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29)。因此,“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3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389、382、399、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货币资本或借贷货币资本作为运动中增殖的价值形式,既不同于货币形式,也不同于现实资本。借贷资本起初虽是以货币形式存在,但后来却作为货币索取权而存在,因为它原来借以存在的货币现在已经以现实货币的形式处于借款人手中。对贷款人来说,它已经转化为货币索取权,转化为所有权证书了。所以,同一数额的现实货币,可以代表数额极不相同的货币资本。并且,借贷货币资本可以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而增加,但是货币形式的资本的积累,绝不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积累。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31)
如果说生息资本使得资本关系具有了拜物教的形式,那么,国债、股票等虚拟资本则使得这种拜物教的形式发挥到极致。它使得生息资本成为“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32),借贷货币资本等生息资本的直接形式尚与现实资本运动存在依稀可见的联系,但是在虚拟资本的场合,这种联系被彻底消灭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33)。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虚拟资本所能表现的双重存在性与其实际获得的唯一存在性之间的矛盾。股票等虚拟资本既表现为现实的资本(包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也表现为这种资本的所有权凭证,从而它既具有代表现实资本的名义价值,又具有反映所有权的市场价值。但是,虚拟资本从而其价值只能存在于后者之中,它只是对现实中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34),尽管这个所有权是可以独立运动的,但是无论其如何转手都不会改变原先的所有制,这就使得虚拟资本的市场价值不同于其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名义价值,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决定方式。一方面,它不代表对现实资本的要求权,而只是代表对收益的要求;另一方面,它所代表的收益是一种“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35),因而具有一定的投机性质。因此,虚拟资本作为现实资本的一种纸质副本,其价值额的涨落不仅不取决于它代表的现实资本价值,而且“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36),且它们大都是纯粹虚拟的。可见,虚拟资本的价值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信用制度可以通过强化虚拟资本“大鱼吃小鱼、狼吃羊”的赌博交易活动而具有“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37)。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信用的发展以及生息资本的扩张是没有限度的,在产业资本主导下,其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38)。一旦产业资本积累过度,大量固定资本就会闲置不用,信用就会收缩。事实上,存在一系列的层级枢纽来规训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扩张,在这个层级枢纽的顶端则是商品货币对于信用货币的“规训”。马克思曾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3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531、528、529、529、530、533、497、546、6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商品货币随之被废除,信用货币成为主导,规训信用的重担转移到不可靠的、有时反复无常的人类机构手中。(40)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25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在这种情况下,虚拟资本呈现出更加肆无忌惮的扩张。
随着货币自身、借贷货币资本以及虚拟资本运动不断脱离物质实体和产业资本的“束缚”,以产业资本积累为主导的资本运动也开始褪去其实体特征,并逐渐显示出虚拟性。具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货币自身形式的虚拟性。货币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职能,而当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可以由“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他符号来代替”,从而使得货币脱去了物质实体,虽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但它并不是财富本身,作为价值形式,却不一定是真实价值的反映。特别是随着商品化市场的不断扩大,那种没有社会劳动凝结的所谓商品不断增加,货币与这些所谓商品交换,成为表现其“虚拟价值”的价值形式。信用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的虚拟性。二是借贷货币资本的虚拟性。在借贷货币资本形式上,货币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利息成为其自然的果实。借贷货币资本最初以货币形式存在,但之后变成货币索取权,只是对价值的权利证书,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三是虚拟资本的虚拟性。虚拟资本就其本质来说,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虚拟资本不同于现实资本,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为转移的。由于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现实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资本上。且在生息资本独立性和自主性运动规律的作用下,虚拟资本的虚拟性存在不断被放大的可能。究其原因,在于虚拟资本的扩张并不一定与资本的持续性再生产相一致,当虚拟资本的扩张违背了资本持续再生产的逻辑时,其虚拟性便在经济中被放大了。
因此,与货币自身的虚拟化相联系的经济过程、与借贷货币资本的虚拟化相联系的经济过程以及与虚拟资本的虚拟化相联系的经济过程共同造成了整体经济过程的虚拟化,成为孕育催生虚拟经济的基本要素。不过,只要经济过程处于产业资本的主导下,虚拟经济的扩张就会受到限制,因为产业资本的“规训”使得货币以及借贷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等生息资本“流回的方式总是由自身得到再生产的资本及其特殊种类的现实循环运动决定的”(4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其流动的时间仍然要“取决于再生产的过程”。然而,一旦产业资本的主导被打破,由货币、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驱动的经济虚拟化就不可避免,虚拟经济便会迅速扩张,并逐渐影响到整体经济的运行过程。
三、金融化、金融化资本积累与虚拟经济的发展
在产业资本主导的条件下,产业资本循环周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或货币资本最终都会以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回流到产业资本主导的循环周转中,从而使其能够在一定限度内保持运动的连续性。但是随着货币、借贷货币资本以及虚拟资本的独立性、虚拟性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脱离产业资本约束的金融化趋势,产业资本主导逐渐被金融化资本主导所取代,从而推动了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
金融化意味着资本积累和占有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货币或货币索取权的形式、所有权证书或权利证书的形式(42)陈享光:《储蓄投资金融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因此,从货币到资本的虚拟性和货币资本运动的独立性会随着金融化发展而不断增强。随着金融化发展,借贷货币资本或生息资本能够在金融领域、投机性非生产领域以及全球范围内实现独立的循环和扩张,脱离并逐渐影响产业资本自身的运动。如图1所示,生息资本在金融领域内部的自我循环使其逐渐脱离了产业资本的束缚之后,又通过在投机性非生产领域内的运动而开始影响并制约产业资本的运动,并最终在国际范围内实现更大规模的循环和周转。显然,在这一过程中主导资本循环周转的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产业资本,也不再是希法亭、列宁意义上的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而是与之不同并逐渐制约其运动的金融化资本(financialized capital)。

图1 金融化资本主导下的资本循环
金融化,无论其借以实现的方式和手段如何,在本质上追求的都是货币和资本的等同或同一性,也就是说,或者使货币具有资本的增殖性,或者使资本具有货币的流动性。随着金融化发展,在金融化资本形式上实现了货币与资本的这种同一性。就金融化资本形成来看,它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产业资本循环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资本过剩和信用过剩。在产业资本主导时期,资本积累主要采取产业资本积累的形式。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张,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4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413、575-5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逐渐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金融资本”,并逐渐在资本积累中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的垄断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造成了大量的资本过剩和信用过剩。哈维认为,这些在初级资本循环中过剩的资本会被集中投入到以固定资本积累为代表的“二级循环”和以公共品积累为代表的“三级循环”中,以实现资本主义的“时空修复”。(44)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但是,Aalbers发现,过剩的资本不一定会流向二、三级循环,而是大概率地流向“四级循环”,即以纯粹的资本投资为主的空间地理中,而在这一过程中就会产生金融化。(45)Manuel B.Aalbers.“The Financialization of Home and the Mortgage Market Crisis”.Competition & Change,2008,12(2):148-166.
金融化资本形成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金属货币的废除与信用的延长。经历了由商品货币到纸币再到信用货币的演变过程,货币逐渐脱离了物质形式的束缚。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贵金属货币退出历史舞台,货币完全脱离商品的外壳而与商品相对立。与此相对应,以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为主要形式的生息资本也开始挣脱产业资本的规训,逐渐在金融领域内部实现自我循环。在满足第一个条件的前提下,产业资本循环积累的大量货币资本剩余开始涌入金融领域,并随着CDS、CDO等证券化工具的出现而以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平方”甚至“立方”的形式在金融领域内部迅速膨胀起来。因此,金属货币的废除和信用的延长使得生息资本越来越偏离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基础而独立发展起来,形成主导金融化阶段的资本形式和资本运动形式,并不断放大金融体系的投机性和不稳定性。
首先,金融化资本在金融领域内部的积累能够使得生息资本脱离产业资本的束缚,从而实现其在金融领域内的自我循环。当信用货币脱离了商品货币的束缚后,国际货币秩序便因缺少货币锚定物而陷入混乱,货币的品质遭到重创。(46)陈享光、黄泽清:《货币锚定物的形成机制及其对货币品质的维护——兼论数字货币的锚》,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4)。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金融领域内部这种借贷资本或虚拟资本的积累,“既不同于它由以产生的现实积累,也不同于以贷放的货币为中介而实现的未来积累(新的生产过程)”(4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413、575-5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而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积累过程或产业资本运动过程的独立的积累。一旦积累的借贷资本只是“货币单纯地转化”,而不是“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后的再转化”,那么这种借贷资本的积累便与现实积累相脱离了。事实上,金属货币的废除使得信用货币在行使其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容易忽略其价值尺度的职能,加大“货币单纯地转化为借贷资本”的可能性,使得借贷资本或生息资本更容易脱离产业资本的“规训”,从而使其能够在金融领域内自我循环、自我膨胀。
其次,金融化资本在投机性非生产领域的积累使得生息资本逐渐影响并制约产业资本的运动。当生息资本脱离现实积累的束缚后,其所代表的货币资本会表现为频繁的收缩和扩张运动,货币资本的价值也会随之上下波动,从而增强了投机性。因此,金融领域内部各类金融资产价格的膨胀催生了一系列与之相联系并为之服务的投机性非生产活动。在金融化资本的作用下,金融领域之外的一切具有使用价值或收入流的物品、领域,无论其是否具有真实的价值,都可以通过货币化、资本化以及虚拟化的方式被纳入证券化金融资产中,从而建立了其与金融领域内生息资本的联系。随着金融化资本的不断积累,金融板块正逐渐占据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从而不可避免地会把资源从其他板块抢走,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核心板块,如制造业、基础设施以及教育行业等等。(48)保罗·罗伯茨:《冲动的社会: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短视,世界越来越极端》,9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金融化能够使这些行业拉长债务链条、积累债务规模,并使这些“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49)。但是,这种拜物教式的积累使得金融领域内的资本家用“他人的钱”进行投机式的欺诈并且“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5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540、5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再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和循环扩展了活动领域和套利空间,从而放大了生息资本的虚拟性、投机性和增殖性。全球化发展,世界市场扩大并逐渐远离初始生产点,信用必然被延长,并使得全球空间关系的生产变革与信用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51)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26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金融化资本可以通过操纵全球金融市场来获取各个国家的工业利润、金融企业利润以及股息和利息,使得生息资本的相对独立性达到极点,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两极积累:一些国家是完全脱离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或权利证书的积累;另一些国家则是通过货币或非货币金融资产的创造进行资源的国际转移,并通过这种转移来完成现实积累。国际性的金融化资本一方面可以与东道国的垄断资本结合并控制该国的生产条件来影响现实积累进程(52)黄泽清、陈享光:《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各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变动——基于帕尔玛比值的分析》,载《经济学动态》,2018(8)。,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监管漏洞进行非生产性套利交易从而攫取大量的金融利润。大规模非生产性的金融化资本以热钱的形式在不同国家间流入流出,不仅造成金融资产价格的巨大波动,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的资源、财富等进行再分配。
在金融化资本的主导下,原先与产业资本循环联系紧密的货币资本、借贷货币资本、虚拟资本逐渐流向了能够创造货币、非货币金融资产的金融领域、资产价格易于泡沫化的投机性非生产领域以及全球货币、非货币性投机套利市场,使得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并逐步与实体经济的基本形态割裂开来,形成一个全新的虚拟经济形态,即虚拟经济的核心层。而原先受到产业资本主导的,与货币虚拟化、借贷货币资本虚拟化以及虚拟资本虚拟化相联系的虚拟经济基本形态则成为虚拟经济的外围层。实际上,虚拟经济外围层与核心层的分割过程恰恰是货币自身、借贷货币资本以及虚拟资本快速虚拟化的过程。
首先是金融化资本主导下货币自身的加速虚拟化。如前所述,自20世纪70年代黄金非货币化后,信用货币失去了“锚定物”,金融化资本积累加速,货币虚拟化程度进一步扩大。在信息革命、通信技术以及近年来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货币逐渐获得了电子货币、加密货币甚至数字货币的形式,不仅再次扩张了货币自身的虚拟性和它作为财富一般代表的虚拟性,还通过限制国家对于货币创造和流通的监管能力激发了私有部门的“准货币”创造力,从而加快了借贷货币资本的虚拟化。
其次是金融化资本主导下借贷货币资本的加速虚拟化。曾几何时,国家部门和银行等金融部门相互结合形成了“国家—金融联合体”,通过准备金制度、清算制度以及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等宏观审慎约束制度对借贷货币资本及其价格(利率)进行规训,以适应产业资本驱动的生产方式。然而,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化的发展,货币和资本间的界限似乎消失了,货币资本积累远比马克思分析的产业资本主导下容易得多,特别是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创造和货币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借贷)货币资本的很大部分是在银行体系内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信用货币的创造过程已经包含了资本的虚拟性方面。(53)弗朗索瓦·沙耐等:《突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缘由与对策》,5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可见,货币自身的虚拟化过程中蕴含着借贷货币资本的虚拟化,这种条件下积累的货币资本的相当大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像价值符号,只是对价值的权利证书。因此,与这种借贷货币资本虚拟化相联系的经济过程是一种虚拟化程度更高的虚拟经济。
最后是金融化资本主导下虚拟资本的加速虚拟化。信用货币的产生过程不仅孕育了借贷货币资本也孕育了虚拟资本的雏形,而两类生息资本的平衡关系则主要取决于信用货币发展程度和货币管理程度。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信用货币更为发达、货币管理相对宽松,因此其与借贷货币资本相联系的影子银行业务里已经包含了大量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证券化金融资产等虚拟资本。在金融化资本的主导下,虚拟资本的运行开始服从金融化的逻辑,它逐渐渗透到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住房、教育、医疗等行业中,通过对其进行证券化融资的方式改变了这些行业存在的原始目的,以最大限度地增加金融化资本的利润。随着虚拟资本的加速虚拟化,相关领域的经济虚拟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事实上,随着金融化资本的发展,货币的虚拟化、借贷货币资本的虚拟化以及虚拟资本的虚拟化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发展不仅加剧了金融领域内部的虚拟性,还通过金融化资本的运动加剧了非生产性投机领域的虚拟性,并最终借助于全球化的发展而加剧了全球范围内货币和资本的虚拟性,从而促使虚拟经济的核心层逐渐形成。以近年来肆意膨胀的比特币为例,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数字化金融资产,比特币将货币、借贷货币资本以及虚拟资本的虚拟性融合在一起,它一方面能够将产业资本中大量的过剩货币资本吸收到金融领域之中,另一方面还通过孵化一批为其服务的投机性行业,如首次代币发行(ICO)、比特币“挖矿”等,加剧了投机领域的虚拟性。它们的活动和发展不仅不会促进现实资本的积累,而且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造成对环境的破坏。
四、金融化条件下的实体经济分层与“脱实向虚”的传导机制
根据产业资本与金融化资本的运动规律,我们按照资本类型对实体经济作了划分见图2。

图2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层次
由图2可知,区域1为封闭的产业资本循环,即以产业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物质生产领域,表示实体经济的核心层;区域2为生产领域延伸出的与生产过程直接联系的流通领域,表示实体经济的半外围层;区域3为服务于生产领域的与生产过程间接联系的流通领域,表示实体经济的外围层,同时,该区域也是金融发展适当时虚拟经济的外围层;区域4为上文所述的金融化资本占据的三大领域,表示虚拟经济的核心层。图中的实线部分代表了完整的实体经济,包括区域1、区域2和区域3的一部分,而图中的虚线部分则代表了完整的虚拟经济,包括区域4和区域3的一部分。不难发现,区域1和区域2都是较为独立的实体经济部分,区域4是较为独立的虚拟经济部分,区域3则代表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重合部分,而这部分便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模糊认识的根源所在。因此,为了分析“脱实向虚”的完整传导机制,首先需要对区域3进行分析,进而过渡到对区域2的影响分析,最终探究金融化对实体经济核心层,即区域1的影响。
第一,金融化导致的实体经济外围层的分裂是经济“脱实向虚”的第一阶段。在以借贷资本、虚拟资本等生息资本运动为基础构建的经济空间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中的不同资本第一次出现了直接的对立:一方面,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需要利用闲置的货币资本剩余以实现更大范围的积累和集中;另一方面,金融化使生息资本逐渐摆脱了产业资本的束缚,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本不再必须从产业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那里获得收入,而是可以通过抬升金融资产或无价值基础的资产的价格来实现收入的增加,从而促使闲置的货币资本独立成为一种不再依附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式,并且由于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经济空间和流动性、收益性上的比较优势,其对产业资本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货币资本的供求在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个别的产业资本不得不向控制着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的银行家借入货币资本才能完成自身的生产项目,实现其生产过程。在货币市场中,货币资本的需求表现为一个阶级的共有资本需求,而货币资本的供给则表现为资本本身的群体,从而隐含了一定的不对称性。在资本剩余大规模增多、信用持续延长以及金属货币废除的条件下,金融化资本逃脱了产业资本的束缚而迅速积累起来,并逐渐扩大了货币资本供求的不对称性,最终导致了实体经济外围层的分裂。实际上,实体经济的外围层主要包括服务于生产领域的与生产过程间接联系的流通领域,这一领域由于同时受到产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的牵制而能在领域内实现平衡。但是当金融化资本出现后,该领域的资本便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金融化资本的控制,服务于金融化过程下的虚拟资本积累,且逐渐地与其服务于产业资本积累的初衷相违背,从而造成了实体经济外围层的分裂。最明显的一点是,许多不具备货币供给功能的服务性机构开始逐渐获得了“货币”创造的能力,例如脱离资产负债表监控的影子银行业务、连接资本市场供给端和需求端的P2P业务等等。前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流通中的“货币创造机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备了创造货币的能力,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系统性风险;后者则先是创造了大量的资金池,然后将其投到前者的影子银行业务中,从而产生了一种几乎与产业资本积累无关的庞大的虚拟资本或金融化资本的积累模式。
第二,金融化作用下的生息资本向实体经济半外围层的渗透是经济“脱实向虚”的第二阶段。实体经济外围层的生息资本起初是服务于生产领域的,它会通过实体经济的半外围层回流至实体经济的核心层,以完成资本运动的闭环。因此,即使第一阶段的金融“脱实向虚”使得这些生息资本被纳入以金融化资本积累为主导的虚拟经济中,其也势必会与实体经济的半外围层保持一定的联系。否则,当所有的生息资本都无法完成回流时,产业资本循环必定会因无法完成扩大再生产而停滞,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陷入危机和瘫痪状态。实体经济外围层的生息资本因金融化资本的影响而获得了极强的流动性,它们会渗透到一切与生产过程直接联系的流通领域,即实体经济的半外围层,以实现最大可能的资本增殖,这些领域包括交通运输业、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等具有公共性质的基础类行业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医疗教育行业等。房地产、医疗和教育等与劳动力再生产密不可分的行业是生产领域中延伸出的与产业资本积累直接联系的行业,它们属于实体经济的半外围层,具有一定的公共品特征。然而,一旦它们被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由于其产品自身缺乏价值基础,从而没有对价格的价值限制,如果没有一定的外部规制,其价格具有极大的上升空间,随着外围层生息资本的大量渗入,这些行业就会成为最容易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业,其结果必然是挤压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正常消费,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的障碍和困难,最终影响社会生产的质量和实现条件。
第三,在实体经济核心层内,物质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随着金融化的作用而普遍提高并逐渐偏离其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经济“脱实向虚”的第三阶段。实体经济核心层是经济增长的源头,其内部充斥着机器装备、工厂设备等固定资本,因此这一领域是生产发展的核心领域。与生息资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不同,这些固定资本将资本积累限制在一个固定的、与流动资本的流动性相比较为僵硬的领域中,其必须与流动性较高的资本类型相结合才能实现价值增殖,否则便会处于长期静止的状态而出现价值丧失的可能。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借贷形式的货币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内部后便会与固定资本相结合以实现价值增殖,从而获取利息。即使半外围层的货币资本在流入实体经济核心层时已经受到了金融化资本的制约,以产业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核心层也不一定会受到金融化资本的直接影响。究其原因在于,生产领域内部具有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只要其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能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就可以使得从半外围层流入的受到金融化资本制约的货币资本获得价值基础,从而抵消金融化资本的负向影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剩余价值毕竟需要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当金融化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物质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并使其偏离价值基础时,生产领域内部便会出现“价值革命”,价值革命越是尖锐,“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5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的核心层也被金融化资本渗透了,经济“脱实向虚”的“最后一公里”被打通了。
金融化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可以助推以上三个阶段的形成。首先,它可以将金融化资本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传递至金融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催生出一系列金融创新工具并造成这些国家实体经济外围层的分裂。其次,它可以将国际范围内闲置的金融化资本投入到各国的基础性领域和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领域,从而加强金融化资本对该领域的渗透。最后,它还可以将金融化资本融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期权合约、期货合约中,并通过快速买进卖出这些金融化的合约进行套利,从而加剧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性,提高物质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偏离其价值基础的可能性。
至此,实体经济内部的不同资本类型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金融化资本的制约,使得物质生产领域、物质生产延伸的流通领域以及服务于物质生产的流通领域逐渐向虚拟经济靠拢,从而造成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金融化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会对“脱实向虚”产生助推作用。
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货币自身、借贷货币资本以及虚拟资本失去产业资本“规训”的扩张为虚拟经济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货币职能的矛盾运动、生息资本不断脱离产业资本“束缚”的独立运动使得以产业资本积累为主导的资本运动开始褪去其实体特征,并逐渐显示出虚拟性。与货币虚拟性、借贷货币资本虚拟性以及虚拟资本虚拟性相联系的经济过程共同造成了整体经济过程的虚拟性,驱动着虚拟经济基本形态的形成。
第二,产业资本循环形成的大量资本剩余以及信用发展和金属货币的废除为金融化资本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息资本在金融领域、投机性非生产领域以及全球资源配置领域等三大领域内实现独立的循环和扩张,金融化资本便随之出现。首先,金融化资本在金融领域内部的积累能够使得生息资本脱离产业资本的束缚,从而实现其在金融领域内的自我循环。其次,金融化资本在投机性非生产领域、虚拟经济领域积累和扩张并逐渐影响、制约产业资本的运动。最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和循环扩展了虚拟经济领域和市场的套利空间,从而放大了资本流动性、虚拟性和增殖性。
第三,金融化发展和金融化资本的积累、金融体系内部资本自我循环机制的生成、投机性非生产领域和市场的不断拓展以及货币资本的全球流动和配置,加深了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原先与生息资本相联系的虚拟经济成为外围层,而金融化三大领域内的虚拟经济则成为核心层。与之相对应,实体经济也可以分为核心层、半外围层和外围层。其中,核心层是指以产业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物质生产领域,半外围层是指生产领域延伸出的与生产过程直接联系的流通领域,外围层是指服务于生产领域的与生产过程间接联系的流通领域。虽然虚拟经济的外围层与实体经济的外围层相互渗透、互相重合,但随着金融化发展,虚拟经济的核心层与实体经济的核心层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分割开来。
第四,经济“脱实向虚”的传导机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融化导致的实体经济外围层的分裂;第二阶段是金融化作用下的生息资本向实体经济半外围层的渗透;第三阶段是实体经济核心层内物质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随着金融化的作用而普遍提高并逐渐偏离其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之相对应,经济“脱实向虚”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金融化导致的实体经济外围层的分裂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渐受到金融化资本的控制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行创造一般等价物;二是随着金融化作用下生息资本向半外围层的渗透,公共类基础性行业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行业逐渐服从金融化资本的运行逻辑,损害产业资本的积累进程;三是金融化资本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核心层,并使得物质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脱离了价值基础。金融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会加快以上三个条件的形成。
第五,金融化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而演变成世界经济现象,使得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化发展的影响,甚至模仿发达国家的金融化,从而引起一定程度的虚拟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应准确识别虚拟经济与虚拟资本的关系、实体经济与产业资本的关系,从而在分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层次的基础上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主导的金融机制,并采取有效政策抑制虚拟经济发展,防范“脱实向虚”。这包括:政府应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特别是资产证券化进行限制,要审慎推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证券化,以抑制过度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防范货币资本向投机性非生产领域的过度流入而弱化和损害产业资本的积累,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降低住房、医疗以及教育部门的金融化程度,同时鼓励资本、人才向生产性领域流动,强化金融体系对生产资本积累的支持,以促进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化带来的冲击,政府应采取稳健的措施逐步开放金融市场,谨慎实施汇率自由化,防止因过剩国际金融化资本向国内的转移而造成国内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