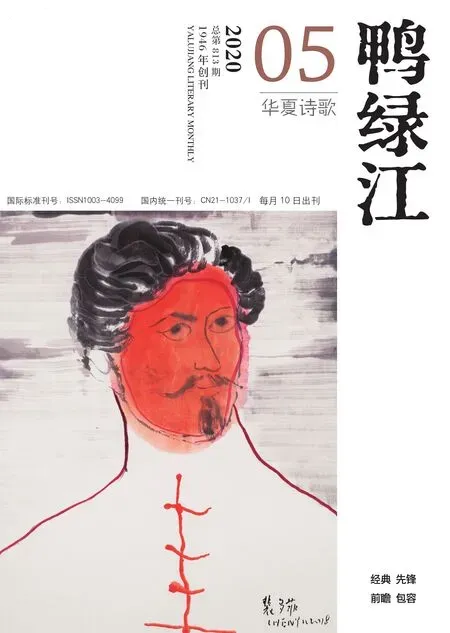深刻的地方(组诗)
沙 克
深刻的地方,你还要我什么
一块田里,种着爷爷和奶奶
一条路下,铺着父亲和姑姑
一个墓园中,妻子的体温还没散尽
这是我从儿时少时开始的牺牲
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地方
我生在外城,打这里栽下童年
是苦是福,我都用时间的肩膀扛着
现在我摸着鬓角的一点白霜
想到了母亲远在外省逐渐老去
身边的女儿就要长大
埋葬着这么多家人的地方
在我的体内怎能不深刻
你还要我什么
除了母亲和女儿
我都给你,只要你让我称呼你家乡
你还要我什么
我的命……也给你
只要你允许我称呼你
家乡
我们家的手
——悼亡妻
月亮的里面
伸出你白皙的手
细长的手
冰凉的手
柔软的手
冬天被水浸泡裂开的手
我们家的手
洗衣服的手
烧饭的手
买菜时还几分钱价的手
为我捶背剪指甲的手
一边摸着肚子里乱动的胎儿
一边织毛衣听音乐的手
天天晚上教女儿读书写字的手
为病人调配处方夜班不眠的
药剂师的手
搀老扶幼亲昵小猫小狗的手
拉扯着我们的家
往前走
月亮的外边
我的手
女儿的手
紧紧握着——
今夜,其实没有月亮
只有一双好看的手

《红日》(手机绘画) 莫金鸣
春天致我
抱住这盛满好酒的月亮
喝光我的血就是喝光
我祖父父亲一切先人的遗产
清空黑夜
注定有一颗火热的头骨代表我
为我恪守的生活方式
钻入腐烂的格局与鬼魅斡旋
格斗,轧死一切害虫
和背后的黑手。一只手表
或者沉默,或者和好
载着月饼、电脑键盘和原来的幸福
运行新的历法
我的魂是鲜花引擎,没有脸庞表情
闪烁着清凉数字
挑起一缕晨曦的喜悦
故乡在压弯的时针上醒来
姑娘们继续储存好梦
尾鳍游在血丝丝的忘情水上
那时我早已离场,谁来阻截隐蔽的死神
一觉睡过清明节
多吃几片安眠药
去梦里的油菜花地会见久别的家人
我们站在黄灿灿的芳香中
面带云彩的笑,面对云彩的笑
用蜜蜂和画眉鸟的话
叙说相隔十年几十年的日子和想念
一觉睡过清明节
不用去郊野的墓地傕生伤感
我们彼此默契,安详
以往的清明节
我经常一个人去几处扫墓沉思
天上的灵魂地下的家人
反过来泪打我的衣衫
他们都早早离世
往我的心里填进一把又一把泥
凝重,不悲哀,有营养
让我的目光里长出浅蓝色的星空
摇曳着一枝又一枝勿忘我
勿忘家人
睡得深一些一觉睡过清明节
附记:在我出生前20 多年,家人中的奶奶、大姑就已离世,在我两岁时爷爷离世,接着另两个姑姑离世。从我不满三岁起再没见过外公外婆,对他们没有一点记忆,直到我18 岁前他们离世也没见过。在我28 岁时父亲离世,37 岁时妻子离世,接着妹婿离世。几十年来,母亲和哥哥远在外省生活,遇到清明节时女儿不在家,我常常独自去几个地方为家人扫墓。当清明诗成为大众的文字娱乐,把不知足的小资流感,矫饰成悲伤的文字而不自知,我无语以对。对我而言,清明节早已不是悼念节,而是家人和我的聚会日。
一个人的中秋
多年来我习惯这个日子
它比太阳还诚信,还准时
不论什么年头,哪一种心情
愿不愿意,它都如期来临
高高悬挂,均匀铺展
它以为我和月饼一样的圆润
能让满桌的人
张开嘴巴的幸福
外面的大树掉了两片叶子
落在我的窗台,我不愿细看
一片枯了,碰了会碎的,一片绿着
像我正在怀念的松柏树林
月光罩着泥路上的脚印
那是家人
走向天堂的痕迹
给迟来墓地的灵魂做指引
人们靠拢着月亮
对视眼神,诉说好多种的幸福
唯独我,端着好几份回忆
代替桌子上久空的位置
我的中秋只剩母亲和女儿
还得向遥居皖东的母亲电话道福
给江南校园的女儿发送短信
然后,为几位发黄的遗像祈祷
做完这些
欣慰的电流在身上流遍
按官家的说法,我还算年轻
却得关闭手机的按纽
免得搅扰,陷入睡眠前的静思
好多年,一个人的中秋
不像炉火,不像冰
而像内衣一点点地贴近
敏感的月光坠下来裹着我
清幽,友好,独享后真的感动
我已经走得很远很远
世纪初,我的女人血肉飘零
载着族人魂魄的车轮碾轧我的身影
我身上的少许物质和血缘被卸除干净
你们从来没看清生命的面容
我已经走得很远很远
族人们,你们敢于扔下我
我就乐意于独身活着
在磷火森森的夜晚身披野菊
和兽骨,吹着口哨走到
撒旦面前朝他的鹰钩鼻子吐唾沫
他也看不清我灵内的行程
我已经走得很远很远
虚白的船,黑亮的马
旭日和落日都是我腿上的想法
我的熟人淡忘我的背影
所有生人看不到我夜行的步伐
我已经走得很远很远
你们所认识的浮肿皮囊不是我
他被迫与各类小丑同登戏台
我是你们的敌人,抽取你们的魂
独身活着,谁也不用担心我的命相
我已经走得很远很远
我的三代族人
你们用死亡换来我烛火燃烧
身轻如风越过峭壁黑渊不在话下
我已经走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