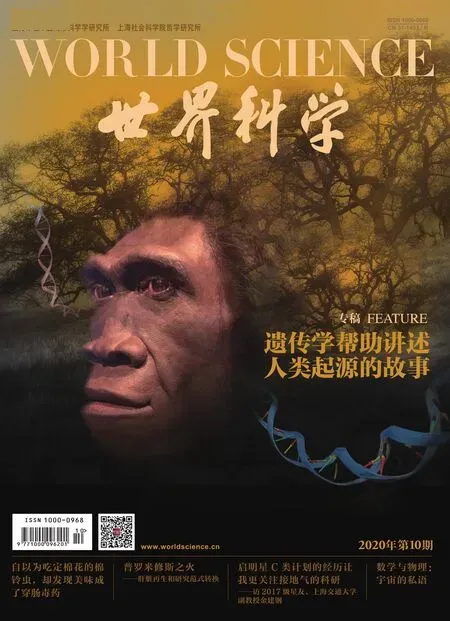必要的敬畏

在敬畏中,我们坚守自然的奇异性,向未知敞开心扉。无怪乎它是科学想象力的核心所在。
当科学范式被打破时,科学家不得不进入未知领域。这就是科学革命来临之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认定的。科学家的世界图景变得站不住脚,学科中公认的真理遭到彻底的怀疑。深爱的理论被发现是建立在沙子之上,延续数百年的解释现在被彻底否定。一种特殊的、富有成效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被证明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伟大的科学革命——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拉瓦锡、爱因斯坦和魏格纳所发动的——都发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此时,仅凭冷静、不偏不倚的理性不足以帮助科学家继续前进,因为学科中太多默认的假定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他们需要飞跃,也不知自己会落在何方。但是,该如何飞跃呢?
为了解释科学家是如何实现这种飞跃的,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在《经验立场》(2002)中借鉴了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情感理论梗概》(1939)。萨特对20世纪中期关于情绪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威廉·詹姆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感到不满,这些理论将情绪视为单纯的被动状态。你可能会坠入爱河或者被嫉妒困扰,情绪发生在你身上,没有任何主动性可言。萨特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情感是我们主动的产物,是有意为之的。例如,当我们愤怒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寻求解决方案,来化解当前的紧张局面。萨特写道:
当我们面前的路变得太难走,或者当我们看不清自己的路时,我们就不能再忍受这样一个严苛而困难的世界了。所有的路都被封住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行动。于是,我们试图改变世界。
萨特所说的世界是我们主观经验的世界。它是欲求、愿望、恐惧以及希望的世界。在他看来,情感像魔术一样改造世界。像巫毒(voodoo)这样的魔法行为会改变参与者对世界的态度。神奇的法术和咒语并不能改变物理环境,但会改变我们的世界,通过改变我们的欲求和希望。同样,情绪也会改变我们的观点,改变我们与世界的交往方式。萨特以酸葡萄为例:摘不到葡萄时,你就自我安慰,“反正太酸了”。虽然你没有改变葡萄的化学性质,但世界还是变得更容易忍受一点了。萨特预见到了当代具身认知的观念,他推测身体行动有助于产生情绪。我们在握紧拳头时愤怒,在哭泣中悲伤。
范弗拉森将这种想法运用到科学实践中去。他认为科学家会利用自己的情绪去处理新的、令人困惑的想法,特别是那些在科学革命期间萌发的想法。如果范式摇摇欲坠,科学家就需要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这需要改变他们自身。也就是说,科学家既要改变自己,也要改变自己的认知。只有在完成这样的改变后,他们才可能接受一个原先被认为荒谬的理论。
这个理论有不少问题。范弗拉森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情感可以帮助科学家。对一个新理论感到着迷或兴奋,或者好奇就够了吗?对旧范式的失败感到愤怒呢?此外,科学家如何利用情绪来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不清楚。萨特有时似乎认为,情绪是在我们的直接控制之下的。但是,目前看来,这并不可信。并不是所有情绪都在我们直接控制之下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萨特和范弗拉森的理论并非无可挽救,我们或许没法直接控制自己的情绪,至少可以间接控制它。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某些特定的活动,只要这些活动有助于塑造我们对各种情况的情绪反应。哪种情绪对科学家的帮助最大呢?我想到的是——敬畏。
在关于敬畏的经典论述中,心理学家达契尔·克特纳(Dacher Keltner)和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将其刻画为一种精神性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情绪。在他们看来,所有明确的敬畏案例都有以下两个组成部分:对宏大的体验,以及对这种宏大的认知适应需求。你可能会对物理上宏大的事物感到敬畏,也可能会对概念上宏大的观念感到敬畏。例如,在《物种起源》第一版(1859年)的最后,查尔斯·达尔文对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表示了敬畏:
这种对生命的看法是宏伟壮丽的。生命的几种力量,最初被注入到一种或多种类型中去。当此星球根据固定的引力法则循环往复之际,从最简单的事物开始,直到无穷无尽的类型,最美丽奇妙的类型,都被进化出来,并且此进化过程仍在继续。
需要认知适应,这让你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事还不明白。你觉得自己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是更宏大事物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敬畏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情感,它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外界环境中去。敬畏也是一种认知的情感,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并不完善。例如,我们可能会在观察夜空时不堪重负,深深地意识到宇宙还有诸多不解之处。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表示最常见的引起他们敬畏的因素是大自然,其次是科学理论、艺术作品,以及由人类通力合作而获得的成就。
哲学家亚当·莫顿(Adam Morton)推测,敬畏这种认知情感在科学实践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试想一位科学家,他很聪明,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并且掌握了最新的研究技术。但是,如果他缺乏好奇、敬畏等认知情感,那么他可能就不会在证据的基础上改变自己的想法,探索新假设,或是注意到意料之外的实验结果。简而言之,他会缺乏成为优秀科学家的动力。正如范弗拉森所言,要想改变研究领域或是接受领域内的根本性变化,你就需要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敬畏可以帮你做到这一点,因为它能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自身之外,让你跳出惯常的思维模式。
许多科学家在他们的自传性文字中提到,敬畏感是如何推动他们的科学工作的。以下来自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解析彩虹》(1998年):
科学能给予我们充满敬畏的惊奇感,这是人类灵魂所能体验到的最高情感之一。它是一种深沉的审美激情,毫不逊色于音乐和诗歌所能带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它的确是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倘若它能让我们确信生命是有限的,那么它就能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环保主义者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指出,敬畏是在艰难岁月中得以恢复的动力来源之一。1956年,为呼应萨特关于情感是避难之源的理论,卡森提出,我们应该鼓励孩子们保持并发展他们的敬畏感,以免其随时间的推移而消逝:
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保持并加强这种惊奇和敬畏的感觉价值何在?对自然的探索只是一种愉快地度过金色童年的方式,还是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我确信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持久而重要的东西。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那些栖息在这个星球的美丽与神秘之中的人们,永远不会孤独,更不会厌倦生活。无论他们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烦恼或忧虑,他们总能找到通往内心满足,重新焕发生活激情的道路。
经验证据表明,欣赏科学也离不开敬畏感。这些研究为理解敬畏与科学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尽管目前它们关注的还只是普通人,而不是科学家。心理学家达契尔·克特纳(Dacher Keltner)、萨拉·戈特利布(Sara Gottlieb)和塔尼亚·伦布罗佐(Tania Lombrozo)在2018年撰文指出,普通人在科学思考时倾向于感到敬畏。相比而言,更容易感到敬畏的参与者能更好把握科学的本质,更可能拒绝“年轻地球创造论”,也更可能拒绝对自然现象的无根据的目的论解释。当敬畏感被引导出来后,人们对科学的看法也会更积极。最近一项研究向参与者展示了BBC《地球》系列的剪辑,其中包括瀑布、峡谷、森林等令人敬畏的景色。另一组参与者则观看了动物们滑稽可笑的视频。结果表明,前一组参与者更可能意识到自己知识的不足。
这说明,引起敬畏对科学实践是有好处的。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神学家和哲学家亚伯拉罕·赫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在《人并不孤独》(1951年)和《觅人的上帝》(1955年)中论证了敬畏的重要性。赫舍尔认为,人们正把世界视作理所当然,从而失去了深度体验世界,并由此敬畏的能力。我们采取了一种自满的态度,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没有停下来思考科学向我们揭示的奇迹。他写道,“现代人掉进了一个陷阱,认为一切都可以被解释,现实是简单的,只需要组织起来就可以掌握。”赫舍尔认为,敬畏和惊奇是应对此状况的良方。
与萨特一样,赫舍尔认为情感是一种认知技术,是我们为了改变世界而有意为之的事情。但与萨特不同,赫舍尔并不认为情感的主要作用是使得一个难以忍受的矛盾世界变得可以忍受。相反,赫舍尔认为,情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世界不是平淡无奇的、纯粹工具性的,而是本身就有价值的,充满奇迹的。深层次的知识,由深刻的科学洞察带来的,或者对赫舍尔来说,宗教智慧,需要我们用这样一些术语来理解世界:作为目的,本身就是美的。正是因此之故,我们需要敬畏。
如何唤起敬畏?赫舍尔认为,犹太人的仪式有此功效:传统犹太人在特定的场合会说出一些祝福。比如,当看到彩虹,或者注意到果树上第一朵脆弱的花朵,或者遇上一位智者,或者听到好消息。这些祝福是具身的物理行为,用来标记应对周遭环境时的特定情绪状态。重复的仪式训练我们的身心对周围的世界做出敬畏和惊奇的反应。通过说出祝福,你会更容易体会到这些东西是多么珍贵和短暂。对赫舍尔来说,仪式不是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的一种形式。恰恰相反,它们是不适应的表现,“惊奇或愕然,语言和观念的失调,正是真正认知的先决条件。”如此看来,犹太人的仪式是陷入困境的现代人的解药。它们将我们从沉闷的自满中驱赶出来,并帮助我们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虽然很容易看出仪式怎样帮助我们在宗教中灌输敬畏之心,但在科学实践中,仪式如何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就不太清楚了。赫舍尔对科学家能否利用仪式来引发敬畏持怀疑态度,“一个科学理论一旦被宣布和接受,就不再需要一天重复两次了”。这种否定过于草率了。否定科学的浪潮正在兴起,科学理论并不是一经宣布和接受就一劳永逸的。即使是早已被否定的理论,如地平说,也在各种虚假宣传后重新抬头。
在科学实践中,已经有一些仪式性的因素,可能帮助灌输敬畏之心。例如,重复某个实验的科学家往往会忠实地坚持原实验的各种细节。事实上,按照哲学家尼古拉斯·谢伊(Nicholas Shea)的说法——
比如说,使用10毫升而不是20毫升或5毫升的溶剂,这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只是说,实验最初就是这么做的。既然它行之有效,就没有人会去尝试改变数量。事实上,有些实验是如此棘手,以至于实验人员对原有规程的文字展现出近乎宗教般的坚持。
因此,敬畏在科学家的日常工作,也就是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会些微调整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动辄全盘推翻重来。但是,正如我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的,敬畏在科学革命中尤其重要。在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们正努力寻找全新的概念和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仪式性的做法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真正需要的是彻底的重新定位。
除了仪式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敬畏感:可以通过阅读他人的著作来体验敬畏。正如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57年一本关于崇高的开创性著作中谈道:
许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事物,在现实中很少出现,但表现它们的文字却屡见不鲜。因此它们有机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在头脑中扎根……
这就与科学有关了,因为科学理论往往包含我们无法直接经验到的东西,即所谓科学中的不可观察对象,如电子、早期宇宙、恐龙和尼安德特人等。如果科学家永远无法证实这些不可观察对象是否存在,那么他们怎么能把它们接受下来呢?
心理学家本杰明·布拉德利(Benjamin Sylvester Bradley)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成功地建立了一种新的范式,部分原因是它借助了浪漫主义或康德主义的崇高概念。虽然达尔文的书并不是第一本用进化论来解释新物种如何产生的书,但他的作品却不同寻常地将科学的严谨与对自然的宏大和复杂的诗意思考结合在一起。在书中,达尔文还经常谈论我们缺少知识,也难以想象进化发生的巨大时间尺度,这些都会引起我们的敬畏。比如说,
拉姆塞(Ramsay)教授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安格尔西岛地层向下凹陷达2 300英尺的报告。他还告诉我,他确信在梅里奥尼思郡(英国威尔士原郡名)有一个凹陷达到了12 000英尺。然而在这些情况中,地表上已没有任何可以表明这种巨大运动的痕迹,裂缝两边的岩石也已经被夷为平地。仔细考虑这些不同的事实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地质历史的久远我们是很难准确把握的,它如同“永恒”一样不可捉摸。
敬畏会增加我们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使得我们能够接受不同寻常的新想法,这对范式的转换至关重要。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的《物理学联系论》(1834)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科学综述,也预见到了一些新奇的想法,比如海王星的存在。这是由于天王星轨道的异常,远在海王星被望远镜发现之前。其他还包括存在太阳系外行星,以及其他尚未被探测到的天体物质。萨默维尔时常借助读者的敬畏感,比如,
天空中的物体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天空的哪一部分不会被光线照亮。无数的恒星,成千上万的双星系和多星系,数万颗恒星组成的星团,还有星云,它们奇异的形态和难以理解的性质让我们感到惊奇。最后,由于我们有限的感官,甚至这些稀薄的幻影也消失在远方。如果这些遥远的天体只是通过反射来发光,我们就不会知道它们的存在。因此,每颗恒星都必须是一个太阳,并且有自己的行星、卫星和彗星,就像我们自己的太阳系一样。而且,就我们所知,无数物质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空间里游荡,我们对它们的性质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它们在整个宇宙系统中的作用。
这种诗意与科学的融合,就是凯瑟琳·尼利(Kathryn Neeley)在她的萨默维尔传记中所说的科学的崇高,“通过科学所揭示的自然景象,能够召唤出人类在上帝面前所感受到的同样的威严和力量感”。
敬畏不仅是科学日常工作所需要的,而且在范式变革时期调整思维方向也至关重要。它为科学家们继续工作提供了持续的情感动力,也为公众灌输了对科学思想的开放态度。精确性和严谨性固然重要,但敬畏所带来的情感驱动才是最重要的——正如赫舍尔所推测的那样,它也许是我们通往知识和智慧的唯一途径。
资料来源 A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