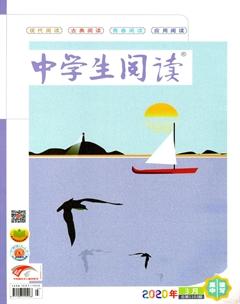命若游鱼
陈恒舒
自从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上斗过嘴之后,中国的文人常常一看见鱼就不淡定。柳宗元《小石潭记》写鱼儿“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实则反衬自己的处境凄苦;欧阳修《养鱼记》写小鱼“有若自足”而大鱼“不得其所”,实则忧心小人当道、贤人失路。直至當代,流行歌曲中亦有《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我们这里还有鱼》等广为传唱之作。在这众多的“鱼系”作品中,明末文人黎遂球的《琉璃盎双红鱼记》是非常独特的一篇。
这篇作品之所以独特,首先在于它并非仅仅“以我观鱼”,而是同时采取“以鱼观物”的视角,设身处地,想象鱼的境遇。在人看来,鱼处在一个极狭小的空间里却不自知,还以为自己存乎江湖;狭小的空间里分明只有两条鱼却不自知,还以为有无数条大大小小的鱼与自己嬉戏打闹;成为人类的玩物而不自知,还以为自己可以毫无顾虑地纵情欢娱。这不是傻是什么?但是转念一想,鱼会怎么想呢?或者说,鱼真的会去想吗?虽是自娱自乐,却也自得其乐;虽是身处一盎,却如畅游江湖。什么拘束、孤独、渺小、卑微,它们根本意识不到,而这不也就意味着不存在吗?
接下去则是由鱼及人的联想。这个联想本身没有什么,但黎氏所想的并不是个人或某一类人的具体境遇,而是生命的终极问题,这就是它的又一独特之处。人生在世图个啥?有人图富贵,有人图声名,有人图功德。然而大部分人忙忙碌碌,到最后不过是一场虚空而已。特别是那些“强而不息”的“不能者”,就好像琉璃盎中的两条小鱼,身陷穷途,满目幻象,困顿偃蹇,渺小卑微,却依然不自知地苦苦求索,或许也会成为“高等动物”眼中的笑话。但是鲁迅先生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如果两条小鱼知道自己一生不过是在小小的琉璃盎中和自己的影子玩耍,它们还会如此欢乐吗?如果《命若琴弦》中的盲人早就知道自己弹断了一千根弦也得不到那复明的药方,他还会满怀希望地弹下去吗?如果人们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很可能是虚无,他们还能享受到奋斗本身的快乐吗?这样一想,不自知是不是也挺好的?
知,还是不知,这是一个问题。黎遂球没有给出答案,说是“将以问夫得道者”。或许,这个问题并不需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