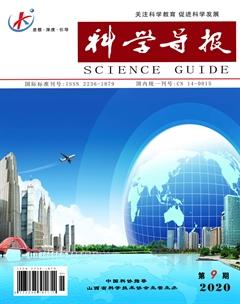边疆民族村落的柔性社会治理探析
张莹
摘 要: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民生以及国家安全中有着特殊重要地位,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的治理能力事关国家的团结、稳定、发展以及各项国家战略的推进,民族村落作为基本政治单位,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机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效结合当地民族特色、文化习俗、传统信仰等因素可更好地达到有效治理,同时对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重要作用,更有助于新时期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的新发展,推动构建适应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机制。
关键词:边疆民族村落;柔性社会治理;文化机制;信仰机制
一、研究概述
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我国重要部分,良性管理机制和协调发展机制是促进稳定发展的前提,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民族地区提供了高度自治的权力。“一带一路”使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登上了新台阶,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国土安全问题,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习俗文化背景各异,构建良性治理机制、把握区域特色及实际情况对民族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吉登嘎查①,是鄂温克旗南部以鄂温克族为主的村落,随着时代发展当地逐步实现了由狩猎向游牧的生计转变。尽管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鄂温克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信仰等方面却一直延续至今,如鄂温克族传统宗教节日敖包节以及信仰的“敖卓乐”神、“白纳查”神、“古雅奇”神等特有的民族文化、信仰等传承至今,深刻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及传统习俗是否会对当地社会治理产生影响?下文将结合实地调研情况进行详细论述。
“治理”一詞在20 世纪 80 年代为学术界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治理研究日渐成熟并产生了相关延伸概念。治理理论的发展完善也促进了我国相关学术研究与理论实践发展。柔性治理的概念由柔性管理延伸而来,是柔性管理与治理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曹召胜认为所谓乡村柔性治理,是指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时,要通过分散化的集体动员、亲情化的话语体系、多元化的治理技术等提升乡村治理绩效。②结合治理理论及柔性治理的相关研究,本文将边疆民族地区的柔性社会治理定义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部门在治理过程中,除运用硬性规章制度外,还将民族文化、民族信仰作为治理机制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文化机制影响下边疆民族村落的柔性治理分析
吉登嘎查是以鄂温克族为主的村落,1981年,红花尔基嘎查根据当地情况和猎民意愿挑选了善意狩猎的17户鄂温克人家迁至乌拉额德勒格,加上原本生活在此的8户人家,共同建立了吉登猎民队。在当地领导的组织安排下过上正规猎民生活,1984年改名吉登嘎查。1997年,为响应国家全面禁猎政策,猎民的枪支全部上缴,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由狩猎向畜牧过渡。
(一)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延续影响
鄂温克族的民族语言、独特服饰及生活习俗一直延续至今通过在吉登嘎查进行田野调查期间的观察与沟通可知,当地管理者多以本地人为主或多熟悉当地语言。村民自治的基础上,管理者的选取仍以民族文化了解程度为主要标准,从而形成更有针对性、管理更有效、服务更便捷的管理团队,方便更高效更好的服务村内居民。服饰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体现,在田野期间可知,历史上的鄂温克人长期生活在高寒地带,对山、土地、天空、太阳等的敬仰和崇拜逐渐渗入衣着服饰之中。在平日着装的袍子上,鄂温克人一般都绣有祥云图案,红色袖口则代表太阳,蓝色代表天空,黄色则代表大地,当地的狍子帽也成为典型特色。嘎查地处原始森林边缘,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大兴安岭及伊敏河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丰富的森林资源、野生动物、名贵药草等,而境内的河流湖泊不仅是难的的自然观光带,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水产资源。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特色饮食,居民发展餐饮行业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地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将居民日常的饮食、生活习惯都纳入到施政考察范围中,力图通过居民适应、日常生活中的惯习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的帮助也体现出当地政府执政过程中对日常生活中文化习俗的重视,这也促成政府形成更加高效、便民的执政体系。
(二)生计文化变迁下的柔性社会治理
吉登嘎查生计方式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1年—1997年以狩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该时期主要延续了传统狩猎模式,男人结伴上山狩猎,回家后猎物共享。第二阶段为1997年至今,该时期吉登生产生活方式转向放牧,主要以养殖牛羊等牲畜、收割草料等为生产生活方式。
在狩猎阶段,嘎查内的劳作分工较为松散模糊,劳作网络圈较大,涵盖到多个家庭,关系网络的凝聚方式以机械团结为主,个体为固定的生存目标为主而聚在一起。而在游牧阶段,嘎查内的劳动分工则更为精准细致,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主体逐渐被树立起来,劳动关系网则呈紧缩趋势,关系网络的凝聚方式以有机团结为主,个体为同一需求、同一目标有选择性的聚在一起。两种生计方式差异下的两种劳作习惯及关系网络也进一步影响政府的政策实施。在狩猎阶段,政府的治理机制主要以监管和协调为主,据当地居民回忆及资料记载显示,在狩猎时期,猎民的打猎用枪由大队统一保管,枪支保管地方以及子弹数量都由行政管理者制定具体细则。而在游牧阶段,政府的治理机制则转换为分配和引导。在生计方式转换为游牧为主后,管理者首要的问题就是草场划分,吉登嘎查草场众多,在进行划分时,除去集体所有的79000亩草场外,其他的则按照家庭人口数和牲畜数量进行分配。通过合理的方式对土地进行划分后,集体草场则由政府管理部门牵头,租赁外包给公司,租赁收益则有村集体和村民共同分红,大约每人可分到1万元。
生计方式差异造成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差异,政府则根据居民的习惯有效调节管理机制,以更合理更有效的方式去引导和管理村落。文化这一柔性因素使政府的治理机制更富有弹性,除此之外,居民意识层面的影响因素也成为政府柔性治理的重要环节,政府的引导作用进一步拓展了牧民的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
三、信仰机制影响下的边疆民族村落柔性治理分析
古时生产力低下,人民对自然界的敬畏衍生出万物有灵的观念,从而产生了信仰,信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反应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的则反应人与人的关系。鄂温克人崇拜对象多种多样,盛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认为宇宙万物,人间祸福皆有神来主宰。
而信仰机制又可分为两种类别:第一种是衍化抽象后的神灵信仰,如自然界的山、水、祖先等,这种信仰机制基于具象化的物质产生,通过不断深化,进而转变为人们心中的神灵信仰。第二种则是民间传统的宗教信仰,如吉登嘎查的萨满信仰。两种类别的信仰机制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一定影响,同时也影响到政府管理部门在治理过程中的政策实施与选择。
(一)神灵信仰影响下的柔性治理
传统鄂温克族主要以狩猎为生,在生计方式由狩猎转为游牧后,打猎时的很多禁忌也逐渐被打破,但仍然流传下来很多传统,如适度捕猎和采摘原则,不滥杀动物和大肆采集野生植物等。狩猎时期,猎民打猎时只有一个信仰,即山神(白纳查),山神形象是在大树上绘制长须老人,在狩猎途中,猎人遇到高山、岩洞、卧牛石和怪石都以为是白纳查神住的地方。从旁边经过时不能喧哗,否则对狩猎不利,认为一切野兽都是白纳查饲养的,捕获野兽是白纳查恩赐的,所以,遇到绘有白纳查神的大树要用兽肉祭祀,在饮酒时也要先敬白纳查。在与当地老人沟通时,他表示火最神圣,需要祭火,一生着火就用酒、糖祭祀,火是最大的,要磕头,还有龙王、土地爷,老天爷等。尽管部分祭祀活动多数已停止,但是在牧区,鄂温克人把农历十二月二十三作为火神回天的日子,太阳落山之后要祭祀火神。
吉登嘎查管理者在治理过程中则充分尊重居民的习俗,如在制定乡规民约时,着重强调用火安全,吉登嘎查村规民约第八条指出:加强野外用火管理,严防火灾发生,加强村民尤其是青少年儿童安全用火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全体村民的消防安全知识水平和意识。在乡村管理中,政府人员尊重传统信仰,而为了安全则以村规民约等方式引导村民学习相关安全知识,在保证信仰传承的同时也保证了公众安全。
(二)萨满信仰影响下的柔性治理
前文提到,萨满信仰与西方宗教信仰不同,它是原生性宗教,即萨满教不是创生的,而是在人类原始社会阶段自发产生的。这也是一系列类似的原始宗教的统称,并没有统一的教义与模式。
萨满教的基本特点是没有宗派、教祖或祖坛、没有具体教义、崇拜多种神灵,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没有集中固定的庙宇教堂、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前文提到萨满一般也分两种:一种是职业萨满,另一种则是家族萨满。而有杰出共享或能力超群的萨满会被信仰者修筑敖包并每年5月份左右前去祭祀。
根據当地民族志记载,当地有几位萨满巫医,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其掌握的技能造福当地居民,萨满巫医“道木琪”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既能通鬼神又能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医更专业的医药人物。在吉登嘎查现有三位萨满巫医(道木琪)传承人:乌云琪琪格是一名赤脚医生,接生技能高超,造福于吉登嘎查;萨仁琪琪格在鄂温克民族医药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擅长用道木疗术治理蛇廯等疾病,她也是鄂温克民族医药的传承者和实践者,曾为课题组提供了诸多鄂温克民族医药方面的信息;娜仁花对鄂温克民族医药各类药材的功能与用法、用量有丰富的指数储备,擅长用各类药材治理腿脚抽筋、习惯性流产、腹泻、烫伤等疾病,是鄂温克民间民族医生。
四、结语
边疆民族村落的治理与传统的乡村治理不同,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民族文化为边疆民族村落治理增添了更多的考量因素,日常生活中民族地区延续的文化与信仰影响着居民的生产生活选择,如何实施良性有效的治理机制对管理者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制度性强硬措施无法兼顾到民族的特殊性,因此柔性治理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边疆民族地区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下,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由于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民族宗教因素复杂以及经济发展限制等原因,边疆民族地区政府治理的水平还较为落后,治理制度与机制不完善、政策工具和行政手段更新不及时等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严重限制了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需要通过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制度安排、健全机制建设为民族地区政府治理的创新提供可持续的制度环境。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要在充分考虑自身内部条件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尽快地去制定和完善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制度与机制,从而为边疆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边疆民族地区各级政府要立足于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实际,不断摸索与实践,统筹协调,综合施策,切实提高治理能力。在具体对策上,边疆民族地区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公共治理思维,统筹协调重大关系,切实增强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逐步健全制度机制,主动应用先进科技,从治理文化,政府职能、治理体制、制度体系、政策手段等多个维度发力优化,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该地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达成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各项任务,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的中国特色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1]曹召胜.从“力治”到“柔治”—— 基于武陵民族地区Y村治理实践的考察[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13—119.
[2]杜孝珍.影响民族地区公共冲突治理的主要因素及政府有效治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8(04):22-32.
[3]胡卫卫.策略行动、草根失语与乡村柔性治理[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1):86.
[4]周平.中国边疆治理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年.
[5]白利友.国家治理视域中的边疆与边疆治理[J].探索,2015(06):116-120.
注释:
① 蒙语中,嘎查意为村落,苏木意为乡镇,旗则代表县。
② 曹召胜.从“力治”到“柔治”—— 基于武陵民族地区Y村治理实践的考察[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13—119.